- +1
我的科學觀|畢勇:倡導多維度評價體系,鼓勵大膽創新
·我們的評價體系中對于失敗的容忍度是偏保守的。人們常說“失敗是成功之母”,成功往往建立在一次次失敗的基礎上,但社會對人或事的評價往往更強調“成功”的結果,而不是如何取得成功的過程。如果我們的評價體系能在鼓勵成功的基礎上增加多維度的評價,崇尚創新和探索精神,就會鼓勵人們更大膽地走一些過去不曾走過的路。
激光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被認為是最快的刀、最準的尺、最亮的光。1992年,我考上了哈爾濱工業大學,本科學的是光電子技術專業,也就是激光專業。這樣一算,我和激光打交道已經有30年了。
報考激光專業,是機緣巧合,走上這條路也更加堅定了我做激光應用研究的信念。哈工大有一位老院士馬祖光,是激光領域的知名學者。我的小學語文課本里有一篇關于他的文章,叫《死光》,描述的就是神奇的激光。那時候我對激光很好奇,直到高考以后看到哈工大的招生簡章,一看有“激光”,就想到了小學課本里的“死光”,就這樣我闖入了激光的世界。
到了研究生階段,我在哈工大攻讀物理電子學專業,學的還是激光,那時候主要研究激光光譜學,偏基礎研究。我總感覺和激光應用離得有點遠,而我的同學在研究激光末制導的雷達,用中紅外激光研究精確制導武器的光電對抗,我很羨慕他們。從那時候起,我一直想做應用研究,做對國家真正有用的研究。這樣的機會終于在讀博的時候有了。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許祖彥(注:中國工程院院士)老師的激光器研究有很強的應用背景,考上他的博士生后,我開始研究高功率固體激光器,后來做了各種各樣有明確應用背景的激光研究,包括百瓦的綠光激光器、鈉信標激光器、可見光的光參量激光器。
在激光研究中越鉆越深,當我走出激光,看到我們國家的科研現狀,我意識到產業化的重要性。博士畢業不久,我參加了國家“十五” 863計劃時期的一次科技成就展,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國家863計劃發展這么多年,在高技術領域縮短了跟國外的差距,但科研成果對國家經濟的貢獻是不足的,90%以上的成果以結題報告、論文、專利的形式結束,科研成果評價很高,但最后沒能走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大門,沒有真正形成社會生產力。那時候我意識到,我們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要邁過這個臺階,真正解決國家和經濟社會發展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
科學家要有科學家精神,要不怕困難勇于創新和擔當,以滿足國家發展需求為目標開展科研工作。我們為之奮斗的事業,一定是可長期發展的、有價值的,而不是追一時熱點。有市場需求、對行業或生活有價值的事,是我工作的出發點。往大了說,研究方向是否和人類的需求匹配,是否跟國家在一個時期內要解決的問題匹配。往小了說,能否解決某個行業或人們生活的痛點問題。如果這些回答都是“是”,剩下的就是堅持。技術路徑考驗的是學術判斷,選擇正確的路徑就一定會有正確的結果,只要我們能夠堅持。
后來將近20年時間,我都在研究激光顯示技術的工程化和產業化,希望在更廣泛的領域發揮激光技術的優越性。到現在,激光在我的生活當中幾乎占了70%,我至少有七成時間在琢磨激光:激光能做什么、激光不可取代的優勢是什么……
在我看來,要做真正對國家和經濟社會有用的研究,就需要倡導多維度的評價體系,鼓勵大膽創新。我們常常在冒險方面偏保守。社會對個人的評價往往不在于探索了什么,而是取得了什么成果。久而久之,以成功為價值導向的氛圍并沒有真正鼓勵冒險創新,而是鼓勵不犯錯。如果我們的評價體系一味追求“成功”,把寶貴的時光、精力和聰明才智用在注水的科研文章上,就是在做“無用”的研究。而如果我們的評價體系能在鼓勵成功的基礎上增加多維度的評價,崇尚創新和探索精神,就會鼓勵一些人尤其是有冒險精神的人更大膽地走一些過去不曾走過的路。
(作者畢勇,系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杭州中科極光公司董事長,長期從事激光技術及應用方面的研究,包括激光顯示技術及產業化、激光全息三維顯示、激光散斑技術及應用、激光前沿應用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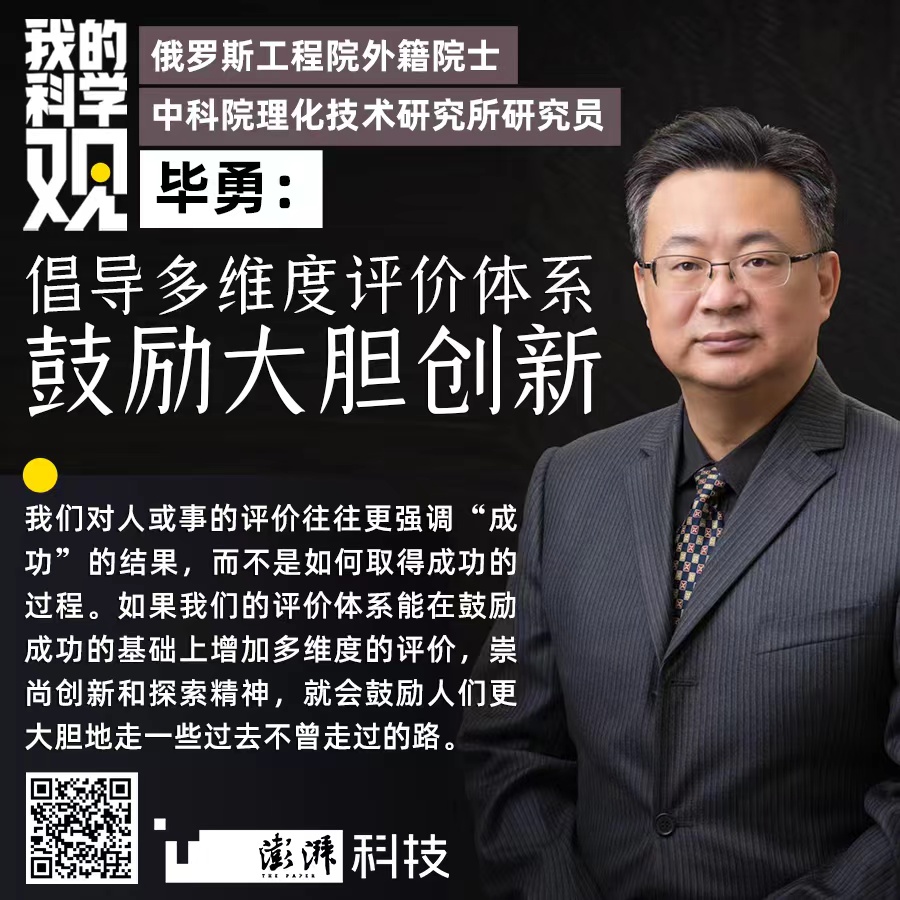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