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要小看“無腦娛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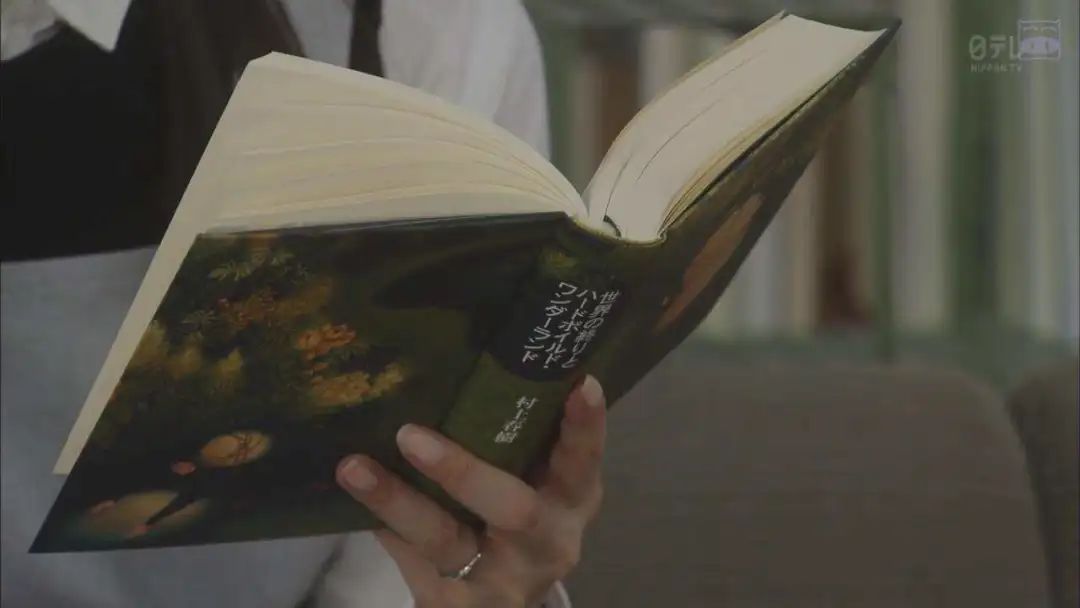
《偽裝夫婦》
網絡小說,尤其是“女頻”的言情小說,經常被認為是膚淺的、用來打發時間的,但這些小說以及改編的影視作品,確實是我們的文化生活中不能忽視的一部分。
關于言情小說,還有什么是我們沒意識到的嗎?影視改編中追求話題和流量的價值“縫合”應該被批評嗎?同為網絡小說,“男頻”和“女頻”有什么不同?
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同倪湛舸教授聊了聊。她目前任職于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宗教與文化系,既是學者,也是作家和詩人,網絡小說是她很感興趣的領域。在她看來,“女頻”小說作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看似是逃避現實的無腦娛樂,實則捕捉到了一些時代的新變化,就已經完成了一個很嚴肅的任務。
01.
言情小說是女性的世情小說
看理想:您一直在研究女頻文中的言情小說,我們往往認為,言情小說就是描寫“浪漫愛”的小說,但您卻將言情小說定義為女性的世情小說,為什么?
倪湛舸:在我有限的觀察里,女頻和言情的關系大概有三種:一,所有女頻小說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言情小說;二,女頻小說以言情小說(無論是何種性向)為主流,這個主流與其他類型比方說武俠、懸疑等有互相交織;三,女頻小說包含最狹義的異性戀言情小說、與之分離的男男或者女女戀愛小說、還有不以戀愛為中心的女性小說。
我個人傾向于把第一種關系里的言情小說稱為世情小說,女頻世情就是以女性作者/讀者群體為寫作/閱讀主體的小說,它可以包羅萬象。我的言情定義位于最寬和最窄之間,與最寬泛的女性世情小說比,言情小說仍舊是浪漫愛小說,但是與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我不打算把言情和非異性戀小說對立起來,在我看來耽美和百合只是言情門下的更細分類。

《黃金時代》
言情小說和世情小說的用法都出現在二十世紀早期。言情在晚清民國時是舊派--也就是“鴛鴦蝴蝶派”--小說刊物里的一個分類標簽,與之類似的還有寫情、哀情、艷情等等,這些分類的源頭是明代文人馮夢龍的《情史類略》,那里面有情貞、情緣、情私等很多卷。
世情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里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明清那些不以神仙妖魔為主角、描摹人情世故的小說,比方說《金瓶梅》和《紅樓夢》,與之對應就是《西游記》、《封神演義》那些神魔小說。所以說言情最早算是商業標簽,而世情是個后代研究者提出的分析范疇。
在通俗小說研究領域,我們經常看到“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被當作世情小說來分析,因為里面除了兒女情長還有大量對社會生活和時事政治的描寫。我們也能看到出現在二十世紀的言情這個商業標簽被用成分析范疇,去研究明清甚至更早的文本。
如果把言情小說看成是浪漫愛小說的話,這種用法是有問題的,因為浪漫愛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初才進入中國,之前的才子佳人小說戲劇里的那個情雖然也是男女之情,但不能等同于誕生于基督教環境的浪漫愛。
早期的言情小說基本沒有女性作者,到了三四十年代才在“鴛蝴”刊物上涌現出女性作者,比方說在《紫羅蘭》上發文的張愛玲還有其他很多人,但是她不認“鴛蝴”或者言情的標簽,覺得檔次太低。
女性和通俗小說的關系很微妙,清代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女性文學其實很難說滲透到了通俗小說這個低層次。清代的女性彈詞說白了是詩體,對文化素養要求很高,非閨秀而不能為;最早給《紅樓夢》寫章回體同人的女性顧太清(1799-1877)是滿清貴族;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年代,我們熟悉的女作家都云集在新文學的陣營,對舊派小說是看不太起的。
所以女性文學和狹義言情小說真正合流要等到二十世紀后半葉,在臺灣就以瓊瑤為代表。瓊瑤最早是在純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的,她的小說里五四遺風非常明顯,后來因為作品太流行,嚴肅文學男作家就開始看不起她了,開始給她貼言情作家的標簽,這時候言情才終于演變成女性寫給女性的戀愛小說。

《黃金時代》
如果說瓊瑤的言情小說模式是家庭作坊,那么她后面則出現了言情小說的工業化大生產。臺灣在九十年代跟美國簽訂了版權協議,在那之前,臺灣大量盜版了出版巨頭禾林公司的浪漫小說(Harlequin romance),后來不能盜了,怎么辦,一是老老實實買版權,二就是發掘本土寫手,按照禾林的商業模式打造本土臺言。
瓊瑤小說和后來的工業化臺言再加上日本女性向漫畫就構成了網絡文學女頻的直接來源,但是明清和更早的中國小說(不局限于世情)、女性彈詞和非通俗的現代女性寫作傳統也是女頻小說的根基。
我想要用女性世情來取代言情,根本原因就是女頻小說的確以言情為重,但是也絕對不能簡化成言情,戀愛故事本身就是棱鏡,可以折射出人間世情的千姿百態,而越來越多的女頻小說更是開始關注女性在公共空間的成長和發展,不會局限于戀愛和家庭生活,現在的無CP是個潮流。
如果繼續沿用言情,那就最好解釋一下,這個情不僅僅是感情、尤其是男女之情,這個情是情態情況情境的情,指的是女性所經歷或向往的現實,所以不如換用世情。世情小說就是從女性視角出發,關心女性經驗的社會小說,不排斥也不局限于戀愛故事。這樣可以更好地強調女頻小說的多元、復雜和流變性。
02.
日常中的顛覆性
看理想:您曾在微博上評論過,男頻的穿越文,穿越過去造反,其實換湯不換藥,女頻的穿越文,穿過去看似老老實實,其實在暗中瓦解男性中心的歷史敘事,女性成為欲望主體這事本身才是真造反。您能否進一步解釋一下,女頻文中實現的“真造反”?
倪湛舸:男頻的穿越文,從多年前的《尋秦記》到比較晚近的《紹宋》甚至還有工業黨們推崇的《臨高啟明》,講述的故事無非是男主(或是男主們)穿越回去,利用后來者的信息差還有現代科技知識,改天換地,成為帝王將相或者建國元勛,這仍然是傳統的成王敗寇敘事。
這種意識形態幻想(ideological fantasy),對現有的歷史敘事沒有什么反思,這里面對科技的盲目崇拜跟科技決定論甚至科學教也沒什么區別,有些涉及到政治體制討論的,也只是鸚鵡學舌。所以我說這不叫造反,這是對既定霸權的認同和強化。

《黃金時代》
女頻的穿越文就要復雜得多,不是說女頻穿越文就天生高級,但至少它們不會天生低級。大家往往會看不起女頻的穿越,覺得女主穿越回去找帝王將相談戀愛,這不是白日夢是什么?或者有一群女的在那兒“雌競”,干點什么不好非得互相扯頭花?最慘的是哪怕帶著現代意識回去,但最后發現其實還是改變不了什么,歷史的主線沒變,這也太叫人沮喪了吧?但是這些都是需要被反思的刻板印象。
怎么反思呢?大量的女頻穿越小說寫的是當代女性如何回到看似落后的古代去實現自己的抱負,戀愛未必是主線,這些小說只是沒有被影視化而已。
這些故事跟清代彈詞小說里的女扮男裝主題是有關聯的,所謂的封建社會里,現實條件不允許女人出來搞政治,女人只能幻想披上男人皮。穿越小說的策略是跳到一個更保守的環境里,但是給予女性特殊的知識和技能,讓她對環境有更強的掌控力,這種策略是女扮男裝的升級版,從改造自身上升到改造自身和環境的關系。
所以這些故事的意義在于批判作者讀者和小說人物都很難擺脫的各種顯形和隱形的枷鎖,跟《再生緣》相比,這些故事甚至更為辛酸,在所謂已然解放了的現代,女性的自我實現仍然要訴諸于想象。
再來看以戀愛為主線的故事,它們也絕對不能被一棒子打死。以《步步驚心》為例,哪怕女主身邊遍地都是王公大臣,女主其實仍然是個可有可無的邊緣人,故事呈現出的是主流歷史的不可改變,它真正為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有多少經驗、多少聲音和多少追求是被歷史敘事所壓制和摒除的。
和現代女主的穿越行為構成鏡像的是歷史現場里女性參與的被抹殺,也就是說加個人和減個人對歷史進程都沒啥影響。真正的問題不是穿越回去能不能改變什么,而是我們現存的這些歷史敘事,已經被閹割掉了哪些東西。

《黃金時代》
再比方說,被改編成電視劇之前,《知否》也是個穿越故事,大家看小說看電視劇都只看到了一群女人被關在家里斗來斗去,卻沒有注意到這些女人在做家務勞動和家政管理,小說和電視劇都呈現也承認了家庭空間里社會再生產的重要性,無論此舉是無心還是有意,一味批評宅斗無聊的我們才是狹隘的。
說到了宅斗那就肯定還有宮斗,為什么《甄嬛傳》經常被人拿來比擬職場?所謂的后宮不就是照著職場想象出來的嗎?女性職場存在的前提就是女性勞動參與,這方面中國目前的數據倒是真的高于大部分歐美國家,而且社會主義時期的數據更要高于當前。
勞動參與率高不是說女性就肯定因此有地位了,女性勞動參與率最高的是一堆亞非拉國家,有人會說這是因為窮,所以男女都得出來干活;但是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未必會拓展女性的空間,女性被趕回家也是現實一種,職場竟然披著后宮的皮出現,這也算是言情小說映射現實的一個例子。
03.
“縫合”的不僅是作品,也是現實
看理想:有一些小說也會被讀者詬病,認為其中包含了很多像“嫡庶尊卑”“重男輕女”這樣的封建思想。不止小說,許多熱播劇都舉著關注女性問題的大旗,但呈現出的價值觀卻給人“縫合”感,《夢華錄》和《卿卿日常》都因此受到了許多批評,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倪湛舸:給人以縫合感的作品是常態,因為現實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走向和層面,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思想和實踐不是線性鋪開的,而是攪成一團亂麻,所謂的現代也有很多種,這就是亂麻里還有亂麻。既然現實不是直線的、平面的、光滑的,我們就沒有必要去苛求作品按照單一標準做到盡善盡美。看到封建殘余就批評,發現閃光點就表揚,該干嘛干嘛。
《夢華錄》和《卿卿日常》我都只看了前面幾集,后來覺得不好看就不看了,大家批評的《夢華錄》貶低妓女,《卿卿日常》讓女主做妾,我也看不慣,也跟著一起罵,但是我不會說這些劇沒有做到關注女性問題,它們真的關注了,而且提出了問題,其實它們自己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所以我以為它們還是有價值的,無意中暴露問題才是它們的價值所在,的確劇方可能想要蹭女性主題的熱點,但是劇方自己的性別意識欠缺是劇外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所以這些劇起不到引導作用,給不出正確答案,只能折射出一團亂麻。

《夢華錄》
再者說,我一直在強調的是,任何的作品都不是簡單的封閉完成體而是一個信息流動的場域,是大家討論問題乃至進一步解決問題的跳板或者平臺。文以載道的意思不是說要塞給大家一堆教條,而是說文是動態的道路,我們要循道而進,重新認識和改造世界。
所以,女性世情小說也好,它們所改編的影視劇也罷,不完美是肯定的,糟粕大于精華也很有可能,但真正重要的是它們提供了一個讓女性發聲討論的場域,大家不能因為抱怨作品質量差就放棄這個場域,這個場域里看似微不足道的改變與意識形態、社會機制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遷是配套的,大家毋以善小而不為,也就是說見到小惡要趕緊點明,見到好的傾向要趕緊繼續推動。
看理想:但很多人不喜歡這類作品的原因是,覺得創作者或者團隊僅僅是想利用這些話題的討論度,創造一個商品來賺錢,這種膚淺的呈現可能會消減議題本身的嚴肅性。
倪湛舸:的確,蹭熱點吃女權紅利是個問題,但想要盈利的創作者沒有辦法完全控制消費者怎么處理這些文藝作品,呈現的膚淺也未必不能引發深刻的討論,僅僅忙著批判膚淺和利欲反而會浪費好好分析討論的機會。
我相信生產者和消費者在目前的這套為資本貢獻流量也就是價值的游戲里,還是有能動性的,她們在嘗試一些超出現有權力結構的自我構建。創作者當然在自我表達,而讀者/觀眾者也不只是消極的接受者,她們也會有積極的參與,會有進一步的討論和創作。
這就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審美或者說藝術的獨立。常見的誤解是藝術是獨立的領域,遠離經濟運作,遠離政治干預。但這是不可能的。審美行為與政治、經濟和其他活動始終互相交織,在互動的過程中探索現有權力結構所不能完全控制的新的可能性,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有人可能會說任何東西沾染了商品化和資本主義就沒救了,我倒是覺得完全脫離目前的這套政治經濟模式不現實。我反對公用設施的私有化商品化,但我們的吃穿住行也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經高度商品化,文化也早就成了產業,如何在漩渦內部做出抵抗才是關鍵,而不是幻想有什么不受污染的完美姿態和立場。

《黃金時代》
還要補充一點,嚴肅文學也一直都有商品性,為什么大家不去批評呢?就算不考慮商品性,我們為什么不這樣問:嚴肅作家探討熱點問題為自己贏得文化資本,這樣會消減議題本身的嚴肅性嗎?
批評流行文化如何服務于資本增值是肯定要做的事,但是,我們也需要再反思一下,為什么是流行文化一直在承受全部火力?文化內部的社會等級是怎樣把剝削和增值的游戲搞得更復雜的?現在大家會說嚴肅文學搞審美,網絡文學只是商業行為,我要強調一下這樣的二分不存在,嚴肅文學也是一種市場標簽,網絡文學也有自己的審美追求,未必不能開辟社會現實的其他路徑。
04.
言情小說捕捉了怎樣的現實?
看理想:您曾在講座中說過,做網絡小說的分析,也是在解讀作者的集體無意識,其中反映出來了很多社會現實,比如您提到過修真小說和新時代的危產階級(precariat)的關系——當絕大多數人成為數碼勞工,而極少數人掌握資本和生產工具高高在上,勞資之間的關系就好像修真小說里凡人和仙人的關系,彼此生活在不同的空間、宇宙或者位面。言情小說反映了怎樣的現實?
倪湛舸:反映這個詞可能不太準確,文本和現實互相滲透,不是簡單地各自為政互為鏡像,文學研究者會用捕捉或是重塑之類的詞。當代中國以網絡為媒介的女性世情小說,在我看來,最大的貢獻在于凸顯了數字時代社會再生產的重要性,這一點男頻小說幾乎完全沒有敏感性。
什么是社會再生產,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力需要休息更需要再生,每天我們下班回家吃飯睡覺、休閑娛樂,這就是再生產的一種,而家庭空間里的生殖、撫養和照護更是社會再生產。
工業資本主義年代,社會再生產與經濟生產是分離的,所以會有家庭和職場的區別,會有女性化的私人領域和男性主導的公共空間之分。可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工業資本主義遭遇危機了,開始向信息化轉型。
目前我們就生活在數字資本主義的時代,新的數字資本以信息化的生活經驗為原材料,生產出作為商品的數據,新型的數字勞動不再局限于工廠等封閉空間而是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人的各種機能和經驗是數據的來源,勞動力再生產變得更為關鍵,也不再局限于家庭空間而是溢出到整個社會。
這時候社會再生產和經濟生產的界限就被打破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哈特和奈格利認為原先由女性承擔的、家庭空間里的再生產勞動也就是情感勞動成為所有勞動形式里最提綱挈領的存在。
這方面早就有一群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學者在做深入研究,愛爾蘭媒體研究學者Kylie Jarrett近年來提出了“數字主婦”和“女性化人力資本”的概念,她認為數字勞動的女性化是種普遍狀態,原先的主婦勞動也就是再生產勞動現在演變成各種類型的數字勞動,特征是高強度、高靈活度和低酬勞甚至無酬勞,這種演變對男性女性勞動者都有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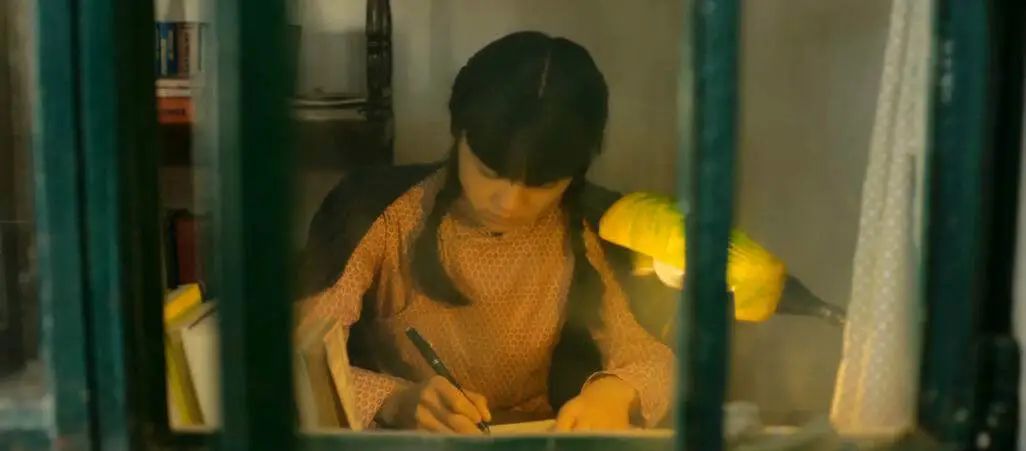
《黃金時代》
我們會抱怨外賣騎手在媒體上被簡化成外賣小哥,這是忽視女性勞動者,其實還有一層問題,外賣騎手無論男女在做的都是女性化的送餐也就是再生產勞動。網文寫手也是無論男女都在做女性化的再生產勞動,騎手配送物質食物,寫手提供精神快餐,這兩種都是溢出到公共空間里的家務勞動。
女頻小說也就是我說的女性世情小說對傳統的社會再生產以及它在數字時代的新發展都非常敏感。我以前覺得《甄嬛傳》和《知否》之類的劇搞來搞去就是要自己生孩子還不能讓人家生孩子非常無聊,但是它們至少關注到了生育這種再生產勞動。
女頻的科幻小說《小蘑菇》虛構了一個后末日烏托邦世界,那里的人類躲在基地里,基地的核心是個繁殖中心,這種設定男作家很難想到。女性在家庭空間外的職場和政界的活躍也有很多小說來展現,還在連載的女性基建文《買活》就很有意思。
我們生活在一個勞動環境惡化、危機四伏的時代,女性世情小說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看起來是逃避現實的無腦娛樂,或者就是資本主義的掙錢渠道,但它們至少捕捉到了這些新的變化,這就完成了一個很嚴肅的任務,而且認識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我相信女性的讀寫群體是有潛力為我們所有人探索出突圍的方向的,當然文化層面的變化離不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變革,這些層面都是互相影響的。
采寫:Purple
監制:貓爺
配圖:《偽裝夫婦》《黃金時代》《夢華錄》
封面圖:《寫不出來~編劇吉丸圭佑的沒有條理的生活》
轉載:請微信后臺回復“轉載”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