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司改何為|劉作翔:司法公開要解決法律化問題

【編者按】
司法改革步履不停,承前啟后。
司法體制改革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和國家司法制度,在憲法規定的司法體制基本框架內,實現自我創新、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的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司法改革進入深水區,黨中央對司法體制改革高度重視,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持續落實有關改革舉措,取得了重要進展。
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上,黨的二十大報告繼續作出部署:“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全面準確落實司法責任制,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2023年,司法改革如何繼續攻堅克難、探索路徑,成為改革的前沿挑戰。時值全國兩會期間,澎湃新聞特別推出專題策劃——“司改何為”,邀請業界學者觀察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知”與“行”,解讀新時代司改所面臨的挑戰,以期為深化司改建言獻策。本篇專稿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所所長、哲學與法政學院光啟學者特聘教授劉作翔。
司法公開的法律化問題待解。黨的十八大以來,為推進司法公開,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建成裁判文書、審判流程、執行信息和庭審公開四大司法公開平臺,要求司法案件從立案、審判到執行,全部重要流程節點實現信息化、可視化、公開化。
在劉作翔看來,司法公開包括結果公開和過程公開,但過程公開更為艱難。相對于結果公開,過程公開是一個更大的考驗。
“面對司法公開國際化、信息化以及國內加大改革力度的大潮,我們對原有的東西可能要進行反思,但并不是說所有的東西都要公開,也需要有限度,還要依法。”劉作翔表示,這就涉及司法公開過程中如何保護公民隱私權的問題,“司法公開不是目的,是為了滿足公眾知情權,通過陽光司法進而促進司法公正,但如果公開傷害了公民的權利就有違初衷了。”
他認為,司法的目的是保護權利,達到當事人之間和諧,尤其是民事審判活動,更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愿,“我們要警惕技術化帶來的兩面性,包括技術范疇和權利范疇怎么銜接和平衡,民主性問題、平等性問題、自由性問題怎么平衡。”
與此同時,當前的司法公開還只是作為一種政策導向和改革措施,司法公開中涉及的具體程序性問題,比如過程公開要不要進入訴訟程序中,結果公開要不要規定到法律中去,還需做長遠考慮。
基于此,劉作翔認為,對于司法公開取得成功經驗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解決司法公開的法律化問題。
以下為專稿全文:
司法公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體制改革的高頻詞。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就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法改革舉措與成效舉行新聞發布會。對于司法公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表示,中國的司法公開無論在范圍、形式,還是在深度、廣度上,近些年來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
司法公開的限度
司法歷來都是一個保守的行當,司法的保守性是司法的一個本質特點,不允許司法與社會有過多的交集,受社會的影響。隨著司法公開國際化、信息化的進程,司法的場域得以擴大。但與此相應的,也增加了社會對司法的影響程度。這里就產生了司法公開的限度問題。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歷史性地寫入了司法公開的內容。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建成了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中國庭審公開網、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四大公開平臺,保障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先后出臺《關于推進司法公開三大平臺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關于人民法院通過互聯網公開審判流程信息的規定》《關于人民法院執行流程公開的若干意見》《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關于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的意見》等十余個司法公開規范性文件。
在我看來,司法公開包括結果公開和過程公開,但過程公開更為艱難。相對于結果公開,過程公開是一個更大的考驗。
一般來說,結果公開通過努力不難達到,但也有爭議。比如,有些人認為判決書上網沒有意義,沒多少人關心,對這種論點我不認同。判決書上網對關心它的人很有意義,有些學者就專門上網看判決書,做司法案件分析。
有些當事人對司法判決的不服,主要囿于對司法過程不公開、不透明的質疑。有法官曾提出,應該把審判過程寫入裁判文書中去,這個思路雖然很先進,但我認為在中國做不到。雖然如此,但也不能因此而影響對整個司法過程透明度的提高,我們需要加大過程公開的程度。
當然,過程公開涉及合議庭、審委會等對案件的討論過程,對這些問題需要從長遠角度思考。過去很多東西被認為是機密,現在可能需要反思。檢察院系統曾經將檢察院的起訴案件視為國家機密,面對司法公開的大趨勢,也在進行反思。
面對司法公開國際化、信息化以及國內加大改革力度的大潮,我們對原有的東西可能要進行反思,但并不是說所有的東西都要公開,也需要有限度,還要依法。
在結果公開問題上,也還存在很多問題。例如裁判文書公開、上網的問題,刑事案件沒有問題,因為它是由法院來掌控的,主要是民事案件和行政訴訟案件。比如,當事人雙方或者一方不愿意公開的,能不能公開?對這個問題,法院系統的意見實際上極不一致。
我曾幾次提到這個問題,當事人只要一方不愿意,就不應該公開。因為民事案件應該遵守平等、自主、自愿的原則,這個原則一定要貫徹到底,當事人不愿意公開的就不應該公開,公開之后可能產生很多的后果,實踐中已經有一些事例了。
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法院的同志說當事人將案件交給法院時就應該有一種預見,即裁判文書公開的問題。意思是說,案件一旦交給法院,就不由當事人掌控了,愿不愿意公開是法院的權限,如果都去遵循當事人的意愿,百分之六七十的案件當事人都不愿意公開。
我認為,不能作這樣的理解。當事人將案件交給法院,是要求法院作出公正的裁決。至于公開不公開,還是要尊重當事人的意愿,不能成了法院強權之事。
防止把司法公開當作政績工程
這里就涉及司法公開過程中如何保護公民隱私權的問題。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公開不是目的,是為了滿足公眾知情權,通過陽光司法進而促進司法公正,但如果公開傷害了公民的權利就有違初衷了。
司法的目的是保護權利,達到當事人之間和諧,尤其是民事審判活動,更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愿。我們現在需要一種逆向思維,要討論的是哪些不能公開,除了法律明文規定的如國家機密、商業機密、個人隱私等,還有當事人的意愿問題。也就是說,案件不屬于不公開審判的范圍,但是當事人不愿意公開,或者說雙方當事人中的一方不愿意公開(指民事案件),認為公開以后會對他造成不利,這種情況下怎么辦?
我的看法是,民事活動還是要堅持自愿原則,這一原則也需要運用到司法公開過程中。我們要防止把公開當作政績工程,追求高比例,當事人的自主權應該得到保護,不能為了追求法院的政績去公開。任何一種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都要考慮到正面的功能以及附隨的相應問題。
也有專家談到,司法是公權力,不能因當事人意愿而影響對公權力的監督(意即公開判決書有利于對司法權的監督)。這種說法有待商榷。比如,雖然案件屬于公開審判,但當事人不愿公開他的材料,就應當保障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尤其是在法院信息化建設過程中,我們更要警惕技術化帶來的兩面性,包括技術范疇和權利范疇怎么銜接和平衡,民主性問題、平等性問題、自由性問題怎么平衡,包括對隱私權的保護。
比如,目前蓬勃興起的征信系統的建立本來是一件好事,但現在的一些做法是否存在侵犯公民權利之嫌。像對于一些輕微的違章行為如地鐵逃票行為,是否要放到征信系統上進行嚴懲,這樣做合適不合適,需要思考。
從法律上講,罪刑法定,罰當其罪,對一個人的懲罰要與其違法行為相匹配。罰當其罪應是法治原則,不能無限加大處罰和懲罰的力度。以此來看待民事案件當事人不愿意公開判決的問題,更是應該得到尊重的。有學者講,在美國逃票罰得更嚴重,但我認為中國還不能和美國相比,民眾意識的程度不一樣,還有一個教育和觀念的培育過程。
解決司法公開的法律化問題
還有一個庭審直播的問題。司法公開的主導權,目前基本上還是掌控在法院手里,一些案件的直播基本上由法院來主導。但和主導權相關聯的一個問題就是選擇性公開,這是被整個社會輿論詬病的大問題。目前的選擇性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是對某個案件的選擇性;第二是在案件直播過程中的選擇性。當然,法院擔心要是原原本本播出去會不會造成很多負面紛擾,關鍵是看如何掌控審判過程和審判秩序,既然我們要公開,無非就是放大場地。
庭審直播的意義在于,法庭的場域永遠是有限的,再大的法庭容量也是有限的,只要這個案件符合公開審判的要求,滿足公民知情權需求,就可以原原本本地直播出去,解決了審判場地有限性的問題,使無限擴大變為一種現實。
目前,司法公開還是作為一種政策導向和改革措施,但不能說完全沒有法律依據,我認為,我國《憲法》第130條規定的“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三部訴訟法規定的人民法院審判案件要公開審判,其中的“公開審判”就可以導出司法公開,除了法律規定的可以不公開的以外,它的法律依據應該可以從這里做一個引申。但發展到一定時候,司法公開涉及的具體程序性問題,過程公開要不要進入訴訟程序中,結果公開要不要規定到法律中去,這些還需要做長遠考慮。
一線的法官,尤其是院長們關心的更具體的問題是:對于公開審判的民事案件,一方當事人不愿意公開判決書時怎么辦?這些都需要在法律上作出一些規定。最終,司法公開的所有的、相關的、成熟的制度,在實踐中取得經驗的,最終可能要上升到法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解決法治和改革關系問題上,提出了三種路徑:“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實踐條件還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試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規,要及時修改和廢止。”按此思路,對于司法公開取得成功經驗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解決司法公開的法律化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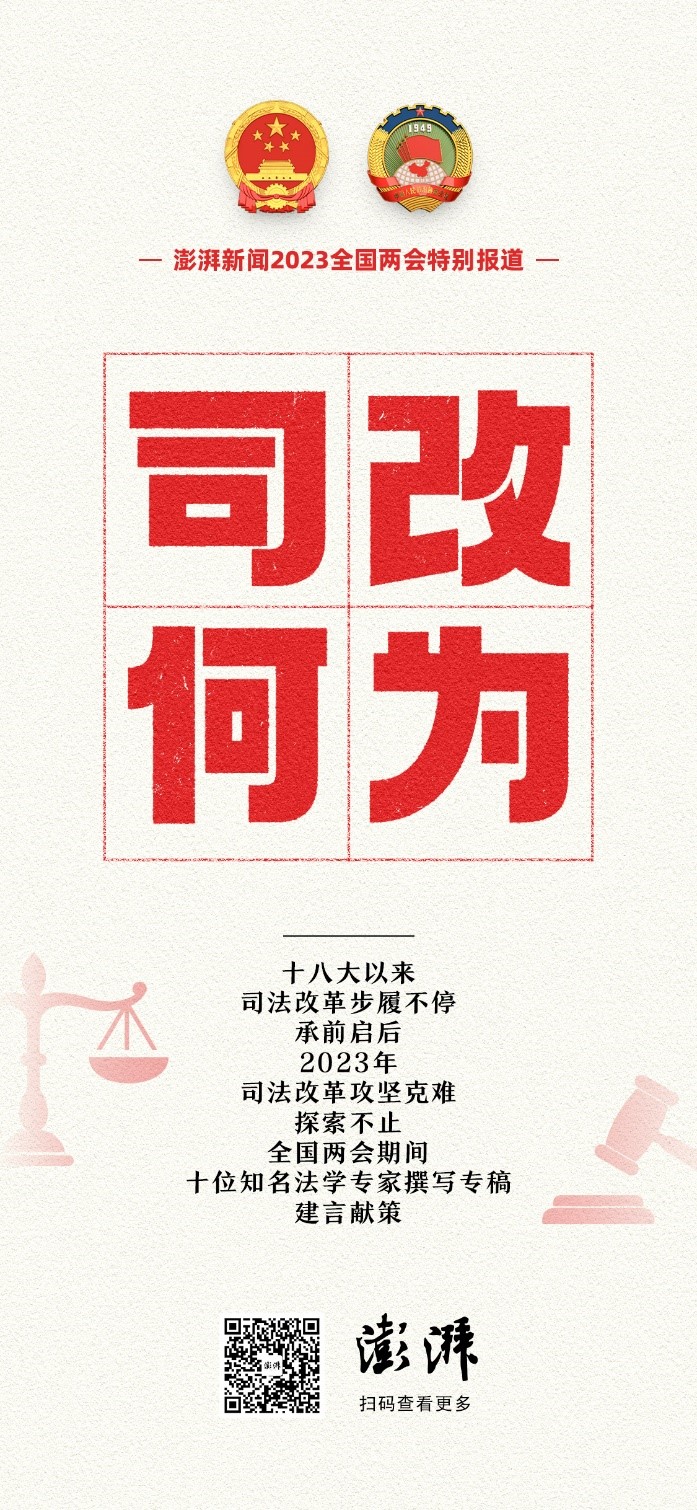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