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康子興評《貿易的猜忌》︱商業、歷史與現代政治

人類事務中的大革命(mighty revolution)已經發生,那么多蜂擁而起的事件走向了古人期待的反面,這足以令我們懷疑,它們將會產生更加深刻的變化。
——大衛·休謨,《論公共自由》
一
在《貿易的猜忌》這部文集里,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給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貿易的猜忌”重新界定了現代政治(《貿易的猜忌》,第2頁,以下書中引用只注頁碼)。因此,盡管他充分肯定霍布斯在開創“新政治科學”上取得的劃時代成就;但洪特仍一反傳統論調,認為霍布斯并非“第一個現代政治理論家”,而只是“最后一個后文藝復興的或‘新人文主義的’政治理論家”。其原因僅在于:“霍布斯拒絕將經濟和商業社會性看作政治的主要決定因素。”(第2頁)霍布斯的理論是反商業的純政治學,他思考政治的方式是前經濟的,因此也是前現代的。就貿易與現代政治之密切關系而言,現代政治學當為政治經濟學,現代政治理論家的頭把交椅則應當交給大衛·休謨,以及更系統地闡釋休謨之洞見、奠定政治經濟學基礎的亞當·斯密。亦言之,判分古今政治的界線為:是否將經濟、商業視為核心政治事務(或國家事務)。
然而,這個判斷必然帶來更深的疑惑:如果政治學的核心議題是秩序的基礎與公共生活的最高形式,那么為何政治理論古今之爭的焦點不在人性與政體,卻在經濟;不在理解政治的方式,卻在某一特定的人類生活領域?為何在現代政治中,經濟與商業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足以定義自身的邊界與形態;古人卻要將其排除在政治視域之外?或者說,洪特極力修正霍布斯(甚至馬基雅維里)在政治學說史上的地位,賦予休謨、斯密以開創性意義,我們應當如何理解他的這一努力?
實際上,洪特的洞見源自休謨和斯密,他在書中頻頻引用休謨的《論公共自由》 (“Of Civil Liberty”)以及《國富論》第三卷來闡述古今政治的革故鼎新。我們甚至可以說,洪特有意借用休謨與斯密的理論視野,來理解現代政治的基本結構與復雜張力,并獲得應對現實挑戰的理論資源。亦即,他思考、寫作的前提是:休謨與斯密在現代社會誕生之初便敏銳捕捉到,并揭示出其內在邏輯與基本結構;現代社會之基礎在十七世紀奠下,其結構一直穩定地延續到當代世界,其內在精神亦無實質變革。正如洪特所言:“《貿易的猜忌》旨在發掘出十八世紀國際市場競爭理論中那些仍然與二十一世紀有密切關系的政治洞見。本書所關注的這段時期,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首次成為政治理論的中心議題。本書避開了中間兩個世紀那些很成問題的修正,將讀者直接帶回十八世紀的智識環境中。政治思想史的最大益處在于能夠揭示意見不同所造成的僵局并消除重復性的爭論模式。《貿易的猜忌》就提供了這樣一種歷史,它將目光聚焦于今天面臨的種種挑戰。”(第5頁)
所以,我們若要正確理解洪特的論斷,我們就需要進入他的視野,關注休謨與斯密的政治歷史敘述,尤其是他們對自身時代之獨特性的理解。的確,在《貿易的猜忌》中,洪特尤為關注休謨與斯密的“歷史意識”。此書由七篇論文構成,但其中兩個篇章的主題都是“歷史”:第一章討論“四階段”論的理論基礎,第五章則圍繞《國富論》第三卷的歷史敘事(“非自然與倒退”次序的政治經濟學)展開。此中又以第五章最為關鍵,因為他對“非自然與倒退”發展次序的解讀融合了他對“四階段”理論的分析,并以之作為比較和對照的基本框架——正是相對于由野蠻到文明,由內而外的“四階段”的自然次序,羅馬帝國衰亡后的歐洲史才是“非自然與倒退的”。所以,我們要想恰切理解洪特的洞見,《貿易的猜忌》第五章尤為關鍵,《國富論》第三卷、休謨的《論公共自由》亦因此十分重要。
二

休謨的《論公共自由》為洪特理解現代政治提供了最為基礎的歷史框架。休謨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論點都成為了洪特的基本判斷。比如,商業造就古今政治分野這一核心論點便源出于此。洪特對之反復揣摩,不僅在導論中予以細致剖析,后又在第五章等處反復引用。不僅如此,這篇文章還影響了洪特對《國富論》第三卷的解讀,并在一定程度上視之為對休謨命題的注腳。
《論公共自由》篇幅簡練,但立意深遠:休謨不僅勾勒出理解古今自由的不同方式,指出商業對現代政治的關鍵作用,也敏銳地看到歐洲歷史中正在發生的巨大革命。我們可以將這篇文章解讀為政治理論史綱要,也可將其解讀為對政治史的簡要勾勒。他將理論與歷史融為一體,并將政治理論視為現實歷史的一個鏡像。休謨就好像歷史畫廊中一位目光敏銳,思想深刻的批評家。他審視著歷史畫作,看到并總結其精神、風格的變革,進而分析其原因,預測其發展大勢。
比如,他認為馬基雅維里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但仍然受縛于時代。馬基雅維里尤為關注君主政府,但《君主論》中的原理無一不在后世遭到駁斥。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馬基雅維里思想淺薄,而是因為其學說不過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反映著特定的歷史現實。“這個政治家犯下了許多錯誤……皆因其生活在過早的時代,從而不能成為政治真理的好裁判。”(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Liberty Fund, 1982, p.89.)世事推移,時代與社會均已發生了巨大改變,商業的巨大力量開始展露,引列強側目。
上世紀之前,貿易從未成為國家事務;論述政治的古代作家也少有人提及貿易。甚至,盡管它已然引起國務眾臣和理想思考者的關注,但意大利人卻對之緘口不言。兩大海權國家獲得的巨大財富、榮耀與軍事成就似乎最先向人類闡釋了廣泛貿易的重要性。(同上,pp. 88-89.)
這是一個巨大的革命,它動搖了古代社會的結構,塑造了新的民情、風俗,甚至“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所以,它也為傳統的政體賦予了新的精神、原則與內涵。“盡管所有政府類型都在現代獲得了改善,但君主政府似乎獲得了朝向完美的最大進步。現在,我們可以確切地稱之為文明的君主國(civilized monarchies),他們是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盡管這些此前只用來贊美共和國。我們發現,它們在令人驚訝的程度上受到秩序、方法與持久性的影響。財產在那里是安全的;工業受到了鼓勵;藝術繁榮起來;君主安全地生活在臣民當中,就像父親生活在孩子當中一樣。”(同上,p. 94)商業令絕對君主制變得寬和,甚至這一趨勢還將繼續深入發展,對利益的思量終將戰勝榮耀與特權,權力濫用會受到治療,絕對君主制政府與自由政府之間的差異將會變得不再明顯(同上,p. 95)。
所以,古人確信科學藝術只能在自由政府中變得繁榮,但休謨發現,這一信念在現代社會中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在君主制的法國,科學與藝術都發展到堪與任何國家比肩的完美程度(同上,p. 91)。休謨遂將此命題修正為:商業唯有在自由政府中變得繁榮。古人的信念不再適于現代社會,就好像馬基雅維里的命題在后世受挫,因為政治理論均有其“歷史性”。休謨對命題的修正乃是對社會“革命”的呼應:商業社會興起,商業成為塑造權力結構、社會風俗的強大力量。自然,商業也可能造就新的腐敗,需要政府嚴加關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商業成為國家事務的核心議題;商業也以重新塑造著歐洲的公共自由,將共和精神以風俗和“權力平衡”的方式輸入君主國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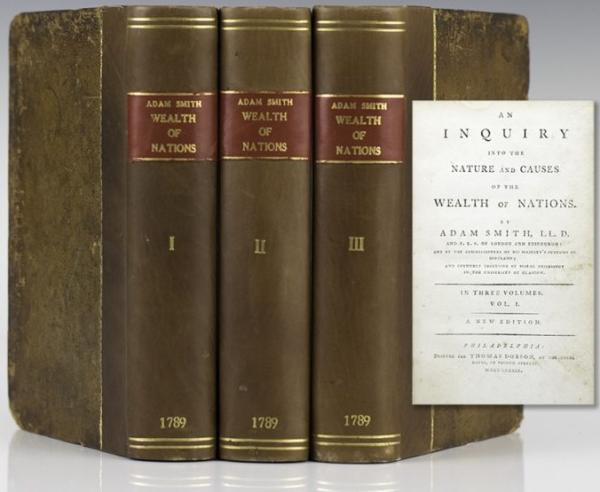
斯密更為系統、細致地闡述了商業塑造歐洲現代自由的歷史。因商業而來的社會革命,正是《國富論》第三卷的主題。自羅馬帝國衰亡之后,歐洲陷入普遍的荒蕪、野蠻狀態。野蠻人征服羅馬,也把他們的習俗融入法律。歐洲施行大地產制和農奴制,土地得不到開發,勞動者財產權得不到保障,生產力普遍低下。不僅如此,歐洲長期實行限嗣繼承制,領主眾多子女中,只允許一人繼承地產。大地產制因此得以固化,避免了因繼承產生的土地分裂。因為大地產制,領主在封地享有絕對權力。因此,無論城市還是鄉村,歐洲也長期維持在一種不自由的狀態。野蠻人摧毀羅馬文明,帶來政治上的奴役、經濟上的貧窮。
由于商業的興起,這種傳統的權力結構逐漸松動,最終瓦解。歐洲在政治上逐漸由奴役走向自由,社會也逐漸由貧窮走向繁榮。斯密將這變化稱為“極重要的革命”。在商業尚未發展起來時,領主只能消費地租中較少的部分,其他地租用來豢養門人和附庸。這些人由于在經濟上依附于領主,便在政治上效忠于領主,從而構成領主重要的權力資源。商業最先在歐洲的邊緣地區發展起來,比如荷蘭等地。由于法律上的壓制,對外貿易最受偏愛;奢侈品貿易因為價值高昂、便于運輸,最受推崇。海外奢侈品貿易逐漸帶動國內制造業的發展,商業的風氣日益深入內陸,并進而影響鄉村。當貿易繁榮起來,領主為了滿足自私的欲望,便會為了昂貴的奢侈品,支付全部土地剩余產物。他購買來精致的工藝品,可完全由自己消費,無需與佃農和家奴共享。為了獨享一對鉆石紐扣,他不惜支付足以維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糧食,同時也舍棄了從中而來的權威。于是,曾經的領主制、大地產制逐漸瓦解,耕作者獲得了更大的權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歐洲因此逐漸從野蠻的風俗中復蘇,走向自由、文明與繁榮。
這場革命是無意識地、自發產生的,并非人為設計的結果。對此,斯密在《國富論》中有這樣一段評論:“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眾幸福的階級。滿足最幼稚的虛榮心,是大領主的唯一動機。至于商人工匠,雖不像那樣可笑,但他們也只為一己的利益行事。他們所求的,只是到一個可賺錢的地方去賺一個錢。大領主的癡愚,商人工匠的勤勞,終于把這次革命逐漸完成了,但他們對于這次革命,卻既不了解,亦未預見。”([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379頁)
現代歐洲重新文明化歷史遵循了“非自然與倒退的”次序:對外貿易推動國內貿易,城市帶動農村,最終導致整個封建政治經濟體系的瓦解,海權的商業共和國(比如荷蘭與英國)取代陸地君主國(比如法國),成為新時代精神的代表。
在很大程度上,洪特將《國富論》第三卷的歷史敘事視為斯密對《論公共自由》的注解,并將商業社會與商業共和國的興起理解為:商業從野蠻人統治和封建暴政下突圍,逐漸獲得自由立法力量的進程。重商主義時代的來臨、“貿易之忌”的出現正是這一連續進程的結果。商業不僅塑造了國內的民情與社會結構,也重塑了國際政治體系。“在大型領土國與專業商業政治體之間的勞動分工,從十六世紀晚期開始就被擾亂了。在所謂的‘重商主義’時代,在節節攀升的軍費開支壓力下,歐洲的主要領土國開始投入到經濟權力的競逐中,努力通過對外貿易產生的盈余來獲得霸權優勢。一種新型的國際體制應運而生,取代了領土國與體量小但專業化的商業政治體(大部分是商業共和國與城市國家)之間親密而互補的關系。在這種新型體制中,領土國憑其自身的努力就已成為國際商業主體……用大衛·休謨的一句名言來概括,在十七世紀,商業首次便成為‘國際事務’。”(349頁)
所以,現代世界是一個被商業塑造的世界。國家榮耀、野心與貿易結合起來,海洋和商業成為國家間競逐爭霸的另一個戰場。“貿易的猜忌”或重商主義體系雖然注入了商人的貪婪與土地貴族的癡愚,盡管在規范意義上,它應合理地受到“不義”之責;但是,在事實和歷史層面,商業和商人綁架了國家,成為了實際的立法者,擁有強大的力量。所以,盡管近代歐洲的發展遵循著“不自然與倒退的”次序,正是這一次序繁育了重商主義體系的腐敗與非理性,然而,它也恰恰體現了商人的力量,以及商業在現代社會中的核心地位。與文明社會發展的自然法與自然進程相比,“不自然與倒退的”次序才是真實的歷史。正因此,洪特認為,斯密借《國富論》第三卷闡發了一種以事實為基礎的審慎的政治理論,并借機批判重農學派的自然法教條主義,指出其罔顧事實,單憑理論體系塑造社會的危險。“現代早期歐洲君主國早熟的商業發展,對他來說是一個棘手的事實,也是具有極端政治意義的歷史事實。誠如斯密之所見,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一定不能回避這一事實,或者被教條主義所束縛而反對它。在他看來,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學會應對過去的歷史遺產。”(356頁)
《貿易的猜忌》英文版
四
洪特對斯密政治理論的分析具有強烈的史學色彩,所以,在他眼里,《國富論》便具有極為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國富論》并不是一部關于永久和平的著作,而是一部關于競爭性經濟戰略的著作。在他的書中,斯密權衡了國家在全球市場中求生存的可能機會。”(第8頁)亦即,《國富論》以斯密對時代與歷史的深刻洞見為基礎,它是時代精神的反映。以此觀之,《國富論》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理解為史書,而非規范意義上的政治哲學作品。洪特所謂的政治理論便具有強烈的史學色彩,而非哲學含義。所以,當他說,休謨與斯密才應當是首位現代政治理論家時,他其實是在對現代性作一個歷史學的判斷:古今的分野正在商業社會的興起。政治理論的變遷不過是歷史變遷的映像,古今政治學的分野自當以古今政治史的分野為標準。
然而,當我們細細推敲,當斯密在闡述歐洲歷史的“非自然與倒退”次序時,他其實闡發了一種更深層次的、基于道德哲學與神學的“自然智慧”。亦即,《國富論》第三卷不僅僅是一篇歷史分析,還是一部極為精彩的自然神學作品。透過這種帶有神學色彩的自然歷史敘事,斯密亦確立起他的“商業社會哲學”。
就此而言,洪特真正的老師是大衛·休謨,而非亞當·斯密。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