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的科學觀|張笑宇:推動科技進步最好的方式:去玩、去消費
·我們這個民族有時候思考問題的方式太沉重。說研發科技就很高大上,說玩就覺得不務正業。實際上,很多一流科學家的科研就是在做他愛玩的事,很多一流的科技成果就是玩出來的。
我本人在研究科技史的過程中,發現的最有趣也最令人感慨的一件事,就是人類歷史上大概有95%的科技發明是被遺忘掉的。
我是在接觸了許許多多在科技史上留下姓名的發明家才敢這么說的。比如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亞歷山大的希羅。希羅是公元1世紀亞歷山大圖書館的館長。這個人被公認為蒸汽機雛形的發明者。當然,如果你看他的那個裝置,還很簡陋,不足以作為動力裝置。但那只是他眾多發明中的一種。他還發明過用蒸汽驅動的自動門,發明過機械式的自動售貨機,發明過可以機械編程的三輪車,發明過各種自動機。想一想,這些都是兩千年前的作品,這是很令人吃驚的。
更令人吃驚的是,希羅的這些發明并不完全是工匠的經驗。他是先有對基礎科學的了解,再做出相應工業設計的。比如記載他蒸汽裝置的書標題叫“氣動力學”,他在第一章先概述了氣動力學的數學原理,然后再列了幾十種發明。這跟當代工程學的研究思路是一致的。換句話說,這是一位兩千年前的愛因斯坦加愛迪生式的人物。但是這么一個人,為什么今天我們對他所知甚少呢?
因為他的發明并未得到大范圍應用,所以少為人知。而未得到大范圍應用的原因又不是一個觀念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結構問題。所有技術在經濟學的觀點上都是降低生產成本、替代勞動力的要素,而在勞動力價格足夠低的情況下,技術替代是很難發生的。希羅生活在古羅馬,那是一個奴隸社會。企業家幾乎不需要為勞動力付錢,因此他的技術在社會生產中無用武之地。當然,他本人并不是掙不到錢和名聲,因為他有一個很理想的買家:神廟。神廟買來自動門和自動售貨機,然后告訴無知的信眾:這都是神力的表現。
這是件很嘲諷的事情:最先進的發明被拿來為最愚民的集團作辯護。但這恰恰揭示了一個道理:不公的社會結構會扭曲技術的應用路徑,令其不能為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
蒸汽動力機械其實是一項在人類歷史上被反復發明的技術,但直到最近一次它的集中大規模進步才帶來了根本性的革新,引發了工業革命。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近代英國首先經歷了商業革命和憲政革命,社會普遍富裕。人們的高消費能力對煤炭產生了大規模需求,同時煤炭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又相當之高。因此,企業家有足夠的動力將蒸汽機應用于生產,工程師也可以賺到足夠的錢,有動力持續作技術創新,這才有了工業革命。
這里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為蒸汽機鑄鋼技術奠定基礎的,反而是一樣不起眼的發明:鐵鍋。在中世紀,人們多數時間使用更廉價的銅鍋。但是當煤炭普及開來之后,銅鍋不能耐受那樣的高溫,所以就有必要大規模使用鐵鍋。鐵鍋的市場很大,于是就吸引了一位叫做亞伯拉罕·達比的工程師改良了鑄鐵技術。他創辦的企業后來成為瓦特和史蒂芬森的供應商,在工業革命的歷史中舉足輕重。
類似的故事也在歷史上多次發生。比如,石油最初被開采的時候是為了照明使用的。煤炭大規模應用后,煤氣等副產品也得到了廣泛應用,當時主要的應用場景是照明。后來,人們發現了更好的照明燃料,那就是石油。洛克菲勒因為創辦標準石油公司而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人,而當時標準石油公司的主要市場就是照明市場。洛克菲勒成為首富之時,內燃機汽車的研發才剛剛起步。人們還不知道這種資源將來會成為那么重要的黑色黃金。
再比如,推動第二次工業革命取得重大進展的化工領域,最早是在紡織業中賺到第一桶金的。第一次產業革命期間紡織業的崛起。蒸汽機帶動紡織機生產成千上萬的棉布,制衣業需要給這些棉布染色,于是需要發明人工染料。我們熟悉的化工業巨頭,例如拜耳、巴斯夫(號稱“我們發明了化學”)和赫希斯特,它們最早的第一桶金都是染料。在這個領域取得商業成功后,它們才從化學品研發延伸到后來的炸藥、化肥、尼龍、塑料、生物制藥等領域。甚至這個領域后來還催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半導體產業。硅谷的起點——肖克利實驗室,最早就是研發PH測試儀的。
從以上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獲得怎樣的對于科技影響社會的認知框架呢?
我個人總結了一個觀察模型叫做“漏斗-喇叭”模型。這個模型說的意思是,人類歷史上可能有95%以上(數字未經檢驗)的技術創新發明是被遺忘的。它們在書上被記錄下來,或者變成了專利以后,就被遺忘在故紙堆里。能夠被我們記住的發明,實際上都是通過了一個漏斗的篩選和檢驗,這個漏斗的名字叫做“商業化”或者“產業化”。通過了漏斗檢驗的技術,可能會反過來對社會生活生產產生巨大的顛覆性的變化,就像喇叭放大聲音一樣,所以叫做漏斗-喇叭理論。
而在商業化過程來篩選技術的時候,我們又會發現,很多技術在雛形時代,由于它的不先進和不完善,它的應用方式和商業模型跟它完善之后是有很大區別的。比如蒸汽機最早并不是動力機械,而是用于地下礦井的抽水。石油最早不是動力燃料,而是照明燃料。后來研發出化肥、炸藥和藥品的企業,最早是給人染色掙錢的。倒退回那個時間點,你也許完全無法想象,抽水機引發了工業革命,燈油帶來了車輪上的社會,染坊制造了人口爆炸和戰爭。
無數當時被看好的技術后來默默無聞,無數當時被人忽視的技術后來攪得人類社會翻天覆地,這說明漏斗的篩選機制是一個很難事先預判的過程。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創造更自由、更寬松的環境,便利更多天才憑自己的喜好去天馬行空地想象和發明,去盡其所能地在市場上取得成功。
近來由于ChatGPT的火爆,人工智能再次引發大家的關注。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漏斗-喇叭”模型案例。
我們都知道,人工智能的理論源頭是1940年代維納等人提出的“控制論”,在當時,韋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等人就使用計算機模擬了神經學家唐納德·赫布(Donald Hebb)提出的“神經網絡”學習模型。這也是當代人工智能領域“深度學習”方法的前身。但是,在60-70年代,這套方法基本是停滯不前的,因為當時的計算機硬件缺乏足夠的能力來建立復雜的人工神經網絡。
直到2010年前后,以吳恩達先生為代表的斯坦福大學團隊發現,使用GPU來運行深度學習的相關算法,效率可以提升70倍以上。這個發現直接導致了深度學習出現“大爆炸”,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打個比方,如果說深度學習是當代人工智能技術的“靈魂”,那么GPU就是深度學習算法寄托的“大腦”。
但是GPU又是從何而來呢?它的第一桶金來源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游戲。發明了GPU的公司叫做英偉達(Nvidia),成立于1993年。它的創始人黃仁勛后來回憶說,1993年的CPU處理速度還不是很快,當時英偉達希望做一個圖形的加速處理器,可以做通用的圖形加速。而這個硬件最大的應用市場就會來自于游戲。
后來也果如黃仁勛所料,英偉達生產的圖形處理器(GPU)因為電子游戲市場的繁榮,蒸蒸日上,接連擊敗一系列挑戰者,成為業內的佼佼者。但沒有人想到,這條技術路徑后來竟然陰差陽錯地掀起了人工智能的技術浪潮。
夸張點說,人工智能這一新技術的方向,是游戲玩家們玩出來的。
這正是我想表達的一種科技觀。我認為我們這個民族有時候思考問題的方式太沉重。說研發科技就很高大上,說玩就覺得不務正業。實際上,很多一流科學家的科研就是在做他愛玩的事,很多一流的科技成果就是玩出來的。我們太習慣以為,歷史是一張有標準答案的考試卷,我們必須努力應試、應試再應試。結果就是,當愛玩的人玩出真正的創新,而這種創新又在高消費社會率先成功商業化,我們只能目瞪口呆,然后繼續壓縮玩和消費的時間,永遠追在人家屁股后面研究。
真正的進步是超出舊思維想象的,真正的技術前景是無法預先判斷的,真正的行業龍頭是政策和計劃塑造不出來的。如果說科技史能告訴我們什么,那就是,盡可能創造一個公平、普遍富裕、寬容和自由的社會,讓大家有錢、有閑地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讓大家把科研當作游戲而不是當作繁重的任務。當我們做了這些有溫度的事情,技術就會在我們不經意的地方回饋給我們真正的驚喜。
(作者張笑宇,系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騰訊騰云智庫成員,得到App簽約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思想史、科技社會學、商業與產業史。著有《重建大陸》、“文明三部曲”系列(《技術與文明》、《商貿與文明》已出版,《產業與文明》待出版)。《技術與文明》一書獲“2021屆亞洲圖書獎”、“2021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商貿與文明》獲“第一屆刀鋒圖書獎十大好書”,“2021亞洲周刊全球華人十大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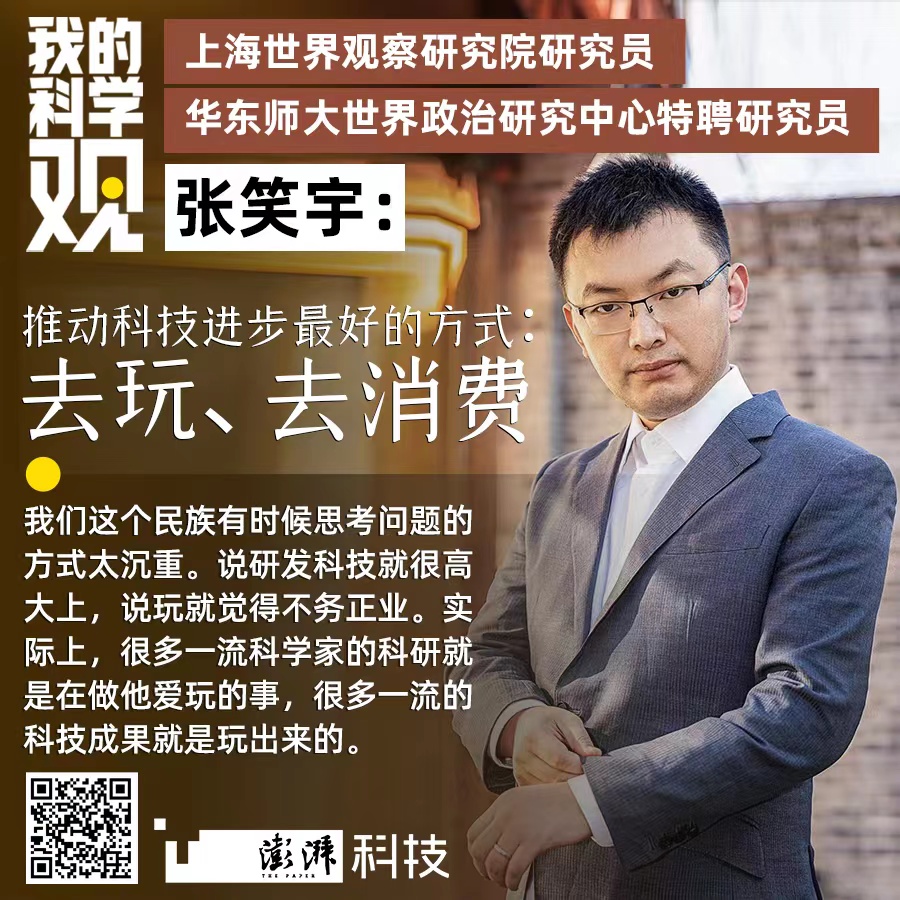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