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感官城市|上海南京路的氣味與情感地圖
本文來自愛丁堡大學教授、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訪問學者講者黃雪蕾,在2022年12月27日華東師范大學校級學術講座上的分享,包括講座及互動內容。由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張春田主持。

2022年3月,上海南京路。高征 圖
氣味非常重要,它不只是簡單的化學反應和神經反射過程,其背后蘊含著許多價值和意義。
我原先是做電影史的,將近十年前對感官氣味研究發生興趣。新世紀以來,感官研究在國際上方興未艾,一開始主要由人類學家發起,之后波及整個人文社科領域。當然,這跟整個大的研究背景,對身體的關注、情感轉向等,都有著深刻關聯。
南京路好像可被理解為中國現代性的切片。它是上海開埠后,英國僑民在1840年代最早修筑的馬路之一,日后發展成整個公共租界的軸心。它基本上是殖民現代性的物質象征,包含了消費主義、現代技術、衛生秩序、中產階級、世界主義、階級差序等等。1949年后,它成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改革開放之后,它又成為消費文化的象征,成為旅游地標。
因為復雜的歷史和地標價值,可以將它視作一個地理文化文本來考察。
凱文·林奇是城市規劃和文化地理學方面的專家。他認為,在城市規劃中,一座城市非常重要的是the mental image。我們對城市的認識,不只是方位地形,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圖像。這個精神圖像(mental image),是直接的感官認識,加上記憶和歷史經驗的疊加構成的。他探討城市,用了繪制認知和情感的地圖(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apping)的概念。后來這個詞被文學史研究者使用,從地理學拓展到社會政治和文化領域。
凱文·林奇的書里認為,mental image主要由三部分組成,identity、structure and meaning,人的感官感知,也是形塑所有這些要素的重要媒介。從這個框架出發,我的研究截取了一個長時間段中的三個片段,來看南京路的氣味和情感地圖的變化。
1850年代是形塑南京路identity的重要階段。就感官而言,“祛味”(deodorization)是突出特點。隨后一個世紀,南京路的空間結構和意義日趨復雜。到了1930年代,南京路最重要的精神圖像,跟物質主義和奢靡相關。到了1950、1960年代,我想強調的是,“再祛味”(Re-deodorization)的操作是如何進行的。
先來看1850年代形塑的嗅覺形象。探討這個問題,必須把它放到全球史背景中。19世紀后半葉,隨著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發展,西方的大都會,比如倫敦、巴黎等,不能適應現代化需要,紛紛開始大規模城市改造工程。Kevin Lynch在書里提到,現代城市規劃中,都市空間的可讀性是個重要考量,嗅覺無疑也被調動去讀解空間,去形塑空間的可讀性。
另一個重要背景是興起于1840年代英國的公共衛生運動。這跟工業革命導致的環境惡化息息相關。英國的議會1848年通過了公共衛生法,可以說是第一次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管理衛生事務,把衛生問題放到了公共領域。當時流行理論認為,臭氣、瘴氣會引發疾病,因此“祛味”在公共衛生管理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這也是普遍認為的現代氣味革命的開端之一。
還有殖民話語中的感官等級秩序。當時的西方人游記作品中,印度、非洲等殖民地和人民都被打上臟臭標簽。關于中國“China stinks”的論述也不勝枚舉。
總之,在這幾個綜合要素作用下,英國僑民來到上海開始建設南京路時,有意無意把“祛味”作為打造城市空間的重要指標。他們是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對南京路的metal image產生怎樣的影響?
在實際政策和操作層面之外,我想首先強調隱形的,對時間、身體和記憶的操控。
來看1856年7月2日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的一段記錄。它是有關南京路糞穢和氣味管理的第一則我能找到的記錄。一位殖民官員被指派在早上6:00-8:00,駐扎一艘船在福記碼頭。Park Lane是南京路的前身,街上所有住戶,必須在這個時間點把“filth”(基本是指糞穢)倒到這艘船上。為保障實施這一措施,他們還派了一名“苦力”監督,而且是佩戴徽章的。
這里可以看到殖民現代性管理的一些典型要素。這次會議記錄,不僅說明了糞穢在殖民衛生管理中的重要性,也可看到現代性中的時間感與身體感的再塑造。
整個工部局會議記錄反復提到中國人太不遵守時間秩序。葉文心教授研究民國上海企業文化時,強調了海關大鐘的意義,這一機械裝置設定了一個公共時間,將其內化到城市生活和市民感知中。這個例子中,南京路的氣味地圖與時間感被人為勾連起來,形塑了南京路這一獨特的identity。當時對華人社會來說,南京路的管理跟華人市政管理形成鮮明差異,《申報》等中文報紙上有許多討論。此外,感官感受會成為記憶,層層累加,變成城市精神圖像的一部分。
再舉個小例子。1938年的《字林西報》上,刊登了名叫Stinky的讀者來信,是一位法國人,他抱怨早上上班路上,總跟糞車發出的刺鼻臭味相遇。他建議,法租界當局應該分發一些法國香水,比如Lentheric這個品牌1930年代開發出的名為“上海”的香水。他又開玩笑說,調香師的靈感一定不是早晨八點的上海領事館路的味道。
這樣的歷史文本,帶領我們去想象這座城市的氣味。城市的氣味又與化妝品工業和香水的物質文化勾連起來,對文化記憶的形塑,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再看一個比較具體的氣味管理的操作手段。當時管理氣味,尤其在上海,重要的手段是填平溝壑。上海地處江南水鄉,天然地貌溝渠縱橫。在當時的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和日常生活中,溝渠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在西方公共衛生理論中,水,尤其是死水臭水,被視為天敵,加上新的生產和交通方式、經濟發展方式的引入,上海的溝渠在19世紀后半期被大量填埋。即使非常小的坑洼,也被認為是滋生臭氣污染的溫床。早期工部局會議錄中,有無數記錄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個重要的技術手段是修建下水道。巴黎和倫敦的下水道,成為19世紀西方現代性的化身,上海的下水道修建幾乎同期展開。1860年左右,當時英國僑民已開始修建下水道網絡。南京路是網絡上的重要軸線。下水道在文學想象和感官文化史上都有重大意義。將污穢驅逐出視覺、嗅覺的感官場域,也是西方現代性的勝利主義的物理象征。這一提升現代都市可讀性的過程,也意味著生態的人為重構和感官感受的再分配。而且,這樣的重構和再分配往往是權力不對等的產物。
1930年代是上海摩登的巔峰。這座半殖民地東方大都市的精神圖像,與物質主義、世界主義和奢靡頹廢緊密相連,留存到今天的“魔都”形象。
氣味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呢?
可以來看一部文學作品,劉吶鷗的短篇小說《禮儀和衛生》,發表于1930年代,是典型的新感覺派小說。作者描畫了南京路街道的三種空間類型,每一種都有不同的氣味和感官感受。
先看第一種空間類型。它是現代辦公樓,主要集中在南京路靠近外灘的地方。男主人公啟明是一位律師,在寫字樓上班。他替一位太太打贏離婚官司后,在闊太太中突然變得炙手可熱,辦公室里每天都有綢緞的摩擦聲和香水胭脂的氣味。
接下來一段,更詳細地描繪了這樣一個春日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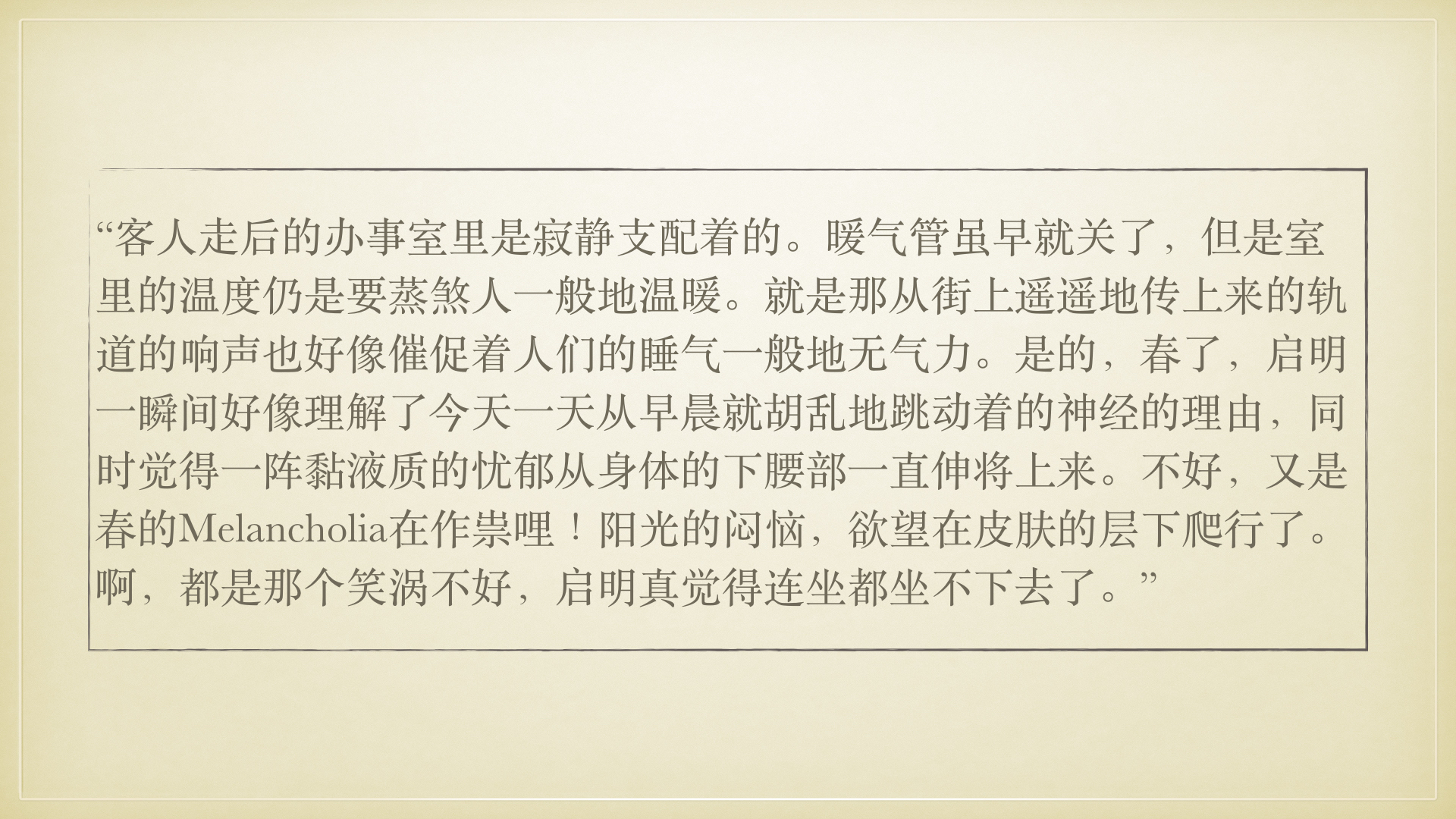
這是典型的新感覺派的描述,強調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感官的綜合體驗,令男主人公欲望蠢動。現代辦公空間里的氣味和感官感受,其他新感覺派作品中也常出現。比如,穆時英的《煙》里描述男主人公的辦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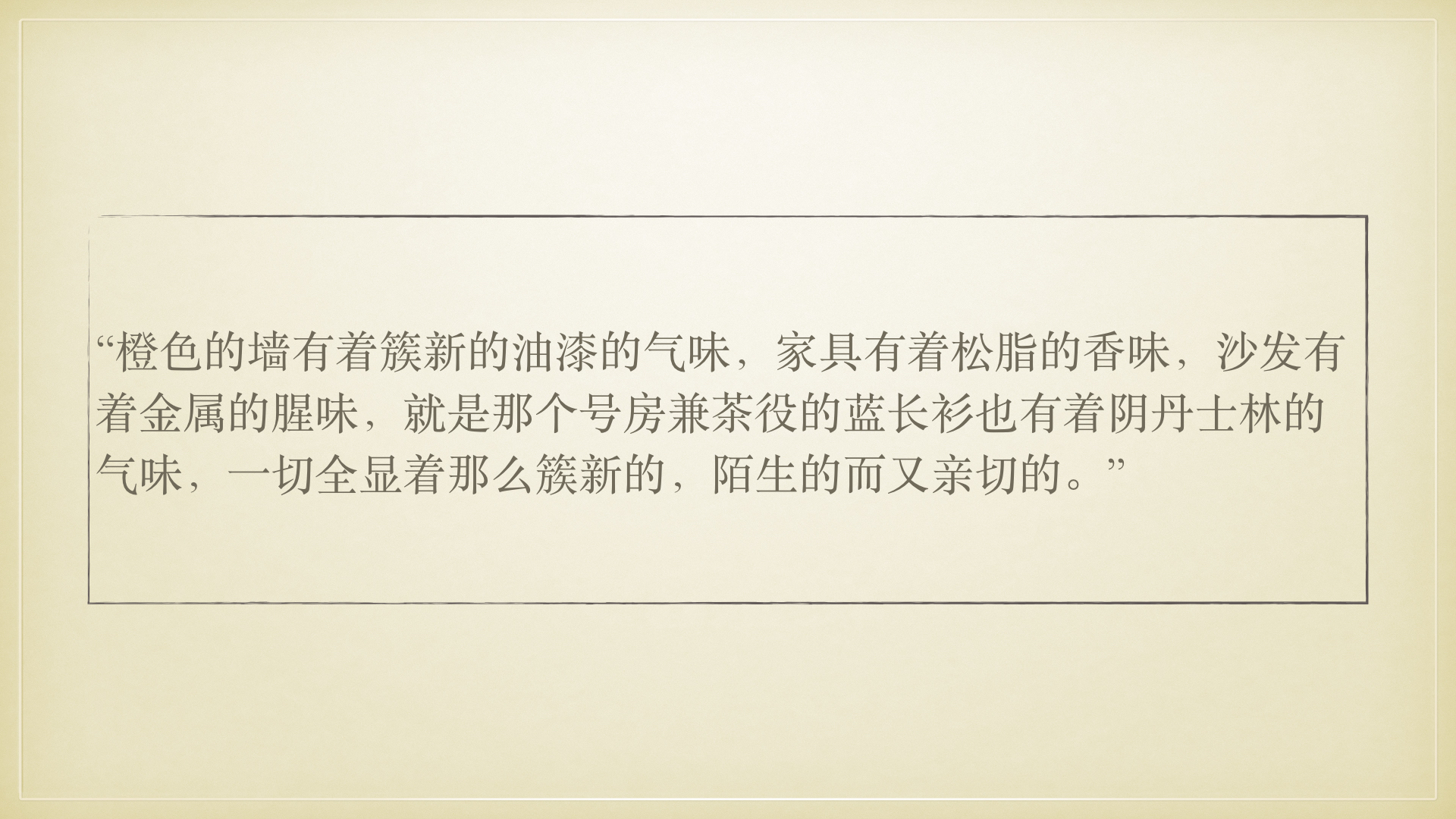
穆時英的短篇小說《白金的女體塑像》中有一段,講一位醫生的感官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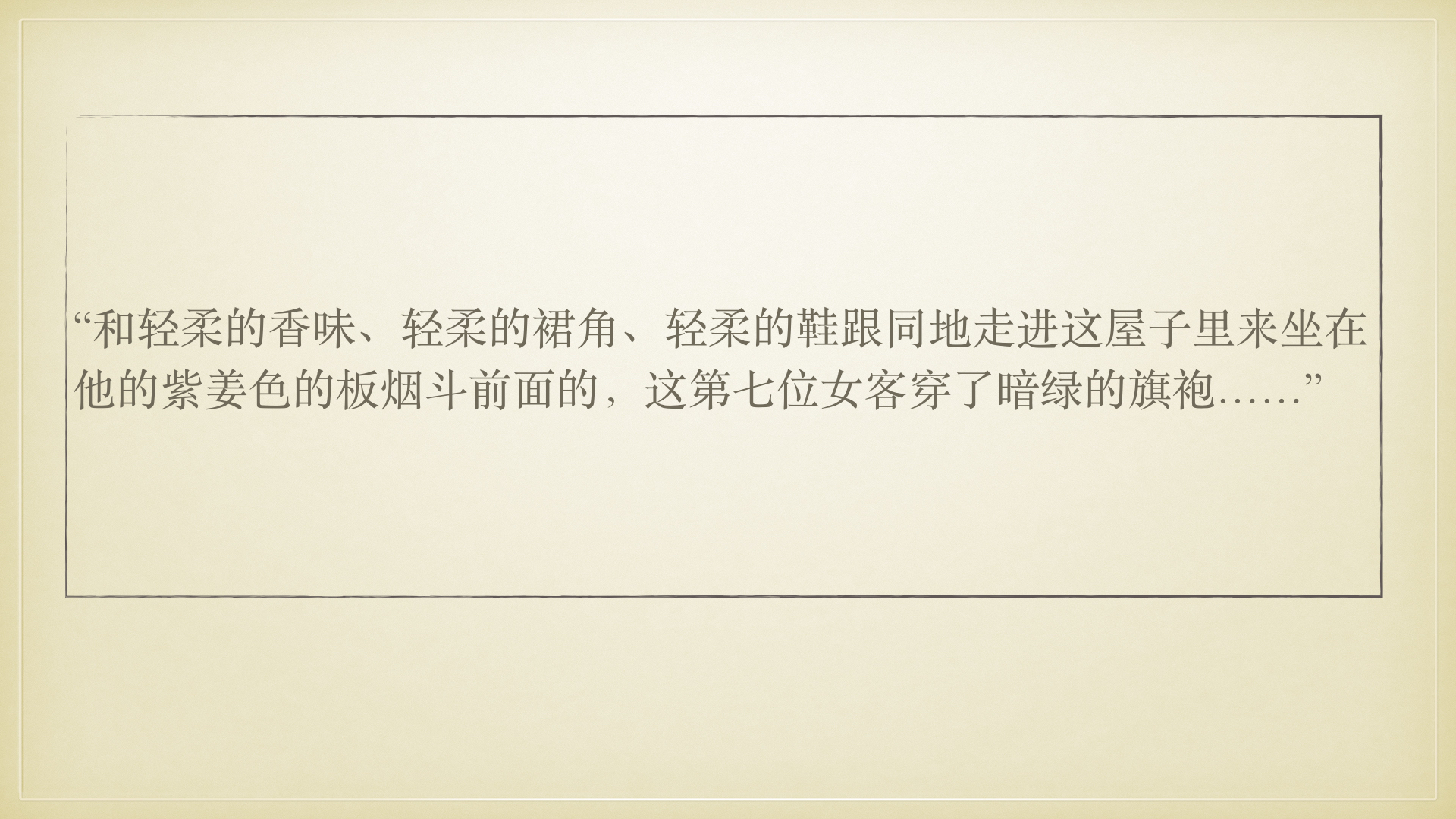
南京路上的寫字樓,延續了1850年代以來的祛味理念。另一方面,這些空間也是對女性開放的,因此變成了一個欲望公共化的場所。感官,尤其是嗅覺,是重要的中介,其中也涉及性別資本的交換,某種意義上挑戰了傳統的性別差序。
讓我們再回到《禮儀和衛生》。律師啟明在辦公室被挑動起欲望之后,決定提早下班,下樓來到南京路上。這一段調動了各種感官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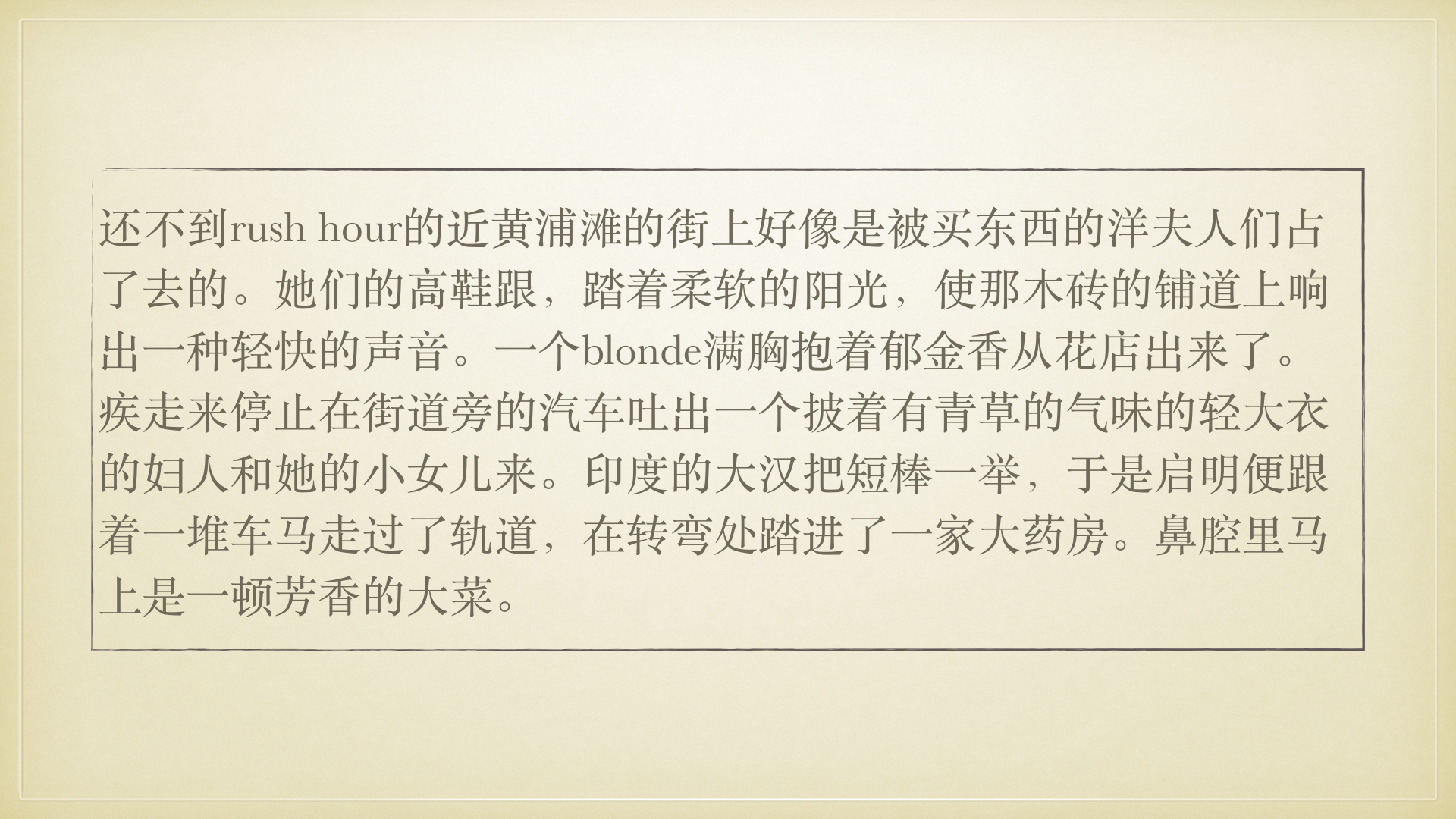
當他來到藥房時,出現這樣一段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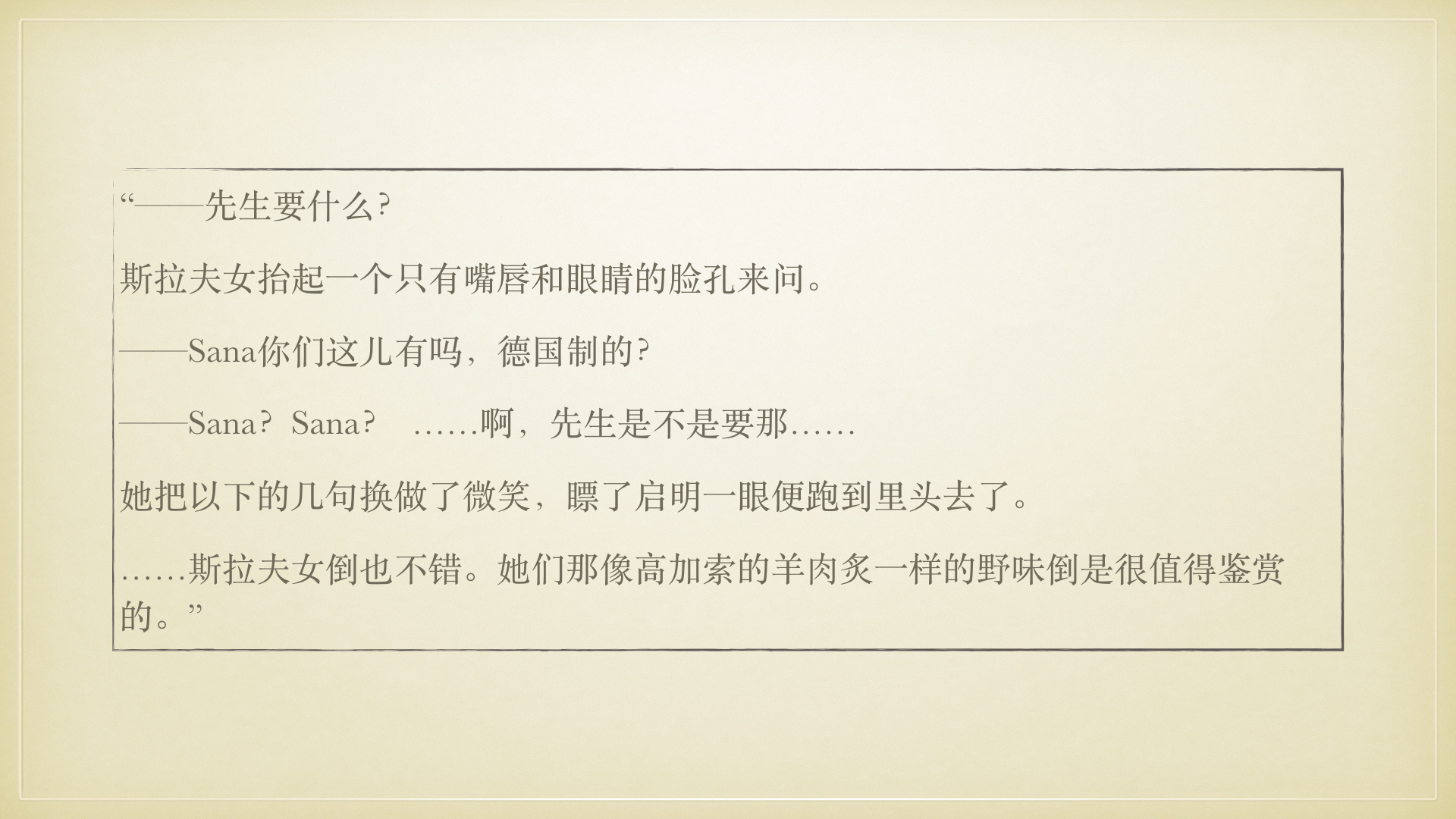
這段描述怎樣解讀?南京路的街道空間里,我們看到的是世界主義的感官和權力游戲,也是半殖民地的現實圖景。洋太太攜帶花香和青草的氣味。低了一等的斯拉夫女,則散發野味的氣息,更挑動欲望。對黃種人啟明來說,他享受這種曖昧的欲望投射。嗅覺是一種既親密又隱秘的媒介,但真正滿足欲望的對象,要去別處尋找。
他去哪里尋找欲望的實現呢?——是離南京路不太遠的一條弄堂。這里又有一段描述:

這里充分體現了分化的種族-空間結構。弄堂里市民生活的空間,也是上海這座城市或南京路街區的精神圖像的組成部分。有趣的是,啟明的感官感受,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上海弄堂蒙上一層異國情調。作為一名高等華人,他采納了西方人的視角。至于滿足自身身體欲望的具體對象,他選擇的是一位中國的妓女。所以,半殖民地世界的分裂感也包括身心的分裂,而感官是折射意識形態的介質。
最后來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南京路的氣味地圖是如何被重塑的。這個文本以南京路為背景,叫《霓虹燈下的哨兵》,是1962年首演的舞臺劇,1964年改編成電影。
作品緣起是1959年開始的“學習南京路上好八連”。好八連是參與解放上海的一支連隊,被派駐到南京路。將好八連列為標兵,與南京路的象征意義有關。只有抵擋住資本主義的糖衣炮彈和香風毒草,社會主義才能夠站穩腳跟。南京路的奢靡感官空間,必須被賦予新的意義。
有趣的是,劉吶鷗作品中的三種空間類型,也出現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氣味同樣是傳達意識形態的媒介。
開頭幾位反面人物出場的空間,類似啟明的現代辦公樓。兩個美國人支持的國民黨特務走進這棟樓,說了這句臺詞:“讓紅的進來,不出三個月,我們叫他趴在南京路上,發霉變黑爛掉。”臺詞充滿了感官上的刺激性。南京路的香氣,與霉味、腐味形成鮮明對照。寫字樓空間象征舊的秩序。新與舊的對決也是香與臭的對決。
整出戲的劇情主要發生在南京路的街道上。第二場開幕是這樣的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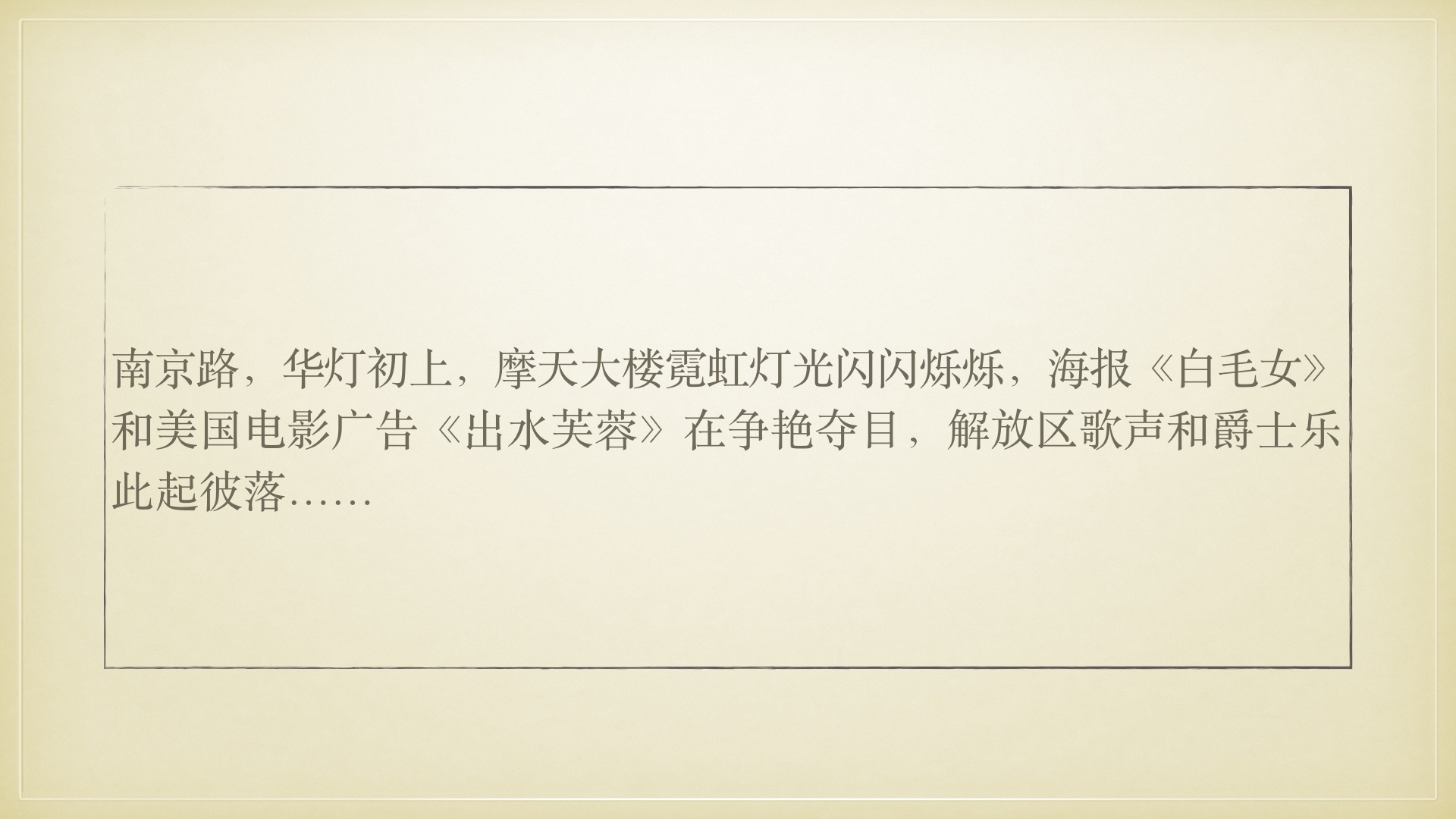
劇照上可以感受到大街上香水胭脂的氣息。這里有先施公司的櫥窗,還有穿著旗袍的女士。
下一幕,一位叫做趙大大的解放軍戰士在南京路巡邏,遇到一個賣花女叫做阿香。
阿香問趙大大說,夜來香要吧。趙大大趕緊躲開,阿香還是抓住不放。趙大大則繼續背身。阿香強調說,花是香花,你看看,白蘭花、梔子花、茉莉花、玳玳花,還有夜來香。隨便撿一枝回去,放在房間里,到夜里保證特別的香,你太太一定會喜歡。趙大大不知所措,繼續用語言強調,小大姐請你站得遠一點,好不好?阿香說,那好吧,我不要你錢,你就去聞一聞,然后把花送到趙大大面前。趙大大繼續回避,把鼻子捂起來。
這段話讓我們聯想到劉吶鷗筆下南京路的春日。但跟啟明不同,趙大大把感官刺激和欲望剝離了開來。他把欲望放在獻身共產主義的精神追求中,這當然是該劇的核心思想。有趣的是,也非常符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
編劇還安排了一位動搖的戰士陳喜。陳喜也是好八連的一位戰士,在南京路上被亂花漸欲迷人眼。這時他的愛人從老家過來,她非常熱切地望著陳喜,而陳喜眼光中似乎有一些尷尬的表情。后來的對話顯示,陳喜嫌她穿的衣服太土。
因為陳喜非常享受南京路的香氣,就發生了下面這段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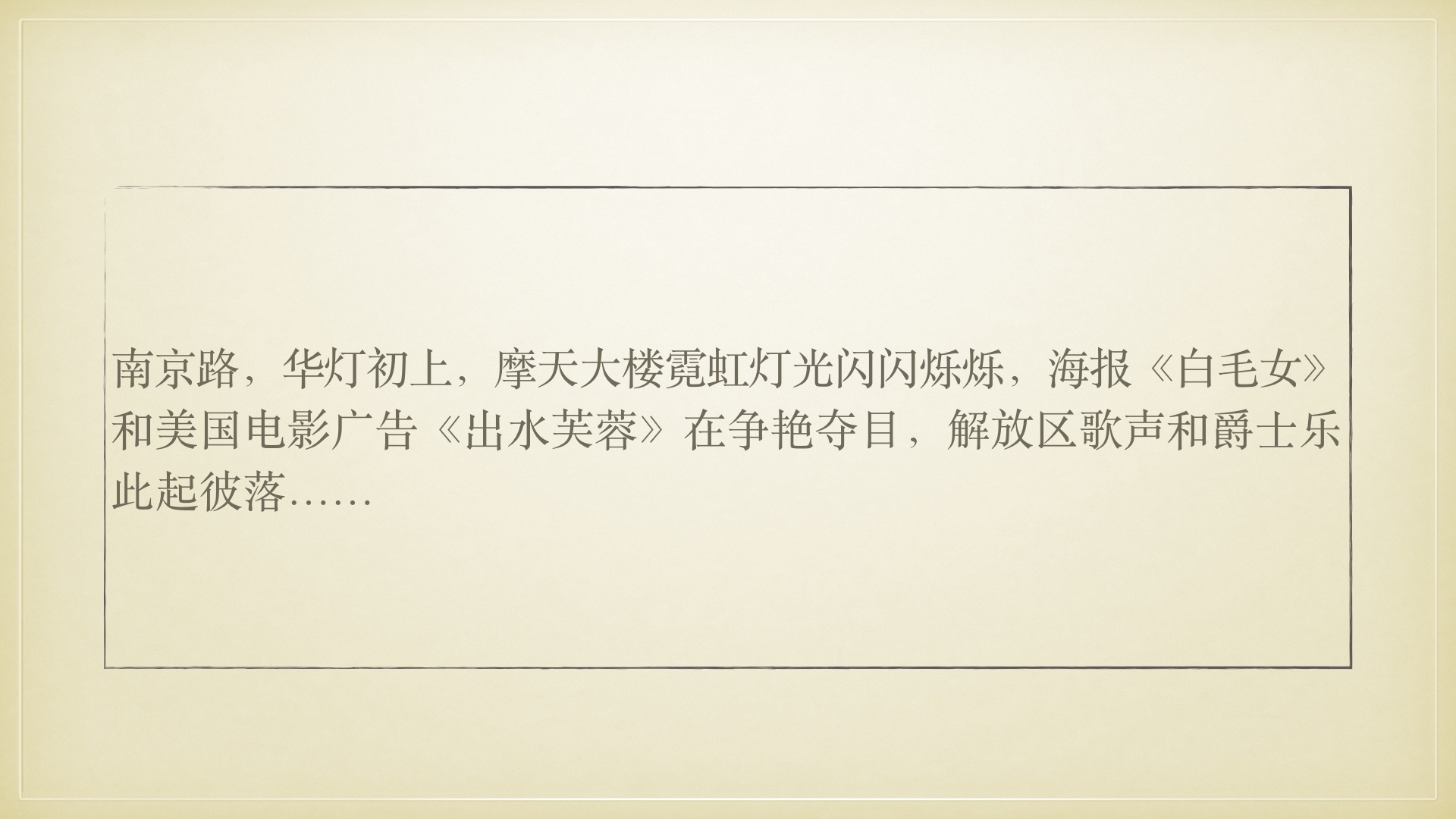
最終,陳喜這個反面教材,被轉化成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教育功能也在感官轉化過程中彰顯。香風一詞,后來成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流行語,資產階級的香風毒氣,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這些政治上的慣用語,都是從這出戲里來的。
再看一個空間,是南京路周邊的弄堂。這里又有一段賣花女阿香跟趙大大的戲。阿香因無力償還欠債而遭遇毒打,將被販賣到香港。趙大大出現解救了阿香,還給她還債的錢,令她感激涕零。這個弄堂大致應該是啟明買春的街區,啟明的故事里,它是半殖民主義夾縫中的情色空間,是滿足小資產階級個人欲望的場所。但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同樣的弄堂空間,意涵更為單一。它是以南京路為代表的殖民現代性的對立面,是勞苦大眾受壓迫的象征性空間。
趙大大扮演的不是尋樂者,而是救贖者。他呼吸著勞動人民的氣息,滿足的是抽象的集體和國族的欲望。把這個場景跟前面的賣花場景放在一起,大家更可以體會到,欲望與感官是如何被剝離的。
有關弄堂空間,還有第六場的棚戶區。根據劇本描述,它離南京路不太遠。蘇州河邊上,當時有許多棚戶區。電影畫面中,我們仿佛聞到潮濕污穢的氣息。劇本還提到餛飩的香氣和五香茶葉蛋的味道,阿香的母親去點香求菩薩保佑女兒不要被拐賣到香港。當然,菩薩沒有幫助到他們,最終是解放軍解救了阿香。在這里,城市的精神圖像被二元化。棚戶區和弄堂,是貧窮、迷信和絕望的化身,而餛飩和茶葉蛋的香氣是人民的感官指涉,他們等待救贖。
來看一處非常有意思的尾聲,是在紅玫瑰和白玫瑰的香氛中做結。這幕戲發生在南京路的花店,間諜和解放軍分別買了一束白玫瑰、一束紅玫瑰。接下來場景發生在咖啡館,咖啡館的味道是殖民現代性的化身。但最終,南京路花店的味道和咖啡館的意涵都被翻轉,變成了敵我斗爭的道具。間諜在白玫瑰中裝了一顆定時炸彈,被手持紅玫瑰的解放軍識破。紅玫瑰戰勝了白玫瑰,從色彩符號學上,也象征了共產主義的勝利。
由此,可以看到南京路的氣味地圖得以重塑,所有新的意義都建立在舊的意義的基礎上。所以,一座城市的精神圖像,是在感官感受中層層累加,與歷史緊密相連。
我簡單報告到這。最后想以2022年底的南京路作結。人們戴著口罩,也可能嗅覺失靈。你聞到的南京路是什么樣的氣味,跟當下的歷史又怎樣勾連呢?它一定會化作我們個體和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提問:氣味分很多種,不僅是香和臭,背后的譜系,牽扯到心理機制。我想了解更多關于個人經驗,比如聞到氣味產生情緒變化,導向什么樣的研究。有沒有一些感官史入門的書籍,或是研究方法導向性的理論著作?
答:香和臭中間有著廣闊的譜系,但目前多數氣味研究的書,重點聚焦在香臭兩極。尤其是除臭。一本非常重要的書,是法國歷史學家阿蘭·科爾班(Alain Corbin)的《瘴氣與黃水仙:18—19世紀的嗅覺與社會想象》(The Foul and the Fragrance: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可說是嗅覺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書里寫的除臭與現代性,變成了主流的研究取徑。
關于香和臭中間,細微的個人經驗和感受,引發的情緒和心理機制,非常值得做感官研究的去探索。人對氣味的感受,有很大的模糊空間,也被現代科學所印證。同樣的化學分子,在不同情境中聞,會聞到不一樣的氣味。科學家認為,人的大腦,視覺處理機制有比較清晰的模式,但嗅覺對應模式不明顯,不是“一就是一”。聞到某個味道,覺得是香是臭,有很多闡釋空間。
對于香和臭兩極化的想法的反思,也跟當下后結構主義有關。我們試圖重新建構一個并不是被啟蒙主義的二元分化、理性和感性這種圖譜決定的視野。關于感官身體,是很好的可以切入的話語。人的個體經驗,包括正經歷的疫情等,每一個人的感官感受、身體感受,都存在巨大的差異和變化,無法用二元對立的方式規約。
至于感官史入門的教科書,David Howes,康斯坦絲?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編了很多書。兩位加拿大人類學家編的書不只涵蓋人類學領域。2018年,David Howes編了一套四卷本的感官研究叢書(Senses and Sensation: Critical and Primary Sources)。2014年克拉森編了關于感官史的六卷本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是通史性的叢書——從古希臘、古羅馬到當代,但重點局限在西方。這兩套叢書中涉及的非西方的研究都很少。。
提問:當前景觀史的研究,強調人對景觀的認知和再形塑,也更強調視覺。這是對前面研究的反思和突破嗎?另外,感官史和景觀史的關系,不知是怎樣的。
答:你提到,景觀史強調人對感官的再形塑,人類學家早期引入感官研究時,一個很重要的論點與其非常接近。就是說,感官過去好像只是科學家研究的范疇,現在強調感官是文化和社會去形塑的,他們喜歡用的詞,是“culturally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這個論點今天并不稀奇。我想強調,某種程度上應跨越這樣一個論述,重新思索景觀本身,或感官本身、化學本身:當病毒把你的嗅覺神經破壞,瞬間什么都聞不到時,這種體驗對我們理解文化和社會有什么樣的貢獻呢?
十年前開始做氣味研究時,我也主要想看我們的文化社會歷史,到底怎樣形塑感官。直到最后快要寫完全書時,才有更深一步反思。
近些年人文學術的發展,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后人類中心主義(posthumanism)等,都是比較前沿的視角。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讓我們從人的角度稍微往后退一步,試圖從動物的、環境的、物的角度,去看這個地球。尤其是2020年以后,疫情及環境問題,給了我們深刻觸動。“人類中心主義”看問題的方式,到了值得反思的時間點。
提問:當我們從作品中捕捉到這樣一些嗅覺元素,可以怎么向“嗅覺”發起正面強攻,關聯到一些我們比較熟悉的命題?另外,比如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中,當時有沒有去爭奪、重新再造嗅覺?
答:古典文學寶庫里,有許多值得研究的材料。2022年10月我在臺灣的中央大學明清文學研究所做了一個演講,當時講了紅樓夢。我不是專門從事明清研究的學者,交流時聽到不少有意思的反饋,從明清文學或更早期文學,都可以重新思索中國傳統的感官視角。
怎樣就嗅覺談嗅覺。我想說的是,不談外圍,是不可能的。氣味不只是感官的問題,它總是關聯很多的意義和價值,這是毫無疑問的。就嗅覺談嗅覺,我想到科學和人文跨界的取徑。兩年前,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叫做Smellosophy。作者是一位科學史研究者,她的方法是采訪很多科學家,寫了類似嗅覺的科普讀本。一個啟發是,可以從神經元和分子的角度尋找答案,雖然未必一定能找到。當然,真正操作起來很難。絕大多數人文學者沒有科學訓練,要討論那些分子式有很大難度。但我讀那本書讀得入迷,它帶領你進入腦神經元,去讀解周邊的氣味環境。
第二個問題,關于左翼文學怎樣爭奪、重塑嗅覺,我自己書里有一章處理二十年代的創造社及魯迅和茅盾。我主要關注的,是這些作品中關于身體和情欲的味道。
除情色小說之外,古典小說中,對身體和情欲的味道,往往是概念化的,主要用蘭麝一筆帶過。到了二十年代,有個很重要的轉向,對身體的描述開始采用一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視角。
比如,聞到一個女性的香味,張資平會說,聞到一種弱醇性的呼吸的氣味,而不再是蘭麝了。這里透射出很重要的近代身體觀和感官文化的變化。
前兩年復旦大學康凌老師的著作《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討論了詩歌中的身體技藝,是從聲音的角度處理的,從詩歌帶來的聲音感中,討論詩歌怎樣與身體關聯,是研究革命的一種不同取徑。左翼文學中,我相信一定也有許多跟氣味相關的,又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