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封閉的山谷猛然敞開”——關于阿乙的三部隨筆集
原創 徐兆正 文學報
《通宵俱樂部》是小說家阿乙最新隨筆集,記錄他在1996至2020年間的寫作。阿乙在書中擷取的片段與場景,有的來自父親的一次托夢、母親的呢喃、鄉友的傳聞;有的來自對病友的速記,對自己和他人生活的圍觀……旨在喚起人們在生活、智識上的熱情。他將目光投向生活中容易為人忽略的事情,始終保持著對周圍事物的觀察,機敏地捕捉生活里那些快如閃電的東西,用寫作讓這些情緒與感覺有機會被“看不見的人看見”。
這部作品風格延續阿乙之前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文章短則數句,長則數千,仿照日記體裁,而實為對“一種感覺、一種情緒”的捕捉與描述,表面看是個人化的產物,而處處能使讀者產生共鳴。它們是作者對自己偶像卡夫卡所做的風格上的模仿與致敬,正是在這種致敬中,作者的寫作獲得更多的自由,出現了更多的想象力,并描繪了更多在生活經驗之外的事物。
評論家徐兆正認為,阿乙此前的隨筆集《寡人》或《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我們多少還能看出虛構與現實的邊界,而在這本新隨筆集《通宵俱樂部》中,由于一場浩大的夢的降臨,作者直接廢除了虛構的真值標準。夢既為阿乙的作品帶來了一種難以言傳的氛圍——人世的似是而非、置身時光的恍然,也在一定程度抵消了當下的嚴峻現實。如同暗戀者的純粹曾賦予阿乙的小說以先天真誠的品格,抵消或補償現實的夢在某種意義上同樣哺育了他的寫作。讀過《通宵俱樂部》之后,關于這一點我們會看得更加清楚。


“封閉的山谷猛然敞開”
——談談阿乙的三部隨筆集
刊發于2023年2月2日文學報
壹
《通宵俱樂部》以前,作家阿乙推出過兩部隨筆集:2011年的《寡人》,2015年的《陽光猛烈,萬物顯形》。“寡人”或不單指“孤獨者”,阿乙使用它,同時也指向了“偏執、孤疑、刻薄、惡毒、軟弱、頹廢、矯情、殘暴、自憐、自私、自棄、恐懼”等等偏負面的自我描述,用前言的話說即:“我像塊陰暗的石頭,大多數時間待在房間里。既不立足于人間,也不存在于冥界,就是在陰陽重疊之處孤零零地活。所見世界早已蕭條,有著昏暗而透明的光芒,就像天空涂了一層薄的硫磺,同時四周刮陳腐的冷風。”這幅自畫像誠然與現實生活的那個作者不符。《寡人》出版的時刻,阿乙已經寫作五年,其間有兩部小說集《灰故事》與《鳥,看見我了》先后面世。因此,這些晦暗語詞更像是作者對個人寫作風格的一次歸納,決定出版它,則表明其開始有意強化這類風格。此刻回想我熱愛阿乙的源頭,便來自對這部隨筆集的閱讀:通讀《寡人》一過,我寫下第一篇關于阿乙的評論,并且向一位朋友要回了那本他借走很久的《鳥,看見我了》。
就寫作時間來看,《寡人》早于《灰故事》與《鳥,看見我了》;就內容而言,《寡人》收錄的多半是卡夫卡式的“小敘事”。作者后來也在諸多場合坦承他的寫作開始于此,是卡夫卡授予他“獨自與上帝交流的權利”。但在正式寫小說后,他并未拋棄這類富有樂趣的寫作,于是也就有了第二本隨筆集。“陽光猛烈,萬物顯形”這個題目在阿乙筆下同樣是一個經久的意象,某次活動上他還原了這一場景:“那時候我非常喜歡一個人,有一天我看到她老遠走過來,畫著個豬血般的口紅,那天陽光非常猛烈,口紅格外醒目,她的清純形象一下子崩塌了。那一瞬間,我感覺整個世界都墮落了。”這段經歷最初見諸《寡人》,后來又被寫入小說《意外殺人事件》與《獵人》,可見觸動之深:“我們說起來只見過五次面——本來還有機會見面的,但當你涂滿口紅在將近一百米的遠處浮現出來時,我轉身跑掉。那天陽光太過猛烈,道路曬得發燙,一經扭曲,我只一眼便看見你的衰敗。時間這東西穩步前進,將我弄得尷尬不已。”


一如卡夫卡,小敘事在阿乙筆下其虛構與真實的比例同樣難分伯仲。虛構的一面,有《寡人》中的《熟悉》《您好》《殺戮》《吳承恩》《吃人者》《賊城》《剽竊》《葉公好龍》《嗯》《畫仙》《醫生》《玉皇大帝》《大鳥》,《陽光猛烈,萬物顯形》中的《豹子》《兒子》《記憶》《逃亡》《忘字》《幽閉》《猿猴》。于創作之初,想必他已寫過大量這類篇幅短小、志異色彩濃厚的故事以為訓練。筆者此前受阿乙委托編選《五百萬漢字》一書時也據此辟出“志異”一輯,收錄了《信使》與《五百萬漢字》兩篇,但更多此類作品,因認定文學自有嚴肅與游戲兩分的心結,阿乙是拒絕將它們歸入“小說”的。直至近年來寫作發生轉向,他開始重新審視這類寫作,才賦予了志異以一定的合法性。《騙子來到南方》中那些千把字的短制,如示以“短章”的《用進廢退》《鉤子》,示以“寓言”的《嚴酷的事實》《想學魔法的孩子》《追趕一只兔子》,其源頭就在這里。行至《通宵俱樂部》,讀者或以為阿乙的隨筆多了些板正,但這正如《未婚妻》的筆法融入幽默一樣,無非是文學的雅與不雅,嚴肅與通俗,“宣示我看見的真相”或“滿足于講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在作者這里已不再是一個問題。
貳
隨筆集非虛構的一面,或可當作步入阿乙虛構世界的一曲暗道,個中有交代虛構本事的創作談,與小說同一主題的速寫,亦有大量讀書筆記。此間印象較深的是他指出《小人》存在地上、地下兩條河流,前者是敘述連貫的故事,后者為若隱若現的細節。若細節未被留意,它們不會干擾明處;惟當注意某些草蛇灰線,又帶著后知后覺的預感重讀整個文本,“地下的終將洶涌而出”,并“推翻人們的一切認識”。相似的筆法也見于《一九八八年和一輛雄獅摩托》《永生之城》《早上九點叫醒我》等篇。離開這些解密性質的副文本,小說仍自我成立,但在讀過小說后進入虛構誕生的現場,自然會生出一番原來如此的感喟。此外,他也將一些向未示人的詩作放進了隨筆集。

《寡人》一書依時間倒敘形式編排,以之呼應了前言提到的卡彭鐵爾“講述時光倒流、返老還童”的小說《回歸種子》,《陽光猛烈,萬物顯形》取字母表形式是受到了《羅蘭·巴爾特自述》的影響。《通宵俱樂部》重新采用時間正序的線索,起首一則寫于1996年:“終于收到來信。捏著它時,我感覺發燙。”這里賡續的是《寡人》最后一節(“這是我第一次喜歡一個異性,像封閉的山谷猛然敞開,大風無休無止地刮進來。”),后者寫于1995年,日后他還會在《偏執》《曠日持久之事它可能的根源》等文細細寫到這段長達八年、見面五次的暗戀,他為“世界有這么簡單這么正常的道理而痛哭”,“一直沒想到它是世界恒在的荒謬”,轉而又覺知“荒謬本身就是合理的一部分”。不過,痛苦的“起源”早已遠去,包括那些燃燒著的時候感嘆號四濺的贊美詩,均已轉化為寫作的源頭。暗戀者的身份褪去后,一個真誠的寫作者就誕生了。
《通宵俱樂部》中,1996年至2012年的部分不抵十分之一;2013年以降,每一年的篇幅逐年見多。這里有決定阿乙寫作的第二重因素:2013年的疾病。此前兩年,他曾三次起意完成自己的第一個長篇,但無一例外止步中篇(《模范青年》《下面,我該干些什么》《春天》)。那個被稱為卡斯特曼的疾病,發作于阿乙第四次向長篇進攻中途——在將《早上九點叫醒我》推進到一半之際,他開始吐血,住院。待病情穩定,方才完成第一部長篇。故此,《早上九點叫醒我》開篇的話亦無妨看作是他在那個時期的內心獨白:“金艷正在度過她人生最難度過的時刻(每個人都有一些艱難的時刻需要度過。面對這恐懼、孤獨、難熬,似乎只有自盡才能解脫的時刻,我們屢次禱告于偉大的時間,求它加速推進自己的齒輪,好將我們帶離現在)。”隨后,他又以這段經歷完成了另一中篇《虎狼》。由《虎狼》肇啟的反顧自身等寫法,直接將阿乙的創作廣義地分成兩段,第一段是2005年到2014年,第二段是2014年至今。
叁
《虎狼》這篇小說里,那個一直以來過分忠實的福樓拜信徒開始在虛構中現身。之于眼下瞬間的記錄,與其說是要為虛構貯存素材,不如說是敏感的意識放緩了時間流動,而他要寫下關于存在本身的震驚體驗。在近似絕對的當下,主人公正在做的事卻是回到過去。這一姿態還將重現于《對人世的懷念》,即一面是“我”循著祖父的腳步走進阮家堰,復又返回故鄉,一面是這些廢墟似的空間忽而被虛構照亮。這兩重特色最終融匯灌鑄為一種“內在性寫作”,這個詞大抵解釋了他在2022年底出版的隨筆集《通宵俱樂部》與長篇《未婚妻》。略有分殊之處,是《未婚妻》代表著從當下跳板向著記憶河流的縱身一躍,《通宵俱樂部》純粹聚焦剎那須臾的所思所想。后面這個題目同樣蘊含了“延宕”的意味,誠如年幼的馬塞爾不愿離開母親獨自上樓睡覺,阿乙同樣渴望無窮無盡、散發著光和熱的夜晚,自己得以參與和朋友的圍爐夜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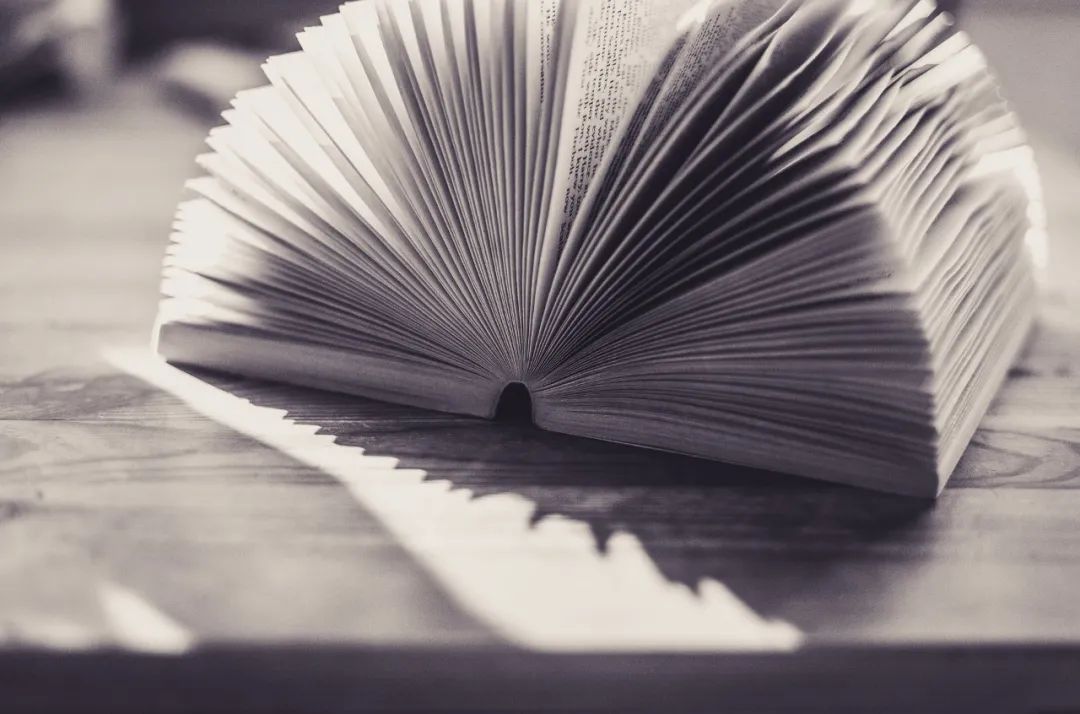
也正是在這個充滿幻想的題目之下,我們讀到了大量略顯驚悚的對病友情狀的速寫與“訪問夢境”的記錄。前兩本隨筆集也有不少關于夢境的記敘,其中多數是醒來后遺憾夢中世界的消失。在《記憶》一文中他這樣寫道:“人重新進入過去,情況類似于救火,能記錄下來的財物有限。有時燒掉的廢墟太難看,還需進行拙劣的重建。無論怎樣,從離開事情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對原貌的掌握。這是做人痛苦的一部分。”此刻,造訪夢境暗示的是作家其時的苦惱:他正在忍受記憶日漸風化的焦灼,在虛構時也頻頻感知無力,于是便渴望重新攫取自己的早年經驗,而這些經驗又早已像鈔票一樣用掉,或是為遺忘的大雪覆蓋。如此,焦灼便幻化為帶有同義反復性質的關于遺忘的夢。夢與現實是一種鏡像關系:夢醒后的悵然是一種經驗的喪失,現實生活中經驗的匱乏同樣是記憶流散的結果。對夢境的書寫構成了指向現實的隱喻——遺忘的夢總是經驗匱乏者的夢。至于《通宵俱樂部》,夢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它不再是焦慮的替代物,而是夢與醒之間的屏障,或者說它是作者為了抵抗自己過早面對登時的恐懼,而必須要在兩種時間的感覺間找到的可以神游太虛的一刻。
對于《寡人》或《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我們多少還能看出虛構與現實的邊界,而在這本新隨筆集,由于一場浩大的夢的降臨,作者直接廢除了虛構的真值標準。夢既為阿乙的作品帶來了一種難以言傳的氛圍——人世的似是而非、置身時光的恍然,也在一定程度抵消了當下的嚴峻現實。譬如他寫到一對年老夫婦在“思來想去”之后想把自己的神童孩子交給國家;一位精神病院護士向“我”轉述聽來的話,某位病人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同時被父親與祖父占有,這個人下決心來醫院,并非他認為自己的精神狀況出現問題,而是他無法調停父親和祖父的爭執。這些片斷,連同每一篇右上角標注的寫作地點——它們往往是“協和醫院”——讀來著實是既有趣又心酸。如同暗戀者的純粹曾賦予阿乙的小說以先天真誠的品格,抵消或補償現實的夢在某種意義上同樣哺育了他的寫作。讀過《通宵俱樂部》之后,關于這一點我們會看得更加清楚。
原標題:《“封閉的山谷猛然敞開” ——關于阿乙的三部隨筆集 | 新批評》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