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聽李敬澤賈樟柯雙雪濤聊故鄉(xiāng),開啟文學(xué)“博物館奇妙夜”
賈樟柯23歲離開山西,去北京求學(xué)。他一度對老家密切的炙熱的血親關(guān)系和家族生活心生抗拒,但來到北京之后,隨著年齡增長,他又突然很留戀那樣的生活。
32歲來到北京的雙雪濤對故鄉(xiāng)是另一種感覺——相比宗法社會,東北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集體社會。他曾以為,全世界的父母都在廠子上班,回家之后身上有油漬。
“你會發(fā)現(xiàn),一代一代的人,滿懷對世界的熱望。為什么我們那么熱愛火車,那么熱愛飛機,因為外面有更廣大的世界。但是飛出去了,走出去了,最后你發(fā)現(xiàn)你有個心病,這個心病叫‘故鄉(xiāng)’。”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館長、作家李敬澤說。
2月5日,由世界最大的文學(xué)博物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打造的人文漫談節(jié)目《文學(xué)館之夜》上線第一期“由故鄉(xiāng)出發(fā),創(chuàng)造你的生活和世界”,李敬澤與導(dǎo)演賈樟柯、小說家雙雪濤、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副研究員李蔚超四人圍坐,暢談故鄉(xiāng)帶給我們的一切。

節(jié)目劇照
“沒有離開,就產(chǎn)生不了故鄉(xiāng)這個概念”
這一場漫談從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塑造的兩個“故鄉(xiāng)”開始,一個是魯迅的《故鄉(xiāng)》,一個是沈從文的《邊城》。
“古人談故鄉(xiāng),葉落歸根,終究是要回去的。”李敬澤說,“但從魯迅的《故鄉(xiāng)》開始,故鄉(xiāng)是你離開、歸來,然后終究還是要離開的那么一個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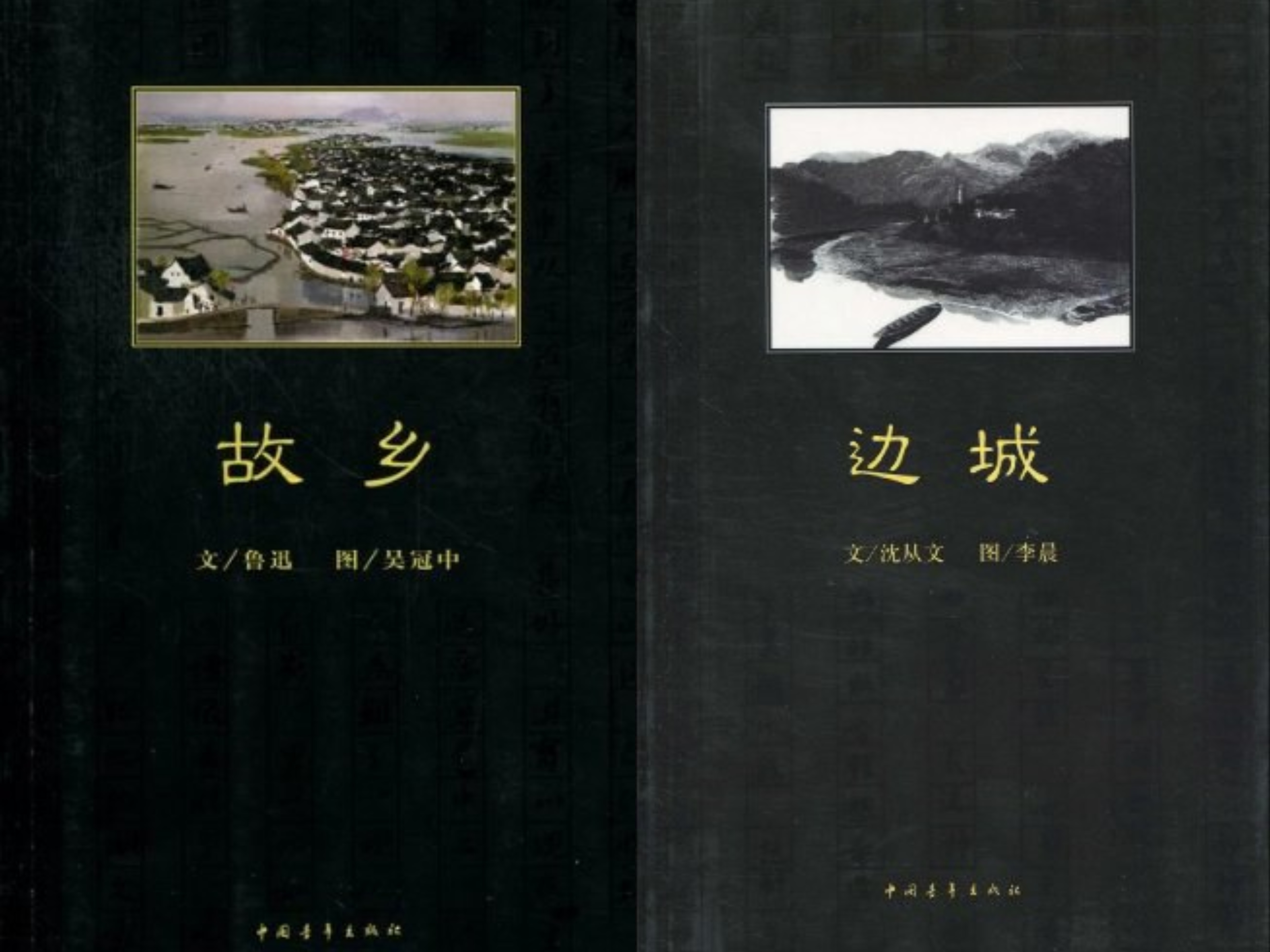
魯迅的《故鄉(xiāng)》,沈從文的《邊城》
李敬澤的父親是山西人,母親是河北人。當(dāng)年因為父母工作調(diào)動,他們家圍著天津、保定、石家莊幾個地方轉(zhuǎn),也讓他對每個地方都沒有那么強烈的認(rèn)同感。他一直記得,小時候去河北姥姥家,人家都覺得這個外來的小孩講普通話,很高級,很洋氣。但他的母親,一個從這個農(nóng)村出去的人,回去后就得換成方言,不然別人會覺得:“你裝什么裝。”
賈樟柯對故鄉(xiāng)的“獲得”恰發(fā)生于離開之后。離開之前,家鄉(xiāng)的一切讓他感到混沌,他甚至沒有意識到那個半山環(huán)繞的小城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當(dāng)他坐在電影學(xué)院里,寫下思念,他腦海中的故鄉(xiāng)才漸漸明晰起來。
雙雪濤小時候也沒有太多對故鄉(xiāng)的感知,他一度以為整個世界都是鐵西區(qū)的樣子。后來上了初中,他從鐵西區(qū)到了和平區(qū),才發(fā)現(xiàn)很多孩子的父母不穿工作服,他們可能做生意,也可能做文職。再后來離開沈陽,他才真正知道故鄉(xiāng)原來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身在其中確實沒辦法理解很多事情。”賈樟柯說,“你沒有離開,就產(chǎn)生不了故鄉(xiāng)這個概念。”
“故鄉(xiāng)有兩個,一個是真實的,另一個是想象的”
開始學(xué)電影后,賈樟柯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很全球化的世界。有時他會感到迷失——我們究竟要拍什么?
還好,他在沈從文的文字里找到了共情,發(fā)現(xiàn)了自己無意識里掩藏的那些珍貴的東西。晚上在自習(xí)室,每一次拿著筆面對白紙,他的思緒就不由地回到家鄉(xiāng),那遙遠(yuǎn)的汾陽。
“如果文學(xué)可以這樣,為什么電影不可以?”賈樟柯意識到,汾陽就是他躲在呂梁山里的邊城,那里的日日夜夜,無數(shù)難忘的人和事兒,讓他落筆下去變成了電影。這電影又是他的國,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他的世界。

賈樟柯故鄉(xiāng)三部曲
另一邊,寫小說之初的雙雪濤也曾感到迷失,他感覺自己總在用一種很別扭的思維和語言,但他也沒有找到很好的辦法。直到2013年10月,他寫了一篇小說《大師》。
《大師》和父親有關(guān)。一想起父親,雙雪濤就想起父親的說話方式,說話形態(tài),那是一個說著東北普通話的男人。雙雪濤突然就找到了一個敘事的節(jié)奏,這個節(jié)奏是通過對話帶動起來的,然后他發(fā)現(xiàn),在對話之外的那些敘事,也都變得柔軟了。
“就是從2013年的《大師》之后,我才發(fā)現(xiàn)了故鄉(xiāng)的存在,或者故鄉(xiāng)的文學(xué)性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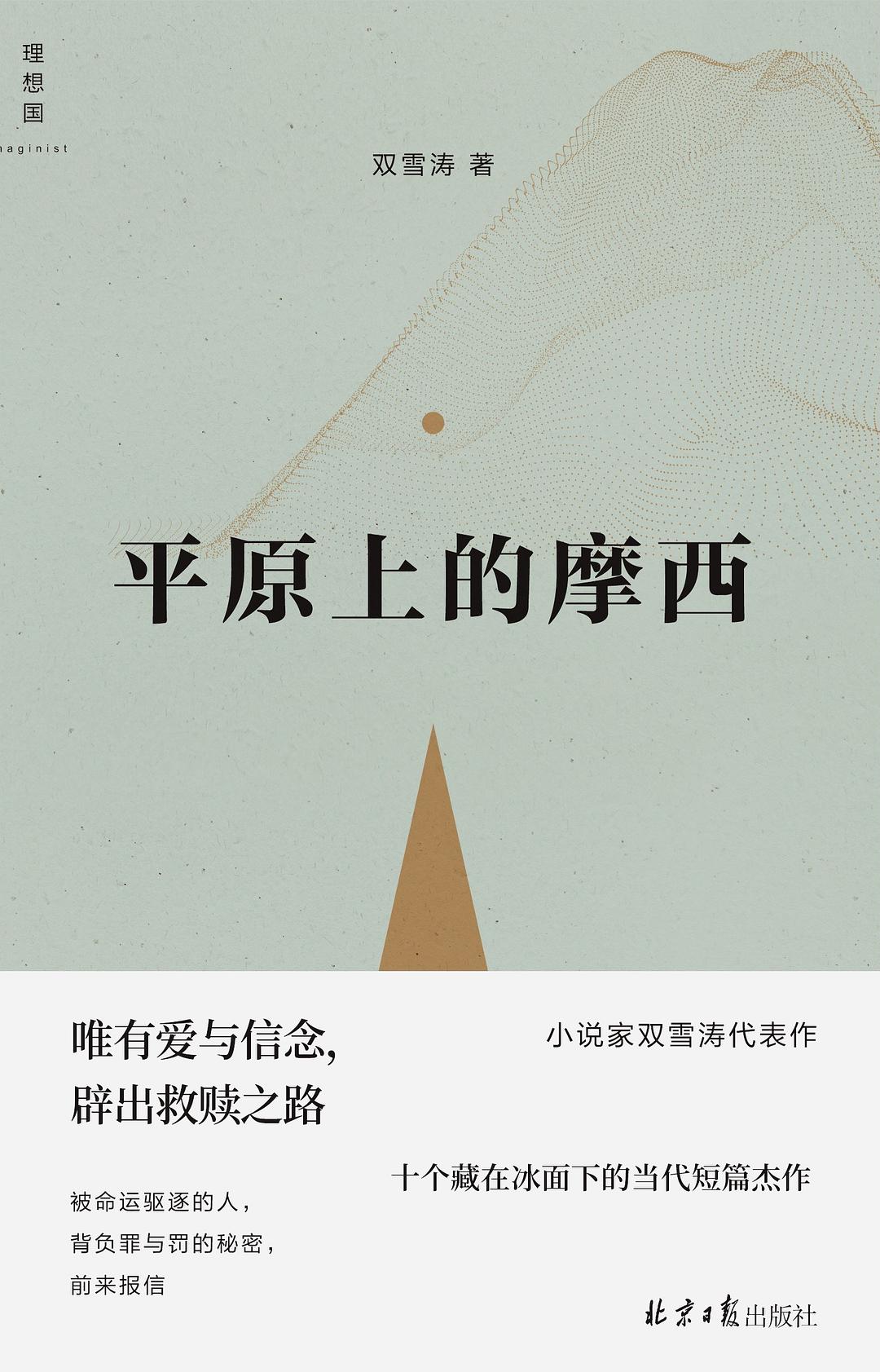
《平原上的摩西》
“對于中國人,故鄉(xiāng)問題完全是個現(xiàn)代經(jīng)驗”
在李敬澤看來,中國人像現(xiàn)在這樣大規(guī)模地離開家鄉(xiāng)也就是這100年的時間,規(guī)模再大的離鄉(xiāng)恐怕也就是近30年的事。
在這之前,絕大部分中國人一輩子生活在自己的農(nóng)村里,別說是離開家鄉(xiāng)了,可能連縣城都沒去過。所以,故鄉(xiāng)問題對于中國人完全是一個現(xiàn)代經(jīng)驗,完全是一個新的東西。
“一百多年來,故鄉(xiāng)這個概念越來越強烈,可能跟我們越來越多的身份焦慮有關(guān)。”賈樟柯說,身處現(xiàn)代社會,每個人都要經(jīng)過多次的身份轉(zhuǎn)變,可能就會有一種迷失的焦慮——“我究竟是誰?”“我是學(xué)電影的賈樟柯,還是半文學(xué)的賈樟柯?我是汾陽的賈樟柯,還是北京的賈樟柯?可能故鄉(xiāng)能帶給我們的是,你最初是誰。不管后來的身份怎么變化,我們都有一個出發(fā)的身份。”
在這個意義上,故鄉(xiāng)也是一個最初的經(jīng)驗。不管未來走得多遠(yuǎn),一定是故鄉(xiāng)給予我們對于世界最初的理解。
李蔚超向澎湃新聞記者透露,在這期節(jié)目之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未來每周都將推出一期《文學(xué)館之夜》,共七期。接下來的漫談主題有關(guān)親密關(guān)系、說話之道、父子之間、跑步文化等,戴錦華、李洱、劉震云、梁曉聲、李誕、張泉靈等嘉賓將參與其中。
“每期節(jié)目都是從文學(xué)經(jīng)典出發(fā),看待今天的生活。”她說,比如第一夜談故鄉(xiāng)是因為2021年是《故鄉(xiāng)》發(fā)表百年,魯迅開啟的現(xiàn)代人與故鄉(xiāng)的情感模式至今影響深遠(yuǎn);第二夜談養(yǎng)貓文化與當(dāng)代人的親密關(guān)系源于一只喜歡趴在冰心墓上的館貓。冰心生前愛貓,她養(yǎng)了一只名叫咪咪的貓;第三夜談當(dāng)代人的說話之道,靈感來自館藏的老舍手稿《多編好相聲》。老舍的小說為口語表達(dá)開創(chuàng)了新的天地,脫口秀演員李誕熱愛寫作,看了老舍先生的手稿頗為興奮。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