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個中國大學生決定休學丨對話另一種生活
“等你上了大學就輕松了”,長輩們的這句勉勵成為許多人高中時期信念感的來源,所有大學招生宣傳片也都在展示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個體在大學能夠擁抱的無限可能,但事實是,與無限可能相對應的是大學生們要應對的錯綜復雜的問題:緊張的人際關系,不符合預期的發展軌跡,處處受挫的落差感……
有些人可能會自己默默消化負面情緒,有些人通過與他人的交流釋放焦慮,也有人通過旅游等放松身心……還有一群人,他們面臨的問題超過負荷的能力,“休學”成為他們的選擇。有數據表明,近幾年全國在校大學生退(休)學率接近3%,每年退(休)學人數約50萬。
怎樣做出休學決定?在此過程中經歷了哪些支持或者反對?從休學到復學,最大的變化是什么?每一個休學大學生的經歷都不一樣,他們的答案也各不相同。

大一時,新聞學專業的極目楚還對傳統新聞傳播領域滿懷好奇,在完成新聞史作業時甚至會生出“我要努力去做更多探索”的想法,但后來在院文藝部的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未來規劃。他逐漸發現他對舞臺的熱愛無可比擬,每一次靈感的迸發和順利呈現都能夠點燃他一天的熱情,他愿意熬夜剪片子甚至翹掉必修課去配合部門工作,同專業成績相比,謝幕時的圓滿與鄭重能給他更多的成就感。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諸多他無力解決的困擾——并不在預期內的保研被提上日程、校內平臺始終無法滿足他做作品的需求、日常安排與心儀的實習時間上存在沖突……他試探著和父母表達了休學的想法,但并未獲得支持,“他們一時間不明白,我為什么就要給自己安排一條似乎莫名其妙的道路”。

在此之后,他試著維持按部就班的大學生活,逃避任何與舞臺接觸的可能,但一次陰差陽錯,他還是坐在了臺下。
演出結束,觀眾們三兩結伴,說說笑笑著離場,而演出的工作人員們紛紛從臺下和幕后穿著統一的服裝走上舞臺,手拉著手鞠躬謝幕,肆意大笑著互相擁抱。極目楚沒有起身,獨自一個人坐在空蕩的觀眾席中,默默注視著臺上這群和曾經的他一樣無比滿足和快樂的人,一剎那淚流滿面。也是在那一刻,他突然就無比確定,“只有這件事情是我唯一真正想做的,無可替代的。”
對于林玥來說,休學的決定來得有些被動和突然。北京的秋天有著絢爛的金色,而她和從老家趕來的母親沒有心情抬頭欣賞,走出彌漫著消毒水味道的醫院,母親手里緊緊攥著林玥重度抑郁的確診單,嘴里念叨著“什么抑郁癥,我們工作這么累怎么也沒抑郁”。突然,她側過臉問林玥,“你輔導員讓你來檢查,是不是想讓你休學?”
林玥沉默了。她在回學校的路上翻看著自己朋友圈,大多是自己玩乙游時啰啰嗦嗦的感慨,鮮少有人點贊和評論,最新一條是,“原來上大學的意義就是一次次認識到并且不得不接受自己沒有所謂的gift這個事實”。
在此之前,林玥從未想過“休學”一詞會與自己有關,她曾一度相信自己能繼續在大學校園里大放異彩,但真正從寧夏小城來到了北京,她每天踮著腳費勁地擠過被六個人生活用品塞滿的宿舍走道,在發現學了十年的舞蹈在舞蹈團其他面試者面前顯得無比業余時難堪地垂下頭,轉專業的想法也在名額稀少的通知面前如童年吹出的泡泡一樣慢慢碎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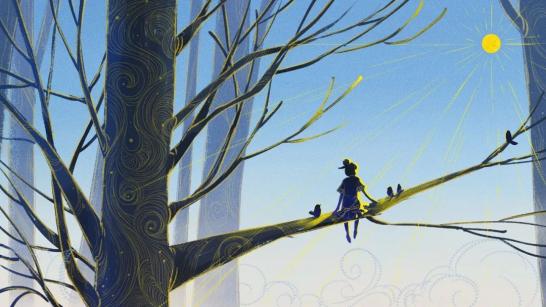
天氣轉冷,林玥越來越沉默寡言,也越來越“懶得出門”,沒有課的時候,她總是蜷縮在陰冷且雜亂的宿舍里,把自己的床簾拉得嚴嚴實實。舍友之間平時幾乎沒有交流,她躲在床簾里面半睡半醒地看劇、刷視頻消磨光陰,餓了的時候下床點份外賣,那些色彩鮮艷的食物是她一天中唯一的亮色。
母親的猜測成真了,當確診單被交到輔導員手上時,他的臉上露出“我就知道是這樣”的表情,斬釘截鐵地告訴林玥,“讓你父母來北京陪讀和你休學一年,只能二選一”。

確定要休學后,極目楚再一次和父母進行溝通,“第一次提休學的時候他們很抗拒,但沖突之后總歸是要給解釋清楚,我也一直相信他們能學會理解我”。
那時,極目楚常常因為實習而深夜回校,每個披星戴月往回趕的路上,他都在地鐵上或者出租車里反復想著接下來要走的流程:和門衛解釋后刷臉入校、在宿舍樓下把值夜班的樓媽喊醒、回到宿舍后盡量避免收拾的聲音吵到舍友……這些事情越想越煩,像每天的夜色一樣厚重,沉沉地壓在他本就焦慮不安的心上。后來為了避免這個流程引發的諸多矛盾,他開始暫住在賓館。
拿著兒子給的地址,極目楚的母親來到了學校附近的賓館,推開門見到極目楚的第一眼,她就已經下定決心,“我要和他爸爸說,一定要讓他休學”。明明才幾個月沒見,眼前的兒子卻因為內分泌失調、暴飲暴食胖得“臉都變形了”,他坐在狹小的賓館房間里,面容疲憊,整個人看起來搖搖欲墜。她之前的擔憂和不理解在一瞬間化作唯一的心愿:希望兒子能夠回到最熟悉、最舒服的地方,好好調整自己的身心狀態。
在辦理休學的過程中,極目楚的班主任、輔導員和朋友們都從不同方面給了他幫助。班主任談起自己波折的大學經歷來寬慰他,輔導員幫助他的父母減輕擔憂,朋友們也都表示理解和認同。
有人回憶起,“他離開的那天,我躺在宿舍睡覺,迷迷糊糊地看見他站在宿舍門口喊我舍友去吃告別飯,然后逆著光笑著和我說,他要休學了,我好像很久沒有看見他那種真心的笑容”。極目楚已經記不起自己那天的微笑,但是確實覺得自己“做好決定、辦完手續后從一個極端的情況里放松了下來”,對于溝通的順利和受到的幫助滿懷感激。

和極目楚一樣,對于大多數選擇休學的大學生而言,他們尚未完全踏入社會,有很多問題需要他人、尤其是“過來人”的幫助。
得知女兒因宿舍矛盾而心情抑郁后,何樺的母親立刻休了公假來幫她辦手續、走流程,一天之內就帶著她離開學校回到了家鄉,休學一年的時間里父母也一直陪伴著何樺,帶她散心,給她找心理咨詢醫生調整狀態。“或許我算是比較幸運的,一方面我家里經濟條件支持我休息一年,另一方面我父母受過高等教育,能理解我,也能在各個層面幫助我”,何樺感慨。
休學手續的辦理涉及到與老師交涉處理已經開始的課程、各流程的辦理與審批、學籍變動等等,往往需要班主任、輔導員來從中協調。
“遇到的一些老師讓我覺得很幸運”,小蘇如是說,因為政策原因差點沒辦下手續的時候,是班主任幫忙和各科老師溝通;而在張帥心中,他的本科生導師和輔導員老師不僅很好地承擔家校之間的連接責任,還能“沒事兒就找我嘮嘮嗑,緩解了我當時的一些負面情緒”。
從學校層面來說,每個學校在允許休學的時長、次數以及具體政策上都有一定的自主權。學校普遍也在努力為休學大學生簡化流程、減弱影響,比如流程可以在回家之后線上辦理,部分大學將畢業年份選擇休學的同學降一級學籍,保證“應屆畢業生”的身份可以保持。

從學校回到熟悉的家,休學人要考慮的第一件事就是——接下來這一年,該如何解釋自己的“特殊”狀態。
何樺曾通過學校的交換項目去美國游學過一段時間,發現那里確實有很多學生“出去見世面”,去旅游,去創業,去冒險……一方面,歐美學校往往十分重視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支持他們自由規劃學業;且那里的大環境更崇尚自由開放,人們基本不會戴上有色眼鏡去看待休學行為,許多知名人士休學甚至退學但最后取得成功的故事被津津樂道。
但回到中國,當自己面臨休學,她發現情況變得大不一樣。中國的大學教育更希望學生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完成學業,重視理論成績,自己和父母也會忍不住對學籍問題、應屆畢業問題有擔憂,過年回老家更是盡量避免和親戚提及此事;而即使真想去實習實踐,很多行業也根本不需要在讀本科生,大多數情況下只能漫無目的地打雜。
張帥自己對休學一年看得很開,開玩笑地表示“除了畢業的時候老一點,我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的代價”,但談到他人的態度,他同樣表示,“我現在都研一了,家里邊人應該還是只有我爸媽和我表弟知道我休過學,倒也不是害怕別人知道……我只是覺得,這種容易被戴上有色眼鏡看待的事情解釋起來非常麻煩,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似乎無論自己對休學的態度如何,休學的選擇在中國注定要承擔來自周圍人和社會環境的壓力,太過主動的“坦誠”沒必要,和父母商量后的避重就輕、秘而不宣成為大多數人的選擇。

有熟悉的朋友來詢問的話,小蘇會簡單解釋休學原因——心理狀態失衡,需要休息,但每次出門遇到鄰居時,她會趕緊戴上耳機快速從一側溜過去,或者在電梯里緊張地盯著樓層升降的數字,心里默默吶喊“快點到啊”,在家庭聚會時她緊緊挨著父母坐,悶聲吃著飯,在父母替自己解釋時尷尬地扯一下嘴角。
坐在從北京回寧夏的火車上,林玥還有點沒回過神兒,她盯著窗戶外倒退著飛逝的景色,在心里盤算著回家后可能面對的訓斥和疑問。而母親也想到了這一點,揪了一下她的胳膊,把嘴巴貼在林玥耳朵邊叮囑道,“別把這事告訴你以前同學什么的,以后家里親戚也別說”。
極目楚母親那邊的親戚受教育水平較高,包容度更強,就讓母親去做了簡單的解釋,而對于父親那邊的親戚,一家三口的應對方式就是欺騙。在他爺爺奶奶的視角里,他已經即將畢業,而之后為什么還在北京,有“實習”“工作”“讀研”等無數個理由可以被用來解釋。
但極目楚比較慶幸的是,自己的目標行業注重工作能力,以結果為導向,在他實習過程中對他休學的狀態并不在意,無論是工作還是日常團建單純把他作為學生來照顧,讓他的實習如預期般順利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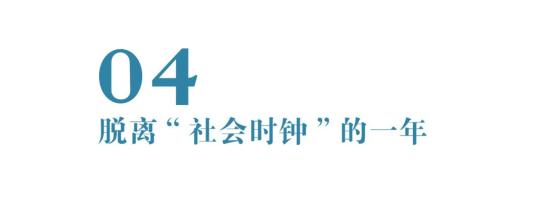
休學的前半年,小蘇很享受無拘無束、沒有精神負擔的生活,但后半年她躺在床上瀏覽大學同學的社交動態時,心里逐漸有了羨慕的情緒,他們在朋友圈里曬著做項目、期末考抱佛腳、打卡學校周邊小吃等日常,似乎生活在離小蘇很遙遠的一個玻璃罩內,而她只能趴在外面看著。
休學的一年時間里,她“沒有干什么特別的事情”,但認識了一些新的朋友,甚至和從前不熟悉的同學有了聯絡,從“社交低能”變成努力體驗“正常的社交生活”,并且確定自己需要、也能適應這樣的狀態。
“剛開始的時候是因為受不了‘社會時鐘’的限制選擇休學,后面交流過程中突然就覺得對所有在社會時鐘里的人有點羨慕,同時又清晰地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會回到那樣的節奏中”。解釋復雜感受時,小蘇提到了“社會時鐘”一詞。
社會時鐘(Social Clock)是一個社會學概念,用來描述個體生命主要里程碑的心理時鐘,反映了社會文化對個體的期望,即在什么階段應該做什么事情,包括求學、婚嫁、工作。“休學”在概念上,是脫離社會時鐘的選擇。

在休學的一年里,每個人對“社會時鐘”的情感迥然不同,有些人完全享受暫時脫離它的自由,每天睡到自然醒,享受散步、讀書、自娛自樂的生活;但也有些人努力維持著自己與“社會時鐘”的連接。
因為肺結核而休學的李果坦言自己除了治病就是“躺在家里打了一年游戲”,且父母考慮到自己的病情也不反對他靜養;張帥覺得這一年可以看成是未來退休養老的一年被挪到了年輕時候,他把自己的休學目標定為“調整”,閑暇時步行去家附近的琴行教教小孩子,手指在黑白琴鍵上跳躍,伴著童聲輕輕哼唱;更多時候,他躺在和宿舍迥然不同的自己的大床上酣然入夢,窗簾拉得嚴嚴實實,一睜眼都不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夜,但再無人和事來打擾他的夢,在宿舍里靠褪黑素才能睡著的傷口被這難得的靜謐悄悄縫補。

休學前,極目楚和朋友在聊天過程中達成共識,“哪怕在家完完全全玩個一年,都是成功的,因為能用這種方式割舍掉很多困擾自己的東西,同時讓自己放松下來,不要那么緊張和被動,就好像被整個大環境裹挾著往前走。”實際休學的一年過程中,他用大半年時間完成了兩段綜藝節目實習,從第一段實習的焦頭爛額到第二段實習的從容不迫,踏踏實實地有了收獲和成長,另外的時間他在家里“徹底地休息”,關閉了許多社交界面,心仿佛在緩慢而平穩地降落。
林玥的家人并不希望她天天在家里無所事事,希望她能與社會盡量保持聯系,于是她先在教輔機構一邊刷手機一邊“看小孩兒做作業”,后來又到家附近的肯德基做短期兼職。在正式員工的指導下穿上一身陌生的制服,林玥盯著鏡子里的自己,一剎那覺得從校園驟然踏入了社會。
忙著幫客人點餐、端上餐品的時候,林玥的腦海里不會有別的念頭,但輪班休息的時候她刷著手機,沒有發社交動態的欲望,看著別人的動態不知道該不該點贊,更不知如何評論。一個個群聊里依舊有人在分享日常生活,但林玥發覺自己與同齡人突然失去了聊天話題,“和大學同學沒有話,和以前熟悉的初高中同學也不知道說什么,不工作的時候感覺有點寂寞”。

如小蘇所說,所有休學的人都將回歸“社會時鐘”的步調,都要面臨復學,而復學之后如何彌合一些裂縫,如何在新的人生空白頁上提筆,成為他們都要思考和努力解決的問題。
人際溝通是無法逃避的關鍵步驟。極目楚并不擔憂和新同學相處,因為其中有一些他休學前就有聯系的熟人,每次走近教室時都能揮揮手打個招呼;他最注重的是和舍友的相處問題——考慮到休學前的宿舍矛盾,他在復學前和舍友們開誠布公地討論了一次,保證接下來能夠和平共處。
何樺所在專業經常混班上課,生面孔不稀奇,但每次上課前她還是會提前一些到教室,默默選一個角落坐下來。她覺得大學的班級概念不像初高中清晰,自己的名字被加進一個新的班集體,無論是他們還是自己都不會太在意,自己社恐也無所謂,反正正常溝通沒有問題。
小蘇經過了一年的“社交鍛煉”,在復學前的暑假就主動聯系新班級的同學,開學后也以積極的新狀態參與到校園生活中,她有了勇氣去嘗試處理之前不敢處理的問題,并且獲得了正向的反饋,一步步確定“我可以真正重新開始了”。
另一方面,復學之后的課程辦理、生涯規劃也需要他們進行相應的調整。小蘇復學的頭一個星期“基本都在跑”,在各個辦公樓、辦公室里不停地辦手續,把系統遺漏的課程一門門加入課表;極目楚則發現,由于學院學生培養方案的變動,自己比新班級的同學缺了幾門課,每次麻煩學委、班長幫忙提供對應老師的聯系方式、找教秘協調補課都會令他感到不好意思;打了一年游戲的李果回到課堂上后,覺得自己“學高數什么的好像比別人慢一拍”,陌生了的理論也需要從頭溫習……時鐘滴答,從休學到復學,他們的腳步好像又回到了原來的軌跡。
但這一次,“心態”成為他們共同提及到的最大的轉變。
從休學到復學,極目楚的社交網絡比以前簡單很多,處理事情的步調也越發從容,不會為了別人的期待去勉強自己達到高要求,按照自己的規劃向目標一步步前進。復學第五周,他認真地在備忘錄里回顧自己的收獲,發在了朋友圈。
林玥這一年里接觸到許多自己曾經“看不上”的人,慢慢發現“每個人的活法不一樣”,她說,現在每天逗逗新養的鸚鵡就很快樂。復學后的生日有點特殊,她的新班級微信公眾號按照傳統出了一期推送為她慶生,新同學們在推送中寫下祝福,夸贊她經常在朋友圈分享的鸚鵡很可愛,夸贊她性格好也樂于助人。林玥轉發了這條推送,配文是簡短而真摯的“謝謝大家”。
小蘇形容曾經的自己陷入理想主義的極端,現在能夠鼓起和人溝通、平和生活的干勁……她加入了學院辯論隊,在每一個招新季忙著轉發推送、招攬人才。
在他們眼中,這并不是“躺平”,只是用一年的時間考慮好最合適自己的狀態和發展路徑,以新的勇氣和信念繼續前行。

時鐘滴答,因為它本來就在那里,無論休學與否,生活都在繼續。
“我不知道休學對我的影響倒是是好還是壞,只能說,每個人都應該是三思而后行”,林玥說道,與新同學間隱約的溝通膈膜還是偶爾會刺痛她。
“可能以后就業時會被問到休學原因之類的,說實話,我沒想好怎么回答。”
小蘇沉思很久,語氣仍然猶疑。
極目楚放下筷子,身體緩慢地向后靠在海底撈的座椅靠背上,休學后在北京做綜藝實習忙到深夜的日子里,他常常和同事來這里補充能量。“每當有人咨詢我,如果有了休學的念頭該怎么做,我的回答往往是,‘你得自己想好’。”
沒有人知道未來如何,但從做出選擇開始,每個人就已經在提筆書寫答案。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文中圖片來源于視覺中國
原標題:《一個中國大學生決定休學丨對話另一種生活》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