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朱玉|路易斯·麥克尼斯:“我為什么要回到你身邊?”(下)
穿越海峽
麥克尼斯的卡里克弗格斯城堡令人想起另一座古堡——皮爾城堡,屹立在英格蘭西北部坎布里亞郡的弗內斯半島:
我曾與你為鄰,你這粗糲的基石!
那年夏天整整四個星期我居于你的視野:
我每天都看見你;從始至終
你的身形睡在如鏡的海面。

喬治·博蒙特爵士,《暴風雨中的皮爾城堡》,1806
1806年,華茲華斯在皇家美術學院的展覽上看到喬治·博蒙特爵士的油畫《暴風雨中的皮爾城堡》,寫下這首挽歌。畫中,城堡在雷電撕裂的天宇下巋然不動,一艘輪船在咆哮的大海上奮力抗爭。人們一般認為這首挽歌寫給一年前遭遇海難的弟弟約翰。但許多學者也指出,詩中哀嘆的“悲痛”與“損失”也指向另一重回憶:“那年夏天整整四個星期”指的是1794年夏末,華茲華斯曾逗留于城堡附近的蘭普塞德村莊,并在萊文沙灘上聽聞羅伯斯庇爾的死訊。此前,1792年底,華茲華斯未及見到女兒出生就被迫離開革命的法國。1793年2月,英國對法宣戰,更阻斷了詩人與法國女友和女兒團聚的道路。因此,盡管挽歌中只字未提法國,城堡周圍的景物顯然構成他人生中一段動蕩歲月的背景,一種涉及法國的生命損失在其中投下巨大的陰影。希尼曾用華茲華斯的案例來說明北愛爾蘭少數群體詩人的典型情況:
當英國向革命的法國宣戰,年輕的威廉·華茲華斯遭受了一種錯位,與現在依然發生在愛爾蘭的狀況非常相似。這位英籍的大革命支持者懷有法國的政治理想,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華茲華斯將這種困境戲劇化,憶起他在教堂參加為英軍成功而進行的祈禱儀式時所感到的孤立、叛變與不忠。華茲華斯說,他的忠心突然裂開一個罅隙,引發令人迷失的巨力,給他的道德自我帶來空前絕后的震動與打擊。
希尼認為,華茲華斯在詩歌中講述心靈的危機與復原,北愛爾蘭的大部分詩歌也是如此,“寫作的最大努力是整合,將全部的文化政治力量重新分配,使之獲得差強人意的秩序”(189頁)。
1813年,同在弗內斯半島,華茲華斯寫下《黑峽谷之巔即景》(“View from the Top of Black Comb”)。極目遠眺,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馬恩島,盡收眼底。在愛爾蘭海的那邊,他還依稀看到“蔚藍的山脊”:
那蔚藍的山脊
是轉瞬即逝的云?抑或那里
我們可見愛爾蘭海岸的輪廓?
華茲華斯暗引彌爾頓在《失樂園》中的比喻,將愛爾蘭海岸(“Erin’s coast”)比作“另一個世界的明亮界限”(“the bright confines of another world”)。但他尚未穿越海峽進入這新世界。1823年,愛德華·奎利南(Edward Quillinan,1791-1851),這位出生在葡萄牙的愛爾蘭天主教徒出版了一本詩歌體書信集《三葉草,或威克洛遠游》(Shamrock Leaves, or, The Wicklow Excursion),其中一條注釋提及華茲華斯,他未來的岳父。奎利南說,華茲華斯的繆斯“似乎從未提醒他,西部的美景為歌而生卻尚未被歌詠;將他自己的浪漫海岸與如同萊德爾、布洛岱爾或阿爾斯沃特(作者按:湖區地點)一樣優美的景色分開的,不過是一道狹窄的海峽”。
六年后,華茲華斯終于穿越“狹窄的海峽”,抵達都柏林。華茲華斯的愛爾蘭之行有其歷史背景。首先,1801年《聯合法案》頒布后成立了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英國人對鄰近的愛爾蘭產生旅游興趣。華茲華斯曾懷著“極大的樂趣”閱讀愷撒·奧特維(Caesar Otway)的《愛爾蘭速寫》(Sketches in Ireland,1827),希望親自拜訪這個“姐妹國家”。奧特維還贈送詩人兩幅絲制愛爾蘭地圖。其次,十九世紀初英國軍事部門發起的地圖測繪活動(Ordnance Survey),開啟了對愛爾蘭地貌的精細測繪。布萊恩·弗里爾的戲劇《翻譯》就反映了這一歷史背景。同時,1829年4月,英國通過了《天主教徒解禁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確認了天主教徒享有擔任教職和參加議會的民事權利。在這些背景下,華茲華斯的愛爾蘭之行就不僅是一場旅游,也是一場交游與觀察。旅途中,他關注時政,與宗教、政界、科學、文學等各界名士往來,體現了十九世紀初英愛之間的文化交流。我們不禁想問,經歷過錯位感的華茲華斯能否理解愛爾蘭人的復雜處境?
1829年8月底,華茲華斯在愛爾蘭皇家天文學家威廉·羅文·漢密爾頓(William Rowan Hamilton,1805-1865)等友人的陪同下,開始了為期五周的愛爾蘭之旅。他們游歷的許多名勝古跡都將被麥克尼斯寫入詩歌的地帶。而麥克尼斯故鄉安特里姆的鷹也成為這次旅行中唯一進入華茲華斯詩歌的意象——“你也被聽見,孤鷹!”(《聲音的力量》,1835)站在敦星克皇家天文臺(Dunsink Observatory)的制高點,華茲華斯俯瞰利菲河谷和都柏林灣;在三一學院圖書館,他瞻仰了世界上最豐富的地圖館藏(the Fagel Collection);造訪了1798年起義的重要陣地威克斯福德郡的醋山;游歷了未來葉芝的故鄉斯萊戈,沿途看到本布爾本山(Ben Bulben)所在的達特里(Dartry)山脈,“一座巨大且輪廓豐富的石灰巖山體浸在深沉的紫暉之中”。兩處地方留給華茲華斯最深的印象,一處在威克洛的圓塔,一個愛爾蘭女人把孩子的腳浸到圣凱文的湖水中,“為了治療跛足”。華茲華斯寫道,那位天主教女人“如此隱忍,如此虔敬,如此樸素純一”,她談起孩子病苦時的溫柔,細述孩子走向康復時“那悲傷的歡樂,足以打動最冷漠的人”。大約一百五十年后,希尼從貝爾法斯特移居此地,將所在的格蘭摩爾村莊比作華茲華斯的格拉斯米爾,寫下《圣凱文與烏鶇》。另一處是前文《訣別》中寫到的凱里郡基拉尼,“基拉尼的三個湖泊……勝過我們任何一個湖”;卡朗圖厄爾山(Carrauntoohil)“比我們任何一座山都更壯美”。華茲華斯甚至說,他希望與一位技藝高超的藝術家聯手,為此地寫一本地貌導覽。(Brandon Yen, “Ireland and the English Lake Poets”, Library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story/ireland-the-english-lake-poets-trinity-college-dublin-library/RgWxlmqA5vTuIg?hl=en)
但他并沒有寫。一百多年后,另一位愛爾蘭詩人懷著同樣的好奇,穿越海峽,來到蘇格蘭西岸的外赫布里底群島,寫下一本游記,以一個局外人的視角觀察島民,通過認識“他者”而反思自我——愛爾蘭。麥克尼斯的《我穿過明奇海峽》(1937)是一部文體松散的作品,融合了日記、詩歌、簡史、對話、戲仿和諷刺信件等多種形式,借助歷史、地理與政治等多重視角。根據本書編者的觀點,這部作品屬于兩次大戰之間流行的島嶼書寫,比如愛德華·繆爾的《蘇格蘭之旅》和休·麥克迪爾米德的《蘇格蘭島嶼》,但它不同于凱爾特復興的傳統,而是著眼社會經濟現實。在這部游記中,麥克尼斯關注的是,在多大程度上,赫布里底群島能夠抵御英國化和商品化這兩種不可逃避的趨勢。他著迷于島國自身的獨立性,并從這些島嶼中聯想到愛爾蘭西部,他父親童年生活的地方以及他父親的父輩棲居的地方。這是一部求索之作,是希望“發現血濃于墨——我體內的凱爾特血緣將被其同類磁吸到表面”的旅程,盡管這種嘗試以徒勞告終。作者以一位局外人的身份開篇:
今年我兩度拜訪——四月和七月——外赫布里底群島。去之前,我并未意識到幾乎所有島民都說蓋爾語,他們的語言就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懂他們的語言,無法深入他們的生活。因此,我以一個游客的身份來描寫他們——一個對島嶼失望、被島嶼挑逗誘惑的游客,來此僅僅是為了提醒自己,在那片土地上,他永遠是一個局外人。(Louis MacNeice, I Crossed the Minch, ed. Tom Herron, Edinburgh: Polygon,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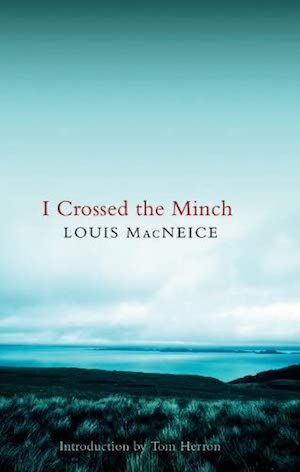
I Crossed the Minch書影
作者自稱為局外人,局外人的視角使他在談論赫布里底群島時能保持一種平衡冷靜的常識,這是他在直接書寫愛爾蘭時所缺少的。他可以在赫布里底群島上觀察一個微縮的愛爾蘭,不帶任何痛苦與憤怒情緒,毫無怨恨地思考一個有別于發展中國際秩序的地方與島嶼社區,并認為世界性社會必須是各種差異社區的聯盟。麥克尼斯強調自身中的凱爾特氣質(“the Celtic in me”),并將這些島嶼和倫敦進行比較:
從血緣上來說,我可能更接近赫布里底人而非倫敦佬,但我全部的成長與教育經歷讓我疏離自然的(或者說原始的)文化,在不列顛的島嶼中,這種原始文化僅存于凱爾特或落后的邊地。我去赫布里底群島,部分原因是希望發現血濃于墨——我體內的凱爾特血緣將被其同類磁吸到表面。這是感情用事且徒勞的希望。一次,坐在河畔與一些劉易斯島民喝啤酒,其中一位唱起了蓋爾語情歌,我強烈地感到自己屬于這群人,而倫敦沉入污泥。但酒精的信念并不持久。
島嶼即孤立:兩者同義。我們以為會在島上遭遇狹隘的邪行。令人震驚的是,島嶼被大陸的邪惡侵略。
他看到赫布里底群島受到了商業的侵蝕,墮落到異族手中,但認為要形成一種更加高級的文化尚需漫長的時間。他反思自己初登島上,曾不近情理地抱怨島民一臉憂郁,但逐漸認識到,“當地人不會熱情地歡迎你。他們會禮貌,體貼,好客,但沒有你,他們會過得更好”。麥克尼斯對待外來入侵的態度由此可見。他觀察到赫布里底島民大多行動遲緩,和愛爾蘭南方人一樣,沒有很強的時間觀念,但他們的語言或思維并不遲鈍,“聽他們說蓋爾語,你會發現他們的言談帶著火、速度和豐富的戲劇性的”,“給他們威士忌,你會發現天主教和凱爾特氣質浮現”。書中也寫到自然景色,并將之與愛爾蘭的風景對比,不經意間流露出麥克尼斯對故土的微妙情結:
大多數關于高地和島嶼的書籍都把當地景色浸入無法遏制的紫色和金色中并多愁善感地描寫當地人民。從我兩次的旅行來看,外部群島的風景并沒有不同尋常地豐富多彩,當地人也缺少那種顯著的魅力和光彩……我們通常期待在游記和地理雜志有關人跡罕至之處的文字中看到的樣子……假如有更多荊豆花,像愛爾蘭那樣,這里的風景會更加動人。七月野花遍地。我并非花草愛好者,更偏愛宏觀效果——祖母綠色的燕麥田埂盤旋在山丘上宛若青蛇,或一片三公頃的草場,開滿紫色野生天竺葵。
麥克尼斯還表達了對蘇格蘭民族主義的看法,借此探討愛爾蘭的政治境況:
外赫布里底群島的很多人是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我總是嘲笑蘇格蘭民族主義是對真實政治感到厭惡的聰明青年的寶貴情感,但在島上,這個概念比在愛丁堡更有意義。蘇格蘭作為一個整體再也不會重新獲得她的統一和獨立的自我意識,但對于大陸之外這些講蓋爾語的群島來說,這依然是一件可能的事。他們的傳統語言無需人為培養;他們的人口少得足以維持真正的社區情感;他們的社交生活依然單一(盡管商品化很快就會在其中制造裂隙);最后大海依然將他們與鄰居分開。用埃斯庫羅斯的話來說,“大海在此,誰會把它榨干?”
他認為讓赫布里底群島實現經濟獨立是“荒謬”的,然而“為保存島嶼的社會和文化獨立而做出一些讓步是可行的”,在經濟上,“群島可以讓自己配合他們更大的鄰居而不臣服于彼”,“我從來不認為,為了保留他們的語言和社區情感,他們就該故意拒絕現代化的優勢”。這些內容反映了麥克尼斯在獨立與聯合、原始與現代之間的思索。他還通過斯托諾韋(Stornoway)的例子說明了英國化的副作用:
地區差異遠不如其共性重要,或者全體島民有別于大多數大陸蘇格蘭人的共性。也許有一天,赫布里底人失去自己的語言,全方位地與其他蘇格蘭人或者(也有可能)與世界上所有說英語的種族合并起來,也許有朝一日這是好事。但那一天還沒有來。迅速英化的副作用體現在斯托諾韋。農場主進城后,用他傳統的節奏和例行方式去換取格拉斯哥倉皇不安的心態和英語公眾圖書館里的爵士文化。
兩次旅行之間,麥克尼斯也寫了一些詩,其中《風笛音樂》通過爵士樂與風笛音樂的對比,反思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在劉易斯島,麥克尼斯參加了兩場音樂會。身穿傳統服裝的風笛樂隊和他們深入脈搏的節奏刺破詩人的記憶,麥克尼斯寫下《風笛音樂》,“為蘇格蘭蓋爾語區、為所有傳統文化獻上諷刺的挽歌”。詩中陰韻(feminine rhymes)暗示風笛的喘息,倉促即興的氣氛也暗示著新的文化無暇與古老的傳統歌謠的完全韻(full rhymes)達成和諧。詩中的音樂鮮活凄厲,節奏、副歌和戛然而止的沉重音調都表達了典型的三十年代的絕望(《傳記》,212-213頁):
不要旋轉木馬,不要黃包車,
我們只要老爺車和西洋鏡。
他們的褲子是雙縐,他們的鞋是蛇皮。
他們的客廳鋪著虎皮地毯他們的墻上掛著牛頭。
“不要……不要……/只要……”是貫穿這首詩的主要旋律,詩人借此思考傳統音樂與爵士樂及其代表的“現代世界的混亂”之間的矛盾關系。 詩中的低音和吟唱提醒我們這首詩是關于赫布里底群島的,但也是全球的。
麥克尼斯如柯爾律治筆下的老水手始終漂泊于迷航。從冰島(“北方始于內心”)到明奇海峽,從美洲到希臘群島(拜倫與民族獨立戰爭始終是旅行的背景),晚年他還作為BBC記者前往喜馬拉雅——“印度洋頗似貝爾法斯特灣”(1955年11月5日書信)。無論在哪里,愛爾蘭始終是他的參照系。在廣播劇《瘋狂的島嶼》(The Mad Islands,1962)中,愛爾蘭與蘇格蘭在象征層面融為一體,詩人關于明奇海峽的認識也變得更加清晰。他在劇本前言中寫道,“我寫這部作品,因為我始終對古代愛爾蘭航行傳說感興趣”。在航海中,“我們所知的世界仿佛分解為它的組成部分”。劇中母親的一番話尤其耐人尋味:
我沒有見過大海——或者嗅過或感受過——已經很多年了。但我曾經住在一座城堡里,北面、西面、南面都是海。哦,那流動的海水和風的裝飾音,海藻的氣味和成群的海鷗!但我現在不能接近大海,只要那個人還活著并浪跡西部的島嶼。水不像陸地,每一滴連著下一滴;從未間斷,沒有阻隔。我腳上的一小滴浮沫,或者我臉上的一小朵浪花,都讓我覺得兇手在觸摸我。只要他還在那里航行,整個大海都被染污。你要去使大海恢復潔凈。(Louis MacNeice, The Mad Islands and the Administrator: Two Radio Play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4, p.9)
《秋天日記》:“我為什么要回/到你身邊,愛爾蘭,我的愛爾蘭?”

Louis MacNeice, Autumn Journal,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2
《秋天日記》是一場由秋入冬的自傳性旅程,作于1938年8月至12月,記錄了二戰前夕詩人的心境。創作之初,麥克尼斯就和艾略特談起這部詩歌:一部“長達兩千至三千行的長詩”,“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日記,但記錄了那段時期我的精神和情感經歷”。全詩“包含二十四部分,每部分平均約八十行。這種劃分給它一種戲劇性”,詩行長度錯落變化,詩句本身“富于節奏且避免抑揚格”,是“迄今為止我最好的作品,既是一幅全景畫也是信仰聲明”(Louis MacNeice, Selected Letters of Louis, edited by Jonathan Allis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p.312)。艾略特收到稿件后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已經讀過《秋天日記》,我認為確實很棒。時常深受感動,更難得的是,對一部長詩來說,整個閱讀過程中,我的興趣始終絲毫未減。部分原因在于你擅長變換韻律,同時,我認為,也在于詩中的意象皆是活生生的意象,而非僅為詩性暗示(poetic suggestiveness)而選取的意象。(《傳記》,223頁)

“費伯詩人”,左起:麥克尼斯、泰德·休斯、艾略特、奧登,斯蒂芬·斯彭德,費伯出版社,1960年6月23日
此前,麥克尼斯在《今日詩歌》(1935)中贊頌了奧登詩歌的時政性和預言性,并指出從今往后“純詩歌”(pure poetry)將越來越少,“心理詩和政治詩”與“長篇作品(史詩、小型史詩、散文詩和自傳體詩)”將越來越多。在《現代詩歌:個人隨筆》(1938)中,麥克尼斯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呼吁不純粹的詩歌(impure poetry),即受到詩人生活及其周遭世界影響的詩歌。”他接著說道,詩人“既是批評者也是娛人者(除非他令人愉快否則他的評論將毫無效力)。今天的詩歌應在純娛樂(‘逃避的詩歌’)和宣傳性言論之間把握中道”(Louis MacNeice, Modern Poetry: A Personal Ess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當他創作《秋天日記》時,這部作品將“以紀錄片的形式容納世界的不純粹,經驗的涌流,看似完全自發,實則精心設計——如膠片上的圖像——在一種無形的想象力的指引下。”(《傳記》,228頁)
《秋天日記》的前言表達了麥克尼斯的詩學主張,尤其是“詩歌首先要誠實”。艾略特也認為,這部詩歌之所以如此感人,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誠實。這篇前言值得全文引用:
我知道這部詩中有夸張的成分——比如涉及愛爾蘭、牛津補選或我私人生活的部分。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果我寫的是說教詩,那么我有義務去修正或刪除這些夸張和矛盾。但我寫的是我稱之為日記的東西。在日記或私人信件中,人們寫下當時的感受;要嘗試達到科學的精準將是——這是悖論——不誠實的。抒情詩的真實不同于科學的真相,這首詩介于抒情詩和說理詩之間。鑒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說理詩的傾向,我想這其中含有某種“人生批評”或暗示一些不僅僅屬于個人的尺度。我的寫作跨越1938年8月至新年,我沒有根據寫作結束后發生的事情來更改任何涉及公共事件的段落。因此關于巴塞羅那的部分寫于巴塞羅那陷落之前,如果我以后視的眼光,根據自己對后來事件的反應來修改之前的段落,我認為是這不誠實的。我也沒有試圖提供如今眾人對詩人的要求——最終的裁決或平衡的判斷。這首詩的性質既非決議也不平衡。我的一些信念,我希望,能在詩文的過程中浮現,但我拒絕使它們抽離于語境。出于這個原因,我會被一些人稱為騎墻派,被另一些人稱為感傷的極端主義者。但我認為詩歌首先要誠實,我拒絕以誠實為代價的“客觀”或明確。
L.M. 1939年3月
麥克尼斯的傳記作者將《秋天日記》比作三十年代的《序曲》(248頁)。但筆者也想到濟慈的《秋頌》和雪萊的《西風頌》,兩位后革命時期詩人對藝術與現實的思考。1936年11月6日到1938年5月,麥克尼斯住在漢普斯特德的濟慈故居(4 Keats Grove),并寫下《花園里的陽光》等名篇。濟慈在1818年至1820年間居住于此。1819年9月19日,濟慈沿著漢普郡溫切斯特的伊欽河散步,寫下《秋頌》,雖詠秋景,卻是對彼得盧屠殺的回應,是關于死亡的沉思。麥克尼斯創作《秋天日記》時,也是剛從漢普郡度假回來,詩的第一句就是“夏日將盡在漢普郡”,詩中也表達了戰爭前夕的沉重思緒。而雪萊的“枯葉”意象也在詩中反復出現(如第一首、第十一首),甚至雪萊的名字直接出現在第十五首首行首詞。也就是說,如同《西風頌》,《秋天日記》也思索毀滅與新生的問題。全詩語氣誠懇,情感真摯,節奏急促,一氣呵成,亦不無辛辣。其中第十六首直接談論愛爾蘭,如火山爆發。
“我又恨又愛”(Odi atque amo)。精通古典文學的麥克尼斯在這部分結尾引用古羅馬詩人卡圖盧斯(Catullus,84-54BC)的著名詩句表達了他對愛爾蘭的矛盾情感,為第十六首詩定下基調:
我們該用生銹的匕首把這個名字刻在樹上?
她的群山依舊青綠,她的河流
汩汩涌過巨礫。
她是討厭鬼是壞女人
第十六首詩的首行僅由三個單詞組成:“噩夢留下疲憊。”“噩夢”啟動詩文,并使之在個人化的夢境/回憶與愛爾蘭的歷史/現實之間交錯展開,激烈而哀傷。首先,睡夢者“嫉妒行動者”,“他們睡去醒來,謀殺暗算 / 毫不遲疑,毫無畏懼”。“行動者”也包括“我毫不妥協的同胞”,“他們開槍殺人從不 / 見遇難者的臉變成他們自己”。這里可以聽見麥克尼斯對葉芝的回聲,在“嫉妒”行動者的同時,也質疑他們的行動。麥克尼斯從莫德·岡寫到胡里痕的凱瑟琳,反思將愛爾蘭女性化的問題:
胡里痕的凱瑟琳!為何
一個國家,如同輪船或汽車,必須永遠是女性,
母親還是甜心?一個女人走過,
我們只見她走過。
走過如一抹陽光在陰雨的山上
然而我們永遠愛她并恨我們的鄰居
而每個人都在他的遺囑中
延續繼承人的仇恨。
詩人沒有作答,而是在一陣鼓聲中追溯了愛爾蘭的動蕩歷史,感嘆自己的疏離,反思愛爾蘭性,追問“為何我們喜歡做愛爾蘭人?”這次,詩人給出了部分答案:
這就是我的國而我覺得自己
離它很遠,上學、定居都在英格蘭,
但她的名字始終如洪鐘
回響在水下鐘樓。
為何我們喜歡做愛爾蘭人?部分因為
它讓我們這些以仙水受洗的
一個莫須有世界中的成員
在感傷的英國人中找到支點;
部分因為愛爾蘭夠小
足以給人家的感覺,
因為洶涌的波濤
使她遠離更商業的文化;
因為人們覺得在這里至少可以
做地方工作而不受制于世界
且這小小舞臺上的幸運兒
或有望實現具體行動的目的。
然而,詩人話鋒一轉,坦言“這當然是自我欺騙;/ 這座島上也沒有免疫”。他批判“建在爛泥上的城市;/ 建在利潤上的文化”,控訴一系列教育、經濟、環境、失業等問題,反思自由邦的孤立主義政策以及南北分治后反映在文學上的民族主義。“紙上墨跡這么黑/三葉草也不能覆蓋”。但在一連串猛攻之后,麥克尼斯以“我的愛爾蘭”顛覆了此前的斥責,最終表達了“血濃于墨”、超越理智的深切情感,是《秋天日記》最動人處:
格里菲斯,康諾利,柯林斯,他們把我們帶到了哪里?
我們自己!就讓圓塔卓然屹立
在硝煙四起的世界!
讓學童們笨手笨腳地摸索
于一種半死的語言;
讓審查者忙于檢查書本;拆毀
喬治風貧民窟;
用蓋爾語競技。
讓他們種甜菜糖;讓他們
在每個村莊建工廠;
讓他們把被害的魂靈分為
綿羊和山羊,愛國者和叛國者。
而北方,我童年生活的地方,
依舊是北方,飾以格拉斯哥的塵垢,
成千上萬的人們找不到工作
站在角落里,咳嗽。
而流浪兒童在潮濕的路面
玩耍——跳房子或滾彈珠;
而每個有錢的人家都有一張松垮的球網
在松軟的草坪上,在濕漉的灌木旁。
冒煙的煙囪暗示
街角的繁榮
但他們用外國纖維制造厄爾斯特亞麻
而賺來的錢又花出去賺更多的錢。
建在爛泥上的城市;
建在利潤上的文化;
言論自由被扼殺于萌芽,
少數派永遠有罪。
我為什么要回
到你身邊,愛爾蘭,我的愛爾蘭?
*****
海德莉·麥克尼斯(Hedli MacNeice,1907-1990),擁有愛爾蘭血統的英國歌手,曾在奧登和麥克尼斯等人的許多劇作中歌唱,1942年至1960年間成為麥克尼斯的妻子。在《路易斯蓋的房子》(題目戲仿傳統兒歌《杰克蓋的房子》[“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Hedli MacNeice, “The Story of the House that Louis Built”, in Studies on Louis MacNeice, Cae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Caen, 1988, pp.9-10)里,她描述了一座“厚磚墻的漂亮房子”:“西面的窗戶望向康尼瑪拉、梅奧和大海。南窗環視多塞特、唐斯丘陵和莫爾伯勒——北窗俯瞰冰島,東窗面向印度。前門寬大并永遠敞開。”這樣的布局使我們想起開篇提及的五塔陣,再次證明了麥克尼斯向多元(“incorrigibly plural”,《雪》)敞開的態度。
路易斯的房子里,前廳門庭若市,往來皆是權貴,“那些認為路易斯害羞、傲慢、禮貌、難以接近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第二間屋有一扇堅固的門,敞向一個大房間。路易斯常靠在那里張望,期待興奮的消息。進入這里的人包括遠方歸來的記者、詩人和演員。下一道門只對少數人開放,屋內家具破舊,有舒適的椅子和爐火,到處都是書。在這兒,麥克尼斯和三兩知己自在相處。這間屋后還有一間很小的斗室,只能容納兩個人:他和迪倫·托馬斯或W. R. 羅杰斯。他會拿著手稿和他們討論創作,“只和他們”。在這之后,一條通道引向另一間屋子,透過玻璃拱頂可以仰望星辰,“在那里,路易斯與上帝獨處,或按他的說法,與那些偉大的精神,希臘或羅馬,或者但丁,鄧恩,斯賓塞和伊麗莎白時期的作家,更近些的葉芝、艾略特和奧登”。通過他們,他謙卑地衡量自己的成就。樓上有兩間屋,第一間空蕩蕩的,他在那里接待偶爾的女性來訪。第二間有畫有花有琴,他生命中的五位女性在那里徘徊……門楣上寫著“愛、忠誠、孤獨與幻滅”。“1963年9月3日,他一邊說著‘我要死了么?’,一邊悄然關上他蓋的房子的門。”
此處應該有本杰明·布里頓(多次與麥克尼斯夫婦合作)的《戰爭安魂曲》(1962)。

麥克尼斯百年誕辰時,希尼在麥克尼斯墓前憑吊,Carrowdore, Co. Down,2007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