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年前遭遇的骨折,給我留下兩塊鋼板與成長的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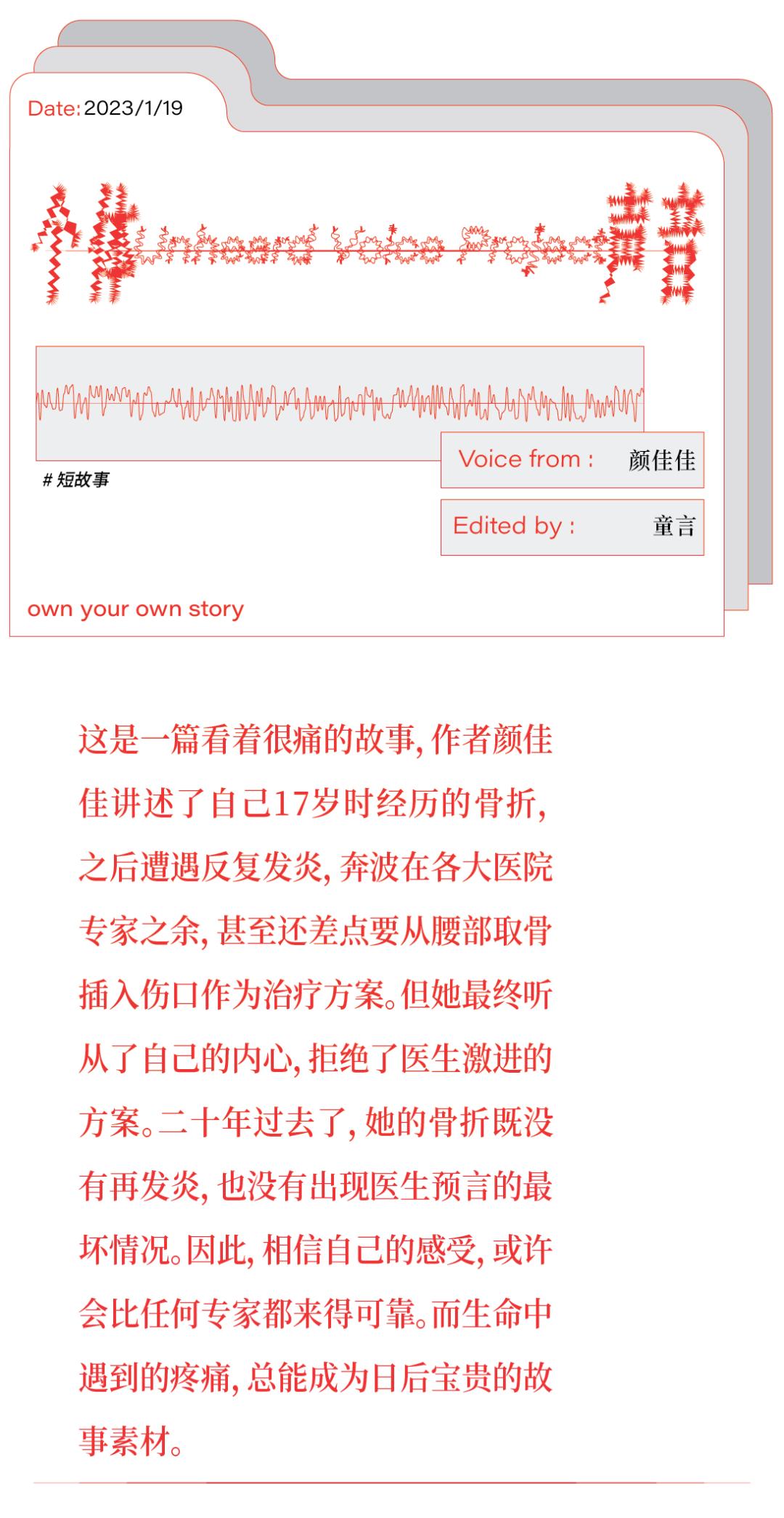

2006年9月1日,我大學畢業后,正式踏上工作崗位的第一天。作為一名新教師,我腦中無數次勾勒出開學第一課中自己的狀態,在心中演練了無數遍,臨進教室前的十分鐘,還是免不了緊張。左思右想,打開抽屜,拿出兩個早就買好的耐克白色護腕,小心翼翼地套在自己的右手前臂上。
一堂課上下來總算還算順利,聽見下課鈴聲響起,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之后一周時間都平穩過去了,直到有一天下課,一個女生興沖沖地跑上講臺,“老師,等等,我一直很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以為她有什么學科方面的問題,饒有興致地看著她。
“老師,你又不是體育老師,為什么上課的時候一直帶著兩個護腕呢?”
她的聲音落地清脆而響亮,一時間,引得班級中的其他同學也紛紛沖我這邊望過來。
我感到一陣陣恐懼向自己襲來,頭上明顯開始汗涔涔的。
“額,沒啥,我個人習慣而已。可以,可以擦擦汗。”
我沒敢看她,在簡短回答之后,趕忙抓起課本,落荒而逃。
回到辦公室,緩緩脫下護腕,下面兩道長長的肉粉色疤痕顯露出來,每條長約12厘米,每道24個針腳,如同兩條毛毛蟲,彎彎曲曲,趴在我的手臂上,乍一看不得不讓人倒吸一口氣,太過鮮明,觸目驚心。這兩道疤痕實在太過明顯,幾乎每個初次見面的朋友,沒聊個幾句,都會把關注點停留在我的手臂上,
“你這手是怎么回事啊?好嚇人!”
“是遇到歹徒了嗎?你和歹徒搏斗了?”
“這疤也太難看了,你怎么不想辦法去弄掉呢!”
“九院的整形不錯,可以考慮去做做。”
......
幾乎每次這種情況,我都會把骨折經歷像倒豆子般細數一遍,往事歷歷,就此浮上心頭。

時間拉回1999年9月1日,那年我讀高二,也是開學第一天,正好遇上文理分班。我在文科班開啟新生活,想到高一時候在提高班里的種種壓力就此不復存在了,不由得暗自松了口氣。第一天上課的感覺很不錯,記得班主任還是個大美女,說話嗲嗲的。
這天天氣異常炎熱,熱得我放學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那時我家住在老北門晏海弄的老房子,沒有淋浴設備,洗個熱水澡需要先燒上一壺熱水。 我把浴盆放好,剛往里倒了兩盆冷水,突然想起換洗的衣服還晾在弄堂里,于是拿了丫插頭就跑出家門去,抬頭一看,衣服被晾在弄堂口高高的電線桿子上,就忙不迭地一路小跑過去收,悲劇就在此時發生了。
只記得還在距離晾衣服的地方一兩米處,我腳下突然被非常沉重的障礙物給絆倒了(事后知道是里弄搞文明城區堆置的一袋三合土),隨后眼前一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由于丫插頭沒有及時脫手,倒地的地方像是一個窨井蓋的位置,手臂像是被什么硬物磕到了,隱約聽到咔噠了一聲,等我掙扎著爬起來,才發現手臂變了形,前臂無力地垂了下來,另外手臂內側出現了一個小口子,從里面涌出濃濃的血來。
我一開始摔懵了,走了幾步才感覺到鉆心般的疼痛,不禁失聲痛哭起來。旁邊有很多人圍過來,但是看熱鬧的多,實際關心的人少。
有個老太見我哭慘了,還在旁邊沖我笑,不知道是想安慰我還是嘲笑我,我挺生氣的,想自己這么慘,居然還有人笑得出來,一咬牙就不哭了。
我爸當時正在做晚飯,聽到弄堂里的動靜,連忙跑出來把我背了回去,打算送我上仁濟醫院。平時感冒發燒一直是走著去仁濟醫院的,離家不過一站路的光景。但這次哪怕挪動一步,我都十分艱難。只好打車過去,當時是下午五點多鐘,正趕著下班高峰,河南南路,人民路上交通擁堵得不成樣子,好不容易上了出租車,坐了近一個小時才到仁濟醫院。這醫院里也是人山人海,看急診的人都把走廊擠得水泄不通。
也不知是不是該著我倒霉,那天看外科骨折的人特多,在我前面就排了三個人,只有一個值班醫生,還去吃飯了。等他回來,又是拍片子,驗血,打破傷風排隊等待折騰了很久。片子一拍出來發現我骨折得非常厲害,尺骨完全斷裂并錯位,醫生說讓我家人回家拿個躺椅和棉被到醫院,他晚上幫我把手上的出血小口給縫上,然后轉頭去處理其他病人,不再管我。
我們覺得他有點敷衍了事的味道,旁邊也有病人替我們抱不平,說這里的醫生不負責任,又說起附近瑞金醫院的醫生處理問題比較周到。我爸媽一聽,決定再去瑞金醫院碰碰運氣。于是在晚上八點多,我們拿了x光片子,再次坐上出租車,去到瑞金醫院就診。

瑞金醫院比起仁濟醫院,勝在環境優雅,兩個相隔不遠,就診人數卻大相徑庭。仁濟醫院被患者擠得水泄不通,而瑞金醫院的急診外科里三個醫生坐在那里聊天,并無患者。我一走進去,三個人立馬都站起來,一看我的手臂情況,就有醫生先上來幫我復位,可惜折騰了10來分鐘都未能如愿。醫生于是建議,這種情況下,人工復位已經沒辦法了,要治愈,只能趕快去動手術,并通知手術室做好準備。
我當時對這個手術毫無概念,以為無非是把手上的骨頭接好,只要一覺醒來,手臂就會完好如初,并不知曉手術后會帶來什么痛苦。于是心心念念盼著手術趕快開始,手臂疼痛有所減緩。在推進手術室之前,護理工給我打了針安定,又幫我把衣服剪開,套上藍色斑馬服。
我媽被醫生叫入辦公室簽字,并商量到底使用國產鋼釘還是進口鋼板,進口的特別昂貴,材料費就要八千多,還需要完全自費。我媽雖然平時比較小氣,但這時候為了我將來著想,還是決定用進口材料。
手術終于在晚上11點正式開始了。躺在明晃晃的手術臺上,護士圍著我一通忙活,不一會兒我的手上,脖子上,腿上都被扎了針,不得動彈。因為是半痲手術,我幾乎是在頭腦完全清醒的狀態下感受了全過程。
我聽見有電鉆在嗡嗡作響,當時還納悶:又不是墻壁打洞,為何我的手術里會有這聲音?后來才知道,這種叫做鋼板內固定的手術,需要在我兩根斷骨上分別鉆上6個小洞,然后把兩塊鋼板固定在我的斷骨之上,再把皮膚進行縫合。這是非常殘忍的手術,這兩根骨頭本來斷裂了就夠疼了,再人為地打上12個孔,那會是什么樣的感受!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治療方案,感覺堪比滿清十大酷刑。
手術進行了一個半小時才結束,由于麻醉還沒失去作用,我暫時不怎么感覺痛苦,又是餓又是累的,很快就睡著了。
好景不長,睡了兩個小時我就被痛醒過來了,一是因為監護室人員進出頻繁,日光燈徹夜通明,二是因為麻醉勁開始過去了,我感覺自己的手腫的厲害,可能比饅頭還大根本無法抬起,只能放在肚子上,它甚至經不起任何輕微的觸碰,哪怕有人在我床邊碰到了床沿,它也能異常敏感地感知到,并且疼痛越來越厲害了。
本來還能閉上眼睛,后來只能瞪著天花板了,護士給的安定和止痛藥一點不管用。到了早上六點多,護士過來通知我說,現在可以吃點東西了,我卻疼得連喝水都感覺困難。每次解手都要使出渾身解數,一抬屁股,放在肚子上的手就痛到不行。我之前從來沒有領教過如此之大的痛苦,沒有心理準備,一痛就開始大叫,結果引來了護士的抱怨。
那個照顧我的護士,脾氣特別不好,態度惡劣,一上來不是安慰我,而是要我克制,說一個病房里有這么多病人,你這么個叫法,別人怎么休息。還說過12個小時就會好的。這一天真是過得生不如死,度秒如年。

自從在睡夢中被痛醒,隨后也從醫護人員口中得知了這手術的個中細節,如此殘酷而猙獰,我多想這是一場噩夢啊,但疼痛感一陣陣向我襲來,愈演愈烈,讓我不得不相信它是真實存在的,我感覺自己的世界快要崩潰了,多么希望有一個溫暖的懷抱把我包圍,一些溫柔的鼓勵的話語縈繞在我耳邊,能幫我熬過這一關。
然而現實的畫風和我期待的完全不同。我在病床上痛苦呻吟,護士動不動就叫我克制一下,不要吵到其他病患,態度傲慢而冷漠;一個掃地的阿姨向我媽抱怨說:“你女兒也太嬌氣了,我就在她旁邊掃個地而已,根本沒碰到她,她也要叫這么大聲,讓我離遠點。”
至于醫生們查房的時候,更是動作野蠻,不僅有人用鑷子戳我剛剛動完手術的手指,更有一位男醫生竟然用大力想把我蜷縮在一起的手指掰開,我含著淚問他為何如此待我,他一本正經地說:“小姑娘,你的手不能一直這樣縮著,要攤開來,這個要自己鍛煉的,否則你的手就一直縮成這樣,將來怎么嫁得出去?”他這么一說,旁邊其他醫生,還有病人聽了也跟著笑了起來,我感覺自己快要淪為他人眼中的笑柄了。
我媽一邊陪著我,一邊也唉聲嘆氣。她一臉疲憊,也不知道怎么安慰痛苦的我,只能拿她自己當年剖腹產的經歷來回憶給我聽,意思是她當時也很痛,所以忍一忍就過去了。然后她又向我大吐苦水,說她已經夠辛苦了,你要體諒一下,要懂事點。她只請了一天假,明天還要回去上班,真是要累死了。
術后12個小時的煎熬并沒有迎來想象中的痛苦減輕,我大罵醫生護士騙人,醫生只得拿來杜冷丁給我止痛,真別說,一針下去果然痛快,手臂感覺很沉重但是失去了知覺,就是副作用來得也快,沒過半小時,我就感覺一陣反胃,直挺挺地起身,把好不容易吃下去的東西全部吐了出來,弄得身上,衣服上,滿床都是。
過了兩天,我的疼痛有所好轉,我對周邊的環境開始關注起來,原來我身處的是一間骨科的骨腫瘤病房,里面大多數的病患,病情都比我復雜嚴重的多,不少還是疑難雜癥,是外省市特地過來求醫問診的。我以前從未聽說過骨腫瘤這種疾病,算是開了眼界了。有一個二十來歲剛剛當上媽媽的女子,來自寧波象山,長得骨瘦伶仃,她腿上長了骨腫瘤,一開始和大家有說有笑的,但是后來化驗出來說是不好,要進行化療,這姑娘馬上愁眉不展了。
后來又住進來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常熟來的,面目清秀,但一進病房就把我嚇一跳,她左手上長了一個巨大的瘤子,連著她的小指,我聽見醫生對她說,目前最好的方案是把腫瘤連著小指截肢,反正小指的功能也不是很要緊,我聽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倒是一副很云淡風輕的樣子。
由此看來,我的骨折手術已經是其中最最輕的病癥了,醫生護士司空見慣,比起其他困難病癥,我這種簡直輕于鴻毛。一周后,在眾病友羨慕的眼光中,醫生宣布:佳佳同學,你可以出院了!

自從出院之后, 手上的疼痛感一天天減弱,從原本每時每刻都能感受痛苦到后來每天只有兩個小時左右痛苦難當,過一會兒就緩解了。
一回到家里,各種親戚朋友前來探望,不僅噓寒問暖,還送來各種營養品,好吃好喝的,光是阿華田,藍罐曲奇,孕婦高鈣奶粉就是一大堆,我阿姨知道我特別喜歡德芙巧克力,一買就是一大盒。
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只米缸里的老鼠,躺在床上一抬頭就看到各種好吃的,頗有點《封神榜》里商紂王“酒池肉林”的味道。一個月下來我日漸圓潤,手的狀態也恢復得不錯,再也不是像饅頭腫脹,手指也開始靈活了,與此同時我還自學了用左手使筷子,梳頭,寫字的技能,頗為得意。面對憂心忡忡來探望我的同學,我很自信地告訴他們,自己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很快就可以返校了。
好日子還沒過滿兩個月,手術刀口處就出現了新情況。問題出在了右手尺骨處的刀疤上。這條刀疤開始變得越來越紅了,摸上去越來越燙,刀疤處出現了類似傷口發炎一般的灼熱感,沒過兩天,刀疤的顏色由紅轉紫,繼而變黑,而且黑中帶黃,刀疤處開始凸起,腫起好大一塊來,疼痛感和神經跳動感加劇,與之相伴隨的是我開始發高燒了。
我一開始沒太當回事,還以為是像耳朵有時候發燙一樣的道理,就拿冷毛巾敷在傷口上,但不見好轉,也沒有告知父母,等他們發現,我的刀疤處已經變得黑紫,頓時把他們二位嚇傻了,家里氣氛開始緊張。那天晚上八點多,我已經上床準備睡覺了,我爸媽竊竊私語,這樣不行啊,立馬帶我上醫院去。
來到瑞金醫院已是九點多的光景,急診室的醫生都是年輕的,看我傷口的情況很是慌張,初步判斷是術后傷口感染,但他們也做不了主,于是決定按最大劑量給我掛抗生素下去,希望可以延緩感染的擴大趨勢。
我爸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配藥,付款,帶我去輸液室,我看見護士把18瓶小瓶裝的青霉素打入我的輸液吊瓶中。18瓶是當時的最大劑量,輸液的濃度超級高,又加上當時含鈉的鹽水溶液已經沒有,給我開的含鉀溶液對血管有強烈的刺激作用,這鹽水每滴一次我都有強烈刺痛,只好把吊針的速度放到最低。
這樣一來,一瓶鹽水吊完整整花了6個多小時,我幾乎一夜未合眼,等到走出醫院,已經是早上四五點鐘,外面寒風凜冽,等了30分鐘才有公交車,經過這一夜的折騰,我回到家倒頭就睡。然而一覺醒來,我的刀疤處仍然不見好轉,反而越發嚴重起來,黑紫色的刀疤變成黃黑色,明顯有發炎化膿。于是又去醫院,繼續大劑量地吊青霉素……但是似乎毫無用處,三天之后,刀疤處依舊腫的高高的,像是在耀武揚威。
繼續掛水已經用處不大,醫生建議做一個切開引流術,再行觀察。于是我又再次躺在手術臺上,這次是門診手術,比較簡單,我自己走進手術室,和上次局部麻醉不同,醫生是直接在我手臂傷口處打麻藥的,這麻藥針從皮膚刺進來直接觸及到我的骨頭,下手極重,把我嚇了一大跳,手也往回縮了一下,以為他沒上麻藥就向我直接動刀子了,我說你怎么可以這樣野蠻,他卻不以為然地說我這是在給你打麻藥呀,怎么不知好歹。切開膿腫部位,醫生拿了一些去化驗,讓我回家等消息。
一天后結果出來了,是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對青霉素有耐藥性,怪不得之前吊的青霉素起不了任何作用。
到了這步田地,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何手術后恢復得好好的,一下子就變成術后感染了呢?問了醫生,查了醫書才知道,我當時是開放性骨折,骨折處已經暴露在空氣中,所以感染的可能性較大,按理說,當時手術后應該就注意到這點,連續一個星期給我吊抗生素也許就沒事了,但結果當時只掛了三天,之后也沒有服用抗生素,醫生說術后感染的幾率只有百分之五,你中獎了。我只得認命,隔天去醫院給傷口換藥,但奇怪的是,十多天過去了,傷口無法完全愈合,并時不時有液體滲出,像一個帶著血絲的洞口,深深地嵌在刀疤上,這里面除了膿水,還會有什么呢?

自從術后感染發生,手臂傷口難以愈合,我們家里的緊張情緒就開始蔓延,返校復學變得遙不可及,只得去學校辦理了休學。與此同時,我度過了一個異常忙碌的漫漫冬日,輾轉奔波于上海的各種醫院。
醫生初步判斷出我是得了一種慢性的疾病,俗稱慢性骨髓炎,并不容易治愈。醫生說如果傷口再繼續感染下去,不僅骨折的地方長不好,不排除有要截肢的可能,當然這是最壞的結果。
一說有可能要截肢,我立刻萬念俱灰,感覺天快要塌了,腦海里浮現的盡是張海迪,史鐵生這些人坐在輪椅上的形象,不對,他們都是高位截癱,我若是截肢了,豈不是成了獨臂楊過了么?難道我要變成這個樣子嗎?于是我整天唉聲嘆氣,連看書吃飯的心思都沒了。
最著急的還不是我,而是我的父母,據她同事回憶說,我媽當時在學校就偷偷哭過好幾回了。但哭和哀嘆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我媽化悲憤為力量,開始幫我四處求診。
當時聽說廣東路地段醫院有一個中醫治療骨折的專家,是什么石氏傷科的第幾代傳人。她的門診掛號異常困難,要早上三點多去醫院門口排隊,我爸就搬了椅子通宵在那里排隊,終于幫我掛上了號。那個專家是個五十來歲的銀發女子,房間里擠滿了人,滿屋子都是中藥的味道。那桌上有一大罐用中藥熬成的什么紅色藥膏,旁邊放滿了各種紗布繃帶,幾乎每個病患上前去就是去換上紅色藥膏,綁好繃帶,帶著一身中藥味道離開。
很快輪到我了,這藥膏熱量很大,敷在手上感覺灼熱,又綁了厚厚的繃帶很不好受。之后又去藥房配回一大堆中藥來,結果這些中藥極其傷胃,服用沒多久,不僅食欲下降,而且胃也開始不舒服起來。因為這個原因,就中斷了治療。
不久又聽別人說,上海的中醫門診部有一個專門治療骨髓炎的中醫,她調配的藥膏是專門針對我的病癥的。去了之后,發現這藥膏和之前廣東路的截然不同,黑得發亮,敷在手上涼颼颼的,簡直和前一個醫生主張完全相反,弄的我們不知如何是好。
我媽有個同事介紹說市六醫院有很多骨科專家,我們又興沖沖起個大早趕過去看,結果醫生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之后還兩次跑到長海醫院和長征醫院,好不容易排了隊掛上號,那老軍醫看了片子后,輕描淡寫地說你們這個病既然是在瑞金醫院看的,就不該上我這兒來,幾句話就把我們打發了。
把上海的各種醫院都跑遍了,我發現幾乎所有的醫生對我的病癥的態度,都處于支支吾吾,很想把我拒之門外的感覺。兜兜轉轉,還是回到瑞金醫院繼續求診。
由于我的傷口感染不是在表面,而是骨髓中,所以要治療起來就異常困難,單靠吃藥,已經無法解決問題,然而又不能再次動手術,只好大劑量地吊抗生素來進行緩解。經熟人介紹,認識了瑞金醫院一位五十歲開外的陸醫生,看起來挺和藹的樣子,聽說我休學在家,還拿他自己的休學經歷安慰我。
陸醫生主張的方法就是抗生素。一直掛一種抗生素容易出現耐藥性,必須換著打抗生素,于是我從頭孢先鋒開始掛起,之后換過克林霉素,羅士芬,還有一種進口的青霉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因為每次都是大劑量,所以我每天都要花上大半天時間在醫院里吊針,每次都是四瓶水,每瓶500毫升,總共兩升水,連續吊了三個多星期,我左手上的吊針孔已經多的如同螞蟻上樹一般密集,一眼看去像是一條細細的黑色虛線,護士小姐每次都要找好久才能幫我扎下一針來,好幾次她們都說,實在是扎不了要扎腿上或者頭頸,幸好后來都一針見血地順利扎在了手上。
終于,在三周后的某一天,從傷口處的膿水里,我突然觸及到了一塊質地硬硬的物體!那是什么呢,我剛剛摸到的時候,嚇得一哆嗦,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覺,大著膽子把那塊東西從這傷口的洞里拖了出來,仔細端詳,居然是一塊白色的碎骨,邊緣毛糙而鋒利,薄薄的,有點像吃蘇打餅干時候不小心掉下的碎屑。
看到這個,我們恍然大悟, 原來反復膿腫的罪魁禍首是它!
這神奇的碎片掉了之后,傷口開始逐漸愈合了!
然而,正當我們放下心來的時候,問題又發生了。

大約半年后,傷口處又再度紅腫,發炎,出膿水,去醫院咨詢陸醫生后,持續不斷的抗生素治療又要開始了,三個星期掛水傷口逐漸愈合。
大半年后的某一天,紅腫又如期而至。得了,再去醫院繼續報到。整個休學的剩余時間和復學后的一年都是在半年一次長時間掛水中度過的。
頻繁奔波于醫院掛水,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說實話,這個病本身其實不太痛苦,就是不消停。它就像尼羅河水每年定期泛濫,而我自己就像希臘神話里的西西弗斯,沒完沒了地進行治療,又周而復始地發作。這條路似乎深淵一般看不見底。
這日子是否有窮盡的一天?這樣大劑量的抗生素療法究竟還要持續多久?一切似乎都沒有定論。沒有答案。
進入高三學習之后兩個月,再度紅腫發作,我媽去瑞金醫院幫我掛號,誰知道那天陸醫生的專家號碼全被掛滿了,陸醫生是看不成了,但我媽不想白跑一趟,于是看看還有什么專家可以掛號,結果陰差陽錯地掛了傷科杜寧醫生的號。按理說換個人看也沒啥關系,反正是找醫生幫我開抗生素治療,都是有據可查的事情,和醫生說明情況就好。
這杜醫生四十來歲,聽口音像是北方人,看起來高高壯壯的樣子。他先是耐心聽了我拉拉雜雜敘述半天的病癥,又拿出我的骨折片子仔細查看。
杜醫生沒有打算給我開抗生素。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一看我的骨折拍片,就馬上指出,片子上有一個很小的白色亮點,那是我開放性骨折后,殘留在手臂上碎骨,這碎骨還不止一塊,并判斷之后還會有較大的一塊碎骨從手臂上掉出,這也是我手臂反復紅腫的關鍵原因。這點判斷能力相當厲害,我們之前看過這么多醫生,從未有人能從我的片子上指出這個碎骨的問題來。
針對我的病癥,他很快就給出了具體的治療方案:進行兩次手術,第一次是將尺骨上鋼板的兩個釘子拔出,做清潔沖洗,保持斷骨處的血液循環,促進骨骼生長,第二次是這么多死骨出來說明我斷骨處缺口大,要從腰部取下一塊骨頭來插入傷口,否則斷骨處無法連接起來。只是入院后要進行兩次手術,兩個手術之間需要間隔時間,所以需要大概一個月的住院時間。當然他也說了,手術有風險,腰部取下的骨頭如果不能在手部存活,也會變成死骨。
這個方案具體、犀利,激進,甚至有點可怕。杜醫生讓我們回去考慮一下要不要接受他的方案。
我內心是掙扎的,手術后的疼痛肯定要遠遠超過目前吊針掛水,尤其這次治療中的第二次手術,腰部取骨,聽著就很嚇人,三年前動手術是突發事件,是在毫不知情,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術后那幾日的生不如死還歷歷在目。這一次是可以選擇的,眼前這個醫生只有一面之緣。但我被他驚人的洞察力和魄力震撼到了。我這種慢性疾病的患者,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他在短時間內居然給了這么具體的方案。我佩服這樣的人,比起一眼看不到頭的抗生素療法,我更愿意選擇他的方案。
雖然高考迫在眉睫,我最終決定賭一把。堅決要求入院手術治療,還寫下保證書,說如果手術失敗,我自己負責。我媽起初有點猶豫,但是看我如此堅決,只好同意了。
由于這次沒有用抗生素治療,我手臂上傷口腫脹發酵到極致,腫的油光發亮,最終潰爛,在飽滿的膿血中,果然包含著一塊大約0.5厘米的骨頭碎塊。
傷口潰爛當天是在學校里上課,我若無其事把這塊死骨從手臂竇口處膿血里掏了出來,竇口處的膿血如同決堤一般流了出來,我拿出餐巾紙擦干凈地上的血絲,并把死骨小心翼翼包裹起來,看得周邊的同學都驚呆了。
“這是你的骨頭嗎?看起來白森森的?”
“這上面還有很多孔洞唉”
“借我看看”
“讓我也瞅一眼”
“天哪,你身上的骨頭自己掉出來,是什么感覺啊”
同學們的好奇緊張,圍繞著我的骨頭議論紛紛,但我好像越發淡定了,我覺得自己有勇氣去面對接下來的手術。
半個月后,我接到了醫院通知我入院治療的電話。這次我主動收拾了行李,當天就自行去醫院住院部辦理了入院手續。

和1999年那次突如其來的手術和住院治療相比,2001年住院則要閑適很多。我開始住院那天正好是周五下午,之后的周六周日則全天無事,這意味著我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生活。想來若不是住院,我應該還坐在高三(2)班的教室里,做著成堆的試卷或是苦命地背著英語單詞和課文,哪會有現在這么大把大把的空閑時間呢?真得好好享受這自由的空氣啊。
第一次手術過程比較簡單,就是切開感染的傷口進行沖洗,然后拔除鋼板上的兩個釘子,用碘伏一類的藥物塞在傷口處即可。我當時是局部麻醉,整個過程中頭腦都是清醒的,剛躺在手術臺上的時候,我很緊張,醫生幫我測心電圖,一直叫我放松一點,因為他發現我的心跳達到一百五十以上,杜寧主任過來叫我不要害羞,說手術很快就會過去的,大概十幾分鐘吧,我一聽才十多分鐘,心說還能忍忍,結果事實證明他們動了不下半個小時才完成。
杜醫生在手術過程中主要并不動手,而是吩咐一個實習醫生進行操作,自己在一旁觀看指導,實習醫生在拔除鋼釘時遇到困難,杜醫生才親自動手。我發現他們醫生對手術并不在意,手術室的氣氛比較輕松,不像我們在電視劇里看得這般緊張,一會兒擦汗一會兒遞工具,因為我的手術臨近中午,這些醫生大概也餓了,于是開始討論醫院附近的小籠包哪家最好吃,說得不亦樂乎,他們對著我血淋淋的刀口居然可以討論吃飯的話題,讓我感到非常意外,原來動手術可以這么輕松隨意,說著玩笑話就過去了。
這次手術比上一次定鋼板輕松多了,術后的疼痛感也沒有上次那么劇烈,大概一兩天的工夫,疼痛感就明顯減輕,沒有用杜冷丁來止疼,我也不會疼得忍不住亂叫,在病房里扮演一個討人厭的角色了。

一切看起來還挺順利的,杜醫生查看了我的傷口后宣布再過一周,如果傷口沒啥變化,就可以進入第二次的植骨手術了。眼看進程過半,我卻開始越來越睡不著了。手術一天天臨近,恐懼感與日俱增。
我在病房里住的時間越長,發現了兩個“釘子戶”。這是兩個長期病號,一個三十來歲的阿姨,在此病房已經住了三年多,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伯,也住了有將近兩年。
我當時感到很納悶,這傷科病房如此緊張,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病患進入,何以這兩位可以在此久住呢?
原來這阿姨和老伯是杜醫生此前的兩個失敗病例。
阿姨三年多前因為騎摩托車發生車禍,導致雙腿和一條胳膊皆有不同程度的骨折。由于第一次手術發生錯誤,骨頭接合處有錯位,于是接二連三地進行了好多次會診,據阿姨說,最長的一次手術進行了12個小時,醫生們都累到不行,手術結果并不理想,骨頭還是沒有完全接合好,勢必要進行再次手術,只是經過幾次失敗,連杜醫生也無法拿出一個可靠的治療方案,所以一直拖到現在。她自己住院已經三年多,早就習以為常,這阿姨幾乎把病房當成自己家,她老公和孩子也不是經常過來看她。
那六十多歲的老伯似乎也是類似的情況,杜醫生建議他一條腿換上人工血管,結果導致下肢無法正常行走,年紀大又不便多次手術,于是在醫院一呆就是一年多,他兒子待他也不好,幾次來看他,兩人都要發生爭吵,整個病區都能聽到。
這老伯倒很愿意和我聊天,說起杜醫生曾多次勸他去瑞金醫院下屬的療養醫院,但他堅持賴著不走,說就怕醫生推卸責任,把他放在療養院就不管了。好在他有勞保,住院幾乎不用自己花錢,一日三餐盡是吃醫院食堂的,倒也省事了。
他反正是退休職工,就把醫院當成家了。
杜醫生不是神醫,雖然他有很多新鮮的治療手法,被眾多人簇擁的身影光鮮亮麗。但手術風險始終存在的,尤其是難度越高的手術,風險就越大。
夕陽西下,這兩個病友一瘸一拐在病房里徘徊,這可能是他們唯一的下床活動。留下長長的影子,這陰影始終縈繞在我心頭,揮之不去。
我若是手術失敗,是不是面臨和他們一樣的處境呢?這手術存在大風險,到底要不要繼續?一道巨大的人生命題擺在眼前,能夠證明這手術會成功嗎?一旦失敗了,我還會要動幾次手術?耳邊又回想起媽媽的話,高考怎么辦?
漫漫長夜,我卻怎么也算不出這道題的標準答案。
離第二次手術只剩三天了,看著窗外天快亮了,我暗暗做好了自己的決定。

我至今不知道當初的決定是否是對的。
第二天早上,杜醫生循例查房,我鼓起勇氣,叫住了在眾多醫學生簇擁中的他,終于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說,我不想在腰部取骨了,我感到很害怕,已經失眠好幾天了,能不能不要取骨了,就直接縫合傷口好了。
他感到很驚訝,因為之前我從未流露出自己對這手術的任何想法,現在馬上就要手術了。
他臉上有點不高興,但表示可以尊重我的意愿。
“既然不愿意冒險,這樣暫時也可以,但是呢,你也要考慮一件事,”他頓了頓說,“你的骨折處缺口比較大,又發過炎癥,影響骨骼生長速度,可能就無法長好了,時間一久,你的這塊鋼板就不好取了。要是取不了,鋼板會一直保留在你的手里,不知道什么時候可能會斷,到時候就比較麻煩。”
“而且鋼板在手上的話,你也不方便提重物的,有些重要的檢測,比如說核磁共振等,也沒法做的。”他補充道,“這些都請考慮清楚吧,和爸媽商量一下再告訴我。”
“哦,那我和爸媽商量一下看看。” 我被說得有些六神無主起來。
根據爸媽的再三要求,杜寧醫生最終更改了手術方案,并沒有從我的腰部取下骨骼來填充,只是對傷口進行了多次反復沖洗 就將傷口縫合起來。第二次手術做得很仔細,歷時一個小時才宣告結束。
這次手術后的疼痛感并不強烈,沒過多久我就可以下床活動了。手指也不浮腫,當時病房里有個音樂學院剛畢業的小姐姐 ,說她最喜歡給連環畫上色,買了一整套紅樓夢連環畫,用彩鉛進行涂色,我看了好奇,也涂抹了幾幅,用的是右手,手指還是挺靈活的。
半年后我參加高考,很幸運地考上了自己喜歡的歷史專業,再后來走上工作崗位,好像都還蠻順利,疤痕處不僅沒有再度發炎,醫生之前設想的種種后果都沒有發生,我也沒再因為這骨折和骨髓炎去過醫院。至此,反反復復糾纏三年多的炎癥問題已經離我遠去了。
很多時候 ,我幾乎忘記了自己曾經骨折和骨髓炎這回事,只有在右手提重物時,才會感受到兩塊鋼板的存在,把重物交由左手。拍照片的時候,會下意識地把右手背到身后。
過去20多年了,手臂上的兩道疤痕顏色慢慢變淡,初次見面的朋友多少會留意到我手上的疤痕,拉著我問東問西,這幾年幾乎沒多少人再把目光投射到那里,我可以站在講臺前滔滔不絕,很少再有學生把關注點放在我手上的疤痕處,至于那兩個曾經被我用來遮掩疤痕的白色護腕,也不知道被丟到哪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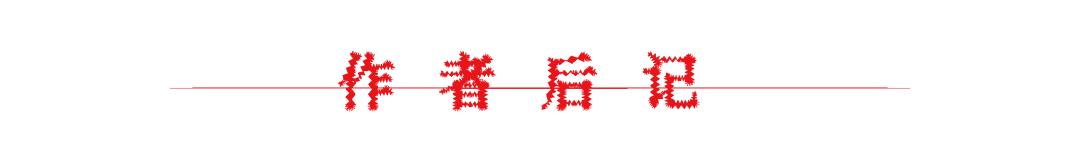
這是一個發生在我17歲時候的骨折以及骨髓炎的經歷,陸陸續續糾纏了三年多,現在想起來還會有痛感,當時覺得是命運的耍弄,現在回頭看看,覺得是一段寶貴的人生財富。這個故事一開始是痛苦,無助,后來是對自己有點感動,在這個過程中,自己其實在思想上是有成長的。我選擇今年年末把它寫下來,希望一切痛苦不堪的過往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變得好起來的。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要有笑對人生坎坷的勇氣。抱抱17歲的自己,帶著微笑前進吧!
非常感謝童言老師對我的激勵和陪伴,這次還收獲到不少寫作技巧,也克制了自己一味宣泄感情的欲望,把重點集中到故事的敘述推進當中去。
原標題:《20年前遭遇的骨折,給我留下兩塊鋼板與成長的勇氣 | 三明治》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