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數字B面:便利性之外的技術塑造
2023年,上海“兩會”期間,多位代表提出關于發展文化產業、提振文化消費的建議。文化產業作為上海的支柱性產業,勢必是未來上海推動新經濟發展加速的引擎。澎湃研究所推出專題《上海文化產業全景報告》,呈現上海文化產業演進之路,關注文化產業的過去、現在、未來。
數字技術、通信技術、算法和智能技術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數字化對文化生活幾乎進行了全方位的滲透。我們要意識到,技術的塑造正在創造一種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也仍應保留思辨的視角,警惕數字技術產生的隱匿的負外部性。
本文通過審視數字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文化生活,從對個體、市場,與全球的影響三方面出發,試圖發現那些隱藏在時代更迭之下的數字化的B面。對數字技術辯證思考,才能在文化產業數字化突飛猛進的同時,真正讓技術發揮向善的能量。
對個體:數字鴻溝下的公平性盲區,與自由和剝削一體兩面的“數字勞工”
數字化技術在日益為人們日常生活提供便捷,與此同時,也正無形中擴大著數字鴻溝。
不同階層、不同年齡,與城鄉群體之間對數字技術的運用不盡相同。在數字技術愈發成為主流生活方式時,那些底層的、老年的、生活在非發達地區的群體,往往對數字的賦能受益甚微,有一部分人原有生活模式被改變,甚至因為信息不對稱而被搶占的生活資源。例如不會網購的人不僅享受不到快遞的便利,而且可能會買不到物資,或者必須要用更高的價格交易。而資本驅動下,文化企業為了迎合特定受眾的需求加大這些需求的生產,導致其他文化需求日漸消失。
例如,根據2020年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數字文化消費初步形成珠三角、京津冀、長三角、成渝和長江中下游五大城市群高地,數字文化消費總量占全國的54.13%,而中西部廣大地區數字文化消費水平和能級偏低,數字文化消費規模較小。
數字鴻溝在區域和階層中擴大,顯示出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失衡。技術如何實現社會“公平性”的道德倫理與社會責任,值得關注。
數字異化,是數字技術影響社會的第二個面向,它幾乎席卷了所有互聯網用戶。
學者周延云撰文指出,數字時代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娛樂和勞動幾乎沒有區別。社交媒體在滿足用戶需求的同時,個人隱私、休息時間與社會資本也被不斷商品化。網絡用戶勞動是生產性的,是被資本剝削的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在這種語境下,“用戶”即“數字勞工”。
人們在網上貢獻點擊時,網絡數據變成了資本可預測性管理生產數字奴隸的依據。依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用戶在線的時間與其為網絡企業創造的價值呈正相關,用戶的在線時間越長,被剝削的程度也就越嚴重。
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將馬克思的異化勞倫理論進一步發展,認為日常生活的空間生產也已淪為資本主義官僚主體生存的基礎和控制的對象,人們面臨被模式化的“功能機器”。
而隨著數字化的推進,智慧城市等概念的提出,則意味日常生活全面的被異化。在物聯網世界,每個人都擁有N個賬號,N個電子身份,數字技術對人進行賽博疊加,一個身體出現了多個輔助電子個體,增加了全球資本主義可以剝削的數量底盤。
對市場:寡頭壟斷沖擊良性競爭,和監管滯后下的侵權亂象
互聯網在經濟社會中的全方位滲透,崛起了無數互聯網平臺,其中一些發展成“巨頭”,在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甚至形成寡頭壟斷。
學者李勇堅曾在《互聯網平臺寡頭壟斷:根源、影響及對策》中提出,在互聯網平臺,壟斷主要表現為數據壟斷、流量壟斷和算法壟斷。
數據壟斷表現為,平臺向消費者提供免費服務時,實則用戶是以數據作為貨幣。通過服務收集用戶多維度數據,獲取用戶畫像,以便平臺利用數據優勢鞏固地位的同時,拓展業務,建立新市場的競爭優勢。決策科學家Francesco Corea曾在其著作《An Introduction to Data》中指出:“數據兩極分化可能導致很少的公司引導和吸引大部分數據流量,而其他公司(幾乎)被完全排除在外。幾年后,這種指數趨勢可能會給該行業帶來巨大的進入壁壘。”
流量壟斷體現在,平臺爭奪著網民日常數字文化生活的“上網入口”角色,讓用戶形成依賴,貢獻時間與注意力,平臺則能利用優勢,拓展其他業務。兩個平臺之間的內容無法分享,和商品交易時的排他性支付手段,都是流量壟斷的典型案例。
算法壟斷是互聯網平臺的獨特性,包括利用搜索算法將益于平臺的結果排列前位,讓競爭對手處于不利位置;進行歧視性的動態定價,即“用戶殺熟”,損害消費者權益;利用大數據算法進行千人千面的推送,在“定制化”推送的同時,也造成了“信息繭房”,難以滿足公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互聯網平臺經濟在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經濟發展、創造生活便利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伴隨擴張,一些平臺形成了寡頭壟斷地位,當壟斷不斷自我強化時,逐漸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行業寡頭的市場份額超過企業份額之和,搭配良性競爭格局,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對寡頭企業本身來說,也會有限制創新的危害。
對市場競爭的另一大危害,是新興數字文化市場的相對滯后的監管體系。
如今,數字文化產業已成為文化產業的主體部分。但數字文化市場在網絡的虛擬空間運行,與傳統市場區別較大,導致傳統文化市場監管政策與法規難以提供有效支撐與保障,而新的監管體系的制定相對市場發展存在滯后,帶來了一段時間內亂象不斷但監管乏力的處境。
據報道,2021年6月,廣州互聯網法院發布成立兩年多來審理的互聯網內容平臺案件情況和典型案例。數字版權侵權占逾九成、社交電商等新型內容平臺糾紛增多,平臺短視頻侵權方式復雜多樣。而受到數字版權侵權的著作權人也常常面臨維權障礙,例如個人能量單薄、訴訟成本高、取證難。
知識產權作為保障數字文化市場良性運行的重要機制,若無法受到應有的尊重與保護,將反噬數字文化市場的健康發展。
版權問題外,隱私權是數字文化時代另一個突出侵權問題。為了享受平臺方提供的服務,用戶不得不讓渡一些隱私數據,甚至滋生出了倒賣個人數據信息的黑市。
技術與監管的關系,讓人想起大衛·霍茲曼曾在《逝去的隱私》的警示,“我們的隱私比北極冰川消融得更快,技術的侵蝕速度超過了法律體系的保護能力。”
對全球:愈演愈烈的數字文化霸權爭奪
對平臺寡頭壟斷的擔憂,放在全球化競爭的大背景下,則會引發國際對數字經濟壟斷和數字文化霸權的擔憂。
數字經濟是文化產業實現趕超式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機遇,而文化產業本身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當平臺巨頭演變為寡頭壟斷,再進入全球競爭與國際政治的語境時,壟斷將進一步實現文化意識形態操縱,形成數字文化霸權的局面。
心理學家Robert Epstein提出“搜索引擎操縱效應”,認為搜索引擎通過對用戶的知識分發進行操縱,能夠有效地影響用戶的傾向,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選舉結果。法國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則提出,每天大眾化的程序推送下,都會生產出數量龐大的“人工群眾”(artificial crowd)。看似用戶自主抉擇的行為,實際上早已被數據算法預測與影響,用戶成了被數據穿透的“工具人”。
學者魏鵬舉就曾表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憑其數字技術的原發優勢和數字媒體的壟斷地位,逐漸將西方意識形態附加于西方數字文化中。例如多國曾把TikTok(海外版抖音)視為洪水猛獸。互聯網平臺所掌握的全球數據,一旦加以分析與應用,便能在國際政治上產生巨大牽引力。
數字技術不可避免地在國際政治的角逐中被重新演繹,而用戶則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數字文化霸權的影響,成了全球化競爭藍圖中的一個個小小的點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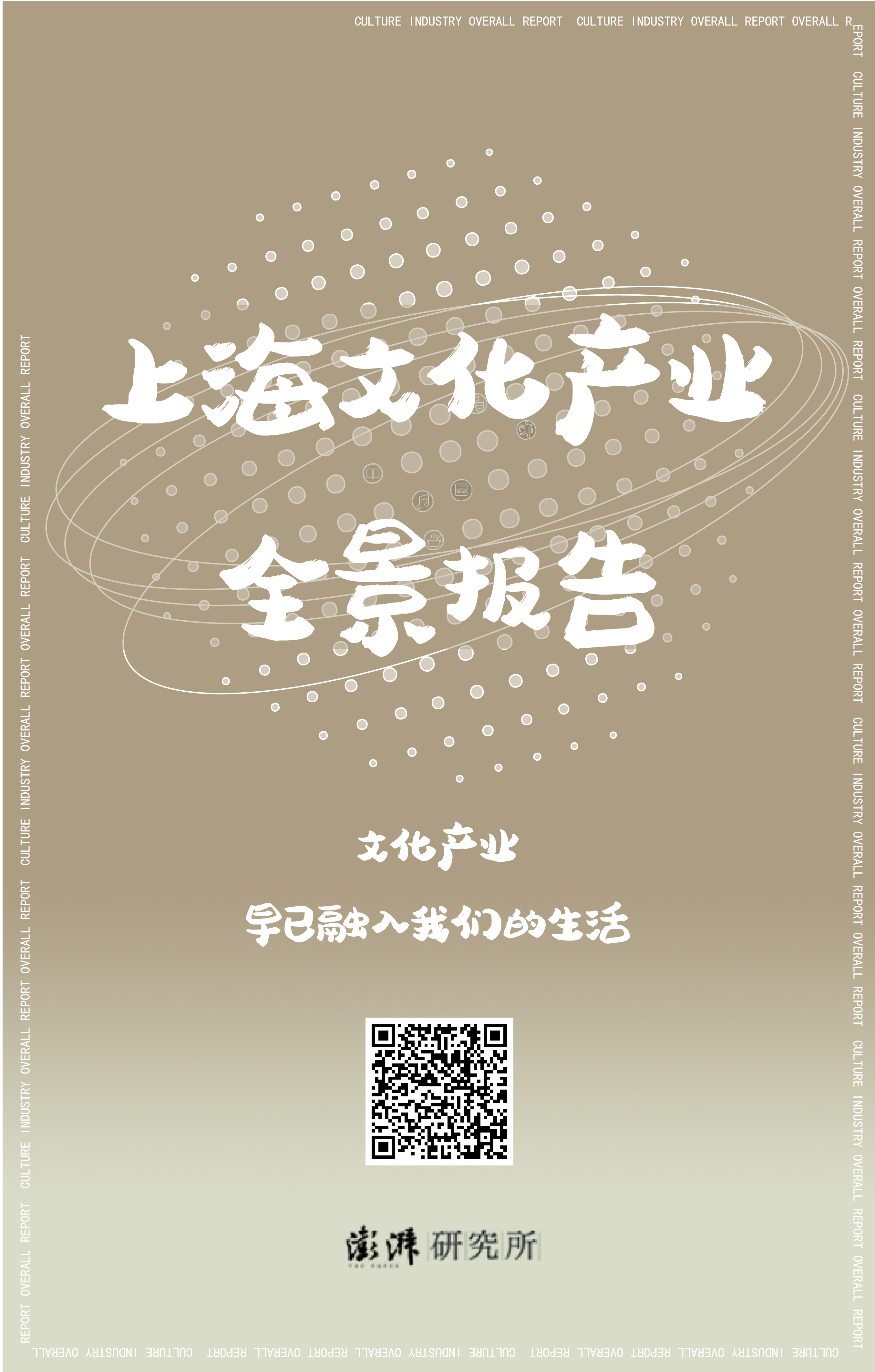
制圖:澎湃研究所研究員 呂正音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