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匯講堂|北方強國石峁被誰消滅了?陶寺的盤龍真是龍嗎?
2023年1月7日,由澎湃新聞網作為媒體特別支持的第159期文匯講堂“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系列跨年四講圓滿收官。最后一講《4000年前,中國王國與王朝的謎和底》提問踴躍,26個有效提問在現場和結束后的微信群中得到三位主講嘉賓——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濤、趙海濤,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邸楠的回答,使聽友對黃河上中游的三個王國和王朝,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有了更詳盡的了解。

19位提問聽友中的八位獲得贈書,主辦方追加了2本陜西考古院黨委書記、院長孫周勇的新書《玦出周原:西周手工業生產形態管窺》(上海古籍出版社)。獲獎聽友分別為:上海楊福興、上海律師王勇、蘭州大學王奕心、西北大學祁翔、陜西師大孔新緣、北京文博人王晶、深圳投資人何仁、武漢華中科大王利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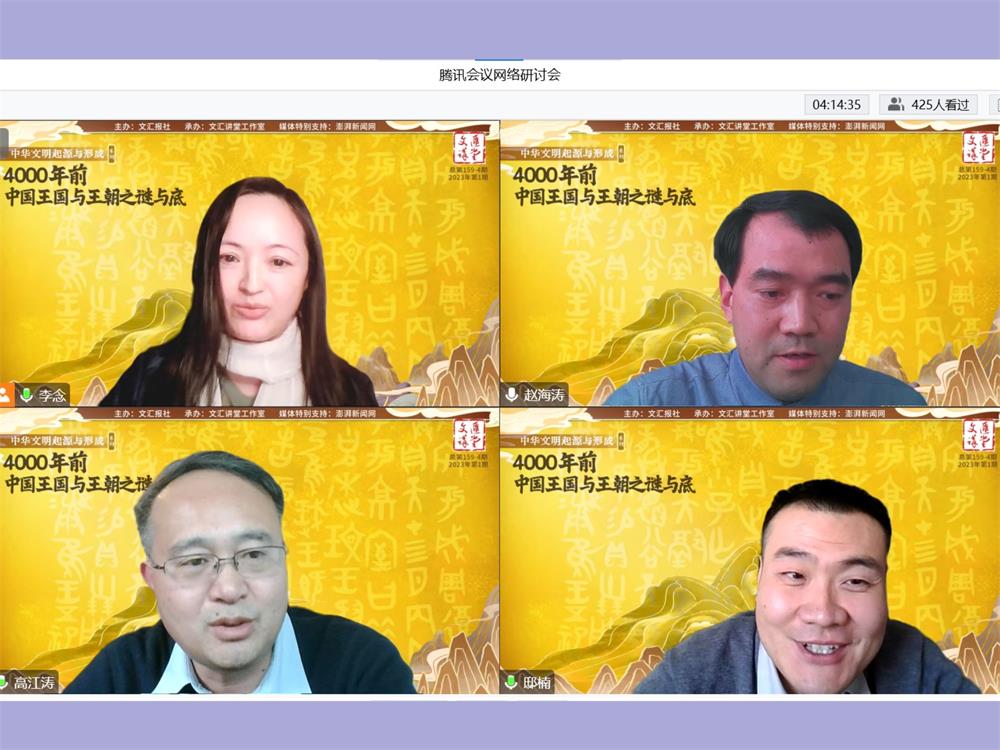
主持人李念主持提問環節,三位嘉賓回答聽友提問
考古是基于現有材料的非確定性推測
上海會計咨詢楊福興:您剛才提到四證,那需要什么樣的證明才可以明確得出陶寺就是堯都的定論?
高江濤:這其實還是一個典型的考古和文獻對應的問題。從理論上來說,一方面,什么樣的證據都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來認定陶寺就是堯都。關鍵“就是”兩字肯定是無法確定的,即使證據再充足。我們看到的也是幾千年前留下來的東西,很多是以物質形態存在的,而許多上層建筑層次的、精神理念層次的東西無法留存下來。所以,多充足的文獻才算是“充足”也是個問題。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我們沒有百分之百的證據,就不能推測說它是什么或者它有可能是什么。
考古學者經常會說,有十分材料說七分話,因為考古是有局限性的,我們發掘的都是留存下來遺存,具有片面性。當然,如果確實存在各方面、不同層次的證據,即“證據鏈”,一環扣一環地都指向了某一個歷史記載的東西,我們還是可以適宜的下這樣的結論。但是,是否要下一個十分肯定的結論,估計任何人都不會這樣做。
從這個角度來說,考古學者的研究與社會的期待之間是存在差別的,甚至是有差距的。畢竟學者的研究是要有科學原則的,只有在證據充足的情況下,才可作出適當的判斷。
考古目的之一,豐富歷史內涵,活化當時場景
上海電力工作者朱偉青:目前研究顯示二里頭可能是夏都,這還需要什么樣的考古來證實?
趙海濤:我的觀點與高江濤基本一致。現在沒有最關鍵的證據或者當時的文字,缺少百分之百下結論的證據,所以現在做這些研究只能說極有可能、最有可能。
因此應當轉向研究其他更重要的實際問題,例如二里頭的內涵問題、王權發展模式、布局和國家結構,從聚落發掘考古現象。通過多種手段、多種學科的合作,去復原當時的社會生活面貌,豐富當時的歷史內涵,進一步活化當時的場景。
4000年左右綠洲文明文化對中國文明的影響較深
上海律師王勇(微信回答):今天三位老師都講到中國,地中、天下之中,那么同時代其他世界文明中心是不是有可比較的地方?當時的中國跟世界其他文明有沒有關聯性?
高江濤:同時代的世界其他文明中心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哈拉帕文明)等當然可以和我們這一時期比較,只是比較的角度和地方是偏宏觀的方面,如他們的文明發展歷程(中國的開始晚)、國家的性質(神權或王權的異同)、國家運轉的模式等等。
實際上,4000年左右影響中國的文明較深的恰恰是中亞、西亞的一些綠洲文明文化尤其青銅文明,此外還有近印度地區。具體到器物主要有海貝、銅器、綿羊、瑪瑙等等。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李旻先生稱之為三大互動圈,可查相關文章。
墓穴的出現很可能與農業、定居有著密切關系
北京科研人陳劍超:請問墓葬制度是從什么時間開始形成的?在此之前人去世后是如何處理的?
高江濤:關于人去世后如何處理的問題,其實方式有很多,例如水葬、火葬等,最終更多呈現的是埋在地下的土坑葬、石棺葬等。從目前的材料來看,埋葬多是有坑的,如果沒有墓坑、墓穴就無法知曉墓葬的形式。帶墓穴、墓坑的墓葬至今約有一萬年,實際上它與農業興起,或者說與定居生活有關。農業形成后,有穩定的定居生活,才會想把先人或者是去世的人安葬好。
所以,墓穴的出現很可能與農業、定居有著密切關系。墓葬安葬方式逐漸形成了墓葬制度,經過發展,會進一步形成一個含有禮器、具有禮制內的墓葬制度。這與文明的出現有關,大約在五千年前后,甚至更早一些。到了陶寺之后,包括二里頭時期形成了一種明確禮制內涵的墓葬制度。
石峁怎么消失,誰又來到了石峁?

石峁城的馬面(左圖)已具備晚期馬面(清朝時期山西平遙城馬面,右圖)功能
石峁遺址里關于祭祀的遺存只有祭祀坑
包頭赤峰學院歷史文化專業學生:石峁遺址是否發現過類似壇廟冢的成組祭祀遺址?
邸楠:2015年,考古隊曾在石峁城外發現過一個石構的建筑,里面有一個方形的建筑,外面還有一道半月形的石墻,最初認為可能是一處祭祀遺存。后來隨著發掘的深入,推翻了原有的認識,被認為是城外一處預警設施。現在石峁遺址里明確和祭祀相關的遺存能見到的就是人頭祭祀坑,壇廟冢暫時還未發現。
皇城臺頂上一萬多平米的大臺基目前只發掘了一些外圍的輪廓,發現一些精美的石雕,這個建筑是否與宗教有關,具體性質目前還無法確定,至于壇廟冢這類的祭祀遺存目前暫時還沒有發現。
朱開溝文化晚于石峁約100年,有取代關系但源和流不盡相同
陜西西北大學學生祁翔(微信回答):石峁文化的年代下限進入夏紀年。根據報道,皇城臺等地點還發現了晚于公元前1800年的遺存。請問石峁文化結束后,其文化和人群的流向是什么?
邸楠:根據石峁遺址的發掘資料,公元前1800年是石峁城址的年代下限,使用雙鋬鬲的原住族群基本消亡,之后一群來自北方使用“蛇紋鬲”的族群占據了這里,有學者將此類遺存稱為“朱開溝文化”。
2019年我們在皇城臺頂上發現了這類“蛇紋鬲”的遺存,他對石峁的一些建筑進行了破壞,又重新修了一些建筑。測年數據顯示石峁發現的“蛇紋鬲遺存”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和城址的年代下限之間大致有100年左右的間隔期。
從文化面貌看,兩者可能屬于不同的考古學文化,源和流也不盡相同。就目前發現來看,它可能與之前的石峁文化有先后取代關系。
至于族群間是否存在親緣關系,目前材料太少,沒有直接證據。
石峁的消亡或與外敵入侵無關,與氣候變化有關
甘肅慶陽行政干事劉繼東:石峁是甘肅慶陽的,有人說石峁是被游牧民族所滅,是否有這個說法?
邸楠:石峁所處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位于長城的沿線,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農耕和游牧的分界線,是氣候非常敏感的一個區域。暫不排除有外敵入侵之后導致消亡的可能,但是目前考古發現沒有證據支持這個觀點,我猜想可能還是與氣候變化有一定的關聯,目前尚未有明確答案。
龍山時代變冷,生業變為半農半牧,與石峁消亡并無必然關系
西安陜西師大孔新緣:榆林地區仰韶晚期和龍山早期生業資源中對于豬的利用是十分常見的,后來對牛、羊的利用開始增多。這對石峁的衰落有什么影響?
邸楠:牛羊的最早馴化不是在中國,而是在西亞,大約在距今5000年前后進入中國的西北地區。這樣重大的變化與環境的變化也有一定的關系。因為仰韶時代是一個氣候的暖期,到了龍山時代逐漸變為一個比較干冷的環境,一些聚落的生業模式也在這個階段出現了改變。
仰韶時代以農耕為主,但到了龍山時代,農業還在進行,但畜牧業比重逐漸增大,轉變為半農半牧的生業模式,這種生業模式貫徹了整個龍山時代,直到石峁的消亡,牛羊增多與石峁消亡應該沒有必然關系。
石峁馬面表明戰爭是當時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蘭州大學博士生王奕心:請問石峁馬面的出現是不是中國最早的防御系統?
邸楠:準確地講,石峁發現的馬面應該是中國最早發現的馬面之一。隨著石峁發現和確認馬面之后,今年在內蒙古中南部、山西晉北一些同時期遺址的發掘中,也在城墻上發現有非常成熟的馬面設施,年代大多與石峁相近,甚至稍微再早一些。但基本都出現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
現在能夠確認的是,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北方地區就出現了比較成熟的馬面、甕城等城防設施,表明這一時期對防御的需求非常強烈,頻繁的戰爭成為居民的生活常態。
石峁或正是一個早期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
榆林石峁管理處魏新麗(微信回答):石峁遺址與遼寧的牛河梁、夏家店石構防御型遺跡等共同構成當時中國的草原邊緣地帶,那么石峁遺址在歐亞草原文化交流中扮演什么角色?
邸楠:石峁自身所處的位置十分重要,這個稱之為草原邊緣地帶的區域,在距今四千年前后可能正是一個早期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石峁發現的一些比較特殊的器物,如石雕、玉器、口簧及少量青銅器,有學者就曾論述過和陶寺、二里頭以及更為遙遠的俄羅斯阿爾泰、西伯利亞葉尼塞河谷同類器物間的相似性,文化間的頻繁交流可能正是本地區早期國家和文明誕生的催化劑。
草原邊緣地帶往往受氣候影像較大的區域,在早期社會,這些地區的經濟模式會比較脆弱,人與資源的矛盾突出,或導致頻繁的戰爭,這可能是本區域出現了對城防設施的極度需求的主要原因。
琮紋飾差異反映出石峁和良渚屬于兩個不同的信仰傳統
武漢教師王利芬(微信回答):石峁(蘆山峁)琮很少有動物紋,皇城臺出現了幾種動物紋,但良渚琮有穩定的紋飾,如何理解這種琮紋飾差異?
邸楠:石峁本身發現的玉琮很少,發現的少量玉琮可能是從別的區域流轉過來的,一些玉琮還被切割進行二次改制。石峁僅有的幾件,不同專家來看過對來源的說法也不一樣,有的覺得像良渚的,有的說是齊家的。
石峁常見的玉器類型主要有牙璋、玉刀、玉鉞、玉鏟、牙璧等,基本都是素面無紋飾,顯示出石峁和良渚應該是兩個不同的信仰傳統。
石峁的動物主要是以石雕的形式表現,風格寫實可以辨識的有牛、馬、虎、蛇、蟾蜍等,還有一些抽象到無法辨識的石雕,這個也和良渚發現的神徽都大體相似不同。目前我們對原始宗教的了解還是比較有限,初步感覺石峁更像是多神教,而良渚更像是單神教。
青銅人面具夸張的眼部表現出原始宗教里對眼睛的崇拜
上海教育領域錢新宇(微信回答):石峁出土過一目小玉人,二里頭有一目青銅人面具,和我們普遍的人面有大不同,為什么會有這種情況?
邸楠:上世紀七十年代曾在石峁遺址征集過一件玉人面,曾有學者考證為《山海經》記載的“一目國”,其實仔細觀察,這件玉人并非一目,從發髻和嘴部造型看,應該是表現一個人的側臉。
印象里二里頭遺址沒有公布過青銅人面具,只見到綠松石牌飾,或許您說的是三星堆遺址發現的青銅人面具,這個和石峁出土石雕上的神面確實有很多相似,都是以人的五官為基礎,進行一些夸張的表現。最夸張的眼部,有的眼睛凸出,有的外面有大眼眶,可能是表現原始宗教里對眼睛的一種崇拜。
陶寺與石峁是親戚嗎?盤龍形象有源頭嗎?

高江濤解答,陶寺的盤龍形象是多種動物的集合體
都邑性大遺址都是以本土文化為主,兼具其他區域典型文化
徐州機械博士張元越:陶寺遺址并非單一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重疊,那么考古當中是怎樣劃分的?
高江濤:不只陶寺,所有史前的都邑性的大遺址,包括石峁、二里頭,其實都存在著所謂的多元的其他區域里的典型文化因素。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特點,即兼收并蓄。
所謂的其他區域的文化因素,并不是指都邑遺址里僅有其他文化的因素,它的主體或是它的核心還是以該遺址為核心的本土文化。陶寺兼有其他不同區域,比如海岱地區、西遼河流域,甚至甘青齊家文化,也包括長江中游、長江下游良渚文化因素和長江中游的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因素。
更有趣的是,其他區域的文化因素還都是當地文化的典型,甚至標志性的器物。最近研究發現,石峁文化中同樣存在屬于長江中游、屬于肖家屋脊文化的特點。需要強調的是,這些都只是一個復雜文化的因素,而不是陶寺文化的主體和主流。
與凌家灘、紅山的龍相比,陶寺的盤龍是三四種動物的集合體
北京文博人王晶:陶寺四個盤龍上的龍形象與凌家灘的玉龍、紅山玉豬龍有什么傳承關系?
高江濤:這是個很專業的問題,與我們每個人都有關,因為我們都說自己是龍的傳人。關于龍的研究有著大量的文章,并且有趣的是,陶寺、凌家灘、紅山這三個遺址都發現了龍。
關于凌家灘的玉龍和紅山的玉龍,首先,凌家灘和紅山的龍都比陶寺的龍要早。現在看來,一個屬于北方,另一個屬于偏南地區。其次,它們有個相同點,三地從形態上來說都是盤龍。
當然,三者的差別還是比較大的,且爭議也較多。例如,有學者認為,凌家灘的龍確實形態豐富,但也有學者認為那是個玉虎。學者對紅山的龍同樣存在不同的看法。早期有先生認為是蠐螬,農村家里耕地時經常會犁住蠐螬。很明顯的它的頭部是一個豬的形象,也有說是熊的形象,甚至其他各種形象。無論如何,它都是一種或者兩種動物形象的展示或者展現。
但是,陶寺的龍就不是一種動物形象的展示,它至少是三至四種動物形象的集合體。首先,它是一個蛇的形象,但同時又有鱷魚的兩排牙齒和吻部,還有方型略尖一點的耳朵,這可能是熊的形象。總之,陶寺的龍盤的動物形象是多種動物的集合體,二里頭的龍也是典型的多種動物的集合體,商代的龍一看就是一個龍的形象。從這個角度來說,陶寺的龍更靠后期,時間上與二里頭、商代如婦好墓里的龍更加接近些。
陶寺與石峁的文化類型屬于一個大系統,但絕非同一類型
陜西考古本科生胡羽心(微信回答):陶寺與石峁的城址在時間上近乎并存,且文化類型相似,而二者同在陜晉豫地區且距離相對較近,是否可以通過考古材料證明二者處于政治聯盟甚至是同一邦國的中心聚落和次級聚落?因石峁奠基坑人頭骨屬于西部少數民族,所以我認為二者不大可能是敵對關系。
高江濤:陶寺與石峁在年代有共存,至少300多年。陶寺可能稍早近100年(新的測年顯示陶寺早期有較多數據是距今4400年)。二者文化類型不同,但若從我們以前常說的“鼎系統”和“鬲系統”的角度說,可以理解為屬于一個大的系統,但絕非同一類型。
二者地域并不近,陶寺離豫西甚至中原腹地較近,陶寺嚴格來說還是屬于盆地(平原)文明,而非高原文明。二者不可能是同一邦國,當然卻可能存在聯盟關系。無論聯盟和敵對關系在考古上很難實證,可以適當合理推測。
邸楠:石峁外城東門人頭坑中的頭骨曾做過體質人類學和鍶同位素的測定,顯示并不是本地居民,也不是西北居民,而是來自于今天東北地區,和夏家店下層文化接近,顯示出石峁和周圍存在遠距離的文化交流,可能是在戰爭中擄掠或者是貿易中獲取的人口。
石峁的西北方同時代的是齊家文化,石峁發現有很多帶雙耳的陶器,大型墓葬里棺外有側身屈肢的殉人,這些都可能是受到齊家文化的影響。
二里頭還有什么輻射到外圍?

趙海濤解答,二里頭晚期鑄銅技術進一步發展,形成了青銅爵、斝、盉、鼎、鉞為主的青銅禮器組合,為商周禮樂文明奠定基礎
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的鬲,具有北方文化特征
西安西北大學碩士祁翔(微信回答):石峁與二里頭,除了牙璋等玉器和綠松石龍形象顯示二者關系緊密外,還有沒有其他例證?石峁與二里頭,除了牙璋等玉器和綠松石龍形象顯示二者關系緊密外,還有沒有其他例證?
趙海濤:還有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的鬲、高領、花邊,具有北方文化特征。是否與石峁有關系、發生關系的路徑,都有待深入探索
二里頭鑄銅技術為商周青銅文明奠定了最重要基礎
深圳投資人何仁(微信回答):二里頭除了牙璋的輻射影響之外,是否還存在對外圍區域和后世的銅器形制影響現象?
趙海濤:二里頭文化晚期鑄銅技術進一步發展,可以造出更大型、復雜的容器,形成了青銅爵、斝、盉、鼎、鉞為主的青銅禮器組合,成為高級貴族等級身份的最重要標志。
青銅禮樂制在鑄造技術、青銅禮器的基本器類、器形風格、功能以及青銅禮樂制度的基本內涵等方面,為后世輝煌、發達的商周青銅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礎,并通過商周王朝的擴展與發展,形成了華夏文化,奠定了古代“中國”的基礎。
(文章首發于文匯APP,原標題為:“北方強國石峁被誰消滅了?陶寺的盤龍真是龍嗎?|講堂159-4④”)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