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攝影收藏?|顧錚:上海沒有一座與其地位相匹配的攝影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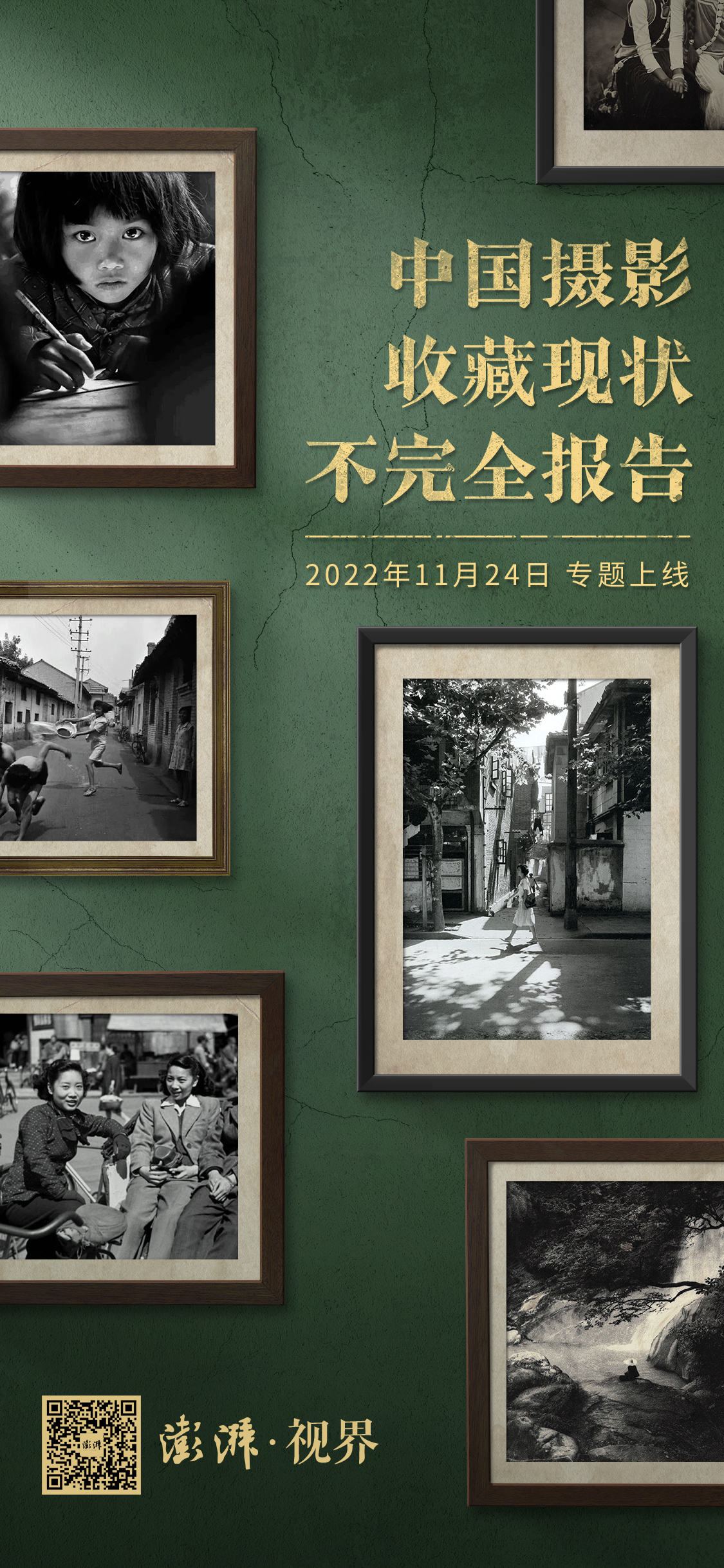
海報設計 澎湃新聞記者 周寰
【編者按】
在中國,攝影收藏還是一件新鮮事。盡管圖片已經是人們日常交流的方式,但收藏攝影似乎仍是一件遙遠的事。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的影像收藏市場逐漸活躍,越來越多的人與機構開始意識到了影像的價值:出色的攝影是時代的見證,也具有藝術價值,連接了個人與集體的記憶。
十數年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顧錚作為學者訪問過許多世界上重要的美術館,也得以接近這些美術館中的攝影館藏,這些豐富而又各具特色的館藏無不給顧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當澎湃新聞記者就國內攝影收藏現狀采訪顧錚時,他自然地將上海公立機構與其他國際大都市的各種機構對于攝影收藏的重視程度進行了比較,并直言希望城市公立機構能夠有建制、有預算來推行和展開攝影收藏。“上海在中國攝影發展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無論從什么意義來說,都是應該進入到現在的收藏議程中來的。而且這也是一種提升上海文化影響力的新的潛力和方向。”顧錚說。

顧錚策劃《記錄中國》展在明尼蘇達大學懷斯曼美術館展出一景,2007。顧錚 攝
澎湃新聞:為什么公立機構需要攝影收藏?
顧錚:吹毛求疵地說,攝影是一種具過程性的實踐,這樣的一種作為實踐的攝影是不可以收藏的。但是,我們可以而且在展開的收藏是收藏攝影實踐的結果和成果,那就是照片。一般來說,收藏的對象是物質性的客體,具體的實踐如果要收藏,只能收藏其成為了最終結果的物質形態,如果是影像收藏,那就是照片或影片。
公立機構如果要收藏攝影,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它本身是什么定位的機構,然后才能夠從自身定位出發考慮展開什么性質的攝影收藏。還要考慮是用的納稅人的錢,你的收藏能不能服務于你的定位所面向的公眾,滿足他們的愿望和需要,同時還要在一定程度上考慮所在社區的需要。其實,更重要的是,然后讓公立機構有一個機制保障收藏的發生是符合公眾需求和利益的。
至于為什么,我在想你這里所指的機構應該主要是文化機構。包括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和檔案館等設施。那它們的使命之一就是保存、維護由照片所保存和體現出來的人類精神活動的過程和實踐。這可能包括了兩個方面,一個是記錄,一個是創造。圖書館和檔案館可能更偏向于具有文獻記錄性質的照片。而美術館和博物館則可能更注重于具有表現性質的以照片形式存在的攝影作品。當然這里也許并沒有一定的嚴格區分。有的時候,跟隨攝影作品一起入藏的可能還有大批具文獻記錄性質的照片,你美術館和博物館難道就可以把這部分剝離了拒之門外?說到這里,我還想說,中國的博物館對于攝影收藏的觀念還比較滯后。你看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那里早已經把攝影作為典藏對象并且確保了專屬空間展示其收藏。中國的博物館如果以典藏對象為古代為職守的話,那中國的美術館是不是應該把攝影納入其有計劃、有方針的典藏規劃中來呢?而且,應該是有建制和有預算來確保推行和展開。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攝影展覽,2018。顧錚 攝
澎湃新聞:從您參與攝影批評與寫作三十多年的視野來看,中國的公立機構,特別是像美術館、圖書館,城市規劃館等等,他們對攝影收藏的重視程度如何?是否能舉出一個正面的例子?
顧錚:隨著中國當代攝影的發展,攝影受到公立機構的關注程度有所變化。一些機構對攝影收藏的認識與態度的變化也在發生。比如,二十年前,曾經有機會陪法國攝影家馬克?呂布去上海某剛剛建立不久的公立機構了解辦展覽的可能性,同時問到是不是有可能展開和建館宗旨相符合的攝影收藏時,對方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考慮。但去年,這個機構舉辦了攝影展覽。這就是一個可喜的變化。不過,雖然各地不時會有一些公立機構收藏了攝影作品的信息傳來,但總的感覺是,這都還是一些一時興起和打秋風式的方式比較多。這當然可能是,是在機構和集體認知沒有一致的情況下,一些意識到了攝影收藏的意義和重要性的主事者的變通之舉。這也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而且這么做也能慢慢改變人們對于攝影以及展開攝影收藏的看法。
但是,能夠持續地、有計劃地、有方針地展開收藏的機構確實不多,即使有的機構已經有了這樣的認識甚至是有了一些具體舉措,有的時候也還是經常面臨“人去政息”的困境。當然,據我所知,現在有一些公立機構在靜悄悄地展開有特色、有計劃甚至是有預算的收藏。不過我還是覺得,這個靜悄悄地展開收藏的方式還是太謙遜了,不利于將攝影收藏的重要性通過比較公開甚至是有點張揚的方式(包括將收藏的作品做展覽擴大影響)來向公眾傳遞更明確的信息,以此提升收藏攝影作品的共識,并且反過來推動包括這些機構的上級領導部門的重視的目的。而如果能夠通過收藏活動來發出更明確的有關攝影收藏的信息的話,相信只會是好事,只會更進一步地吸引大家的關注和引發具體合作的可能性的。

MIT博物館“喬治·克佩斯-照片圖像”展,2017。顧錚 攝
澎湃新聞:從您的游學經歷出發,中國的公立機構的攝影收藏與西方是否存在差距?差距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顧錚:我確實有幸參觀過國外的一些公立機構的攝影收藏,包括美術館、博物館和一些大學的美術館和圖書館的攝影收藏。我覺得國外這些公立機構的最基本的特點是,一旦收藏(包括攝影)形成一定規模,可能就會積極策劃展覽以活化收藏,這個舉措同時也有引鳳筑巢的意義。另外一個就是公開收藏,以利于公眾的接近(access)。公開收藏可能是公立機構最應該落實的做法,也是所有公立機構的收藏都被課以的義務。因為公立機構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來購買的藏品,因此有義務向納稅人公開收藏,也必須對納稅人有回報,服務機構所在的社區的。我以前說過作為公立機構的美術館和博物館應該是一種具有融入社區的主動意欲的“社區公民”。而且公開藏品是對這份公共財富的最大保護。越公開信息的收藏,它就越安全,因為大家(公眾)一起“惦記”著的。這樣就置于眾目睽睽之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防止可能有的損害公共利益的“暗算”甚至是不法侵吞。至于私人收藏,它不受這個公開性要求的節制,但它反而可能以積極公開的態度和方式,來吸引公眾注意,并且形成與公立機構的競爭和壓力。
中外之間的差距就是,中國可能有因為歷史原因形成的收藏,但公眾不知道其所在與內容和規模。而一個值得推薦并且嘗試的方法是可以先做調查。東京都攝影美術館曾經牽頭組織過有關日本的包括了公立機構在內的攝影收藏的全國性調查,并且發布了調查報告。我覺得這個做法可以借鑒,由某個機構牽頭組織,作為推動公立機構展開攝影收藏的第一步。還有一個想到的值得努力去做的是,國外許多博物館是同時展開和擁有攝影收藏的。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是擁有包括了當代攝影的貫穿攝影史的攝影收藏的。倫敦的V&A博物館最近也把攝影收藏給予了更為突出的處理,以增加其吸引力和競爭力。而我們的情況呢?攝影術發明至今已近200年,它所具有的歷史和文化的積累和豐富的實踐難道不可以進入博物館收藏的視野嗎?上海博物館它為什么不可以展開基于中國攝影史的收藏呢?尤其是上海在中國攝影發展的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無論從什么意義來說,都是應該進入到現在的收藏議程中來的。而且這也是一種提升上海文化影響力的新的潛力和方向。

東京都攝影美術館,2012。顧錚 攝

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2013。顧錚 攝
澎湃新聞:城市公立機構如果要啟動攝影收藏,應該從什么方面入手?
顧錚:這個也沒有一定之規。作為公立機構,首先應該從自身定位出發確定收藏目標和方針。此外,有沒有機制(比如學術委員會)、建制(比如攝影部或攝影組)和編制(人員編制)和比較確定的預算加以保障,使得收藏得以名正言順地展開。這可能是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才能夠開花結果的實踐。收藏途徑和方式可能也是多種多樣,齊頭并進。既有通過給攝影家做有品質的展覽而展開收藏的方式,也有四處積極活動征集、獲得有質量的收藏,同時不排除根據每年的預算展開持續的購藏活動。這樣多管齊下的方式,在具有比較明確的收藏方針的前提下展開,可能會逐步地、比較好地形成基于各個機構自身定位的有特色的收藏。
澎湃新聞:公立機構得到藏品后,應該如何處理藏品與公眾以及被收藏者之間的關系?
顧錚:公立機構的收藏行為一旦發生,同時發生的是機構與藏品捐贈者和公眾如何建立信任關系的問題。因為公立機構是以納稅人的錢來展開收藏的,那么如果藏品進入到機構里之后,它們的所有權就發生改變,成為公物了。一定程度上說,進入公立機構里的藏品其實就是由公立機構代行保管之職。但現在時有發生的情況是,捐贈者的東西一旦被公立機構收藏,從此石沉大海,甚至不能自由地借出、進一步參加其它展覽。這些情況的存在,會令后來的有意捐贈者在考慮捐贈時變得疑慮重重。我曾經采訪過攝影家尤金?史密斯的夫人,也是攝影家的艾琳?史密斯。她提起過在考慮響應攝影名作《入浴的智子》中的智子母親的要求,從此不再展出這張作品時,如何面對一些公立機構已經購藏了這件作品,但如果因為智子母親的要求而不能展覽,因此傷害了納稅人的利益的兩難困境。這些捐贈者和納稅人的權利和權益問題,需要從立法上來加以保障,從而促進收藏的健康發展。

紐約國際攝影中心庫房一景,2011。顧錚 攝
澎湃新聞:您認為上海是否需要有一座攝影博物館?
顧錚:歷史地看,近代以來的上海是一個各種媒介,尤其是訴諸視覺的媒介和觀看手段一路演進、競爭與發展的重要場所。而攝影在近現代的媒介競爭的歷史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上海的攝影歷史,由于上海的特殊環境,具備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傳奇、影響、積累和厚度。上海攝影的傳奇及其發達歷史,需要足夠的手段與方式舒展開來盡全力書寫與呈現!而一個具有充實收藏的博物館才足夠揮灑書寫上海和中國攝影的歷史,充分滿足書寫上海和中國攝影歷史的客觀要求,也才對得起上海在中國攝影史和視覺藝術史上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從這一點說,上海應該具有與自己的攝影歷史地位相匹配的專業攝影博物館。從國際上看,國際上可以與上海匹敵、媲美的超級大都市,如東京,巴黎、紐約、柏林等,都有各自定位明確、性格鮮明的專門的攝影博物館,收藏攝影作品,推動攝影發展,擴大攝影的影響。
在現代都會的要素配置來說,有無攝影博物館,似乎成為了檢驗一個城市是不是國際大都市的標準。而一個城市有了一座甚至多座攝影博物館,那么一個城市就多了可以讓人進入城市了解攝影和這個城市與國家的關系的place和site,這樣的場所和景點,甚至因為其獨特的魅力而成為城市的文化地標。它既可以視覺地展示攝影的魅力和歷史,同時本身也可以成為城市的景觀和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久而久之,這個甚至幾個攝影博物館本身,也可能和所展覽的內容一同成為了城市的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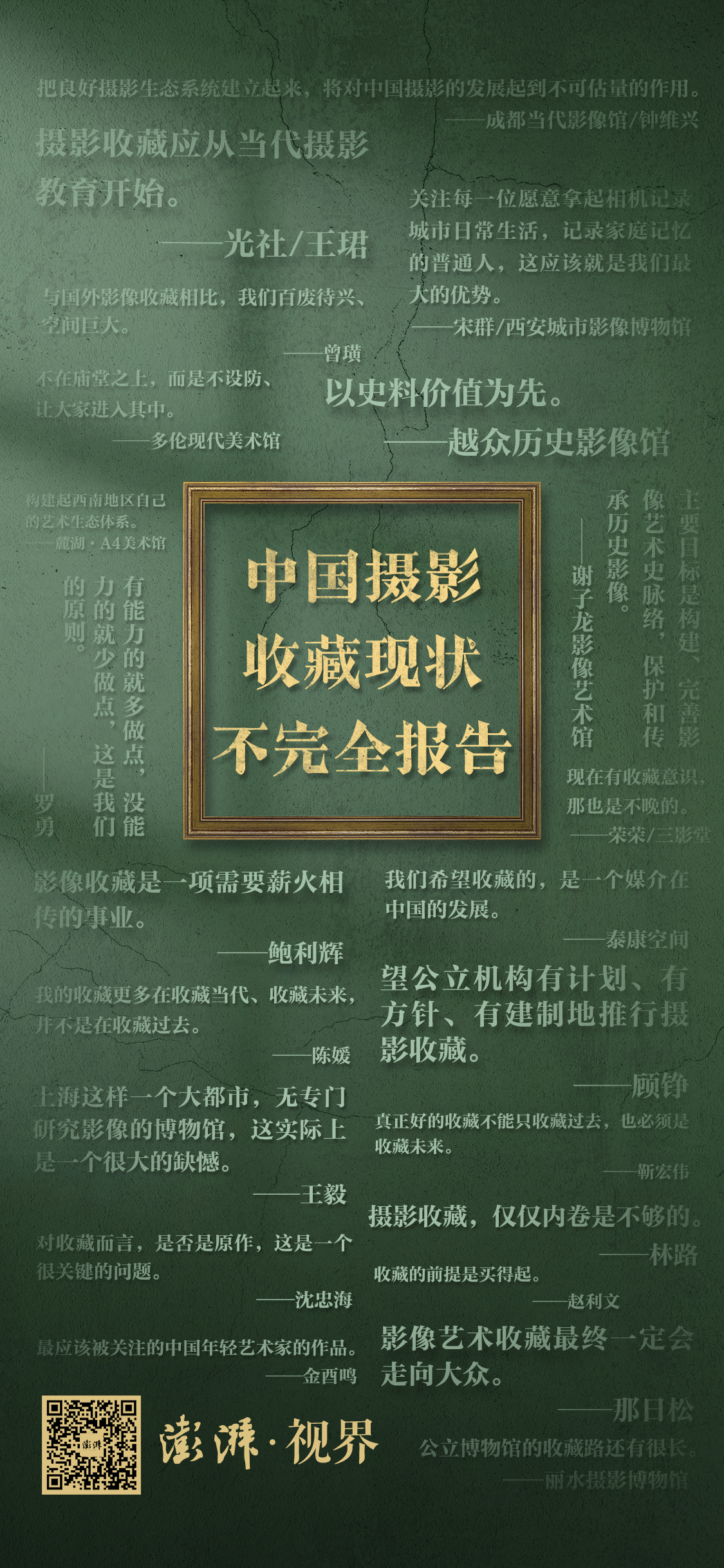
海報設計 澎湃新聞記者 周寰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