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往愛爾蘭文學的島嶼,和遠方命運相似之人漂泊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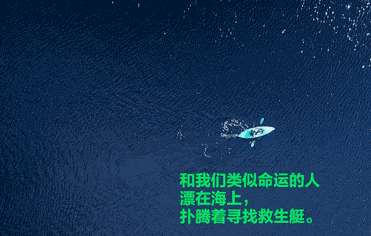
詹姆斯·喬伊斯、奧斯卡·王爾德、W.B.葉芝、薩繆爾·貝克特,談到愛爾蘭文學,我們會想起這些經典作家的名字,近年頗受關注的青年作家薩莉·魯尼也逐漸進入我們的視野里。這個小小的國家其實還有更多文學風景值得我們了解。最新一期的《單讀》來到文學傳統豐厚且依然富有文學活力的愛爾蘭,譯介在本地文學讀者里受到推崇但在中文世界介紹得還很少的、獨具一格的十二位當代愛爾蘭小說家及其作品。
本期特邀曾旅居愛爾蘭、現居英國的作家顏歌和群島圖書出版人彭倫兩位擔任客座主編,在他們看來,這些愛爾蘭作家的寫作關注大時代陰影下漂泊著的個體命運,以文學的眼光進入歷史,將“北愛爾蘭問題”、移民議題和晚期資本主義圖景化為故事背景,刻畫底層勞動人民、每個小人物在歷史洪流中經歷的傷痛,對尊嚴和救贖的渴望。“與此同時,他們也在描繪當代人心靈困境上入木三分,那種在空虛的人生中無從找到自己存在意義的頹喪,那種想要與人相擁卻發現人與人之間無法跨越的隔閡的無奈,我們都是命運相似之人,正在尋找一艘救生艇。”
今天夜讀,帶來顏歌對愛爾蘭文學的閱讀感受和推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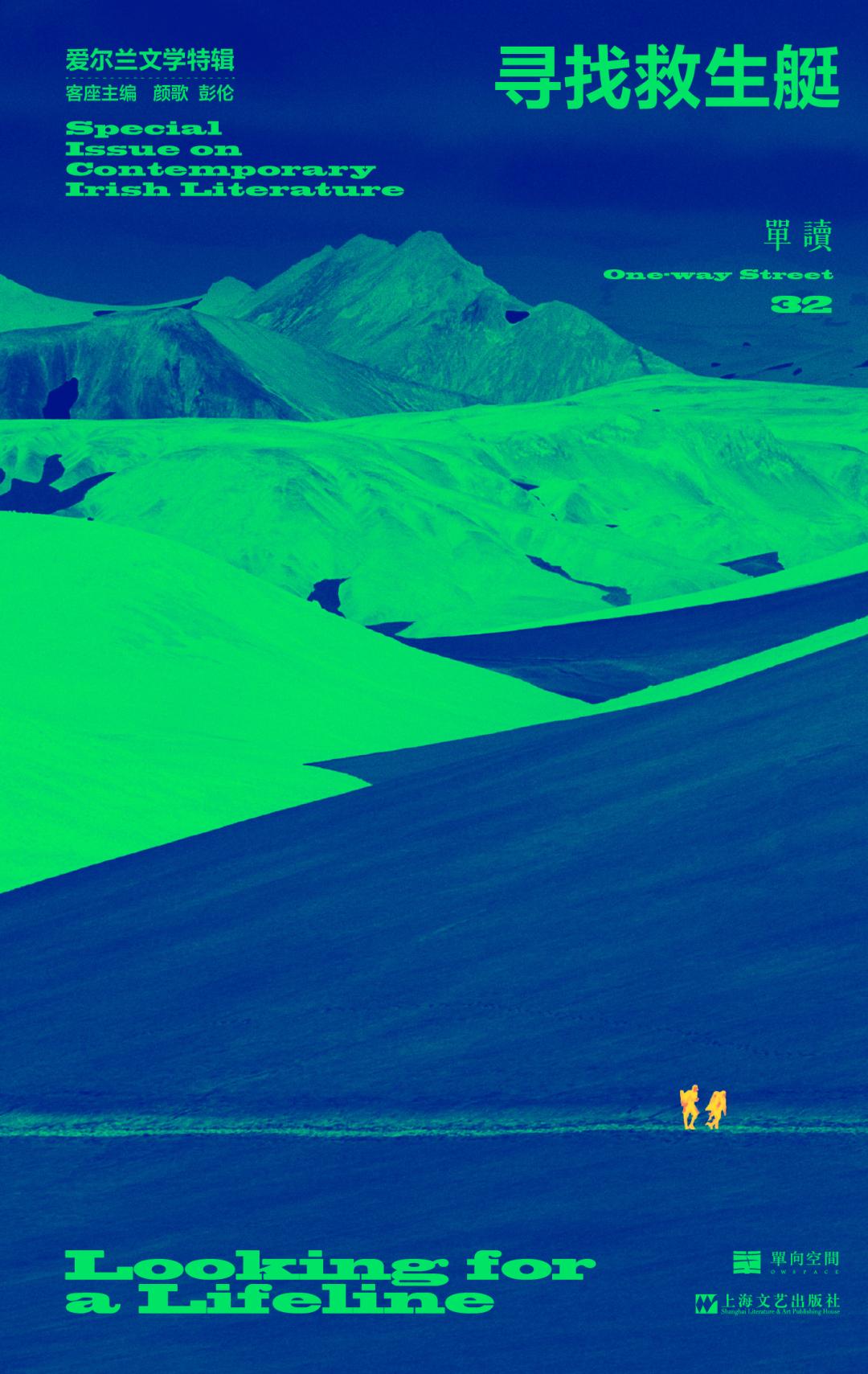
單讀|上海文藝出版社
故事里的世界(節選)
文 / 顏歌
我是在2015年搬到了都柏林以后開始廣讀愛爾蘭小說的,歸根結底,是為了讓自己和身邊的世界發生一些聯系。我寫小說寫了二十多年,讀小說的時間就更久,因此,比起現實世界,文學世界似乎和我的關系更近——如果我無法從文學里進入愛爾蘭,那現實的愛爾蘭對我來說就是虛無縹緲、遠若幻境的。只有拿起書,讀了《死者》(“The Dead”),才覺得阿倫碼頭邊上不再只有荒禿禿的紅房子,反而充滿了小圣誕夜車馬往來的賓客歡笑;讀了《基拉里峽灣》(“FjordofKillary”),才發現梅奧郡酒吧里酒鬼的囈語不再晦澀難解,倒成了末世荒誕的長短句;讀了《歡迎光臨》(“Show Thema Good Time”),才會在每次開長途車路過馬林加時不再抱怨寡淡的風景和索然的服務站,而是去仔細看這空曠的大地和在這份空洞里尋找意義的人們——對我來說,只有通過愛爾蘭的小說,現實的愛爾蘭才變得具體而意味深長,現實中人的話語才音律飛揚。這片土地被剝削和壓迫了多年,這里的人永遠都在苦難里爬行,永遠在懺悔自己的罪,祈求無法降臨的救贖;與此同時,他們又以無與倫比的方式向外敞開著自己,去感受,去表達,滔滔不絕,醉話連篇,詛咒,歌唱,吐出來最是引人捧腹又催人落淚的句子。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詩人的國度,因此,也是短篇小說家的國度—整個愛爾蘭島上到底有多少人在寫作,具體數字不詳,但是作家所占的人口比例一定是驚人地高。

剛剛過去的七月,在西科克文學節(West Cork Literary Festival)上,我在本地酒吧遇到了剛剛被任命為《刺人虻》(The StingingFly)新主編的莉薩·麥金納尼(Lisa Mclnerney)。她跟我講起她來之前終于看完了夏季刊的征稿。這次征稿特別面向之前沒有發表過作品的文學新人。“我本來以為不會有多少稿子,”莉薩跟我說,“你猜猜我們收到多少份短篇小說?”
我搖搖頭。“一千兩百多份。”她說。
而她需要從這一千兩百多份投稿中選出十四篇來發表。“不可能的任務。”莉薩嘆口氣,嘬一口啤酒。
這一次給《單讀》編愛爾蘭文學特輯的任務,雖然不如莉薩的任務那樣不可能,但也談不上輕而易舉。我的想法是選一些新的、之前沒有在中文世界被介紹過,或者相關信息還很少的作家和作品;此外,比起那些因為強化愛爾蘭的刻板印象而在海外得到廣泛傳播的作品,我更愿意選一些在本地的文學讀者里受到推崇的作品——但這樣的選擇思路也可能會帶來一個難題。
“很多愛爾蘭作家尤其喜歡用本地話、土語,甚至自己造些新詞,所以我感覺翻譯起來可能會很有難度,我是應該選一些好翻的,還是就選我喜歡的?”我問彭倫。
“就選你覺得好的,翻譯的問題我們來解決。”彭倫說。

得到了這樣的保證,我第一個就把凱文·巴里(Kevin Barry)的小說放上了我的單子。凱文·巴里是愛爾蘭最具影響力的當代作家之一,他充滿了方言、俗語、粗話的文學表達深深影響了現在愛爾蘭的青年寫作者,也是西愛爾蘭作家群體中的核心人物。
一直以來,我總是偏愛西愛爾蘭的作家。他們的故事總是發生在凄風苦雨的斯萊戈、梅奧、戈爾韋,故事里的人講話總是帶著濃烈的口音,有掙扎,有絕望,有暴力,總是一片似乎要摧毀一切的黑暗,而這黑暗里僅有一絲若有若無卻引人入勝的光亮。凱文·巴里是這樣的,莉薩·麥金納尼是這樣的,科林·巴雷特(Colin Barrett)和約恩·麥克納米(Eoin McNamee)的故事也被這奧克斯山脈下的同一片土地所孕育。
凱茜·斯威尼擅寫超短故事。這個集子里的三個故事是我選出來的,拿去問她要不要取個名,她就說不如叫《三個愛情故事》(“Three Love Stories”)吧,我忍俊不禁。“愛情”這個詞她點得實在是絕妙,充滿了反諷。不用說,她的故事們是借“愛情”之名寫生活的荒誕和人與人之間的不可交流,換言之,是“反愛情”。同樣“反愛情”并有一個絕妙標題的還有露西·考德威爾(Lucy Caldwell)的《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惡》(“All the People Were Mean and Bad”):疲憊的母親、總是缺席的丈夫、令人窒息的長途旅行、哭鬧的女兒和懷著不明善意的陌生男人,第二人稱的敘事,正像是孤索的女主角在喃喃自語——讀這些故事,我總是忍不住想起一個王小波式的問題:到底人生中的相遇是看似毫無意義,實則意味深長;還是表面上充滿深意,本質卻毫無意義?
妮科爾·弗拉特里(Nicole Flattery)的《歡迎光臨》和溫迪·厄斯金(Wendy Erskine)的《格洛麗亞和馬克斯》(“Gloria and Max”)從不同的側面來討論這個存在主義的問題。這兩個故事看似說的是個體人物的相遇,實際上又各自映著大時代的陰影:在弗拉特里的故事里,是晚期資本主義的都柏林;在厄斯金的故事里,是“北愛爾蘭問題”之后的貝爾法斯特。

貝爾法斯特,光是這城市的名字本身就充滿了緊迫和張力。“有人說我們這些人只會寫‘北愛爾蘭問題’,但只要是一個北邊的故事——不管故事里面到底發生了什么——哪兒可能和‘北愛爾蘭問題’無關呢?”我的一個北愛爾蘭的作家朋友有一次對我說。
“北愛爾蘭問題”是愛爾蘭島上一個巨大的傷口,這傷口被切得太深,腐爛、疼痛得太久了,就算是在《貝爾法斯特協議》之后被打了麻醉劑、縫合了起來,才剛剛要開始愈合,又重新被脫歐的種種波瀾撕扯開,汩汩流血。
路易斯·肯尼迪(Louise Kennedy)的《剪影》(“In Silhouette”)寫的就是這樣一個滿是鮮血的故事,一個家庭的破滅,從一個女孩到一個女人,失去兄長,尋找一份似是而非的愛情。第二人稱、現在時,把過去和現在,倫敦和北愛爾蘭織成了支離破碎又交錯相連的一卷。
同樣是一個破碎家庭的故事,丹妮爾·麥克勞克林(Danielle McLaughlin)的《部分獲救者名單》(“A Partial List of the Saved”)則像是一出輕喜劇,然而,當這輕喜劇發生在北愛爾蘭,卻有了更多的意味。故事里面沒有人死去,但他們的旅途的背景中卻滿是亡靈:泰坦尼克號的遇難者;被鎮壓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英國部隊殺掉的愛爾蘭人,他們的銅像在鄉道邊立了將近一個世紀。也是在貝爾法斯特,簡·卡森(Jan Carson)的筆下栩栩如生的是這座城市里的勞動階級和底層人民,他們都在身體和精神的疾病里煎熬著。他們找到的救贖是一個從波蘭移民來的姑娘,傳說,跟在這外國姑娘的身后跳入泳池里,就會有奇跡發生。

在這輯的最后一個故事里,我們將回到都柏林,卻發現梅拉圖·烏切·奧科里(Melatu Uche Okorie)所寫的都柏林和我們從凱茜·斯威尼那里所讀到的那個城市大相徑庭。一群來自非洲各個國家的難民聚集在都柏林的臨時安置所里,煎熬、焦慮,而又無比鮮活。奧科里這個“新愛爾蘭人”作家在《小旅館的這日子》(“This Hostel Life”)里一開頭就干了件非常愛爾蘭的事——拿自己人開涮:“你知道吶些個尼日利亞人的,他么時時刻刻都想干仗。”像所有其他卓越的愛爾蘭作家一樣,在奧科里的故事里,英文作為文學語言被拆開解構,又以有機的、地道的方式組合,再響起來,讓我們聽到眾生的聲音,各有特色、輕重、鄉音,相互間頂嘴、罵架、揶揄,通篇喧雜卻又聲聲入耳,句句都寫在又痛又深的現實里。
2017年的夏天,我推著剛剛滿月的兒子到都柏林卡布拉(Cabra)的一間診所,準備給他打預防針。在候診室里等待的時候,我的手機里忽然收到了一封郵件。寫郵件的人是露西·考德威爾,她說她從《愛爾蘭時報》的文學編輯那里得到了我的郵箱,希望我不要介意她冒昧地來信,她說她正在著手編輯下一年的費伯愛爾蘭新小說集(Being Various:New Irish Short Stories),準備收入總共二十一位現在愛爾蘭文學界的代表性作家,她又接下去說:“作為小說集的編輯,我想要重新思考‘愛爾蘭作家’到底意味著什么,也很想去拓寬這個概念,這概念應該包含出生在愛爾蘭但成長于別處的作家,從別處來但選擇以愛爾蘭為家的作家,也包括那些不知怎的發現他們自己就住在了愛爾蘭的作家。因此,我特別希望你能給這小說集寫一篇小說。”——當時,我一手抱著不斷扭動的嬰兒,另一只手握著隱隱發燙的移動電話,不確定自己是否因為過度缺乏睡眠而產生了幻覺。“‘愛爾蘭作家’到底意味著什么?”好幾年以后,編著這一期愛爾蘭文學特輯,我的腦子里回響起來露西當時問的這個問題。我應該以什么準則、什么要求——如果我有這個資格的話——去選擇收入這一輯的作家和小說呢?

▲ 電影《風吹麥浪》
在我看來,愛爾蘭作家都和英文有著復雜的關系,從喬伊斯開始,他們就總要顛覆和解構這原本來自殖民者的語言,把它變得本土,古怪,自我,滿是新意;愛爾蘭作家們都是創造聲音的高手,敘事聲音也好,對話也好,句句都有棱有角,栩栩如生;愛爾蘭的作家愛幽默和諷刺,不管故事的底色如何苦難壓抑,他們永遠都可以苦中作樂,讓你大笑出聲;愛爾蘭作家也很會抒情,雖然他們一般不輕易這么干,但一旦抒起情來,一定是要“山無陵,天地合”的——多年了,每次想起《死者》的結尾,我都要流下淚來。
歸根結底,愛爾蘭的小說家和天下所有的小說家一樣,其實是最我行我素的。當小說家進入他們的故事里,開始寫作的時候,一切別的事物,包括他們自己在內,都變得不重要也不存在了,唯一要緊的只是眼前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風景、世界不斷擴大,充實著物品的細節、聲音的余韻、植物的觸感,將最終覆蓋并取代小說家肉身所在的、所謂真實的世界。現在,是進入故事里的世界的時候了。
原標題:《前往愛爾蘭文學的島嶼,和遠方命運相似之人漂泊旅行|此刻夜讀》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