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靠放血來退燒、治嗓子疼?不靠譜,別信
原創 李清晨 果殼
很多人近期都經歷了發熱,除了口服退熱藥物這個措施之外,可能是治病心切吧,有些人也在情急之下嘗試了別的手段,比如放血療法,甚至有些官 V 也跟風做了推薦。
大家無須訝異至今仍有人會覺得放血療法對退熱有用,因為這與人類的思維定式有關,很多人也不了解大部分疾病的一般規律。
靠放血治發燒,恐怕得不償失
就發熱來說,根據體溫數值曲線的不同形狀,可大致分為稽留熱、弛張熱、間歇熱、波狀熱、回歸熱、不規則熱等熱型。
簡單理解就是一個人即使正處在發熱的狀態中,他的體溫數值也不大可能恒定在某一數值一動不動,如果在病人體溫恰好剛要進入低值之前,針對病人實施了某種措施——比如放血——那就很有可能讓人認為是該措施導致了病人體溫的下降。

發熱的時候,體溫很可能在坐過山車丨pixabay
再加上放血療法本身帶來的安慰劑效應,讓病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期待中的關心和照顧,這都能讓病人產生癥狀緩解、病情減輕的感覺。
但放血療法畢竟是有創操作,尤其是有些人是在手指尖放血,這是人類神經末梢分布最密集的區域之一,不小心傷到都會痛得人立刻縮手(這個反射甚至可以不經過大腦就能完成),更別說有意去穿刺和切割制造的疼痛了。

想想都疼丨pixabay
雖然說所有的治療方式都有其固有的風險,但為了一種根本不可靠的治療方式,承擔這樣劇痛的代價,實在得不償失。
更何況,很多人是在毫無醫學基本功培訓的情況下在家中進行放血操作,指望著他們非常嚴格地遵循無菌操作也不太現實,因此,在疼痛之外,還要讓病人承擔可能出現感染的風險,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放血療法歷史很長,各地都有
在現代醫學成熟以前,放血療法很有可能是被人類應用最久的治療辦法。
在我國漢代成書的《黃帝內經》中記載有:“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瀉有余,補不足。”到了唐代,孫思邈在《千金藥方》中也對放血療法有所闡述,直到后來的歷代醫家,逐漸完善了放血療法。
但中國古代進行的放血療法一般令病人出血較少,一般也就 3~5 滴,至多不超過 10 滴,這與古代西方的放血療法看起來好像區別很大。
按照古代西方的醫學理論體系,很多疾病的原因都是身體內血液超負荷,所以治療方式那就是大量放血。翻閱西方醫學史,有的時候難免會生出疑問,到底有多少人其實不是病死的,而是被放血療法提前害死的呢?

失血過多,會死丨pixabay
比如說著名作曲家莫扎特和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均極有可能是被放血療法提前給送走的。
同樣是放血,為什么古代中國和西方的放血療法會有如此顯著的不同?
這可能與他們對血液的不同認識有關。
在 1628 年威廉·哈維提出血液循環學說之前,古代西方的醫學理論中占據主流的是血液潮汐學說,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血液產生得很快,即使不放血也會被人體很快消耗掉,所以,他們放起病人的血來,也是大刀闊斧不怎么心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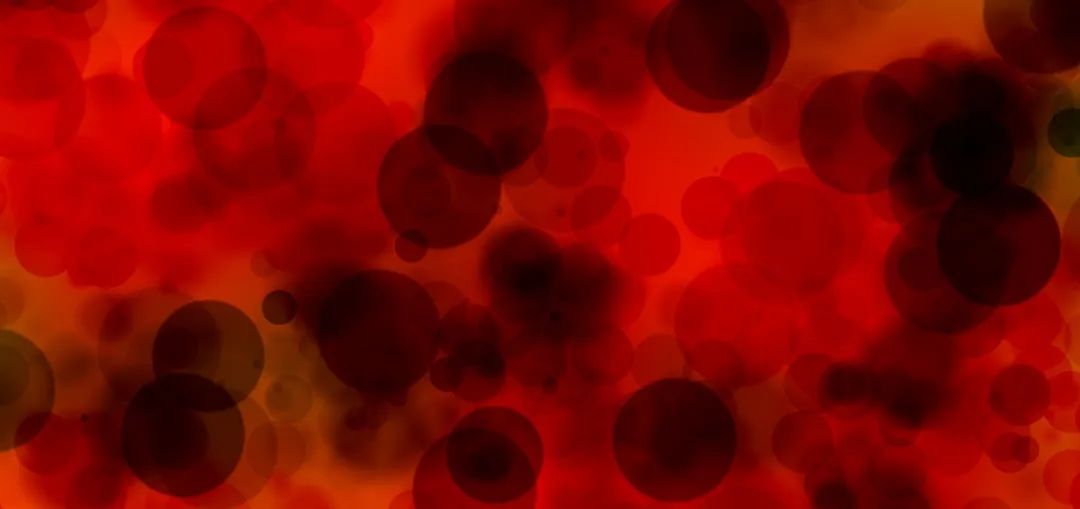
pixabay
中國古人雖然沒有像哈維一樣提出那么精準的血液循環理論,卻也猜到了血液很可能是循環的。
《黃帝內經》中說:“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
當時的學說雖然并未詳細闡明心臟的泵血機制,但至少避免了大量放血對病人的傷害。
現在,我們有更好的方法應對發熱
隨著醫學的進步,尤其是微生物學和抗生素領域的進步和臨床試驗方法的普及,逐漸有一些設計嚴謹的對照試驗證明,放血療法非但對發熱病人無益,還會增加病死率。這對流行了數千年的放血療法來說,真是兩面夾攻釜底抽薪的打擊。
比如英國醫生Alexander Hamilton在1816年研究放血療法時,將366名患病的士兵隨機分為3組,一組病人接受放血療法,另外兩組接受其他方法治療,這3組士兵的基本條件大致相同。結果是不放血的兩組分別有2例和4例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療法的一組死亡35例。
大約同時期的法國醫生Pierre-Charles-Alexandre Louis 利用大樣本隨機對照試驗的方法證明,放血療法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無效的。
但老醫生們是沒有那么容易認錯的,他們尤其不愿意承認,有些病人事實上就是被他們治死的,他們堅持說:“我們遵從的是最佳觀點,我們認為自己沒錯,所以我們是清白的。”(語出[美]道格拉斯·斯塔爾《血:一種神奇液體的傳奇史詩》)
傳統是有慣性的,有些觀念并不會隨著科學理論的進步自動消失。所以,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在眾人的恐慌里,我們看到放血療法再次沉渣泛起是毫不奇怪的。
孔多塞在《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指出:按照我們能力發展的普遍規律,我們的進步的每一個時代都是要產生某些偏見的,但是它們卻遠遠延伸到了它們的誘惑力或它們的領域之外;因為人們仍然保留著自己幼年時的種種偏見、自己國家的和自己時代的偏見,哪怕是在已經認識到了全部必要的、足以推翻它們的真理很久以后。
以現代醫學對發熱的理解程度,理論上早就不應該再讓任何形式的放血療法有存在的空間了,但我們還是非常遺憾地看到這類療法雖已不再是主流,卻也沒有徹底消失。

圖源:圖蟲創意
也許只要醫學尚不能徹底根除疾病,不能100%令所有病人對治療滿意,就一定會有一些病人希望奇跡出現,尤其是當醫生忽略了疾病治療過程中科學之外的社會心理因素,就會有病人轉而向神秘主義、向古老的治療方式求助。
作者:李清晨
編輯:odette、高奇奇
封面圖來源:pixabay
一個AI
希望大家去血液中心放(康復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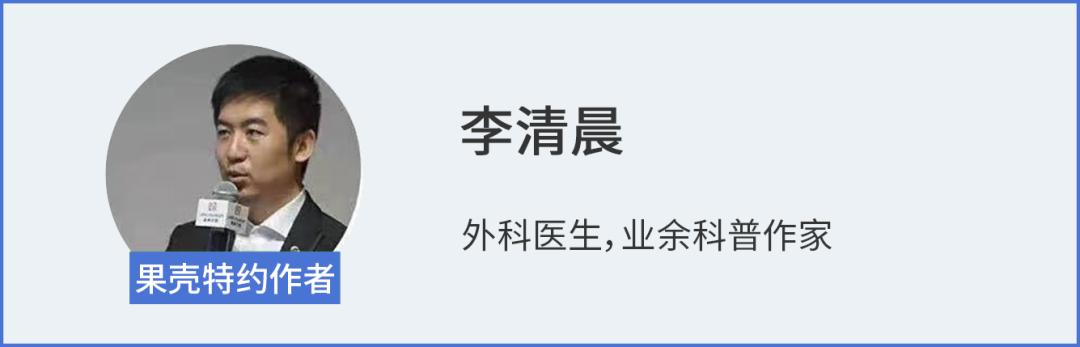
參考文獻
[1] Milne I, Chalmers I. Alexander Lesassier Hamilton's 1816 report of a controlled trial of bloodletting. J R Soc Med. 2015 Feb;108(2):68-70. doi: 10.1177/0141076814566587. PMID: 25721115; PMCID: PMC4344449.
[2]Morabia A. Pierre-Charles-Alexandre Louis and the evaluation of bloodletting. J R Soc Med. 2006 Mar;99(3):158-60. doi: 10.1177/014107680609900322. PMID: 16508057; PMCID: PMC1383766.
本文來自果殼,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