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科林·瓊斯談恐怖統(tǒng)治與大眾政治

科林·瓊斯(章靜繪)
科林·瓊斯(Colin Jones)是英國學術院成員,2009-2012年英國皇家歷史學會主席,倫敦瑪麗女王大學歷史學教授,著名的近代早期法國和法國大革命史家。瓊斯擅長研究長時段歷史,格外關注醫(yī)學史,他撰有《舊制度和大革命時期法國的醫(yī)院和護理業(yè)》《近代早期法國的醫(yī)學世界》《從路易十五到拿破侖的法國》《十八世紀法國的笑容革命》等。其中尤以《巴黎傳》(2004)為著,該書獲英法學會的伊妮德·麥克列奧德獎,已有中文譯著。2012-2015年,科林·瓊斯獲得利弗休姆研究基金,其研究重心轉移到恐怖統(tǒng)治上,尤其是熱月政變事件。2021年11月,瓊斯出版了《羅伯斯庇爾的倒臺:革命巴黎十二時辰》。該書為我們理解熱月政變、恐怖統(tǒng)治的性質乃至大眾政治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加之獨特的按小時分章的敘事結構,贏得了林·亨特、大衛(wèi)·貝爾、彼得·麥克菲等一眾大革命史家的稱贊。
從近代早期法國的歷史到法國大革命史,從醫(yī)學史到經(jīng)久不衰的恐怖統(tǒng)治研究,從長時段歷史再到微觀史,科林·瓊斯的研究重點、視角和方法都有了不小的轉變,但其中也有瓊斯一以貫之的主旨和歷史關懷。為了了解瓊斯的學術經(jīng)歷和史學旨趣、進一步理解他的史觀、研究方法和史學思想,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張弛和博士生葉樹彬應《上海書評》之邀對瓊斯進行了一次書面采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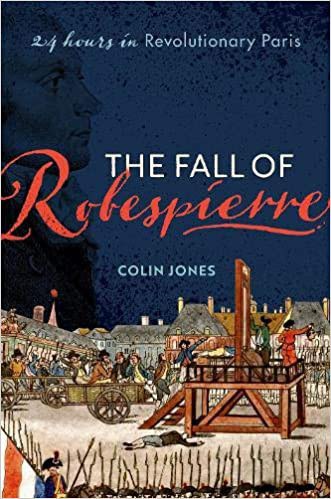
Colin Jones, The Fall of Robespierre: 24 Hour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021, 480pp
我注意到,您以長時段的歷史研究見長,尤其是在慈善、笑容和巴黎城等特別領域上的研究。但近二十年來,您轉而投身于法國大革命史這一充滿爭議且已被眾多史家深耕過的史學領域。為何您最開始會選擇研究近代早期法國的慈善史,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延續(xù)了這種研究風格?此后,為何您轉變了研究重心?
瓊斯:我出版的許多作品都涉及長時段的歷史。例如,我涉足了從最早的時代以來的法國和巴黎歷史,以及十八世紀的法國史,我還與人合著了一本關于十六至十八世紀法國醫(yī)學的著作。這歸因于我早年受到了費爾南·布羅代爾作品和年鑒學派的浸染。然而,我的出發(fā)點仍是法國大革命,我的博士生導師正是研究“革命軍”(armée révolutionnaires)的杰出史家——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我的博士論文關注的是大革命期間窮人救濟的起源,旨在估量大革命對窮人生活造成的影響。這一我們稱之為恐怖統(tǒng)治的時段,見證了激進的社會福利政策的成型,正如我的博士論文和首部著作所示。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著手研究熱月九日,只是通過聚焦于“恐怖統(tǒng)治”而回到了我熟悉的領域。
具體來說,在《偉大的民族:從路易十五到拿破侖的法國》中,我留意到,您是通過前熱月時期的政治和熱月神話的角度來審視熱月九日的,這種視角所扮演的角色正像您后來所稱的“灰姑娘”——事件自身未受到應有的關注。但之后,您更加注重熱月九日這一事件本身。對此,我不禁想問,是什么促成了您史觀的變化?為何您會選擇研究這一特殊時段的革命歷史并將之作為一個研究計劃?
瓊斯:熱月九日通常被描繪為大革命關鍵的一天——如同1789年7月14日或1792年8月10日——因此,將之作為一個研究主題,無須證明,更何況熱月九日向來屢遭忽視。的確,當我開始為了我的著作而著手研究時,我非常希望保持相同的敘事框架,保留我在《偉大的民族》里做出的大部分分析。但我意識到,熱月九日這一天通常都是從羅伯斯庇爾及其國民公會的敵人這兩個角度進行敘述的,而我需要將巴黎民眾納入其中。當我開始閱讀卷帙浩繁的熱月九日文件記錄時,我意識到這本書需要截然不同的分析和敘事。將這一天視作二十四小時內緩慢展開的復雜進程,需要緊密甚至一絲不茍的探查追蹤,這看來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我決定冒風險,以深描的敘事方法、按小時分章的結構,在二十四章內描繪這一天從午夜到午夜的歷史。
迄今為止,關于這一時段的大革命歷史,您已完成了數(shù)部作品,包括兩篇關于庫爾圖瓦報告和熱月九日民眾冷漠態(tài)度的論文,一本聚焦于羅伯斯庇爾倒臺的著作。這些作品構成了您研究計劃的一部分,您是否可以向我們解釋一下,您是怎么構想和組織這一研究計劃的?
瓊斯:我原本的計劃是以著作的形式來描述這一天的歷史。但是,當我意識到著作將會采取的獨特形態(tài)時,我認為在期刊文章中發(fā)表我的研究,以獲得更為廣泛的學術受眾,是明智之舉。在第一篇文章中(《美國歷史評論》,2014年),我試圖表明,巴黎民眾對羅伯斯庇爾的命運漠不關心這一史學共識是錯誤的:恰恰相反,他們滿腔熱情地投入到推翻羅伯斯庇爾的運動中。在第二篇文章中(《法國歷史研究》,2015年),我試圖證明,國民公會與巴黎民眾在熱月九日這一天聯(lián)合推翻羅伯斯庇爾,這一史實在接下來的一年內遭到了嚴重的篡改。我明白,我計劃撰寫的著作不會為這一點留下位置,但它也是我分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
在《羅伯斯庇爾的倒臺》中,您認為熱月九日不意味著恐怖統(tǒng)治的結束;您認為“恐怖”是后人創(chuàng)造的時代錯置的術語,因而拒絕使用“恐怖”這一詞。在這種情況下,您如何看待以下觀點:恐怖統(tǒng)治可能只是一個史學現(xiàn)象,而非一個歷史上存在的統(tǒng)治體系——正如米歇爾·比亞爾和瑪麗薩·林頓最近在他們的新書(《恐怖統(tǒng)治:法國大革命及其惡魔》)中所說的?
瓊斯:正如讓-克萊蒙·馬丹極其有力論證的那樣,“恐怖統(tǒng)治”這一術語作為攻擊共和二年政府的手段,只在熱月九日之后才出現(xiàn)并流行開來。我的研究方法正在于試圖從這一天的進程來觀察熱月九日,不高估后來對這一現(xiàn)象的解釋。我關注的是行動者、行動、意圖和后果。結果也迅速明朗了:在熱月九日,“恐怖統(tǒng)治”完全不存在于任何人的心中。因此,我排除掉了這一術語,我覺得我的決定是正確的。史家們傾向于認為,“恐怖統(tǒng)治”有代理者——我在書中的觀點是:個人和機構確有其代理者。革命政府、或是政府委員會(救國委員會,公安委員會)的確施行了恐怖政策——但這并不是1793-1794年這段時間內政府決策的決定性特征,比如,它忽略了軍事行動和福利政策。或許,主張“恐怖統(tǒng)治”存在的觀點在史學研究中已然根深蒂固,難以徹底消除,但我認為,用引號來使用這一詞或許是有用的。
既然熱月九日已不再是一個如“灰姑娘”那般的角色,而是如您所說的,大革命中最為典型的巴黎革命日,那我們該如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法國大革命的這一天?它仍然標志著法國大革命典型政治文化的結束嗎?
瓊斯:熱月九日這一天經(jīng)常被認為是“恐怖統(tǒng)治的終結”。如果我前述的回答是無誤的話,那便不能認為這一天終結了“恐怖統(tǒng)治”,因為“恐怖統(tǒng)治”在當時尚未存在于人們的腦海中。同樣,這一天也沒有瓦解掉施行恐怖政策的革命政府。熱月九日之后,革命政府仍在繼續(xù)施政。在國民公會的會議中,塔利安先行發(fā)起了主動攻擊,隨后政府委員會的成員主導了攻擊羅伯斯庇爾的行動。這是意在除掉羅伯斯庇爾的一天。但推翻羅伯斯庇爾導致的后果使得結束恐怖統(tǒng)治成為可能。熱月九日之后,由于某種滑坡效應,對羅伯斯庇爾轉的攻擊變成了對共和二年革命政府政策的攻擊。這正是我在上述的第二篇文章中試圖解決的問題——但這是一個宏大的議題,可以做更多的分析。
我注意到,您的研究方法下列史學流派頗為不同:法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社會史和修正主義、后修正主義史家的政治話語分析。它更多的是一種偏重社會和情感分析的微觀史路徑,一種如您所界定的“情境式”視角。您為何會以這樣一種歷史視角來重新詮釋一場經(jīng)典的歷史事件?
瓊斯:從其余波至今,熱月九日一直以來都充滿著爭議。我的研究方法在于試圖解釋隨之發(fā)生的事情,以及探尋真正發(fā)生了什么。這種方法并不排斥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或后修正主義的視角和方法,不過,或許這種檔案導向的實證主義對于一名英國史家來說更易于接受,這點我不太清楚。但我希望我的論述能夠促進對革命政府歷史的重新思考和再理論化。可以說,我的論述是通過“從下向上看”和“從檔案里往外看”的視角構建起來的,它會對現(xiàn)存的論述提出嚴正的質疑,無論它們的角度如何。
至于情感史,我試圖明確的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在熱月九日當天的下午和晚上,每一個巴黎人都迫不得已要在支持羅伯斯庇爾和巴黎公社或是支持國民公會之間做出選擇。他們也明白,它們的命運系于正確的選擇之上——如果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那就會被送上斷頭臺。事實上,不少于一百名的羅伯斯庇爾支持者在當天便是這么做的,他們在熱月十日至十二日被處決了。要描述這一天的歷史,怎么可能不考慮這一天無處不在的情緒呢!但是,如果說個人做出的決定是高度情緒化的,那總體而言,它仍基于一種極為理性的考量,此即權衡他們自身的命運和大革命的未來,以及現(xiàn)行政治體制中何種因素才是他們最為珍視的。他們一致選擇了法治,選擇支持一個看起來將會贏得戰(zhàn)爭且會履行福利承諾的政府(盡管仍以恐怖為武器),這個政府的背后是一個通過男性普選建立起來的國民議會。他們拒斥了與巴黎公社相連的起義傳統(tǒng),而在當時巴黎公社已與羅伯斯庇爾過從甚密。羅伯斯庇爾對未來的計劃對于大多數(shù)民眾來說晦澀難懂,連我也自己也是這么覺得的!
法國左派向來有一股尊崇羅伯斯庇爾的思潮(但法國左派內部也有一支不同的聲音,它強烈批評羅伯斯庇爾,認為羅伯斯庇爾在原則上走上了拋棄大眾民主的道路)。比起英美學界典型的反羅伯斯庇爾主義,我對這一股思潮深感同情。在我的研究最后,我自己的感受是,盡管羅伯斯庇爾擁有許多令人欽佩的品質,盡管他不斷地呼喚人民,他依然讓人民十分失望。可悲的是,在隨后的熱月反動時期,這一點同樣發(fā)生在了推翻他的人身上。
您的研究基于那些數(shù)量極為豐富的熱月九日報告,這些報告是保羅·巴拉斯下令收集的,但各派史家?guī)缀醵紱]有留意到。我很好奇,您是怎么在米什萊所說的“手稿迷宮”中找到這些材料的?您又是如何在原創(chuàng)性研究中利用這些材料的?
瓊斯:那里有極其豐富的材料供史家使用,但這些材料從未被充分利用過,即使它們的存在眾所周知。首先是國民公會委任的、由代表庫爾圖瓦負責執(zhí)行的熱月九日官方調查報告。其次還有大約一百五十份來自巴黎四十八個區(qū)的報告,涉及熱月八、九、十日的關鍵活動,這是熱月九日晚統(tǒng)領國民公會武裝力量的巴拉斯下令收集的。此外,得益于阿爾貝·索布爾和雷蒙德·穆尼耶的巴黎各區(qū)激進分子名單(《巴黎各區(qū)人員目錄》,1985),我在檔案中找到了至少是涉及當天部分時段的個人陳述,并查閱了這些材料。最終,我還有數(shù)百份真正意義上的微觀敘事材料,它們讓我得以拼起關于這一天的模糊圖景——盡管考慮到時間這一因素,它更多的是一部諸多事件組合成的電影,而非單一的靜態(tài)鏡頭。
在閱讀您的作品時,我發(fā)現(xiàn)您的研究有三個鮮明的特征:堅實的史料基礎、偏浪漫主義的寫作風格、深刻的反思。其中浮現(xiàn)出了儒爾·米什萊舊式但依舊經(jīng)典的大革命研究。您也引用了很多米什萊的文字和論據(jù)。同樣,您對索布爾的大革命民眾運動研究的批評,也讓人看到了米什萊批評路易·勃朗的影子。從這點來看,您的研究是否受到了米什萊的啟發(fā)?我們能否認為,在你們二者的研究間,存在一種延續(xù)性?
瓊斯:不僅僅是米什萊,我還要引用馬克·布洛赫,后者曾說道:歷史學家就像是食人魔,其獵物應當永遠都是人肉!無論如何,我從米什萊的感知里尋得了奇異的靈感:當他埋頭于積滿灰塵的大革命檔案中時,他仿佛看到民眾從墳墓中站了起來。當我在研究熱月九日這一天時,我的觀點與米什萊產(chǎn)生了共鳴——巴黎民眾以一種相當新穎的、不同于以往史家所用的方式在講述他們的故事。在我的書中,我盡力忠誠于他們的故事。
我對阿爾貝·索布爾在共和二年無套褲漢運動研究上闡述的觀點深表敬意,盡管如此,他的杰作仍誤導了史家,讓大家以為在巴黎民眾中,無套褲漢是唯一值得認真考慮的政治角色。在我的書中,我從米什萊的包容性角度來看待巴黎民眾,我只將無套褲漢視作一個更廣大現(xiàn)象的一部分。
您對熱月九日及其余波的研究,細致入微,出類拔萃,其中您非常注重民眾在歷史中的位置。對此,我想知道您的研究在熱月九日史學中的位置,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熱月九日研究,又在多大程度上重新詮釋了法國大革命?此外,您認為對于熱月九日,還有許多地方值得進行研究嗎?或者,我們是否能最終斷言,“熱月九日已經(jīng)結束了”?
瓊斯:如果我的書成為下一代人必讀的經(jīng)典著作,我會感到很高興。但拭目以待吧!關于大革命在這一天結束了的說法被夸大了!如果史家們在讀完我的著作后,感到需要重新審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包括“恐怖統(tǒng)治”的性質、民眾運動、巴黎的公共輿論狀態(tài)、大眾政治的本質——這的確恰好是以羅伯斯庇爾為代表的,我也會感到欣慰。
1958年,索布爾出版了他研究無套褲漢的博士論文。1962年,尤爾根·哈貝馬斯出版了他關于公共領域的著作——盡管這一著作歷經(jīng)數(shù)十年,才成為史學主流。我想盡力做到的,是將這兩項研究結合起來,運用到大革命中,而不僅僅局限在哈貝馬斯的主題——啟蒙運動中。索布爾有時在文中會透露出某種觀點,即巴黎民眾只在1789年才發(fā)現(xiàn)了政治——但正如我已說過的,我感覺到,無套褲漢的所思所行無法代表巴黎民眾的政治觀點。1794年巴黎的公眾和公眾輿論,的確存在。
眾所周知,在法國大革命研究領域,英國有一出眾的分支。最開始批評法國大革命經(jīng)典詮釋的,便是英國的修正學派史家,盡管他們很快便被后修正學派史家蓋過了鋒芒。自那之后,已過去了許多年。我很想知道,英國的大革命史研究現(xiàn)狀如何?您的研究可以歸入這一分支嗎?
瓊斯:我不認為英國存在一個自主的、有著獨特研究路徑且對學界有巨大影響的大革命史家群體,對此,我感到些許的難過。最好還是將我們歸入到整個英語學界——特別是要考慮到,相比之下,美國有眾多積極熱忱的大革命史家。有許多史家在英國接受訓練,以練就一個更堅實的檔案工作基礎(在英國,大革命檔案就只有一列“歐洲之星”之遙!),也有許多史家去到了美國,以便更好地沉浸在思想史和理論議題的氛圍之中。即使如此,仍有許多例外。我便是在“從下向上看歷史”思潮時接受的訓練,意圖成為一名社會史家,但我對文學史、文化史和醫(yī)學史也有著強烈的興趣。一直以來,在研究方法上,我尤為不拘一格;在選題上,我也頗顯怪異。我試圖向所有的史學流派學習和取材,包括你談到的以及其他流派,但是,我當然也對它們保持著高度批判的態(tài)度。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