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本《使女的故事》,不足以概括她
原創 宗城 硬核讀書會

《使女的故事 第二季》劇照。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現在對于中國的讀者來說并不陌生。《使女的故事》原著在劇版走紅后成為暢銷書,阿特伍德的名字也傳遍了大江南北。但多數人不了解的是,反烏托邦題材只是阿特伍德作品的冰山一角。
她的創作不拘泥于任何形式、題材,她曾出版過詩集、寫過現實主義的小說,她的評論集也充滿了智慧的閃光。
阿特伍德儼然已經是這個時代的記錄者,這也是她的作品值得被銘記的原因。看見這個世界的殘缺,并把它記錄下來,阿特伍德認為,這是每一個個體都能做到的事。
?作者 | 宗城
?編輯 | 王亞奇
1939 年11 月 18 日,時值加拿大一年一度的體育盛會“格蕾杯”足球賽后不久,整個世界正面臨著籠罩上億人的戰爭陰云,法西斯在歐洲加速進軍,被軍國主義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于兩年前制造了南京大屠殺,印度、東南亞、越南、非洲、伊比利亞半島也深陷在昨日世界消失的恐懼中。而北美是一片相對寧靜的土地,風暴降臨的前夜,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來到塵世。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名字“瑪格麗特”與媽媽重名,為了區別開來,她被家人昵稱為佩吉(Peggy)。
阿特伍德曾說,她有兩個名字,所以有雙重身份,瑪格麗特負責寫作,而佩吉負責其他的一切。
分身寫作,可以作為理解阿特伍德的鑰匙。她寫作勤懇,想象力豐富,大膽地進行不同體裁的文學實驗。在阿特伍德的作品里,讀者既能看到精靈、哥特、女巫、靈性寫作的一面,也有正面強攻型的女性書寫與政治寓言,還有一些輕快的語言實驗、懸疑、科幻和反烏托邦,阿特伍德仿佛擁有一個巨型的胃,吞吐著大量素材,當她榮獲全美書評人協會獎的終身成就獎時,授獎詞的一段話頗具有概括性:“她不是一個女人,而是20個女人、30個女人。作為作家,她擁有那么多不同的聲音。”
作為一位全能型作家,阿特伍德的創作涉及小說、詩歌、戲劇、評論、漫畫、音樂、時尚,她曾憑借詩集《圓圈游戲》獲得加拿大總督文學獎,還為一首名叫《弗蘭肯斯坦怪物之歌》的搖滾樂寫過歌詞,與此同時,她積極參與公共議題,為性別暴力受害者發聲,她創作了《為被謀殺的姐妹而歌》;身份政治與辯論自由的議題發酵時,她與J.K.羅琳、福山等人聯名簽署了呼吁辯論自由的“公開信”;多年來,阿特伍德沒有說為了愛惜羽毛、營造作家的神秘感,就放棄對于爭議話題的介入。

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圖片源自紀錄片《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筆耕不輟是為力》

新世界的推演者
如今,她最知名的作品是反烏托邦小說《使女的故事》,但她早期其實是一位詩人,迷戀神秘主義、泛靈情結和中世紀藝術風格。
《圓圈游戲》展現了她隱喻的天賦,這部詩集的文學性強于她的許多小說,比如早期的《可以吃的女人》《人類以前的生活》《神諭夫人》《肉體傷害》,而她的小說技藝在短篇集《藍胡子的蛋》中走向成熟,隨之《使女的故事》出版,阿特伍德涉足反烏托邦體裁大獲成功,這種對于未來的推想,超越地域和意識形態的束縛,極大地考驗作家構建一個世界的能力,卻可能是阿特伍德感到最自由的領域。
《使女的故事》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陳小慰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7
《使女的故事》的辛辣諷刺,也寓言了女性的處境。“在未來世界里,自然環境被嚴重破壞,伴隨著核事故、化學污染、病毒試驗及其引發的生態污染危機,全球人口出生率驟然下降。美國部分地區建立了男性極權社會 Gilead(基列國),女性被當做國家財產,失去作為正常人的權利,她們中有生育能力的人被稱為‘女仆’,淪為統治階級的生育工具。”
《使女的故事》不是幻想,而是阿特伍德對女性生存現狀具有切膚體會后的文學書寫,一種以反烏托邦形式進行的“現實再編碼”。

《使女的故事 第二季》劇照。
在這方面,厄休拉?勒奎恩的寫作對阿特伍德深有裨益,勒奎恩在《黑暗的左手》《一無所有》中展現了小說作為“思想實驗”的方法,阿特伍德沿著她的步伐繼續邁進,她擅于將神話、宗教、寓言、歷史案例和科幻元素融合,創作出諸如《證言》《盲刺客》《別名格蕾絲》《羚羊和秧雞》《洪水之年》和《瘋癲亞當》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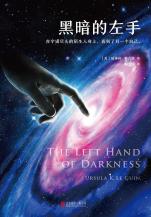
《黑暗的左手》
[美] 厄休拉·勒古恩 著,陶雪蕾 譯
讀客文化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12
但和專注于純粹想象、不去指涉現實的作家不同,阿特伍德的作品具有強烈的介入現實的野心,女權主義、身份認同、氣候危機、極權主義等,阿特伍德的作品具有高調的政治性。
阿特伍德曾經在2010年秋與勒奎恩有過一次公開對話,勒奎恩在對話中區分了“科幻小說”與“幻想小說”(fantasy):前者是“關于可能發生的事情的預測”,而后者是根本不可能發生,但值得推演的存在。阿特伍德意識到“科幻小說”的優勢,比方說借著科幻的殼,言現實所不能言之事,在這方面萊姆的《機器人大師》是杰出的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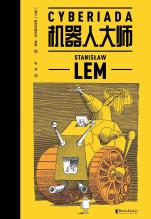
《機器人大師》
[波蘭] 斯塔尼斯瓦夫·萊姆 著,毛蕊 譯
果麥文化 | 浙江文藝出版社,2021-4
科幻小說可以大膽地推演人類進化的形式、未來社會的生態,用科學知識與想象力去探究文明演化的邊界。她也意識到“科幻小說”的局限:淪為點子文學的風險、對于設定的依賴、內在的人類中心主義等。
相較而言,幻想(或謂之“推想”)是一種更不受限制的寫作方法,更接近文學的內核,那就是自由與運用自由的能力。不是為對抗什么,而是為了創造什么,不是把自己固定在一個對抗者、技術主義者的角色,而是在打破限制中,創造一個新的、湛藍的世界。
我們不妨說阿特伍德是一位杰出的“推想寫作者”,推理、想象、對正反烏托邦(ustopia)的合理演繹是她長篇小說的優勢。她對于權力關系格外敏感,在這方面她仿佛是福柯理論的文學演繹者,她能夠生動地描繪出女性在父權社會中被客體化的進程,也能在精妙的結構里,表現出烏托邦灰暗的一面。

《使女的故事 第三季》劇照。
可以說,阿特伍德是21世紀將推想與文學融合得最好的作家之一。阿特伍德在她的論文集《在其他的世界 科幻小說與人類想象》中分享了自己大量閱讀科幻小說后的思考。從科幻小說與神話、宗教之間的關系,到漫威、《哈利·波特》、《阿凡達》,從對于喬治·奧威爾、厄休拉·勒奎恩的討論,到對于人體冷凍術、人工智能、控制論、女性生存現狀的剖析,阿特伍德慷慨地分享她的見識,在她的大腦里仿佛裝有一座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她展現出小說家與時俱進的能力,那源自于廣闊的好奇心、精準的問題意識、結構能力和對于人類情感與社會演進的洞察。
《在其他的世界:科幻小說與人類想象》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蔡希苑 / 吳厚平 譯
上河卓遠文化 | 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4
書中,阿特伍德寫到:“在文學作品中,每一處風景都是一個思想,而每一個思想也能由風景塑成,正反烏托邦亦是如此。”

反抗凝視
阿特伍德并不許諾一個左翼藍圖的玫瑰色幻夢,也沒有滑落到“存在即合理”的保守說辭。其實在反烏托邦作品之外,阿特伍德也寫過雋永的回憶流小說,例如入圍布克獎決賽名單的《貓眼》。
《貓眼》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黃協安 譯
讀客文化 | 河南文藝出版社,2022-4
《貓眼》創作于1988年,彼時的阿特伍德已經年近50歲,歲月使她的閱歷更加飽滿,也讓她的筆觸更加細膩悠長。《貓眼》彰顯了阿特伍德耐心講述女性故事的能力,小說從一位女畫家回多倫多舉辦畫展說起,她在故地重游中回憶往事。阿特伍德在這種過去和現實交織的敘事中,誠懇地探討女性的友誼、親密關系、身份認同、父權制對于女性潛移默化的影響。
《貓眼》講的其實是女性的主體性如何被塑造,在這塑造的過程中,有多少是自我的,有多少是社會文化與周遭目光、權力關系潛移默化的規訓。小說中伊萊恩與科迪莉亞的關系復雜而微妙。

《使女的故事 第四季》劇照。
起初,童年時習慣了游牧生活的伊萊恩在隨父輩回到城市后,很不習慣人類主流秩序里的目光和規范。在女孩們的世界里,伊萊恩如同一個闖入的異類,一個不守游戲規則的野蠻人,為此以科迪莉亞為首的女孩們試圖戲弄她、懲罰她,令她服從既有的相處規范。她們把她埋進后花園一個新挖的洞里,令她在黑暗中感到被孤立的恐懼。又將伊萊恩的帽子扔進溪谷,命令她自己撿回來。
她們是女生,卻在男權社會的浸泡中習得了男權的控制術而不自知,或者享受上位者的感覺,在權力和情感操控中無形中內化了男權。當伊萊恩終于習慣了父權社會的法則,成為一名小有名氣的作家,她開始用畫家的視角重返記憶的現場。

《我的天才女友》劇照。
整部《貓眼》,其實就是阿特伍德用文學寫的《凝視與反抗凝視》,是她通過具體的故事入手,告訴我們父權社會如何通過密集的凝視規訓一個女性的心靈,再到通過伊萊恩的筆觸,展現女性自我的凝視,用女性的筆觸,去拆解一切冠冕堂皇口吻下的控制、物化與將女性視作客體的手段。正如書中所言:“漸漸地,我開始想要我以前沒有想到過的東西,辮子,睡衣,錢包。一個世界在我面前慢慢打開。我看到了一個女生的世界。”
這讓人想起費蘭特的《我的天才女友》,兩位作家都敏銳地感受到女性關系之中微妙的角力。阿特伍德很細心,她盡量避免對關系的刻畫淪為狗血,而是耐心地鋪陳女性交往中的暗流。出身、力量、興趣、交往對象、對比、嫉妒、渴望、權力關系的拉扯,直到她們長大,更強力和懂得運用世俗規則成為寵兒,另一方相比之下似乎暗淡,但強力的一方知道,那蛛網般與后者共享的記憶,始終是她身體里的軟肋。

《我的天才女友》劇照。
2017年,阿特伍德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圖書俱樂部的訪談中談到:“我們感知時間的方式完全是主觀的。除此之外,時間如同一個迷宮,錯綜復雜地連接著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并為我們的未來鋪平道路。因此,時間的概念從來都不是直截了當或線性的,而是‘方塊形的’,它崎嶇、朦朧,充滿了由我們制造的障礙。”

在時代的浪潮中
需要看到的是,阿特伍德是一位關心新技術的作家。她的小說閱讀感受很契合當下的場景,一個由流媒體、影視劇、元宇宙、互聯網等元素構成的“疊影時代”——一個我們被層疊的影像和錯亂的信息包圍的時代,源源不斷的“觀看”正在發生,每個人都在宣稱自己看到了真實。
在《別名格蕾絲》《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小說里,阿特伍德捕捉到不同敘事者對于故事講述方式的影響,影視劇的節奏也影響到她的創作,她的語言善于快速捉住觀眾,在精彩、快節奏的故事中,提供一種潛在的喚起能力——喚起讀者內心被壓抑的某種情緒。
《盲刺客》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韓忠華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10
在《使女的故事》《證言》里,阿特伍德沖擊了“男人關心的才是政治的、公共的”這種陳腐觀念,她把女人關心的、恐懼的放在小說中心,用寓言的方法揭開女性面對的森嚴世界。阿特伍德看見了文學和政治的交叉性,但在文學創作中,文學仍是第一位的,不是政治或熱點的附庸。
《證言》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于是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7
和門羅專注于一個領域幾十年如一日的打磨不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一位思維敏捷、精神充沛的雜食作家,她將公共議題與嚴肅文學融合,在不同文體的穿梭中打破層層森嚴的戒律。
阿特伍德展現了文學作為思想方法的可能、與現實周旋的新的方式。阿特伍德的小說既是好看的故事,也是具有嚴肅文學內核的作品,她懷著充沛的激情投入到虛構這門藝術,在虛構的世界里,她又足夠冷靜、沉著,將世界的部分真相隱藏在幻想瑰麗的文字中。
阿特伍德對寫作者的啟迪不是文體創造層面上的,而是推想的層面,是文學如何進入公共議題,又不折損深刻性這一面,也關乎在這個時代,如何書寫一部好看且耐人尋味的小說,在故事中安放某些難以概括的復雜情感、日常生活中驚心動魄的瞬間。在這些層面,阿特伍德是當代的杰出表率。

《使女的故事 第三季》劇照。
原標題:《一本《使女的故事》,不足以概括她》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