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福、施一團隊揭開猴痘病毒復制機器面紗,論文已發《科學》
提起猴痘病毒,人們可能已不再陌生。今年7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猴痘疫情為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截至12月,全球110個國家已確認造成超過8.2萬人感染。今年9月,重慶就曾有一例境外輸入病例,我國香港、臺灣也報道過類似病例。
事實上,猴痘病毒被發現至今已有60多年,卻一直處于科學研究邊緣。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高福/施一團隊最新研究揭開了猴痘病毒復制“機器”——聚合酶全酶復合物的高清結構,為抗痘病毒藥物設計提供了靶標。相關論文12月16日發表于《科學》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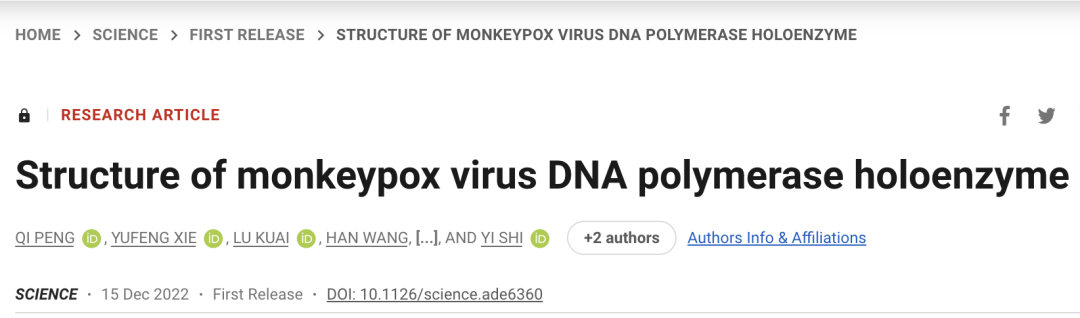
高福/施一團隊最新研究的相關論文12月16日發表在《科學》雜志。圖片來源:中國科學報
“做研究一定要平急結合,‘平’時干的事要能解決‘急’時的需求。”中科院院士高福強調。
關于此次研究,《中國科學報》分別采訪了兩位論文共同通訊作者高福院士和施一,以下為主要采訪內容。

高福。圖片來源:中國科學報
潛在的威脅
今年5月起,英國、西班牙、美國等全球十多個國家相繼發現猴痘確診病例,此后病例數量大幅增加,引發國際關注。
據報道,猴痘潛伏期通常為一到兩周,發病后主要表現為高熱、局部淋巴結腫大及全身水皰膿皰,伴有出血傾向。
那么,猴痘病毒的傳播力如何?傳播途徑有哪些呢?
施一介紹,猴痘病毒此前主要分成兩支:剛果盆地(中非)分支和西非分支。前者毒力較強,病死率可達10%~13%左右;西非毒株毒力較弱,病死率在1%~3%左右。由于猴痘一直以來主要在非洲地區流行,非洲以外的國家大多為與攜帶猴痘病毒的嚙齒類動物接觸而發生的輸入性感染,這也使得該病毒研究處于邊緣地帶。
他表示,最近歐美非流行國家暴發的猴痘毒株跟西非分支比較接近,但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進化,毒力大為減弱,目前可以看作一個新的西非變異分支。
“以前,猴痘病毒主要是通過接觸傳播,從動物傳給人。現在研究表明,已經出現了人際傳播,通過近距離呼吸飛沫也能夠傳播。”施一說。
據介紹,猴痘病毒屬于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屬),與同為正痘病毒屬的天花病毒是“近親”。不同的是,天花僅能在人群中傳播,而猴痘則同時存在于野生動物群體,屬于人畜共患病毒性疾病。
這也意味著,通過疫苗接種可以在人群中消滅天花,而人們卻無法給野生動物打疫苗,這使猴痘比天花更難滅絕,可能跟人類長期共存。
研究者表示,盡管猴痘病毒在我國并未流行開來,但只要其他國家持續存在,就有外來輸入和流行的風險。
據介紹,接種過天花疫苗的人群對猴痘病毒感染具有一定的免疫防護能力。但1980年全球消滅天花后,天花疫苗接種隨之停止,這使得我國“80后”之后的群體大部分并未接種天花疫苗,對猴痘病毒缺乏免疫防護能力。若其持續變異,可能對社會發展和人類健康造成廣泛的潛在影響。
揭秘“復制機器”
科學家已經發現,與人和其他動物一樣,痘病毒也是以DNA作為遺傳物質。不同之處在于,猴痘病毒會在宿主細胞的細胞質中形成“復制工廠”進行基因組復制,產生首尾相連的DNA串聯體。然后,在解離酶的作用下分解成單個病毒基因組,再進一步組裝,形成新生病毒粒子。
據介紹,猴痘病毒復制機器的“幫手”有很多,至少需要8種病毒蛋白相互合作才能完成整個過程。不過,其核心則主要由“三位一體”組成:聚合酶F8、可持續因子E4和A22異二聚體。
這三者組成聚合酶全酶復合物,直接負責合成子代DNA,是理想的抗病毒藥物開發靶點。但目前缺乏這個復制機器核心的高分辨率三維結構,以及基因組可持續合成的分子機制的認知仍不充分。
利用冷凍電鏡技術,研究人員首次讓猴痘病毒DNA聚合酶全酶的結構“無所遁形”。
他們揭示了猴痘病毒基因組復制的分子機制。F8亞基和E4亞基的結構與痘苗病毒中相對應的蛋白結構非常相似,具有典型的DNA聚合酶和尿嘧啶糖苷水解酶特征。而A22亞基屬于痘病毒特有的蛋白,可以分為N端、中間和C端結構域。其中N端和C端分別與E4和F8結合,在病毒聚合酶全酶復合物組裝中起到“中間橋梁”的作用。
“了解聚合酶的工作機制,可以有的放矢地開發藥物阻斷其與DNA結合或復制活性。比如現在有一種靶向痘病毒聚合酶的核苷類藥物西多福韋,就能摻入到DNA合成鏈中,抑制聚合酶的功能。”施一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還解析了猴痘病毒如何保持其高效的基因組復制能力。
此前研究提示,在進行DNA合成時,猴痘病毒聚合酶與B家族其他DNA聚合酶(如人DNA聚合酶和酵母DNA聚合酶)合成不同,不會通過增殖細胞核抗原(PCNA)或PCNA類似蛋白,與產物dsDNA相互作用提升聚合酶的可持續合成能力,而是通過A22-E4形成的異二聚體來保證可持續合成能力。
在該研究中,研究人員更正了此前針對猴痘病毒另一個近親——痘苗病毒聚合酶可持續合成機制研究所推測的聚合酶全酶模型,此前的研究認為聚合酶和尿嘧啶糖苷水解酶之間沒有相互作用。研究人員發現,聚合酶全酶復合物結構中,E4尿嘧啶糖苷水解酶與F8聚合酶直接相互作用,并與聚合酶的N端結構域和外切酶結構域組成一個閉合的模板進入通道,形成“前置滑動夾”。
“DNA聚合酶如果沒有滑動夾,容易從DNA上掉下來,所以一般都需要有一個夾子套在DNA上,讓它保持穩定。”施一解釋,而前置滑動夾是猴痘病毒為代表的痘病毒所特有的,之前研究的其他病毒DNA聚合酶(比如皰疹病毒和非洲豬瘟病毒)的可持續合成能力,與人和酵母等真核生物的DNA聚合酶一樣,都是通過“后置滑動夾”的機制來實現的。
“如果把滑動夾的模板進入通道堵上,病毒就不能通過這個通道進行基因組的復制了。”施一說,這一發現可以用于抗痘病毒藥物的設計。
病毒防控需要持續的基礎研究
從今年5月國際猴痘疫情暴發后開始,研究團隊僅用了3個月時間就把論文投給了《科學》,并被快速接收。這與合作團隊長期致力于病毒研究積累的底蘊分不開。
施一是2005年加入導師高福院士團隊進入病毒領域的。近二十年來,高福團隊先后研究了禽流感病毒、非洲豬瘟病毒、埃博拉病毒、新冠病毒、寨卡病毒、沙粒病毒等十余種病毒。相關研究范疇涵蓋從病毒入侵機制、病毒復制機理到產業應用轉化的全鏈條。

施一。圖片來源:中國科學報
按高福的話說,“科學問題一定要和社會問題有效對接,研究成果或是走上書架,進入教科書;或是走上貨架,變成產品,解決實際需求。”
目前,該團隊的多個成果已經轉化為服務大眾的產品,應用于實踐中。如新冠蛋白亞單位疫苗、單抗和檢測試劑等。
經常與各類病毒打交道,如何規避風險呢?
據介紹,我國相關病毒的研究對實驗室有著嚴格的安全資質要求。以猴痘病毒為例,目前只有個別P3實驗室有活病毒操作資質。
高福院士表示,盡管微生物所也有P3實驗室,但由于其處于奧運村人口密集居住地帶,被認為無法開展相關研究。他呼吁,用納稅人的錢建設的實驗室,有關機構要盡快批準使用,使其發揮應該發揮的作用。

彭齊、施一、高福、齊建勛、蒯璐、王寒(從左到右)。圖片來源:中國科學報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如何窺探病毒的核心基因組呢?施一介紹,實驗室會利用猴痘疫苗的另一個“近親”——正痘病毒屬痘苗病毒在P2實驗室進行研究。這兩種病毒的基因組序列相似性較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猴痘病毒的特征。
另外,他表示,盡管實驗室無法在活病毒上進行研究,但可以在實驗室合成相關基因表達病毒蛋白,在普通實驗室進行操作,進行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研究,這也大幅降低了相關研究的安全資質要求。
“對于一些具有潛在大流行能力的病毒,需要做全面的基礎研究布局。如提前了解病毒感染和傳播特性、有針對性地開發疫苗和藥物,通過持續的基礎研究總結不同病毒的共性,尋找潛在的廣譜預防和治療手段。”施一表示,下一步研究團隊將根據現有基礎研究發現,探尋治療猴痘病毒的藥物。
(原標題為《高福、施一團隊揭開猴痘病毒復制機器面紗,論文已發〈科學〉》)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員彭齊、清華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系博士生謝宇鋒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人員蒯璐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研究人員齊建勛、王寒也參與了該研究課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員施一和高福院士為本文共同通訊作者。該研究得到了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國科學院戰略重點研究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中國科學院青年創新促進會等項目的經費支持。)
相關論文信息:
10.1126/science.ade6360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