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流浪100天,能治好精神內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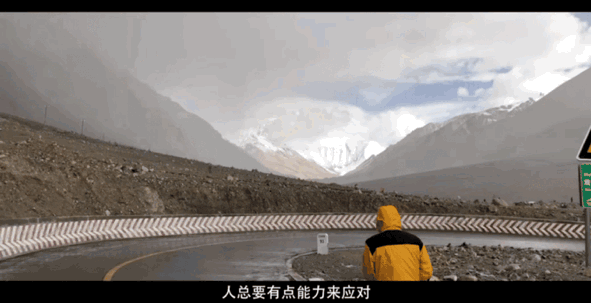
“大多數人不愿意離開城市,是不愿意放棄熟悉的舒適圈。在這個過程中,你其實放棄了對外界的探索能力。“
如果不是在大理遇到小福,我大概會對她敬而遠之。
在北京的互聯網大廠做銷售時,這個女孩是有點“兇狠”的。早7點到晚11點全年無休,不和同事多說一句話,連上班的路上都在瘋狂簽合同。領導讓她帶徒弟,她反而質問領導,說自己來這兒不是交朋友的,除非你拿客戶和我換。
“今天你站在Top 1的臺子上是小福姐,明天下來你就是小福,落差很大,你會完全被工作規則規訓。”
現在的小福已經從獎金和并不真誠的祝賀聲中離開,她穿著一條朋友贈送的手工長裙,站在蒼山溫柔的綠草地上,面朝像小動物一般翻滾跳躍的云朵,在心中規劃著下一次出行。

小福和曉宇一起,看大理的山與海。圖/《三十而已,退休去山里》
近兩年興起的青年返鄉熱潮,其實并不是新鮮事。
早在2010年,“逃離北上廣”的敘事開始流行,就有一批年輕人因為受不了城市高昂的房價和被擠壓的生存空間,選擇從宏大激昂的“他鄉”回到貌似風平浪靜的“故鄉”。他們想著,即使沒能在世俗意義上成功,但至少得留住生活的體面。
但逃離的后續,大概率是逃回。早已習慣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標準,即使真的來到田園牧歌中,仍會被源自城市思維的焦慮圍堵;刷朋友圈時說不定會猛然驚覺,30多歲,是不是該結婚生娃了?
相比于逃離,小福和丈夫曉宇從北京出發、自駕環游中國、決定定居到大理的軌跡更像是游牧。他們并非被動放棄城市里的工作,而是主動探索并找到了一種更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當“內卷”“內耗”成為當下城市生活讓人身心倦怠的共同情緒,反向激發出的“擺爛”“躺平”心態此起彼伏時,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真的能解決現實的一團亂麻嗎?
懷著這樣的疑問,我們在大理和小福、曉宇共同生活了幾天,試圖為這個當代難題尋找解法。
01
說走就走這事兒,不能沖動
小福和曉宇家的院子不在熱鬧的大理古城,要到達他們居住的龍龕碼頭,得先穿過一片郁郁蔥蔥的莊稼地。
初秋的季節,高大的玉米稈上已經掛上了飽滿的果實,陣陣清香撲鼻而來;車輛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左右搖晃,仿佛故意要人把浮躁的情緒甩掉。

車窗外大理的山和云。圖/《三十而已,退休去山里》
小福和曉宇養了三只狗、一只貓,庭院里還有海棠果樹、水蜜桃樹、杏樹和李子樹。每逢3月,小福和她的朋友們就會組織花見酒局,誰家院里的樹開花了,就去誰家的樹下喝酒。還沒長住大理的時候,花見酒局一過就是小福和曉宇出發的日子。
“喝完酒,正好該開車走了,等到深秋,我們再回到大理。”

花草簇擁的閑適小院。圖/《三十而已,退休去山里》
兩人出門旅行,一定不會缺席的還有一只名叫“追風”的俄羅斯獵狼犬。這位回頭率超高的“美男子”站立起來比人還高,在山林間邁起步子奔跑,很像《指環王》中的“馬中之王”影疾,自帶一圈光芒。

這個夢想中的小院是小福和曉宇共同孕育的家,也是他們探索過很多種可能的生活方式后目前落腳的地方。
在定居大理之前,兩人都在北京打拼了很多年,挨過社會的毒打,體驗過被折磨到不認識自己的滋味。
曉宇在北京做公關,經常需要跑全國各地做展覽和發布會,忙到每天早上醒來,都得先想想是在哪個城市;小福在大廠做銷售,曾經為了名和利爭得雙眼通紅。
忙碌、疲憊,但內心好像又有個大大的缺口,這些情緒我們都太熟悉了。
改變發生在2018年。那年小福30歲,正值她的土星周期,她和丈夫曉宇做了一個重大決定:雙雙辭職,去中國邊境線上流浪100天。

“中國幅員遼闊,全世界95%以上的地形都能在中國找到。” 圖/《三十而已,退休去山里》
這聽起來是個標準的“逃離北上廣,回到田園牧歌”的當代神話:厭倦了城市的卷,就去山河湖海里躺平。但小福和曉宇覺得,“躺平”絕不是他們這個年齡該干的事;做出離開大城市的決定,很即興,但并不沖動。
“總是有人羨慕我們,說我們逃離北上廣,是說走就走的旅行。你看到的是說走就走,其實我們是在有充足準備的情況下去追求自己所喜歡的生活。”
小福所說的充足準備,既有實操層面上的,也有精神層面上的。
在出發之前,小福花3個多月制定了細致到魔鬼程度的旅行攻略,所有行動都有強大的word文檔和Excel表來支撐。比起上網查資料,她更喜歡用old school的紙質指南,研究透每一條道路、它們的背景故事、可以怎么玩、中間可能有什么變故、需要準備什么樣的物資等等。
一旦選擇了一條路線,摩羯座的小福還會拿別的書去佐證;制定了方案A,一定會有備選方案BCD。她把自己規劃的旅行攻略一筆一畫都寫在草稿本上,如果在路上遇到朋友也想去攻略中某個地點的,她還會撕下一頁送給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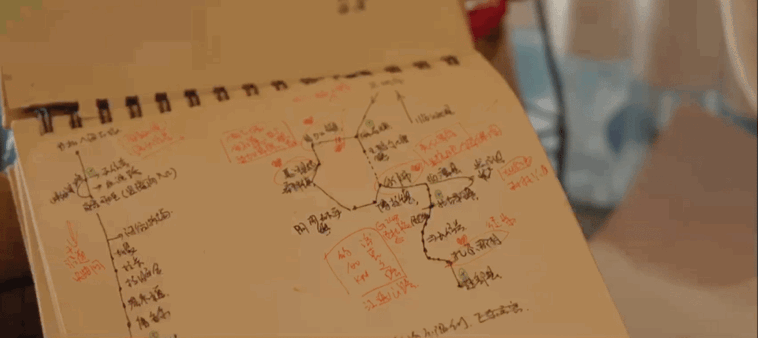
為了適應旅途中不同情境,小福和小宇在出發前鉆進車里,演練了三種不同的睡法:踏踏實實的睡、踩一腳油門就能走的睡、少挪東西的睡。他們晚上把車停在小區里,早上從車里出來,鄰居們都驚呆了。
小福負責攻略,曉宇負責落實,后來兩人兩狗一車,真的在路上流浪了100天。
在羊湖領略過自然的純凈、在珠峰感受到人類的渺小, 到最后兩人越玩越快樂,越來越覺得怎么沒有早點出來。曉宇問怎么辦,還回去上班嗎?小福說回不去了,心玩野了。

02
留在城市才需要莫大勇氣
時間回到18年前。初到北京時,小福還是個胖胖的高中女生,住在酒仙橋的鐵皮屋里,第一次遠離家鄉獨自考學。屋子一樓住著出租車司機,二樓是男女混住的宿舍。因為不習慣住宿條件,她把所有的床鋪被子用開水燙了一遍,燙壞了還賠了一筆錢。
后來小福考上了中戲,學舞臺管理,漸漸開始了找自己的旅程。在北京的十數年間,她在中央電視臺做過節目、在招商銀行的雜志做過編輯、在互聯網大廠的銷售崗上沖過金字塔頂尖,還作為美食編輯享用過流動的盛宴。
談到城市工作對人的異化,小福并非一味批判,而是強調了經歷對成長的必要性。她認為,做銷售時為了搶客戶不擇手段,自己都很討厭自己,但這個過程一定會有的:“你不知道這個社會的樣子,怎么能知道哪種生活更好呢?你總要體驗壞的,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好的,是吧?”
與其說是試錯,小福和曉宇更看重的是感受和體驗,無論是痛苦的還是美好的。
“之前在城市做過那么多份工作,就是積累能力的過程,人總要有一點能力來應對這個世界的繁雜和浮躁。”小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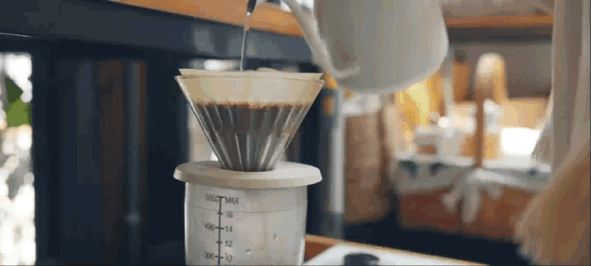
小福的愛好很多,旅行、咖啡、紅酒、手工等等都是她應對世界的方法。圖/《三十而已,辭職去山里》
這里提到的“應對”很關鍵。應對不是逃避、不是放棄、不是死磕硬碰,而是換一種方式,身體力行地去實踐另一些可能性。
在成功的標準越來越僵硬固化,買房買車、二孩三孩被印在人生軌跡檢查表上等待打鉤時,很多年輕人們雖然怨聲載道,但不得不逼自己擠進這條賽道。在這樣的主流框架之下,小福、曉宇的“出走神話”顯得更加夢幻。他們也表示,自己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怎么敢放棄一切離開北京到大理,流浪在路上。
然而,小福覺得這個問題從根本上就帶著狹隘的預設,為什么離開城市就叫放棄呢?
“我沒有放棄過任何事情,我們只是去追求我們更想追求的,我反而覺得留在城市里需要莫大的勇氣。你天天就在家、地鐵、格子間之間打轉,這個環境也許不完美,但也給了你一些安全感。大多數人不愿意離開城市,是不愿意放棄熟悉的舒適圈。在這個過程中,你其實放棄了對外界的探索能力。”
“我們喜歡每天都不一樣,我們喜歡接觸不同的人、看不同的風景,而不是每天同一條地鐵線,同一撥同事,同樣的工作重復再重復。我們在不停地跳出過往兩年甚至過往兩天所習慣的舒適圈,我根本不想裝修一個房子,我就想好好搞一臺車。我知道我這輩子是可以在路上的,不會錯。”

說著說著,小福和曉宇給我展示了去年在德令哈拍攝的視頻。少有人知道,海子詩歌中那個寄托著孤寂荒涼的旅途愁思之地,同時也是中國儲能最大的光熱電站。在兩人的鏡頭下,德令哈的沙漠銀光浩渺,光伏板組成的圓形矩陣像天外來物一般莊嚴佇立。

“你要到現場看,那才叫厲害!”兩位候鳥的思緒已然從蒼翠的山間草甸飄向了更加廣闊的天地。
03
我還沒玩明白呢!
在不確定成為常態的大環境下,小福和曉宇有大半年沒有出遠門旅行了。他們原本想在今年完成一個“小城計劃”,挑10座小城市,每個地方住一個月,做人文方面的視頻內容,但因為疫情反復沒能成行。
現在的兩人在蒼山半山腰經營著一塊營地,提供露營場所,也會呼朋喚友玩飛盤、烤燒烤、放電影。即使是“困”在大理(這個說法有些凡爾賽),小福和曉宇仍然過著很多人夢想中的生活。我不禁疑惑,能夠選擇不上班、做自己喜歡的事,前提是否要財富自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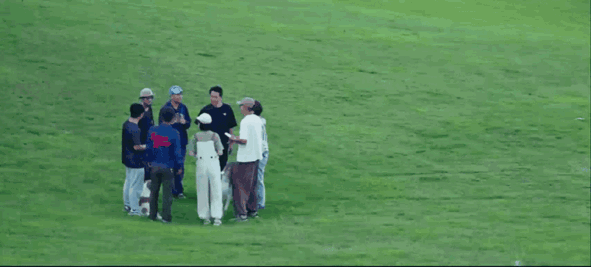
曉宇一口否定了我的預設,還反問了我對“財富自由”的定義:到底什么才算財富自由?是有源源不斷的金錢去追逐物質上的極致,還是有足夠的儲備和能力來追求自己喜愛的體驗?
兩位候鳥告訴我,他們更注重的是心態和精神上的體驗。
比如小福做美食編輯時經常受邀享用一些chief table,她覺得很高級,會帶著曉宇一起。但曉宇會把整塊的牛排留下,走出酒店后左轉去吃了一碗蘭州拉面。“他不見得不比我快樂,所以,財富自由因人而異。必要嗎?我覺得大可不必。”

小福和曉宇帶著追風在洱海邊散步。圖/《三十而已,退休去山里》
實際上,“財富自由”并非簡單地指積蓄,它也包括能夠隨機應變、利用手邊的資源為自己供血的能力。
從離開北京起,小福和曉宇的所有動線都會有個plan B。比如在大理做起了民宿,有一份收入支撐愛好;因為愛玩,想著不如直接把愛好變成收入來源,就做了私定游;后來他們開始做旅行博主,有了關注,有了小名氣,又可以接商單。一直到最近,不能出去浪,就在大理專心做營地。
他們給所有的事情制定一個最底線的計劃,包括養老:“我們不是說兜里面只有兩個銅板就跑出來 ‘擺爛’了,我們有一些在路上賺錢的方法,也為自己留下了一些至少到老年我不揮霍,還可以有吃有喝、不給別人找麻煩的資本。”
想一直在路上流浪,確實不是件容易事,小福和曉宇還在探索著良性的運轉方式。耗費精力的程度也許和格子間上班不相上下,但這是兩個人在毅然選擇追求心中所愛后,全身心認可的旅程。
“我最近連續工作三個月,一天都沒休息,非常累了,但是你現在跟我說去西藏,我可以馬上出發就走。”曉宇說。

在采訪的最后我問小福,對流浪是怎么理解的,她想了想,回答道:
“浪是一種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我沒有被束縛住,我去選擇了,我有我的能力去支撐。我覺得浪是一種贊美,不是所有人都能玩得這么好,玩和浪也是一種能力。”
“我們這一代人一定是自我的,我不想給任何人添亂,我不白吃一口飯,我還是想創造一點價值,哪怕是一點個人價值。我不擺爛、不躺平,哪怕我把酒喝明白了、把石頭看懂了、把咖啡豆讀明白了,哪怕是這都行,我可以讓已有的生命過得更好。但我還沒活夠、還沒玩夠、還沒玩明白,所以,我們會繼續流浪下去。”

學者張慧在題為《中產階級逆城市化的移民現象——以大理為例》的研究報告中寫道:“逃離北上廣”和“返鄉”敘事背后的精神訴求,不僅關于人們對現代城市生活的不滿,或是普遍性的失落,更關于在一個不允許失敗的環境里,一部分年輕人試圖尋找一份出路、一個可能。
從城市出走,與其說是地理上、物質上逃避式的“自我下放”,不如說是在嘗試一種精神性突圍。
計劃在35歲之前開車到埃菲爾鐵塔下的小福和曉宇,顯然和“躺平”不沾邊。
“不是所有人都會 ‘玩’這個東西,我們做自己擅長的事,發揮自己的能量就可以了。到了巴黎鐵塔之后,我們還會有下一站,然后再下一站、再下一站,我們永遠不會對這個世界失去好奇。”這對迫不及待想要出發的自由靈魂如是說。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