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再見愛人2》,婚姻的一地雞毛

“它會讓你變得刻薄。愛會讓你刻薄。要是你覺得離不開誰了,你就會對他們刻薄。”
——愛麗絲·門羅《苔蘚》
伴隨著張婉婷和宋寧峰屢次上熱搜,離婚綜藝《再見愛人2》引發(fā)熱議。這檔綜藝選取了三對出現(xiàn)感情危機的夫婦,他們或離婚,或處于離婚邊緣。和第一季不同的是,這一季加入了六十歲以上的夫妻搭檔,嘉賓爆發(fā)的沖突也更加激烈。
在《再見愛人2》的觀察團里,第一季陣容基本保留:胡彥斌、孫怡、郭采潔、沈奕斐、黃執(zhí)中、千喆,新加入吉娜和易立競。
節(jié)目組通過展現(xiàn)三對年齡段不同的夫妻的問題,用意已經不只是探討婚姻框架內部的問題,也在促使觀眾思考和他人的相處方式。
弗洛姆曾經提倡將“愛”作為一門藝術來修煉,而小說《圍城》引用英國古諺語形象地描繪:“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
多少滿腹經綸的人,在婚姻這門藝術上栽了個大跟頭,又有多少人其實都不知道如何愛自己,于是更加懷疑是否有能力長久愛別人。
在“愛無能”和“親密關系”成為公共議題的今天,借助《再見愛人》系列,不僅能使我們探索綜藝節(jié)目與情感教育之間的關系,也能反躬自省,在親密關系這堂課上,我們究竟遺忘了什么。
01.
張婉婷和宋寧峰:
親密關系里的窒息感從何而來
“張婉婷讓人窒息”、“張婉婷發(fā)文”、“張婉婷哭著自我反省”、“張婉婷7次打斷宋寧峰說話”……光是看這些詞條,不難想象張婉婷在節(jié)目中的形象有多么不討喜。但是在吐槽之前,有一個細節(jié)值得留心。
節(jié)目第二期播出那周,是張婉婷被罵上熱搜的時候,而當第三期上線,觀眾對張婉婷的討論明顯發(fā)生轉變。雖然仍有辱罵,但有更多人試圖從張婉婷的角度思考問題。
究其原因,是因為第二期的張婉婷表現(xiàn)得劍拔弩張、咄咄逼人。她屢次打斷他人說話的表現(xiàn),自然會讓觀眾感到厭惡。
而在第三期,張婉婷打斷別人對話的情況明顯變少,她變得節(jié)制,宋寧峰與她互換角色表演對方的片段,乃至宋寧峰夜色中站在高處向她呼喊“我不是木頭……我們別分開好嗎?”都成為二人的加分片段。
由此可見,同一個人做出不同的事,在剪輯的放大之下,可以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觀感。你永遠不知道,在剪輯的壓縮和編排下,一個人在節(jié)目里的表現(xiàn)和真實生活相比有多大的變形。
張婉婷看似強勢,但她的內心其實很脆弱,需要被別人在乎、被別人愛,她所有的憤怒是一只柔軟刺猬長出來的刺。
當宋寧峰幫別人說理,不跟她站在一起的時候,她表現(xiàn)出憤怒,因為那一刻她感到孤獨。當她發(fā)現(xiàn)盧歌可以讓宋寧峰開心,她對宋寧峰的占有出現(xiàn)動搖時,她用強勢表現(xiàn)出一種宣誓主權般的姿態(tài)。所謂控制,也是害怕失去。

或許,“令人窒息”的張婉婷也有她的原因,而不是無緣無故的恨。在家庭中,她是帶孩子更多的一方。經紀人的職業(yè)身份本就要處理許多人際瑣事,回到家又是一地雞毛——孩子的哭哭啼啼,家庭內部的亂七八糟。想必要顧好一個家,容易讓人精神崩潰。張婉婷在學習做一個母親,可沒有人教她這一課。
張婉婷的控制欲和屢次打斷他人說話的表現(xiàn)被人詬病,但隨著節(jié)目推進,也有許多觀眾指出張婉婷是在家庭中承擔更多事務的一方,這一方更容易因為瑣事消耗而產生情緒波動,而節(jié)目組對于素材的剪輯,也是觀眾不可不察的一點。
身為局外人,執(zhí)著于節(jié)目剪輯的張婉婷孰是孰非或許意義不大,但這段親密關系、在節(jié)目中形象的變化、隨之引起的輿論,恰好是綜藝節(jié)目呈現(xiàn)親密關系的典型范本。
通過這組關系的呈現(xiàn)、觀察團嘉賓對于二人做法的點評,會促使我們思考在一對一關系中,過于強勢是否有助于良性溝通?過于沉默、面對問題習慣性回避,又是否是另一種極端?
進一步推演,可以思考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家庭事務分工對一個人的影響;如果伴侶疑似出現(xiàn)心理病癥,自己或朋友應該怎么做;兩個人墜入愛河,在短時間內懷孕,怎么協(xié)商下一階段;如何避免讓愛情淪為工作,讓家成為最窒息的地方?
02.
Lisa和艾威:步入老年的婚姻
如果說,張婉婷和宋寧峰這組關系處理的是“我很愛對方,但對方有時讓人窒息,我該怎么辦?”,艾威和Lisa則像更為傳統(tǒng)的父權式婚姻。
艾威善良、仁義,可他和那些父權式的大家長一樣,喜歡妻子聽他的話、順他的意。他習慣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不喜歡做飯,不喜歡做家務,家務活主要交給Lisa,自己在外面努力掙錢。他經常給Lisa下判斷,但很少有耐心好好聽Lisa講完一段話。
在艾威的敘述版本里,他散盡家財為Lisa治病,術后Lisa卻不愛惜自己的身體,經常打麻將,有一回甚至到第二天上午才回家。
但在Lisa的敘述版本里,打麻將并非到上癮的地步,每周一次的麻將時光是真正屬于她的時間。艾威總說為她好,卻從來沒有真正明白她去打麻將背后的心理原因。而所謂的喪盡家財,其實也是夫妻的共同財產。
所以,僅僅根據一面之詞來判斷一對關系的是非對錯,容易陷入“羅生門”式的困境,《再見愛人2》做得較好的一點,是它至少提供了一個平臺,讓雙方都可以走出原本的環(huán)境,有一個契機好好表達自我壓抑已久的想法。
而觀察室嘉賓能做的,就是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乃至專業(yè)意見。在演播室加入一個心理學、教育學或社會學專業(yè)的嘉賓,其實非常重要。
無論是艾威還是張婉婷,他們都打著“我是為你好”的旗號來支配伴侶的意志,這恰恰是他們時而讓人感到窒息的重要原因。
某種程度上,他們在婚姻里都給自己灌輸了一種獻祭感。獻祭的一方,會把生命的所有重量都放在婚姻上,所有的生命意義都只能從犧牲與回響中獲得。
獻祭者并非真的甘心獻祭,他渴望同等回報。可如果對方做不到,他就會想,“為什么我這么苦這么累,你卻一點都不照顧我?你為什么不能跟我付出一樣的東西?”
當雙方朝著疲憊的深淵下墜,愛情成為對錯簿,它離死亡也就不遠了。
這種窒息感觀眾其實相當熟悉,生活中最喜歡跟我們說“我是為你好”的,不就是我們的父母嗎?所以,觀眾一邊感到窒息,一邊又感同身受,他們在里面看見伴侶,也能看見自己的父輩。令人窒息的親密關系,不只存在于明星夫妻,它縈繞在父權社會關系網絡里的時時刻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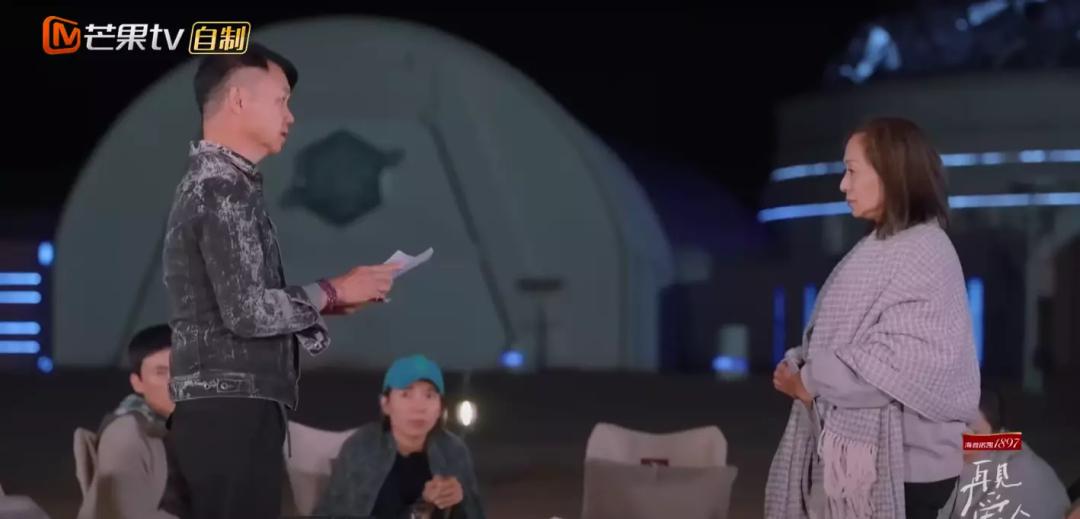
通過Lisa和艾威,觀眾也可以看見老年伴侶需要面對的問題:愛情、疾病、孤獨、死亡。
在《一個人最后的旅程》里,日本知名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分析了老年人居家看護醫(yī)療的實際狀況,以及多位臨終者的真實案例,探討了一個人有尊嚴地走完最后一程的可行性,一個人晚年處境背后的社會結構原因,以及性別、親密關系、看護資源等要素對年長者的影響。
無獨有偶,作為一對步入老年的伴侶,Lisa艾威夫婦的婚姻問題糅雜著更多生死因素。
因為目睹過Lisa重病,艾威對死亡和陪床有難以言喻的恐懼;二人已經分居,他們都在承受著晚年的孤寂,而Lisa同時要克服疾病對身心帶來的巨大改變。她曾經是風華絕代的選美小姐,在疾病的摧折下日漸憔悴,她曾經終日與病魔斗爭,術后又要克服疾病引發(fā)的心理后遺癥。
Lisa艾威夫婦在節(jié)目里也直白地談到了死亡的問題。艾威說,到這個年紀,兩個人都會考慮生死,他們其實都希望對方是先走的一個,那么另一個人就可以幫對方料理身后事。Lisa和艾威都十分在乎對方的健康,卻又因為健康問題,不得不分開。
借助艾威和Lisa的視角,《再見愛人2》呈現(xiàn)了疾病對親密關系的沖擊和重塑、老年人被壓抑的愛欲表達,以及在老年親密關系中,那些關于愛情又遠遠不止于愛情的部分。
03.
蘇詩丁和盧歌:花束般的戀愛?
相比之下,盧歌和蘇詩丁的關系是非常青年的。就目前播出的節(jié)目來看,二人的矛盾相對而言沒那么激烈。
他們欣賞彼此的才華和容顏,在一起有默契的話題,他們在世界各地笑容歡暢,可是他們在乎自己的理想勝過和另一方生活。
從節(jié)目中呈現(xiàn)的內容來看,雙方的愛還沒有到互相犧牲的程度。盧歌想要有一個照顧他的人,他覺得蘇詩丁更在乎自己音樂事業(yè),可蘇詩丁也可以反問,為什么盧歌不能為了她搬去別的城市?
他們是最匹配的戀人,卻不是能一起為彼此兜底的愛人,他們在一起又分開的原因,或許就是因為他們太過相似。

二人的關系很容易讓人想起日本電影《花束般的戀愛》,尤其是盧歌,他雖然有才華,但還處于一種充滿著玩心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終會面臨生活險灘的考驗。
在《四種愛》中,C·S·路易斯提到了情愛的重要:“情愛因此奇跡般地把典型的需求之樂變成了所有樂趣中最典型的欣賞之樂……在情愛中,一種最為強烈的需求,最為強烈地把對象看成是本身值得贊賞的,這要比她與愛人的需求關系更加重要。”
曾經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然而當情愛變婚姻,他們是否真的了解了對方,愛那個燃燒火焰下灰暗的角落?
情愛之后,更大的劫數是生活,是能夠看到你最粗糙的一面,知道你脆弱、不安甚至患病的靈魂,是一起吵過不知道幾次一起柴米油鹽過后,還有底氣說一句:“我會為你托底。”
04.
離婚綜藝的放大與遮蔽
或許,離婚綜藝的基本好處,在于它提供了一個反觀的機會。它把從前許多被壓抑、被認為不重要的問題擺在臺面,讓我們意識到與他人相處中被默許或忽視的東西。
比如艾威和Lisa,如果不上這個節(jié)目,真正敞開心扉對話,艾威還要多久才能意識到自己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義?Lisa在默默忍受的習性下,又會壓抑自己內心的表達多久?

綜藝節(jié)目通過故事、剪輯、嘉賓點評、話題制造來形成一個情感教育的廣場。它不是一個中心化的場景,而是每個人都來點評一番,其中具有專業(yè)素養(yǎng)的人士起到引導作用,但最后還是回到觀眾對自身及周邊問題的思考。
說到底,綜藝節(jié)目不是權威導師,它更像是一個窗口,一個鼓勵大家思考的契機。《再見愛人》最大的意義,就是促使觀眾思考:在親密關系這堂課上,我們究竟遺忘了什么?
但另一層面,綜藝節(jié)目非紀錄片,其固有的模式、對戲劇性的追求,使得它在進行情感教育時存在根本的缺陷。
首先,在為期半個月的旅途中,離婚綜藝提供的是一種“夏令營模式”,一種通過美好景色、生活的例外狀態(tài)和攝影機共同組成的濾鏡式生活。
正如觀眾都能意識到,節(jié)目中播出的“夫婦在臥室里吵架”片段一定有攝像機在場,嘉賓們很大程度上存在矯飾自我、刻意隱瞞部分自我問題的可能。當然,這未必是虛偽,只是面對攝像機時人的本能反應。
如果這不是一檔戶外旅行節(jié)目,而是把場景更多設置在家庭內部,比如呈現(xiàn)大量女性在家庭中的細節(jié),是否也會影響觀眾對參與夫婦的評價?
這暴露出“夏令營模式”綜藝的固有局限,它們確實能呈現(xiàn)愛人在旅途中的悲歡離合,但更接近普通人日常生活質地的,是學校、職場、租房、家庭內部,乃至廚房這樣一個關鍵的場所。
夏令營模式的氛圍,天然會美化或遮蔽掉一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浪漫化的綜藝模式,與更為日常、瑣碎的常規(guī)生活終究無法混為一談。

其次,平臺通過剪輯、生成文本、投放熱搜、引導話題來左右觀眾的感受,是不可忽略的一點。
當演員在綜藝節(jié)目里扮演真人,面對七八臺攝影機吵架,剪輯師再根據各方要求,把一天的素材量剪輯成兩個小時,一個人在節(jié)目中的模樣和他真實生活的全貌,究竟有多大出入?我們可以言之鑿鑿地根據幾分鐘的視頻斷定一個人的性格或人品,但如果下一期嘉賓表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一面,又該如何理解?
后期剪輯是可以塑造性格的。在綜藝節(jié)目里塑造人設甚至不需要劇本,只要把需要的素材整合在一起即可。
制作組對故事性和流量的需求,使得綜藝節(jié)目放大了戲劇化場面,誘導觀眾憤怒、站隊評議節(jié)目參與者,成為當代輿論場的常見現(xiàn)象。此外,演播室里的觀察團就愛情談愛情,卻沒有及時延展出心理學或其他維度的討論時,或許也是一種遺憾。
以張婉婷和宋寧峰為例,在爭議最大的片段播出時,觀察室嘉賓們其實沒有跳出“譴責女方”的視角,提出更深層的討論。
此外,明星的婚姻問題,和非明星的工薪群體面臨的問題存在參差。
在明星面臨的婚姻危機中,往往是親密關系內部的問題。但在普通人面對的婚姻危機里,愛情不只是愛情,門第、出身、階層、職業(yè)發(fā)展、家庭事務分工等等,占據了更大的影響比重。
倘若照顧小孩太累,明星夫婦可以雇傭保姆,但是對普通人來說,出這筆錢沒那么容易。明星夫婦也許早早就能在大城市安家落戶,但對于在大城市打拼、收入普通的更多人來說,即便結婚了可能還過著合租的生活,而合租與工作的雙重壓力,其實更容易滋生矛盾,進而影響親密關系。
因此,公眾人物的婚姻對普通人有參考價值,但不大。
05.
從零開始探索“最小單位的革命”
在《愛的藝術》里,弗洛姆強調:“除了努力積極發(fā)展你的全部個性,使之形成一種創(chuàng)造性人格傾向外,一切愛的嘗試都一定是要失敗的;沒有愛自己鄰人的能力,沒有真誠的謙恭、勇氣、忠誠、自制,就不可能得到滿意的個人的愛。
在罕見這些品質的一種文化中,獲得愛的能力注定是一個難以達到的目標。任何人都可以捫心自問,他知道有幾個真正會愛的人。”

弗洛姆在書中闡釋了愛情與犧牲的差異、愛情與自我中心主義的差異,如果一段關系只有自我中心主義,沒有對于另一方的寬忍、謙虛、勇氣和一起創(chuàng)造生活的信念,那不能稱之為愛情。同樣,如果這段關系里只有默默忍受而不再有自我的光彩,那不是愛情,而是自愿為奴。
在以權力和邏輯構建的父權世界里,征戰(zhàn)和事業(yè)常常被認為是宏大的,而情感教育卻被邊緣化。所以從小到大,我們上過很多關于成功的課,不斷和他人競爭,但始終沒有一堂關于親密關系的課,教我們如何去愛,如何守護親密關系。
正因如此,離婚綜藝才成為了延遲的情感教育。當離婚綜藝成為公共議題,它不是愛情這門課的終極答案,但可以是重新出發(fā)的第一盞信號燈。
知易行難。無論說了再多,親密關系的實踐都能讓理論家一敗涂地。亂哄哄的你方唱罷我登場,最后光鮮亮麗,又一地雞毛。除了圣人,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都經不起放大鏡的審視。
當我們看到他人婚姻華袍下的虱子,是否可以想想,如果我進入婚姻,真的能做得更好嗎?其實每往下想一步,內心就如臨圍城深井,甚至會產生婚姻恐懼癥。

倘若說《再見愛人》是一次情感教育,它最后回到的,不是教導別人怎么處理愛情和親密關系,而是反躬自省。局外人笑局中人,局中人冷暖自知。
關于愛情,詩人馬雁說過一段話:“愛情就是一種拯救,我想。是對生活無意義的拯救,這種拯救并不能使生活有意義,但卻可以使人在快樂中忽略生活意義的問題。”
這讓人想起巴迪歐說的“愛是最小單位的革命”,在一個保守化回潮、創(chuàng)造性被壓抑的年代,探索“最小單位的革命”,一種真正基于平等、互助、從內心深處蕩滌奴性的愛情,未嘗不是從零開始的改變。
撰文:宗城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