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孫若風: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傳統
文言是中國古代書面語的主要形式。它建立在先秦口語的基礎上,并在諸子和史學家的手中成熟起來。漢代的口語與文言已拉開距離,但文言沒有退出語言舞臺。漢代文人不僅豐富和發展了文言,而且開創了書面語與口語分離的局面,使之成為綿亙兩千年的傳統。兩千年里,文言在書面語中的至尊地位一直是不可動搖的,雖然白話也曾試圖分庭抗禮,并也確實占據了一些領地,但終究沒有成為文言那樣的正統。白話、俗語不能登大雅之堂,稍有越軌,就會立即遭到驅逐。
語錄是口語的記錄,雖然經過加工和提煉,但仍保持口語面貌。先秦時期,語錄體是人們最得心應手的文章樣式,《論語》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語集錦,《孟子》記錄了孟子與人的大量對話《莊子》中的對話多為作者杜撰,但足見語錄體是怎樣的受歡迎。史書也有以記載口語為主要內容的《戰國策》、《國語》等。漢以后,因為文言與口語分道揚鑣,語錄體也受到冷落。清顧炎武就嚴厲批評過后世的語錄體:
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從門者,多不善于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1]。
錢大昕解釋這段話說:“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心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2]他們反對后代語錄的理由主要是,語錄用的是口語,缺少必要的熔裁,因而鄙俗乏采。這種觀點并不為所有文人所贊同,但有相當的代表性,顧炎武說:
自嘉靖以后,人知語錄之不及文,于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云,下法文中,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3]。
文言的勢力實在太強大了,語錄體還沒有熱起來,就因“人知語錄之不及文”而被拋棄了。語錄成了書面語的禁忌,清李紱在《古文辭禁八條》中將語錄列為所禁的
第一條:
禁用儒先語錄。語錄一字始見于學佛人錄龐蘊語,相沿至宋,始盛其體,雜以世俗鄙言,如“麻三斤”、“千矢橛”之類,穢惡不可近。而儒者弟子無識,亦錄其師之語為語錄,并仿其體,全用鄙言,如“彼”、“此”自可用,乃必用“這"、“那”字;“之”字自可用,乃必用“的”字;“矣”字自可用,乃必用“了”字。無論理倍與否,其鄙亦甚矣。《魯論》具在,孔門弟子記圣人之言,曷嘗如是鄙語哉!南宋以還并以語錄入古文,展卷憮然,不能解其為何等文字也[4]。
“這”、“那”、“的”、“了”這些詞在白話文翻身之后可進入任何莊嚴的場合,但在當時文言的壓迫下,統統被打上“鄙”的恥辱標記,并成為語錄不當存在的理由。
文言的另一對手是大眾語,即所謂的市并俚語和村豎野詞。下層社會的語言活潑恣肆,一派天真,對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方巾學究尚能穩住陣腳,拒絕大眾語的挺進,斥之為下里巴人,視之同鄭衛之聲,維護文言的一統天下。也有一些文人則沒有固守文言城池,讓出部分地方作為大眾語的立腳之地,如部分文學體裁,但即使在這些人的眼中,文言也是正式的書面語言。明代馮夢龍《序山歌》、李開先《詞謔·論時調》肯定了“田夫野豎”、“里巷婦女”的矢口寄興,但都沒有表示文人也可用這種語言。清代袁枚欣賞詩歌中的口頭語,認為“口頭語說得出便是天籟” [5],但又將口頭語限定在詩歌語言的圈子內,文章語言則是“不可俚”、“不可時”(《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李紱在《古文辭禁八條》中將這種語言也視為文章禁忌:
禁用市井鄙語。詩有俗語,若子夜歌、竹枝詞多用諺語。至于古文必須典雅。《戴記》謂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子長亦謂“言有雅訓,薦紳先生難言之。”昌黎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柳州謂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庶可免市井之陋。
嚴格地說,詩歌語言常常并非書面語言,因為相當多的詩歌就是口頭文學,歷代民歌是這樣,包括被文人奉為圭臬的《詩經》中的“國風”。這就是文人在詩歌上對民間語言網開一面的原因。在他們看來,正式的書面語只能是文言。
文言就這樣雄視書面語世界,口語在流水般地更迭著,文言王國卻巋然不動。直到五四時期,文言才受到強有力的沖擊,經過幾番激烈較量,即文言與白話之爭,文言終于勉強退讓。文言作為舊時代的聲音,與舊時代一起過去,它也作為那個時代的符號,成為那個時代社會和人生的標志。
與語言學上尊從以先秦語言為基礎的文言相對應,文學上有“文必秦漢”的口號。雖然這一口號出現在明代,但它所代表的傾向很早就發端了。
“文必秦漢”意即文章寫作以先秦兩漢為榜樣,而先秦文章又是最高范本。兩漢之所以會成為文章寫作中的“亞圣”,是因為在時間上與先秦最近,“去圣未遠”,繼承和發展了先秦文學傳統。揚雄很難說是兩漢文學最有成就者,但他無疑是文學上的多面手,而且他既是創作者,又是文學理論家,因此,他的見解特別值得重視。他在《自序》中說:
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高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于內,不求于外,于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邊逸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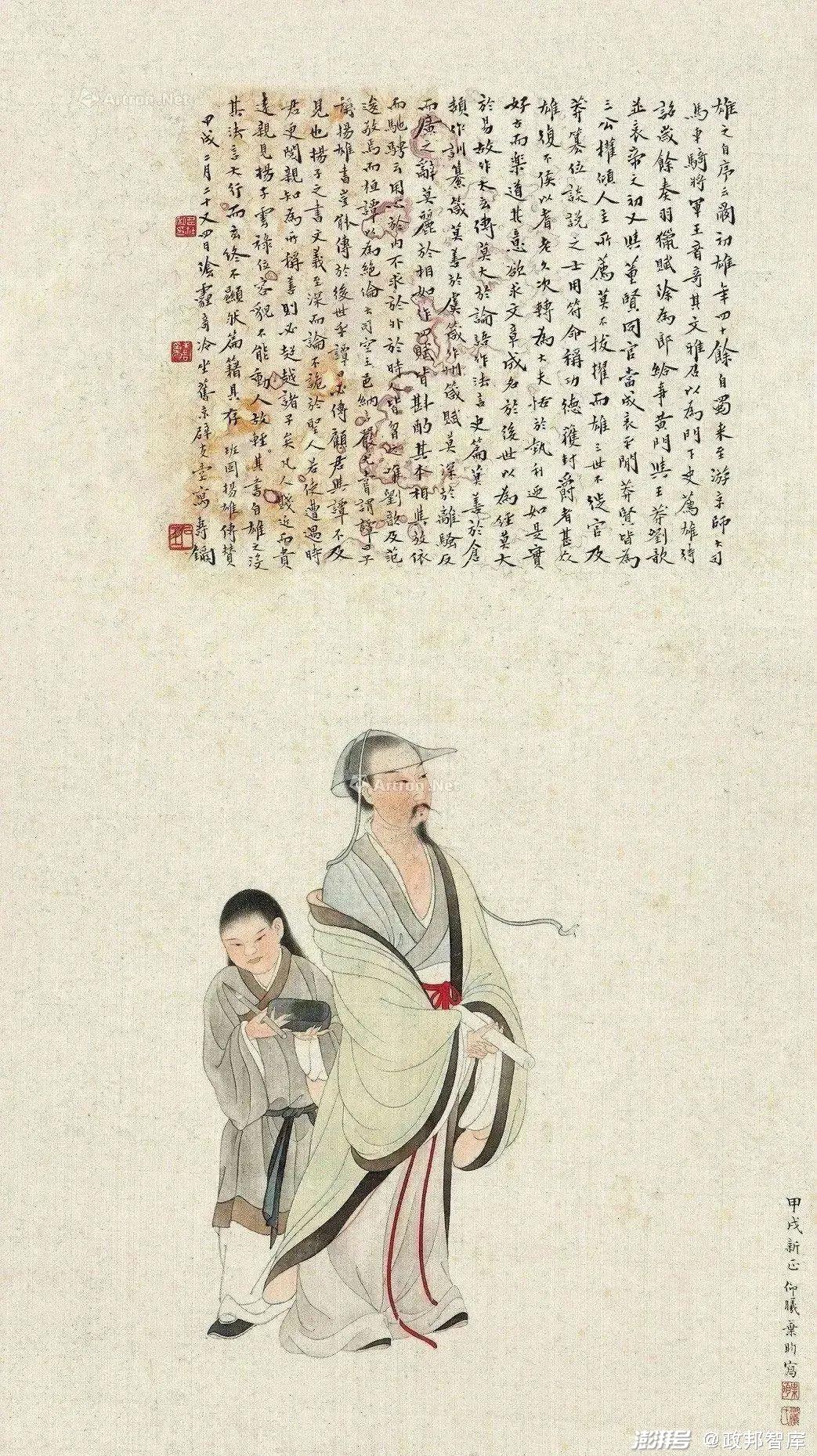
揚雄取法的對象主要在先秦,傍及漢代司馬相如。由于他首倡在先秦散文規范中寫作,故被后來的古文運動推為先驅人物。
魏晉六朝文學在一定程序上偏離了先秦兩漢軌道,但很多人并沒有忘懷于以前的模式。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中說: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
他認為,所有文體都萌芽于先秦,以先秦的某類文體為根端。先秦文章不僅是后來文章的源頭,還是不可企及的范本和無法超越的疆域:“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越,終入環內者也”。他相信先秦散文是后代文章寫作的寶庫:”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劉勰的這一思想雖然并沒有徹底地貫穿在他的所有理論中,而且,在當時的創作實踐中也很少有響應者,但是,通觀魏晉六朝文論,幾乎沒有人敢正面否定先秦散文。人們在創作中可以自由活動,但不能在理論上無視以前的權威。
對先秦兩漢散文范式強調最力的還是古文運動旗手韓愈。他在《答李翊書》中主張向古人看齊,“志乎古者必遺乎今”,寫好古文要學慎始習,以先秦兩漢文章為師: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7]。
他提出,學習古人就要學其正宗,“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只要學的是三代兩漢之書,而且是好書,那么寫作古文時就能“取于心而注于手,汩汩然來矣”。柳宗元也是古文的大力倡導者,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盛贊”恢恢然有古人形貌”的作品,并總結了先秦兩漢優秀散文的特征,主張有針對性地借鑒它們: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以厲其氣,參之盂、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8]。
在柳宗元看來,先秦兩漢文章無論是內在精神,還是表達方式,都可以給后人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韓柳對于古文的再發現,為文章寫作樹立了不變的樣板,宋代的歐陽修、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試圖接近這個樣板。
(此文未完待續)
注:[1]《日知錄集釋》卷十九。
[2]同上。
[3]同上。
[4]奉國堂版《李穆堂詩文全集》:《穆堂別稿》卷四十四。
[5]《隨園詩話》卷二第六十九.
[6]《漢書·揚雄傳》,百衲本《二十四史》
[7]《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十六,四部叢刊本.
[8]《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三十四,四部叢刊本.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