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馬欣榮丨在割裂的世界尋找彌合的可能:評《我們和他們?》
文 _ 馬欣榮(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
過去幾十年來,很少有話題像移民(migrant)這樣在西方社會得到廣泛的公共關注。在英國,有關移民的探討頻繁見于報端,出現在公共討論中,見于議會辯論中。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當權,民眾中總有人對政府的移民管控不力、遣返非法移民和對難民問題的處理表達不滿。在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和此后英國脫歐的背景下,被民粹裹挾的排外的民意,似乎與西方社會以往倡導的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念格格不入,影響了英國、歐盟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這個時代似乎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全球化,卻也比任何時候都更急于區分“我們”和“他們”。
?Us & Them? The Dangerous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我們和他們?——移民控制的危險政治》,以下簡寫作《我們和他們?》)出版于歐洲難民危機和英國脫歐之前。在這本書中,時任牛津大學教授的布里奇特·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重新審視了我們所處的這個被建構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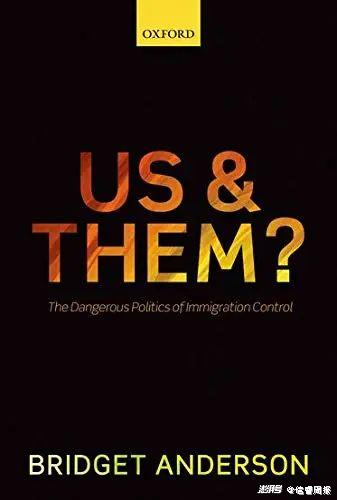
Us & Them?
Bridget Ander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公民”與“移民”(非公民)有多種形態,常常被理所當然地用來區分人群。在英國公共媒體和日常政治語境中,移民通常情況下并不用來指代那些具有靈活的公民身份、不受國籍限制的精英階層,而是主要用來指代從全球南方國家遷移而來的底層窮人。換句話說,移民代表著技能不高的勞工、尋求庇護者以及不具有合法身份的人,這個稱呼背后有一種階層化和種族化的想象。
然而,誰可以被算作公民,擁有公民身份?移民指的是誰?與移民有關的敘事是如何在作為日常生活的政治中被呈現的?不同于主流社會科學研究在現有的分類基礎上對概念進行機制和因果分析,安德森退后一步,帶領讀者重新反思在當代社會中被視作理所當然的一些概念,并梳理這些概念是如何在現有的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體系中被塑造的。
與一般的學術著作不同,《我們和他們?》開篇講述了一個伐木工人與森林王國的童話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個貧窮的伐木工人離開森林里的家,抵達了一個富裕王國的邊境。守邊的衛士堵住了他的去路,他對衛士說,雖然自己很窮,但特別勤勞,保證會用勞動讓這個王國變得更偉大、更富裕。衛士同意放他進入,正如這個窮人所言,五年之后,他的勤勞工作讓王國更加富強了。此時他向衛士請求說,如果你認可我的價值,我可以再多提一個請求嗎?可以允許我在森林里的妻子和孩子來這里和我一起謀生嗎?明智又公正的衛士欣然同意了伐木工人的請求。于是他和家人永遠地生活在一起,為這個偉大的王國工作。
在現實中,這個想要進入王國工作的伐木工人可能是逃離暴政的難民,可能擁有一定的技能,可能拖家帶口,也可能是一名單身的女性。理想的結局當然是他/她被接納并融入一個充滿包容的王國。但是,美好的結局往往只出現在童話故事里,在現實社會中有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邊界。這些邊界是攔阻愛琴海上偷渡者的船只,是位于美墨邊境的邊界墻,更是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因此,思考誰是“我們”和“他們”,就是在嘗試理解公民和移民在多大程度上彼此相通,又在何種意義上各自不同。

希臘邊境的敘利亞難民營。
圖片來自Unsplash @Julie Ricard
安德森用“價值的共同體”(community of value)引領全書。她認為,要理解英國乃至全球當下的移民問題,首先要回到對公民身份的理解上。現代國家宣稱的公民身份并非單純指法律所賦予的身份,而是指代因人們共享著的一系列價值而形成的共同體。在英國的國家話語中,這些“價值的共同體”被表述為法制、人權、自由以及對勤勞工作的尊重等。“價值的共同體”之內的人們被分為好公民、失敗公民(如罪犯)以及非公民(即移民)。而通常情況下,移民更容易被想象成是難以管控的、非法的,甚至與犯罪聯系到一起。
在《我們和他們?》一書中,安德森從歷史的視角對移民控制進行了回溯。在14世紀的英國,底層的窮人與土地和領主緊密相連。那些脫離領主的掌控、離開了他們本該勞作的領主土地的人被稱為流浪者或無家可歸者(vagrants)。這些人在當時被認為是失控而危險的, 是對社會秩序的一種潛在威脅。這樣一套對流動的勞動者進行管控的邏輯對于現代人來說并不陌生,只是當時的管控對象是國內流動的窮人,而現在移民管控的對象是跨越國境而來的外國移民。

What is Called Vagrancy (1854), Alfred Stevens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歷史上的英國是一個向外移民及殖民的帝國,其真正意義上迎接較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是從20世紀中期開始的。當時的移民主要來自位于西印度群島、西非以及南亞等區域的前殖民地國家。二戰后,作為英聯邦的子民,上述殖民地國家的勞動力極大地參與了英國的戰后重建,補充了宗主國因戰爭而欠缺的勞動力,使英國不需要像其他西歐主要國家那樣從鄰國引進客工(guest workers)。與此同時,因二戰而尋求庇護的人們也被英國社會熱情地接納。來自奧地利和意大利的難民代表著一群反抗強權、追求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強者;來自蘇聯國家的戰士、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以尋求庇護的難民身份到來,被認為是自由民主價值的勝利。而這段對勞工移民和難民的接納歷史,在2000年前后出現了新的轉向。
彼時,來自欠發達國家以及歐洲一體化之后的移民叩響了包括英國在內的全球北方發達國家的大門。與之前體面地投奔自由國家的移民和難民不同,這些人大多是渴望改善生活的勞工或因戰爭和政治原因導致的難民,其中也包括被認為是借難民之名而來的經濟移民。在一些媒體的渲染之下,對這些外來移民的排斥與政客的政治動員相互強化。時任工黨領袖參選的政治口號之一是便是關于移民的:“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人”(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這句口號為以底層民眾為主的選民描繪出回到福利時代的美好藍圖,應允本國公民以工作機會和福利,這對于一部分選民來說極具吸引力,但在安德森看來,且不說無法界定什么英國工作以及誰是英國工人,這樣的政治動員與全球化時代的工作和雇傭關系的市場邏輯本身也是相悖的。在全球資本產業鏈下,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性和靈活雇傭正在取代原來福利國家的固定工作制度。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本土勞動者極少受雇于不穩定且收入較低的3D(Dirty, Difficult and Dangerous)工作,這類工作更多是由來自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外籍勞工移民承擔的。這一具有時代特征的全球經濟格局不是政治口號可以輕易改變的。

跨國灰姑娘
藍佩嘉
吉林出版集團, 2011
從事3D工作的勞工移民、非法移民以及被人口販賣者是安德森的重要研究對象。她指出,這些是在“價值的共同體”中被認為最不符合道德標準的一群人,往往也是在媒體和公共輿論中被污名化程度最高的一群人。實際上,“非法”首先是由法律建構起來的一種身份,并不意味著這些人的行為反常,也不意味著犯罪。移民的非法身份并非一成不變的,非法入境者可以通過申請難民庇護或其他身份合法化項目成為合法移民,這在2004年歐盟國家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早有實踐。而且無論是英國還是其他國家的研究都發現,非法移民的犯罪率并非高于本國公民,那種夸大非法移民犯罪率的報道具有一定的誤導性。安德森的研究印證了社會人類學家德·吉納瓦(De Genava)提出的移民可遣返性(deportability)[1]的后果,即可遣返性將移民與公民做了本質的區分:犯罪的公民雖不符合“價值的共同體”,但并不會被遣返出境;未犯罪的非法移民則隨時有可能被遣返出去。可遣返性導致非法移民更容易接受被剝削的工作,甚至不敢爭取被法律保護的基本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社會對移民的聲音并非鐵板一塊。基于人權的基本原則和對“好公民”的理解,地方性的社群也在進行著一些反對遣返的實踐。比如,作者在書中所舉的庇護城市運動 (the city of sanctuary)的例子。參與這些運動的人大多來自地方社區,他們之所以反對遣返以及相關的官僚決策,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看到了身邊的移民個體和家庭對所在社區的切實貢獻,這些面臨遣返壓力的人包括勤奮學習的學生、教會事務的參與者和社區服務的志愿者。他們雖然有某種“非法”的標簽,但其行為符合“價值的共同體”的“好公民”標準。另一方面,地方性的社群尤其警惕與移民相關的強制性權力的擴大。因為“強制的危險在于它可能永遠不夠強硬。越是強制執法,越多的問題可能會被掩蓋”[2]。而作為共同生活在社區中的鄰里、朋友和同事,為尋求庇護者提供有安全感的環境和建立友善的關系,對移民管控保持審慎,是對強制性權力無限擴張的一種抵制。

“庇護城市運動”的logo
盡管這本書以媒體報道、政策文本為主要的資料來源,較少如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樣側重于訪談,但其對全球不平等的關切和底層視角始終一以貫之。在這本書中,“移民”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群面目模糊的人,我們可以在作者冷靜客觀的分析背后看到一組群像:在愛琴海客船上喪生的難民、渡過多佛海峽的偷渡客,以及大洋彼岸因美墨邊境筑起邊界墻而被迫與家人分離的移民。從歷史的維度來看,現代移民所經歷的,也是離開領主土地的流浪者和來自殖民地的勞動者曾經歷的。用作者的話說,當代英國公民眼中的“他們”,其實在歷史中,也可能就是作為平民的“我們”。而面對喧喧嚷嚷的反移民聲音,安德森給讀者提供了另一種視角:與其說難民危機和移民問題正在影響歐洲,不如說歐洲的危機正在影響著一群流動的普通人——那些被稱作移民或難民的人。
本書開篇所講的進入森林王國的伐木工人的故事隱喻了現代社會的普遍性問題。在高歌猛進的現代社會,主權國家在面對各種各樣的“他者”時,普遍用一套控制移民的體系允許一群人進入,而將另一群人拒之門外,這并非英國所獨有。
公民身份不僅關乎傳統國家與公民在社會契約下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它也是一種世界體系,決定了什么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進行跨國流動。具有全球北方國家(如美國、歐盟國家)身份的人,比那些來自欠發達國家的人享有更多的全球流動的特權。而在同一國家內部,底層勞工的跨國流動機會遠低于具有彈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的精英階層。齊格蒙·鮑曼在《全球化:人類的后果》中對此也有十分生動的描述:“對第一個世界,即日益超越民族和疆界的世界的居民——全球商人、全球文化經理和全球學者而言,國界已被夷平……對第二個世界的居民而言,移民控制、居住法、‘清洗街道’和‘零容忍’政策所構筑的墻垣越筑越高……前者隨意地暢游四方,其樂無窮……所到之處總受到笑臉相迎、熱烈擁抱。后者偷偷摸摸地出行,經常是非法偷渡,坐的是擁擠不堪、經不起風浪襲擊、隨時有可能下沉的小船,卻要比那些坐豪華郵輪的人掏更多的腰包,而且到處遭人白眼;更有甚者,如果觸了霉頭,到達目的地時,會被抓起來,立即驅逐出境。”[3]

全球化:人類的后果
齊格蒙特·鮑曼
商務印書館, 2013
對于那些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掙扎于生存問題的人來說,即便知道會被剝削,依然不斷地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進入更為發達國家,接受這些國家對他們權利的各種限制,因為在他們看來,“比在海外受剝削更差的是什么?恐怕就是不能在海外受剝削”[4]。安德森想要在《我們和他們?》一書中闡述的觀點在于:是全球不平等的結構產生了“移民問題”(the problems of migration),每個人都是這個結構的參與者,因此,不應該將“問題”簡單歸因于移民本身。從這里出發,我們才可以在這個割裂的世界,尋找一種彌合的可能。
(復旦大學羅思雨博士對此文亦有貢獻,特此感謝。)
參考文獻:
[1] DE GENOVA N. Migrant 'Illegality' and Deportability in Everyday Life[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2,31: 419-447.
[2] ANDERSON B. Us & Them? The Dangerous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6.
[3] 齊格蒙·鮑曼. 全球化: 人類的后果[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3: 86.
[4] MARTIN P. Managaing Labor Migration: Temporary Workers Programs for the21th century[R]. Geneva: ILO, 2003: 30.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85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