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楊吟竹丨自由意志、測謊儀與“讀心術”
文 _ 楊吟竹(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博士在讀)
面壁者羅輯,我是你的破壁人。——《三體II》
我們的顱骨包裹著的果凍狀物體,重約1400克,濕潤黏稠,脆弱易毀,卻隱藏著不可穿透的無限宇宙。人們向來著迷于觸碰這片不可觸及的宇宙:在科幻作品《X戰警》中,擁有讀心能力的X教授是最強大的變種人之一;在《三體》中,擁有碾壓性科技的外星智慧生命“三體人”唯獨不能看穿人類的思想,由此誕生的“面壁計劃”[1]讓個體的大腦成為人類的最后一道防線。
如今,讀心術已不再是獨屬于至高者的領域。隨著當代神經科學,尤其是腦電圖(EEG)、腦磁圖(MEG)以及神經影像學技術的發展,讀心術似乎已在地平線上顯現,易朽的凡人也能觸手可及。人類的每個心理狀態都對應著特定的大腦活動模式,通過EEG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手段測量大腦活動,隨后用計算機進行模式識別,就能“解碼”出與這一特定大腦活動模式相關聯的心理狀態,并有可能從大腦活動中直接讀取人們的想法——這也就是“讀腦術”(brain-reading)或“解碼心理狀態”(decoding of mental states)。如今,借助相關技術我們已能解碼出非常具體的視覺圖像、記憶內容,乃至決策與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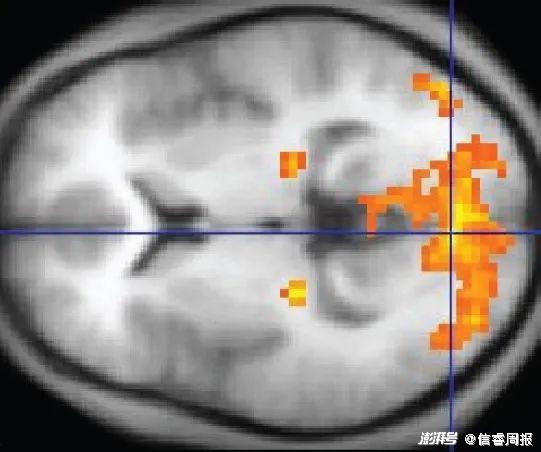
該fMRI圖像中,黃色部分為大腦中的活躍區域。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不過,在倫理層面,人們對讀心術有著數不清的擔憂。譬如在《少數派報告》與《心理測量者》描繪的反烏托邦世界中,基于解碼大腦活動而設計出的先知系統能夠提前偵測有犯罪意圖的潛在犯,并在其尚未實施犯罪行為之前就進行逮捕乃至處決,但這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讀心術不僅有可能侵犯人們的隱私與自由,甚至有可能帶來一個恐怖的新世界。

《心理測量者》中,警察通過特殊槍支識別對象的反社會人格系數,從而在案件發生之前就關押/處決潛在犯
讀心術蘊含的力量使人心馳神往,也令人心生畏懼。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伴隨著前所未見的風險。在這一背景下,神經倫理學應運而生。一方面,神經科學領域的進展給傳統的哲學與倫理學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飽受爭論卻停滯不前的問題也被革新。比如,在人類是否擁有自由意志的問題上,以往的哲學家只能紙上談兵,但本杰明·里貝特(Benjamin Libet)卻通過實驗(Libet's Experiment)發現,能夠根據人們做出行動的幾秒之前的大腦活動預測出未來的行為,這代表著人們或許并無自由意志。[2]隨著更多神經科學實驗的開展,這柄利劍能否劈開纏繞已久的戈爾迪烏姆之結?另一方面,神經科學這一學科本身以及與之相關的神經技術又派生出嶄新的倫理學問題,一些隱蔽卻持存的問題也被淬亮。比如,以讀腦術為基礎的謊言檢測若被證實有效,這項技術是否應被大規模使用?在下文中,我們將以解讀意圖(intention)的讀腦術為例,分別對以上兩個方面展開討論。
人類擁有自由意志,能夠自由地選擇、自由地行動,并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從古至今,大多數人對此深信不疑,這一信念也構成了法律與倫理體系的基石。在羅馬法中,構成犯罪的必要條件包括犯罪行為(actus reus)與犯罪意圖(mens rea),后者指的是必須有實施犯罪行為的主觀意圖。因此,一個人不用為那些并非自己自由選擇的行為負責,且一個人能夠自由選擇,就意味著此人在當下可以有別的選擇,而不是只能做出某一行為。
然而,當代科學的物理主義世界觀對上述圖景構成了沖擊——行為由大腦的生理學過程產生,大腦則依據自然律運作,這些自然律都能被還原為最基礎的物理定律。如果行為像被預設的程序一樣,不過是一系列被預先決定的因果律過程,那么我們其實并沒有能力做出規定程序之外的選擇,因而我們并不擁有自由。里貝特實驗就是這種常識圖景與科學圖景撕裂時最戲劇化的體現之一。實驗結果表明,在你有意識地決定要移動手指之前,從EEG記錄的大腦活動的準備電位(Readiness Potential)中,就已經能夠看出你即將移動手指——無意識的大腦信號先于有意識的決定。該實驗結果一發表就引發了軒然大波與強烈質疑,盡管如此,它還是經受住了一代又一代可重復性實驗的考驗,一些繼承其精神的改進實驗也不斷涌現出來。

Neurophysiology of Consciousness
Benjamin Libet
Birkha?user, 1993
在追隨里貝特腳步的當代實驗中,存在一個不再僅限于簡單的“移動手指”意圖,而是涉及更為復雜的高階抽象意圖的研究,[3]這避免了對原實驗中運動決策本就只需較低程度意識水平的批評。在這項新實驗中,被試需要就給出的運算數字自行選擇“相加”或“相減”,研究者并不能提前知道其選擇是什么,但是通過分析fMRI測量的大腦活動模式,研究者能夠以約60%的正確率“讀”出被試選擇的運算方式,也能解碼出那些可預測被試運算行為的大腦活動模式在何時出現。[4]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無意識的決策出現的時間要比被試報告的有意識決策早好幾秒。
這樣的實驗結果是否顛覆了我們對自由意志與主觀能動性的直覺,也撼動了我們對道德責任的信念呢?這不只是哲學家關心的形而上學問題,也將對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但舉起反對旗幟的人絕對不在少數。比如,一些非決定論(indeterminism)的支持者會認為,量子力學挑戰了物理世界的確定性,因此那種完全被因果決定的世界觀本來就是錯誤的。相容論者(compatibilists)則會認為,一個被因果決定的世界與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不矛盾,需要重新審視的是對“何為自由”的定義。更有甚者認為,從自由意志到道德責任的理論跳躍是不合理的,無論人們是否擁有自由意志,都不能對道德責任構成挑戰。本文將暫時擱置這些傳統的哲學問題,把目光聚焦在與讀心術相關的質疑上。
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你可以有意識地“撤回”(veto)箭在弦上的行動,那么這是否保住了一種反向的自由意志(free won't)?里貝特本人就支持這條思路。他認為,行動前無意識的大腦活動的啟動掩蓋了一種內隱的自由選擇,即到底是在啟動之后繼續行動,還是取消行動。在有意識的行動意圖與無意識的大腦活動之間的幾秒時間,足以給一次可能的“撤回”留下余地。
在一些實驗[5]中,研究者要求被試在看見綠燈后自由地決定何時按鍵,但如果綠燈轉為紅燈,則必須停止一切行動。結果顯示,在無意識決定后較早期的時段內(行動前數秒),如果紅燈出現,被試完全可以做到停止行動。但如果紅燈出現在行動前200毫秒以內,開弓就沒有回頭箭了。

在一系列神經電位和肌電反應之后,被試仍有可能撤銷自己的按鍵行動(BP)。
圖源:SCHULTZE-KRAFT M, BIRMAN D, RUSCONI M, et al. The Point of No Return inVetoing Self-Initiated Movement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2016, 113(4): 1080-1085.
存在“撤回”已經啟動的運動的可能,似乎說明了準備電位確實能預測后續行動,但未必能決定后續行動。或許我們可以后退一步,將解讀從決定論式轉向概率論式。根據后者,人們的決策與行動并不會被那些先于行動的無意識腦信號決定,但會受其影響。這些無意識腦信號更像是一種推力、一種能對后續行動進行某種限制的傾向,它們能改變行動的概率,但不能因果地決定行動的發生。
另一個問題是,里貝特類型的實驗在設計與技術上是否真正反映了我們關心的問題?盡管涉及加減法的實驗相較于僅涉及手指運動的實驗已經“高階”了許多,但相比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復雜決策,它依舊非常簡單。自由意志所涵蓋的內容要遠超于此。正如前文所述,簡單粗暴的模式識別是目前破解大腦密碼的主要技術手段。為了將大腦活動模式翻譯為相應的想法,它需要在兩者之間建立穩定的聯結,而此種聯結需要測量被試不斷思考某一想法時的大腦活動。但在現實情況下,某一想法與其心理狀態的映射關系可能不是一對一的,而是任意的、無限多的,這或許也部分解釋了前文實驗中讀心術不盡如人意的正確率。目前的讀心術只適用于一些極為有限的心理狀態,而在面對現實生活中模糊多變、即興隨意的想法時仍然捉襟見肘。
與之相關的是,目前的技術也難以應對極大的個體差異。人們的想法通常由過往的經驗塑造,而不同的個體經驗所產生的與同一概念相關的聯想和引申則天差地別。或許正因如此,不同大腦之間解碼心理狀態的細節完全不同,不具有跨個體的可遷移性。此外,即使面對的是同一個體,讀心術也不具備跨時間的可遷移性。目前的解碼過程預設了心理活動與大腦活動模式之間的靜態聯系。然而,在較大時間跨度與持續學習的塑造下,同一個體對某一想法的相關聯想也會發生改變:在談及“理想”這一抽象概念時,曾經的你與現在的你所注視的還是同一片景象嗎?
如此看來,我們或許沒必要大驚小怪。強大的通用讀心機離我們還有十萬八千里,人類的自由意志也沒那么容易被推下神壇。西比拉系統距離孵化產生還差10086個槙島圣護,而在三體人入侵地球之時,我們多少還是可以指望一下“面壁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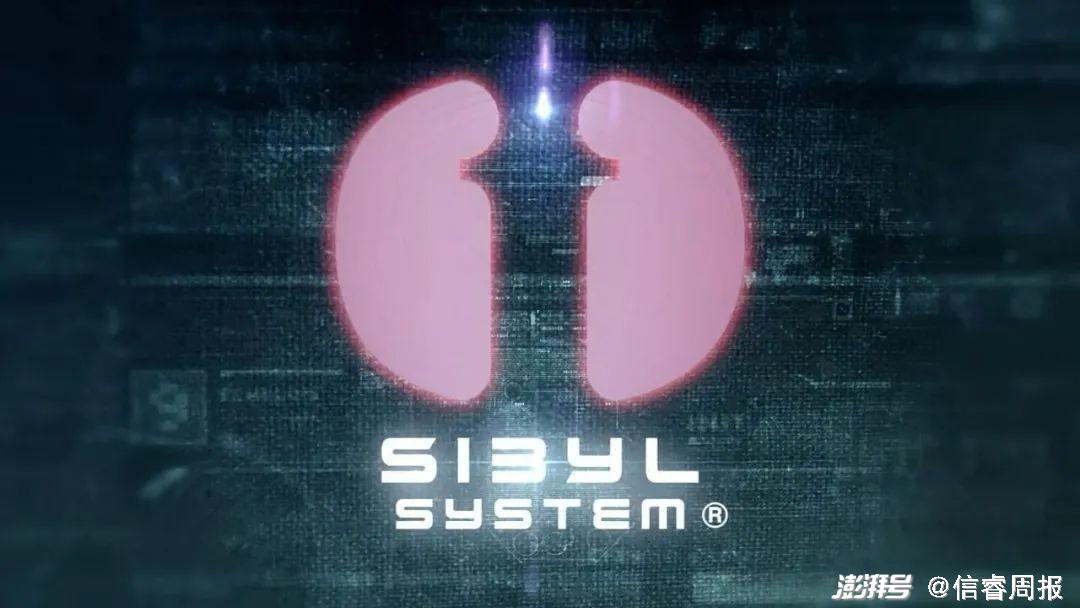
《心理測量者》中能夠“讀心”的西比拉系統是由數百個特異者的大腦組成的
但且慢,即使我們尚未擁有能夠實時、高精度、適用于不同個體且無需長期校準的讀心機,前文提到的技術與實驗依舊指向了一些需要引起關注的神經倫理學問題。比如,讀心機可以被當成測謊儀使用,它無需解碼出受測者腦中的所有想法,而只需讀取一個意圖:說謊了/沒說謊。這是一個簡單的二元決策。所以,即使通用讀心機無法得知受測者為何說謊、其腦中的小劇場編排了什么劇情,能得出是否說謊的結論也頗為有用。傳統的測謊儀器度量的是一些身體指標,如皮膚電導、心率和呼吸頻率。這些指標有效的前提是受測者在說謊時會有較高的喚起(arousal)水平。不過,喚起水平會受到許多其他心理狀態的影響,比如過分的緊張會導致誤報,而老練的受測者能通過控制自己的喚起水平操縱檢測結果。
相比這種間接的度量方式,基于讀心機的測謊儀可以克服上述困難。目前大多數用以測謊的讀心機都會使用fMRI,也有一些使用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在實驗中,研究者會要求被試在一些簡單的問題上說真話或是說謊,并通過對比兩種情況下的神經影像來確定與欺騙相關的腦區。[6]進一步地,可以在目標腦區使用邏輯回歸或一些非線性的機器學習算法,來區分受測者哪次說的是真話,哪次說的是謊言。自2006年起,已經有一些美國公司開始將基于fMRI的測謊技術用于法律、商業和家庭生活中。
但是,在我們為技術的進步歡欣鼓舞之前,有必要冷靜下來思考一些更為初步的問題:測謊技術能否從實驗室直接跨越到現實生活?首先要考慮的是技術的準確性問題。在實驗室環境下,被試說謊是因為實驗者要求其這樣做,現實生活中人們說謊則有各式各樣的原因,其中往往摻雜了復雜的情感因素。很多時候,說謊者的大腦會探測到更高程度的情感波動,而在這種情況下訓練出來的測謊算法很有可能只能區分出受測者哪次受情緒影響更大。這樣一來,在測謊算法應用到新的受測者身上時,人們在想到引發高度心情起伏的事情時說出的真話會被分類為“假”,而更擅長情緒控制的人說出的假話也會被分類為“真”。
與之相關的是基礎概率(base rate)帶來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先要區分算法的敏感性(sensitivity)和針對性(specificity)。前者指的是能在受測者確實說謊的情況下正確地識別出說謊情況的概率,后者指的是能在受測者并沒有說謊的情況下不發生誤報的概率。在一些研究[7]中,敏感性高達百分百的算法卻只有較低的針對性,這會導致在并沒有人說謊的情況下錯怪了很多老實人。我們可以假設人群中存在說謊者的基礎概率本來就很低,但即便如此,也很容易發生大批冤假錯案。
那么,要達到多高的準確性,測謊技術才能投入使用?如果這一技術被大規模使用,較高的假陽性(false positive)率可能會使受冤枉的人被污名化,在尋找工作時遭遇歧視;而如果為了降低假陽性率選擇降低敏感性,也可能要為此付出不小的代價:美國中情局特工巴拉維(Humam Khalil Abu-Mulal al-Balawi)在順利通過測謊儀測試的情況下,作為雙面間諜殺死了七名中情局特工。這固然是傳統測謊儀的疏漏,但這樣的問題在神經讀心術的技術手段下也難以避免。在敏感性與針對性不可兼得的情況下應該偏向哪邊?這都是神經倫理學家需要思考的問題。

傳統的測謊方法。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無論我們是否做好了準備,讀心術都已經降臨。目前看來,它既不是阿拉丁的神燈,也不至于成為潘多拉的魔盒。神經倫理學能幫我們澄清一些令人憂心的問題,也能幫我們更好地面對這些問題。它教我們在何時保持警惕,在何時無需恐慌,又在何時應當將注意力從令人目眩神迷卻只是虛晃一槍的問題上移開,放在那些當下更需要被關注的問題上。
參考文獻:
[1] 部分人類個體(“面壁者”)僅在自己的大腦中完成戰略計劃的制定和執行, 不以任何形式與外界交流, 通過將行為與思想分離, 使敵人無法判斷其真實意圖。
[2] LIBET B, GLEASON C A, WRIGHT E W, et al. 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 (Readiness-Potential)[M]//Neurophysiology of Consciousness. Boston, MA: Birkha?user, 1993: 249-268.
[3] SOON C S, HE A H, BODE S, et al. Predicting Free Choices for AbstractInten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110(15):6217-6222.
[4] 有趣的是, 在這里能解碼出內容的腦區和能解碼出時間的腦區是分離的。前額極區與后扣帶回(Frontopolar and Posterior Cingulate)能預測被試究竟想做加法還是減法, 但不能預測決策的時間;前運動輔助區(Pre-SMA)能預測被試做出決定的時間, 但不能預測決定的內容。
[5] SCHULTZE-KRAFT M, BIRMAN D, RUSCONI M, et al. The Point of No Return inVetoing Self-Initiated Movement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2016, 113(4): 1080-1085.
[6] FARAH M J, HUTCHINSON J B, PHELPS E A, et al. Functional MRI-Based LieDetection: Scientific and Societal Challenges[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2014, 15(2): 123-131.
[7] ANDREW KOZEL F, JOHNSON K A, GRENESKO E L, et al. Functional MRIDetection of Deception after Committing a Mock Sabotage Crime[J]. Journalof Forensic Sciences, 2009, 54(1): 220-231.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84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