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離題|我們只能遠望別人的彼岸
【編者按】
《離題》是澎湃人物的記者手記欄目。所謂“離題”,是寫在報道之外,也是記錄報道未能窮盡之處。有一篇報道從0到1的過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還有報道者的一些沉思。
這篇手記來自《柳智宇下山做咨詢:“要面對自己的無力感”》和《“零分考生”徐孟南這些年:上了大學(xué),仍在“南墻”前徘徊》兩篇報道的作者葛明寧。報道描畫了兩個看上去截然不同卻處境相似的人,他們有過執(zhí)念,也有過空想,有說不出的苦悶,也有回不去的過往。無論如何,他們在真實逃離了一些俗世的期待之后,選擇了一種“彼岸”,哪怕他們落子有悔,至少還記得來時的路,也直面過生活的晦暗、混沌了。

與喜好談?wù)摾硐氲娜苏f話,很容易陷入一種虛無。對方的構(gòu)想很好,但無法指給你看,因為,那不是現(xiàn)實中的東西——“‘尚’不是現(xiàn)實中的東西。”他們會對你強調(diào),說自己有過深思熟慮。你只好點頭微笑,帶著滿頭滿腦的懷疑。
他們還都習(xí)慣在自己的講述中隱身,把自己的各種具體行為解釋成外物的鏡像,可能難免帶幾分驕傲,覺得自己是一面明鏡。而作為觀察他們的記者,我們則會苦惱,因為這面鏡子折射出的影像實則帶著主觀痕跡,又過去多年,與新聞意義上的事實很有距離。
比如,從前的北京大學(xué)數(shù)學(xué)系高材生柳智宇,本科畢業(yè)后出家,到寺廟里待了十多年。今年九月,接受我采訪時,他回憶自己走向佛教的原點——在華中師范大學(xué)第一附屬中學(xué)讀書的時候,他感到同學(xué)們讀書很焦慮、很苦;他住得離學(xué)校很近,經(jīng)常眺望著學(xué)校的教學(xué)樓和宿舍,為同學(xué)們祝福。

在柳智宇的這一段講述里,他,一個有血有肉的少年,變成了一個空中的視角;而幾乎與柳智宇望宿舍同一時間,一個學(xué)業(yè)上沒那么突出的安徽高中生徐孟南,也在左右打量自己的同學(xué)。在他眼里,有一些是勤奮但不特別聰明的,他覺得他們過得很苦,徐孟南思忖,要是壓力小一些,他們反而能學(xué)得好些。
這兩人自己的生活反而沒那么好看。柳智宇埋頭做題,也讀經(jīng)典,當(dāng)時看起來是一個滿口道理的老成學(xué)生,有的同學(xué)很不喜歡他;徐孟南上課睡覺、下課泡網(wǎng)吧,過著一種似乎荒唐又無聊的生活。后來,他為了宣傳自己設(shè)計出的教育改革方案,選擇在高考卷上大肆涂畫來制造新聞。有媒體在事發(fā)后兩個月內(nèi)采訪到他的班主任,班主任只形容他,內(nèi)向、不壞、不愛學(xué)習(xí)。
他們當(dāng)然不是嚴格對仗的關(guān)系,我與兩位采訪對象相處的時間也比較有限,不過,恰好對他們的采訪安排在前后兩天,我的感受顯得更深一些。這兩個出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的人都提到過自己有“無路可走”的感覺——在他們的描述中,人生中最重要的選擇之一是被一種大于他們自己的理想或熱情推著上路的。
我在想,難道真有人能自我認識并成為“道”的容器嗎?在熱情與犧牲之外,這些人沒有其他的情緒和體驗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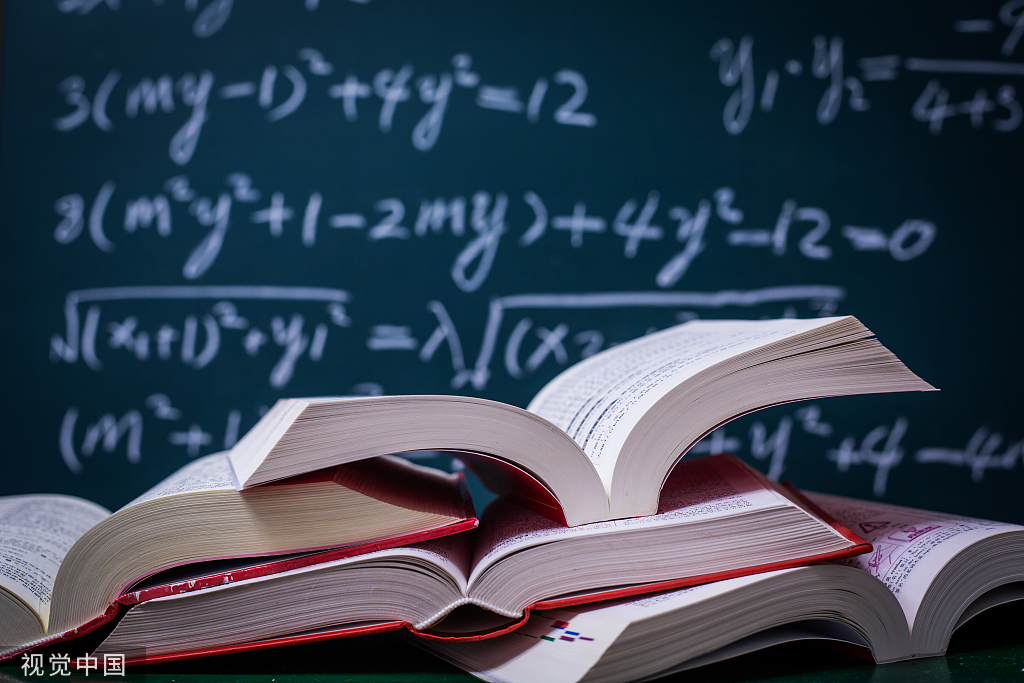
要說這些“猛士”有什么情緒,我所知覺到的,恰是一種也許比他們最觸目的行為本身更不討人喜歡的感受,那就是對實際生活的深刻的厭煩。
柳智宇一度很喜歡學(xué)數(shù)學(xué),以為這么好的學(xué)問可以用來溝通天地,不過,他讀高中時幾乎自覺地摒棄了日常生活。他為了學(xué)數(shù)學(xué)強烈要求自己不打游戲、不戀愛,父母以為是暫時的,他自己覺得是永久的。進入北大,卻逐漸發(fā)現(xiàn)數(shù)學(xué)好像只在教室黑板上才驚心動魄,與大千世界幾無關(guān)系。
他說了一句顯然會讓觀眾感到有炫耀之嫌的話:本科同學(xué)大多要不轉(zhuǎn)行搞金融,要不轉(zhuǎn)行搞計算機。可能在很多人看來這都是很好的出路。但柳智宇不喜歡,這距離他設(shè)想達到的境界相距太遠了。
在社會意義上,徐孟南好像“低”得太多,雖然他也曾是一個鄉(xiāng)鎮(zhèn)中學(xué)里的優(yōu)等生。兩個采訪對象苦悶的內(nèi)容各異,但是差不多的無法發(fā)泄。徐孟南也有一些讀書上的聰明,但容易緊張,不耐受學(xué)業(yè)壓力。他不對什么人抒發(fā)自己的難處,想來也是少有人能理解一個學(xué)習(xí)不錯的學(xué)生怎么會厭學(xué);在他的回憶里,父親和老師們都用一種世俗的邏輯教導(dǎo)他要上進——離開農(nóng)村,到城里去找一個辦公室工作,成家立業(yè),最好幫一幫兩個弟弟。可是徐孟南樸素地覺得城里憋悶,住在鄉(xiāng)下比較好。
一個在北大,一個發(fā)生的時間早一些,在蒙城縣第二中學(xué),他們都感到學(xué)習(xí)很沒有意思,或者,用一種更精神化的表達:很沒有意義。
我們總是忘記,一個占據(jù)優(yōu)勢的人,也有可能不喜歡這個游戲,這可能是一種非常簡單的不喜歡,與普通人在每天的生活中經(jīng)歷的樁樁件件的刺痛,并沒有什么區(qū)別;而一個人可以出國讀博士,不意味著他樂于出國讀博士;這是一種想當(dāng)然的思維模式。
哪怕我們認同某一行為將有好的結(jié)果,也不能否認它的過程可能極其痛苦,或者計量之下,它有過低的“性價比”。
他們身邊的社會好像沒有提供一個溫和一些的出口,如果處理不了厭煩,他們只能投往當(dāng)時自身也并不了解的“彼岸”,即寺廟,或者一個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的“壯舉”。這是一種真實的困境,一種“無路可走”。
他們后來又有了各自的生活。對比之下,我還想要喟嘆幾句,我們這些疲勞的“正常人”,是不是已經(jīng)生活得只余下厭煩,而不太記得憧憬過的彼岸在什么方向?
我們沒有過自己的彼岸嗎,無論它多大意義上實際存在?我們沒有過青春年少的愚蠢和勇氣嗎,沒有過自己版本的豪言壯語,哪怕是一時的、輕佻的、酒后的,說要為了它忍受外界的敵視與傷害嗎?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