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播客作為公共史學的一種方法——專訪漢娜·以實瑪利
采訪+撰稿 _ 趙釗

漢娜·以實瑪利(Hannah Ishmael)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的高級研究員,也是英國黑人文化檔案館(Black Cultural Archives)館藏部和研究部的負責人,長期從事公共史學與數字人文多學科研究,探索去殖民化話語下的檔案公共性和數字性,以及檔案的媒介實踐可能性。她本人也是播客愛好者,參與英國黑人文化檔案館播客的策劃與制作。此次對話圍繞播客作為公共史學方法的實踐展開,并從漢娜個人研究實踐的角度思考了公共史學播客實踐的策略、結構、可能性與局限性。
播客這一媒介出現距今已有20多年,但對公共史學的實踐者來說,這種數字化的敘事形式似乎仍然充滿了未開發的潛力。
漢娜·以實瑪利:在社交媒體和Web 2.0平臺出現并對社會產生顛覆性影響之前,歷史學者搜集一手資料并策劃公共史學實踐主要通過電子郵件、電話、口述和收集物品間接進行。20世紀80年代,“音頻博客”(audioblogging)出現,后于21世紀初流行起來,被廣泛用于分享故事和信息。近年,歷史主題播客的數量增長迅速,內容創作者們把這一新興媒介作為傳播歷史知識與分享相關研究的平臺。
歷史學界一直都在關注播客的發展。2016年,美國歷史協會(AHA)圍繞播客的歷史舉辦過一次圓桌討論。2019年,美國國家公共史學委員會的一次研討會討論的主題就是播客。是年2月,《公共史學學家》(The Public Historian)刊發了與會學者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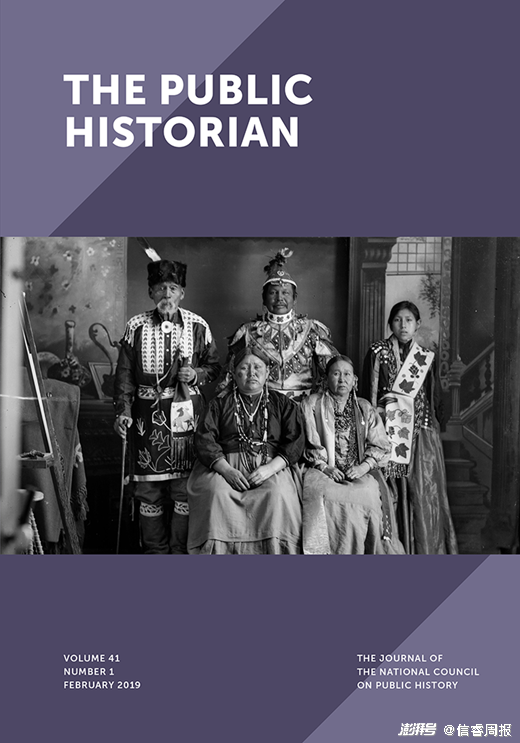
The Public Historian, 2019年2月刊
當我們嘗試將播客視為公共史學的一種實踐方式時,有必要先討論其含義及意義。您如何理解公共史學?
漢娜·以實瑪利:我一直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公共史學的定義仍然存在爭議,關于它是否形成了一個學科、子學科、領域、實踐或從屬于職業歷史學(professional affiliation)的爭論仍在繼續。我通常稱之為一個“領域”,它包含了廣泛的實踐、專業訓練和研究主題。我認為有必要讓這個領域保持靈活性,不斷接受爭論,這在教學環境中尤其重要。公共史學的教學目標是培養下一代公共史學家,他們理解的公共史學應該是不斷變化的、動態的,而不是一套固定的實踐或研究方法。
在我對公共史學的理解中,不變的是“公眾”始終居于中心地位。作為一個在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領域,公共史學是為應對日益嚴重的學術工作危機而做的一種嘗試。事實上,公共史學學者早已意識到,這個術語可以用于該領域創建之前就業已存在的史學實踐,例如博物館策展和口述史研究等。與之不同的是,無論公共史學是為公眾、由公眾還是與公眾,或是它們的某種結合,“公眾”始終居于中心。需要注意的是,這里談論的是許多不同的“公眾”,而非一個單一的群體。公共史學可以發生在學院之外,也可以發生在學院內部,這也動搖了人們對作為一門專業學科的學院歷史的傳統理解。
播客如何成為公共史學的一種實踐方法?
漢娜·以實瑪利:在投身公共史學研究以前,我的學術背景不僅是跨學科的,也是多學科的:我曾學習計算機科學、信息情報和數字人文。在我看來,可以把公共史學的播客實踐看作一種公共史學的數字化轉向,這種轉向也許在檔案數字化上體現得更明顯。公共史學的數字化有力地突破了原本根植于地方的研究,使研究傳播的范圍更大,這種空間性的突破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實現當下人們對有爭議的歷史的理解。阿蘭·梅吉爾(Allan Megill)曾指出,公共史學預先并沒有一個清晰的傳播目的。20世紀初,在電視、網絡等數字技術和受到新技術影響的新的歷史呈現媒介被發明之前,一些評論家已經意識到,媒介不僅需要有再現當代社會的能力,而且能使“過去”充滿活力。歷史的數字化使得參與形式變得多種多樣,人們可以通過網站、播客、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電子游戲和社交媒體來探索歷史知識和思想,更好地理解過去的時代創造歷史的過程,并就當下社會問題進行跨時空的歷史對話,以此獲得新的視角來審視社區、身份和文化,回應所處時代和社會的諸多矛盾。
談到播客作為公共史學的實踐形式時,事實上又回到了我提到的公共史學的目的與意義。根據美國公共史學委員會,公共史學通常被定義為傳統課堂之外的歷史。播客正是如此,它將歷史帶到了傳統學院之外,將“過去”變得可接觸(accessible)。不論是對歷史專業學生還是對普通大眾,播客都擴展了歷史知識可能的傳播范圍,同時兼具教育功能。這些特性為公共史學學者帶來了特殊的挑戰和機遇。就公共史學學者而言,播客提供了一種履行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方式。正如耶魯大學的貝琪·比斯利(Betsy Beasley)和紐約城市大學的大衛·斯坦(David Stein)所說,播客允許學者利用“知識和技能為公共利益服務”。同時,播客打破了傳播學術歷史研究或歷史知識的傳統模式。許多歷史學者或從業者選擇播客是因為它容易訪問,并且相對其他媒介制作簡單。

On the Record
The National Archives
收聽平臺:Spotify等
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托什(John Tosh)曾在其著作中提到“歷史之戰” ,即學院歷史與大眾普遍接受的通俗史之間通常有一條鴻溝,在確立事實和確保論點的嚴謹性方面,兩個群體存在著明顯的分歧。這種矛盾是否也體現在播客中?
漢娜·以實瑪利:學術界和普通公眾對過去的理解存在的差異和矛盾十分有趣,這也是公共史學研究中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對于研究公共史學的學生或專業學者而言,學習或了解專業的歷史只是許多人了解過去的一種方式,而不一定是所有人都選擇的方式,這具有一定的門檻,有時甚至可能是擴大歷史知識受眾的絆腳石。除此之外,廢除感知到的等級制度也是公共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公共史學提出了“共享權威”(sharing authority)這一關鍵問題,即公共史學如何采取不同的形式,在這一背景下誰被賦予權威,為何“過去”是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呈現的等等,這也強調了學院歷史學者只是參與再現過去的眾多伙伴之一,而不再是唯一的權威聲音。
這又引向了另一種爭論:作為公共史學實踐的播客如何共享權威?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布萊恩·巴洛夫(Brian Balogh)曾在其播客“背景故事”(BackStory)中評論道:在全球十大最受歡迎的歷史播客中,只有一檔是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制作的。雖然他的說法存在夸張的成分,但是可以說明歷史學者亟待加入到播客的制作與策劃中,以更正或規范那些所謂的歷史播客,形成一種公共史學播客范式。播客可以被看作共享權威的一種實踐,許多業余歷史愛好者也在嘗試將播客作為自己發聲的媒介,或介紹家族史,或講述怪誕的歷史故事等。在我看來,公共史學家在策劃播客時,或許可以提前預設并搭建起學者與大眾的交流框架,并在這個框架內確定敘事策略。在歷史學者與公眾之間搭建溝通框架是有意義的,也是困難的。

BackStory
Ed Ayers, Brian Balogh 等
收聽平臺:Spotify等
在播客這一媒介下,公共史學學者應如何考慮敘事和語言?
漢娜·以實瑪利:歷史類播客的使命是為普通觀眾探索“過去如何在當下產生回響”,這反映了公共史學強調公眾參與和講述故事(storytelling),鞏固了歷史學者富有歷史知識地、批判地與他人交流的義務。公共史學關注不同的受眾對象,并在具體的表達中使用特定的敘事策略。播客這一媒介提供了這一可能性。播客為公共史學家講述“過去”(包括故事、檔案或研究項目)提供了機會,在某些情況下,音頻敘述可以配合實物檔案或展覽展開。一般而言,歷史劇和講座相似,都有一個固定的線索,包括引言、正文和結論,發言人會介紹相關的歷史演員,并將他們置于預設的歷史背景中,通常以一個主題或時間順序為中心,這種敘事模式也應用于一些歷史類播客。
如前所述,公共史學越來越多地被當作一門用來處理我們和過去之間關系的學問。對公共史學學者而言,思考更個人化、地方化或隱私化的歷史似乎更為重要。當前,已經有許多播客以項目的形式呈現個人敘事,而非直接講述歷史故事所處的更大的歷史背景。事實上,從情感的角度呈現歷史本身并不是一件壞事,但通過這類播客所帶來的情感多少有些容易被剔除。這種個人的歷史制作或歷史意識和我們在更官方的場所(如博物館、紀念館等)制作的“歷史”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我也常常在思考,歷史類播客是否也在某種意義上框定了過去。
我們總是在強調歷史學者的責任,即歷史學者負有應對當下危機的意識和能力。您提到播客更多地被個人化地使用,是否可以認為播客可以保護、展示、解釋可觸及和不可觸及的“遺產”,引起共享的歷史(sharing history)?
漢娜·以實瑪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歷史學都不愿承認其研究的受眾是普通大眾,但如今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與公眾接觸也是歷史學者的職責之一。作為歷史學者,我們從深厚的歷史知識出發,能做些什么來參與當下的敘述和討論?我認為播客至少是一種方式。
我相信,公共史學是一種為社會正義而努力的實踐,它探索種族、階級、性別和性的交叉性。公共史學學者也在嘗試利用播客再現“敏感歷史”或“傷痛歷史”,以對抗當前的一系列現實危機。例如,一些亞洲史學者嘗試利用播客等來回應反亞洲種族主義等現實危機;No-No Boy(“不-不仔”)項目通過民俗音樂、故事和影像檔案講述亞裔美國人的經歷,用聲音形式彌合日本監禁營幸存者的歷史、越南戰爭期間的生活史等歷史創傷;英國黑人文化檔案館則創立了“去殖民化檔案”(DTA)社群,通過播客Community Spotlight(“社區聚焦”)重新解讀英國黑人歷史和近現代泛太平洋身份認同。

DTA.LIVE RADIO
DTA
收聽平臺:Apple Podcasts 等
公共史學并不僅僅是對過去的轉譯,也不只是歷史學家向聽眾講述故事,而更強調將歷史服務于群體或社區,尤其是針對沒有發聲渠道的邊緣群體和非主流文化。我想,你提到的“共享的”(sharing),一方面可以理解為一個群體共同的過去,另一方面則是來自這個群體之外或其邊緣的人在了解這些歷史后形成的某種個人化的體會。播客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進一步推動了民主化的數字公共史學實踐。例如,近年出現了許多LGBTQ+(性少數群體)歷史播客,大多由業余歷史學者主持。
公共史學的迷人之處正是這種互動的存在,公共史學學者不僅在吸納專業歷史學者對過去的理解,也關注著歷史參與者的努力,以及在這種互動中發展出來的一種包容性的知識生產方法。
播客作為公共史學實踐的一種方法,是否存在局限性?
漢娜·以實瑪利:技術和傳媒形式對我們解釋歷史造成的屏障無法完全消除,播客不可避免地具有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特點,且可能陷入懷舊。歷史類播客有可編輯的優勢,例如制作人通過將仔細挑選的原始音頻與其他元素混合以完善敘事結構。可以說,播客在操縱故事方面比直播媒體更有優勢。真實性與播客內容的歷史準確性相對應,而客觀性與主持人制作播客的動機相對應,由于制作人的個人利益以及播客的可編輯性,他們與客觀立場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隨著越來越多的播客來自更大的制作團體,這種客觀性也隨之被復雜化。
公共史學所涉及的各種不同的互動是這一領域如此豐富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意味著這樣一個情緒和情感的維度(emotional andaffective dimension)在傳統學術實踐中缺失了。相較將客觀歷史作為其最終目標的傳統學術實踐,公共史學話語中的互動往往圍繞著情感和身份——自豪感、羞恥感、歸屬感或排斥感,直接影響現實世界。這也意味著,作為公共史學學者和更廣泛地研究“過去”的學者,我們應該對使用過去的方式及所涉及的情緒保持警惕。
從學院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公共史學研究事實上已經超出了對公共再現過去準確性的關注和質疑。然而,另一個潛在的局限性在于,公共史學往往被簡單地視為一種向學術界以外的公眾傳達歷史知識的手段(盡管這是公共史學的一個方面),這種二元互動關系往往簡化甚至弱化了公共史學在“交流”上的意義。事實上,許多的學院歷史學家可能根本不會參與公共史學的研究和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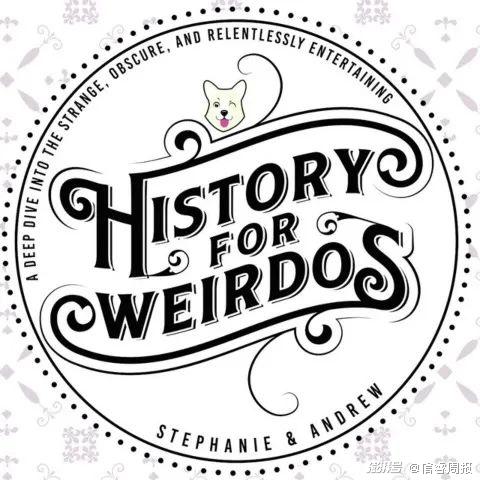
History For Weirdos
Andrew & Staphanie
收聽平臺:Spotify 等
您如何看待播客作為公共史學未來的發展潛力?
漢娜·以實瑪利:如上所述,尤其是隨著有關數字和社交媒體影響的研究的激增,公共史學領域的國際合作和跨國交流一定會繼續發展,并變得更加豐富,因為有越來越多的案例研究聚焦于特定的國家,這一點在《國際公共史學》(International Public History)期刊上得到了證明。我很希望未來能在公共史學研究中看到更多的跨國研究,公共史學學者和從業者也應該繼續參與正在進行的關于非殖民化的對話并采取行動。我還希望能看到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學院歷史學者只是參與歷史創作和理解過去的眾多合作伙伴之一——這并沒有削弱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作用,而是為未來的合作和研究開發出令人興奮的潛力。最后,我希望公眾對公共史學的“接受”不是將之視為一個邊緣領域,而是與歷史研究和實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已經開始看到,各國公共史學研究生課程正在不斷增加,英國許多本科核心課程也正在引入公共史學,公共史學正逐步進入主流學術研究,但我們仍有一段路要走。
就播客而言,它至少在學術或學術邊緣領域仍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播客憑借其對媒體和大眾特性的掌握,結合學術性的歷史知識和研究,能夠有效地傳播給普通觀眾,扮演著歷史的傳播者角色。此外,播客這一媒介也為專業的公共史學學者提供了特殊的可能性。我們正在嘗試將這種音頻材料作為一種創新的教學工具用在公共史學教學中,例如,一集研討或重述某個中世紀歷史事件的播客節目可以從2015年一名歷史學者的角度進行寫作,在2020年進行制作并由主持人重新敘述,在2021年被播放給學生收聽,它能夠以閱讀、寫作等方式壓縮時空。除了這種媒介作用,我們也在思考播客是否可以作為公共史學研究的原始材料。這也是公共史學與傳統的學院歷史學最大的區別之一,即我們的材料并非一定是來自檔案館的卷軸,個人的經驗也可以被看作資料來源。目前,一些數字公共史學學者從公共記憶與個人記憶的角度考慮這種數字存儲和組織的不同方法,從日常更新的社交媒體到播客,通過用戶生成內容和眾包活動創造數字個人記憶,并通過網絡和社交媒體創造一個“中介自我”(mediated self),這些也可以在未來的公共史學研究和實踐中發揮不同的作用。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84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