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深圳40年,一代代新人如何在此碰撞、再出發

近期,作家吳君最新長篇《同樂街》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說以深圳同樂村40年變遷為背景,寫了這個保留著獨特的集體股份制合作公司生產模式的村落中的落后戶陳有光與“90后”社區干部鐘欣欣之間的摩擦、沖突及和解,既展示了在共同體觀念感染下人民內部的碰撞和融合,又呈現了一代新人融入土地和人民的過程。精刪版首發于《人民文學》2021年第5期。
《同樂街》是吳君繼《我們不是一個人類》《萬福》之后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她還著有短篇小說集《親愛的深圳》《皇后大道》等。部分作品改編為影視作品、舞臺劇,有作品譯成英、俄、蒙等文字。曾獲首屆中國小說雙年獎、百花文學獎、北京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等。誠如青年評論家陳培浩所說,這部長篇小說從寫作的過程(掛職駐點、深入扎根)到作品題材、價值取向,都體現了重回社會主義文學經驗的選擇,與此同時,也體現了兩種文學傳統的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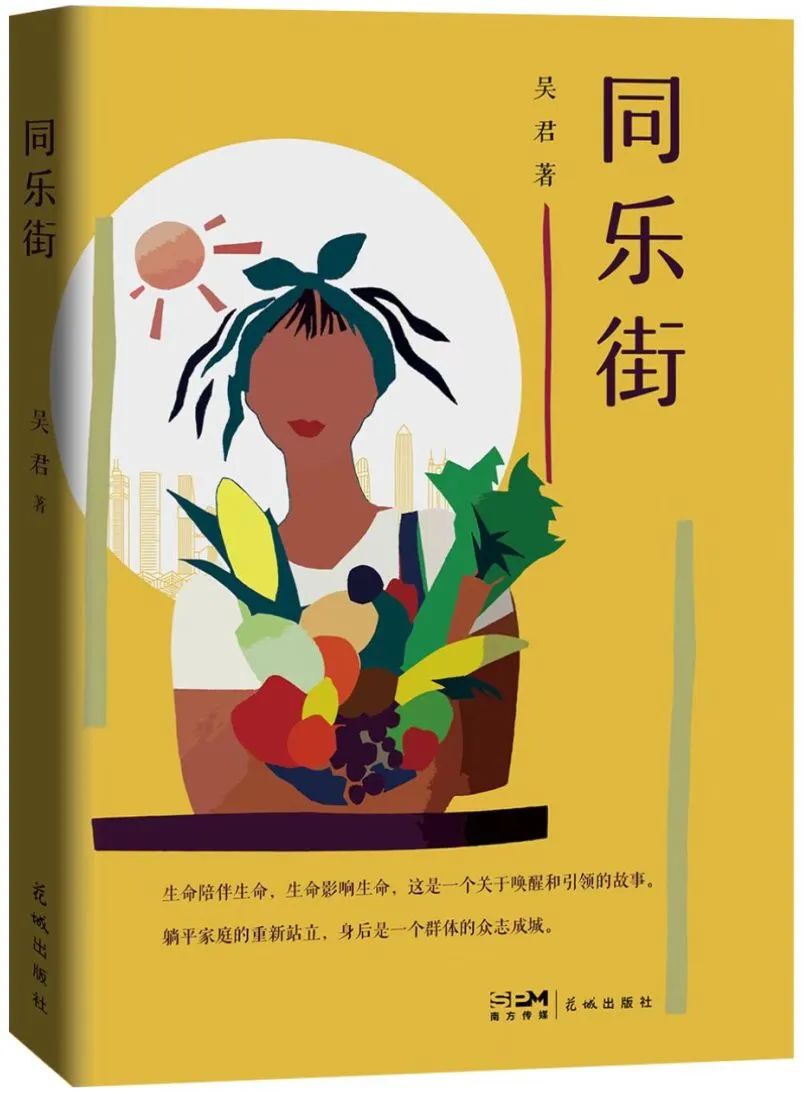
吳君《同樂街》
兩種文學傳統的交融 文 / 陳培浩
《人民文學》雜志在微信推文導讀中,強調了吳君在《同樂街》中將細節作為敘事推動力的“不落窠臼的藝術章法”。在我看來,這部作品可能還隱藏著一個社會主義文學傳統再出發的議題。
一般而言,1949年以來的文學被歸入當代文學,但當代文學內部卻存在著“人民文學”和“人的文學”兩個差異的文學傳統。人民文學傳統亦即左翼文學傳統、革命文學傳統,或狹義的社會主義文學傳統;而“人的文學”傳統則涵蓋80年代以來的啟蒙主義、人道主義和先鋒主義。這二個文學傳統各領風騷幾十年。很長時間里,當代作家的寫作依然是沿著“人的文學”的延長線前進。不無意味的是,吳君的《同樂街》自覺地置身于社會主義文學傳統和譜系中。
1949年以后的社會主義文學經驗,擁有一套完整而獨特的理論和方法,比如兩結合、三突出,比如社會主義新人,比如對于歷史本質的執著。對于人類生活之集體性、理想性和烏托邦性的追求是社會主義文學經驗的重要特征,但“十七年文學”并非沒有留下教訓。因此,今天,社會主義文學再出發,必須面對的不是一個傳統的激活,而是多個傳統的兼容。換言之,站在人民文學傳統,如何吸納“人的文學”傳統;站在民族形式、中國氣派立場,如何將古典的、外國的文學資源也兼容并蓄。
《同樂街》從寫作的過程(掛職駐點、深入扎根)到作品題材、價值取向,都體現了重回社會主義文學經驗的選擇。我想有心者不難發現,近十年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正發生著從個體到共同體的美學轉型。《同樂街》也是此中的一個節點。今天,當代文學寫作重新激活“十七年文學”經驗,并非重回一種單向的集體美學,而是導向一種溝通個體與集體、自我與他者、民族與世界的共同體美學。吳君們要處理的,不但是把生活的細節和文學的肌理帶入大時代的典型場景,將個體細小的美學和集體宏大的歷史視野結合,還應該將理想化的新人、英雄和草根、具體、在場的人民聯結起來,只有寫出洋溢在土地深處和人民身上那種明亮的歡樂,新人的理想和歷史的視野才更有力量,共同體美學才真正有效。吳君選擇的寫作方向,值得期待。
作品選讀
陳家人本來屬于安分守己的性格,也習慣了守著老日子慢慢過。前邊倒也不覺得如何,大家一樣經歷挨餓受窮,到香港、泰國各處揾工、找事做,到后來的包產到戶、“三來一補”、騰籠換鳥高科技,一直到現在的粵港澳大灣區。其間,陳家周邊人換屋換車又娶媳婦,才將陳家這一戶襯得越發暗淡,臉上無光,陳有光越發感到難受。陳有光因離開工廠之后在外面干了幾年零活,再回來時,同樂的變化很大,他心里便沒了底,感覺跟不上節奏。只說工作這一項,他就完全找不到調門了。別人懂的,他不懂;別人有大學文憑,他還只是個高中畢業。這么一來,陳有光顯然就被落下了。
陳有光最喜歡的事就是在同樂街上瞎逛,因為這條街可以連上寶安二區前進路那條街。那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地方,只有見到這條街,他才覺得這個世界沒有完全拋下他,他還認識這個世界。在這條街上,如果遇上人,他通常會主動搭訕:“喂,你認為我哋有冇可能番到當年呢?”半個小時前,他夢見自己在過山車上旋轉,他手腳冰涼四肢發麻,大喊了幾聲停下,但過山車轉得更快了,他暈得什么都看不清,眼前瞬間變成黑屏。終于他被自己嚇醒了。
有人搭腔:“你講乜?我聽唔明。”
“真的,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有的。”陳有光眼睛死死盯著對方,表情也是煞有介事。
對方不解地問:“什么意思,你是說我們全部人回到當年嗎?”
陳有光仰起臉對著天空幸福地說:“一切皆有可能,你知唔知 ‘三來一補’?”
對方說:“什么是‘三來一補’?是新的股票還是期貨?”

陳有光放平了臉,定定地看了一眼對方后,再把眼睛移開看下遠處,他判斷不出對方是有意捉弄他還是真的完全不懂。陳有光于是說:“你做乜學我講嘢。切,連外來加工都唔知咩,話你知,就係流水線,女工知唔知道,喺當年珠三角嘅工業區,有玩具廠、服 裝廠、鞋廠、電子廠,就係來料加工呀。”見到對方還沒反應過來,陳有光便樂了,繼續碎碎念:“報關員知唔知,二線關、邊防證、暫住證、拉長......”見對方完全不明白自己說的是什么,陳有光則會夸張地仰天長笑,見對方不理他走到遠處,陳有光又會失落,他指著對方的背影道:“你哋做乜啊!有錢大曬啊!做乜唔同我講嘢,我做錯咗乜?”陳有光有些慌了。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么,同樂發生了什么,怎么連個聽懂他說話的人也沒有了。這樣的事情在最近幾年并不鮮見,導致陳有光白天躲在屋企,只有到了夜晚,他才敢去同樂街逛。他舍不得睡,想捋捋自己這半輩子和同樂的來龍去脈。可是他發現自己常常在某些點上卡住,大腦沉得轉不動。看著馬路對面一眼望不到頭的高樓,還有那些光鮮的面孔,陳有光感慨萬千,他并不明白這個世界憑什么就拋棄了他。
有時陳阿婆突然會接陳有光的話:“真係可以番番以前就好嘍,我就唔使食咁多苦,唔使咁攰,做住官太太,邊個敢睇低 我。”兩個人夢游似的對上幾句話,像是擔心被什么驚醒了,陳阿婆很快便會關了門窗回房睡覺,而陳有光也像是乖了些,不再發出聲響,沒人知道這是不是陳阿婆想出來治自己仔的好辦法。
現在的陳阿婆不喜歡與人交流,因為同樂街的人不喜歡抱怨,不想和負能量的陳阿婆說話。他們現在跟對面街那些寫字樓里的年輕人學得越來越務實,越來越不想管閑事。陳阿婆常年緊鎖眉頭,面貌發生了一些變化,同樂人有幾十年沒有見過她笑。她恨老公把分紅全輸了,妒忌兒媳有分紅,對孫子陳小橋從小溺愛,百依百順,有時還會幫助陳小橋欺騙父母。擔心兒子陳有光拿她的財物去 賭博,她把自己的一只玉手鐲常年戴在腕上,導致摘不下來。每次陳有光輸了錢,看陳阿婆的手腕,陳阿婆便會哭天搶地,導致同樂人都知道陳有光又輸了錢。陳有光只有這一處又小又舊的房子,老祖宗留下來的住了幾代人的舊屋。別人家房子換了一次又一次,而陳有光家還在原地,陳有光終于成了釘子戶。一條拐來拐去的同樂街因為他陳有光一家被影響了,至今還沒有動工。
“搞我呀?你們可以動手拆呀。”陳有光笑著挑釁,“怎么樣?怕了吧。”隨后陳有光哈哈大笑。

他越發嘗到做釘子戶的好處,主要是實惠很多,光是這段時間,便不斷有人過來送米送油,一年到頭里外算算,夠吃很久。這樣一來,陳有光便越發不想動了。那一份給他安排的合作公司里丟人現眼的工作,他早就不想干了,索性也就請了病假不去上班。后來每到節假日前有人過來送米,陳有光不僅沒有感謝,反倒賣乖:“同樂對我唔住,你哋嚟做乜嘢,想揾我配合做出成績咩?”出到門口的干部無奈地交換眼神,默契苦笑。合作公司換了一位又一位干部來做陳有光工作,都沒有成功過,話還沒有說上半句,便被這一家罵出來。陳有光一家用的招數可謂五花八門,甚至 有次遇見一個女干部進門,陳有光竟當著老婆歐影的面調戲人家:“你是北妹吧,皮膚好白好靚呀,和我當年交往的那些差不多,你幾歲啦,有冇男朋友?”一串不靠譜的話拋出之后,場面頓時尷尬,女干部只想著對方簽了字快快溜掉算了。到后來,就連開發商的好奇心也被激發出來,親自上門送米送油,希望陳有光轉換思想,不要再拖后腿。陳有光家的房子不僅影響交通和觀感,嚴重點說,還會影響同樂的整體開發。這樣一來,原本就懶得生蛆的陳有 光更加不愿意出去做事了。他說:“我愿意配合呀,前提是給我多加23平方米,算補償我這么多年的損失,要明白我可是為改革開放立過功的功臣。”
“這個不符合規定吧陳老板。”開發商一臉無奈,不知道怎么 答,點頭哈腰遞上煙點著,隨后連招呼也不打便退了出去,轉身那 一刻眼神明顯厭惡了起來。這些話讓一些合作公司的工作人員不知如何應對,只得回去報 告社區領導說這個陳有光果然厲害,軟硬不吃,你和他談工作,他 就講歷史;與他談家常,他就說大道理;如果跟他講原則,他又怪 我們社區不正視他的處境。真是不知他的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想對癥下藥卻不知他得了什么病。然而就在2020年,陳有光四十七歲的這一年,他遇上了“90后”鐘欣欣。
(《同樂街》吳君/著,花城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原標題:《吳君《同樂街》:深圳40年,一代代新人如何在此碰撞、再出發》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