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彈性工作制度怎么來的?工作家庭因此更平衡嗎?
原創(chuàng) 嚴(yán)肅的人口學(xué)八卦組 嚴(yán)肅的人口學(xué)八卦
本文作者:何雨辰
責(zé)任編輯:張洋
彈性工作制在近五年來變得越來越流行,尤其是疫情以來居家辦公也更加常見。傳統(tǒng)工業(yè)中標(biāo)準(zhǔn)化的勞動契約、工作場所和工作時(shí)間變得越來越靈活,工作狀態(tài)與非工作狀態(tài)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朝九晚五的工作變成了下午晚上的工作;人們從工廠的車間里和高樓大廈走出來,公司的組織形式變得不再可見。出勤規(guī)定寬松化,工作場所分散化、網(wǎng)絡(luò)聯(lián)結(jié)電子化成為了彈性工作體系最重要的三個(gè)特征。
彈性工作制的緣起
貝克在《風(fēng)險(xiǎn)社會》中這樣描述靈活辦公的起源:社會的發(fā)展是以一種利潤導(dǎo)向的理性化的不變邏輯而發(fā)生的,而靈活辦公也不例外,它緣起的力量在于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即企業(yè)為了提高生產(chǎn)力而對勞動的使用方式及其包含的組織可能性進(jìn)行去標(biāo)準(zhǔn)化。
通俗一點(diǎn)講,從傳統(tǒng)工業(yè)模式到靈活辦公轉(zhuǎn)變的前提是傳統(tǒng)就業(yè)系統(tǒng)通過信息技術(shù)、社會政策和法律的現(xiàn)代化浪潮進(jìn)行了結(jié)構(gòu)性改革。隨著電子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部分勞動可以被機(jī)器所替代,此時(shí)組織中需要的人員就相應(yīng)減少了。同時(shí)也產(chǎn)生了專業(yè)性和技巧性較強(qiáng)的監(jiān)督、指導(dǎo)和維護(hù)工作,這些工作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進(jìn)行局部任務(wù)的聯(lián)合。企業(yè)可以依據(jù)訂單情況靈活安排這些崗位的工作時(shí)間,讓生產(chǎn)時(shí)間不受工作時(shí)間的限制,從而大幅提高生產(chǎn)力,還可以通過不充分就業(yè)將一部分企業(yè)風(fēng)險(xiǎn)轉(zhuǎn)嫁到雇員身上。組織的靈活性就因此增加了。
除了工作時(shí)間的靈活化,電子信息技術(shù)可以消除勞動分工中各個(gè)相連領(lǐng)域的直接協(xié)作,傳統(tǒng)勞動組織中集中的模式開始變得分散、傳統(tǒng)的勞動契約關(guān)系也被打破,人力組織的形式變得非職業(yè)化,全職工作也開始朝著兼職工作發(fā)生轉(zhuǎn)變。

靈活辦公的出現(xiàn)對就業(yè)者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包括不充分就業(yè)對收入、社會保障、晉升帶來的風(fēng)險(xiǎn),但勞動者也相應(yīng)獲得了一定能夠“獨(dú)立處置自己生活的自由和自主”。由于傳統(tǒng)觀念中彈性工作制涉及的主要對象是女性,圍繞靈活辦公對就業(yè)者的影響(尤其是益處)的討論中總是離不開性別和“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話題。
彈性工作制對性別和家庭的影響
1
能否在家庭內(nèi)減少性別沖突?
在貝克看來,當(dāng)今性別沖突爆發(fā)的根源是女性對平等的期待和不平等的現(xiàn)實(shí)之間的矛盾,以及男人的共同責(zé)任的口號和舊有角色任務(wù)的保留之間的矛盾。傳統(tǒng)的工業(yè)社會在性別與家庭方面保留了封建社會的遺產(chǎn),人類勞動力的商品化是分裂的,因此有工資的雇傭勞動就預(yù)設(shè)了不計(jì)報(bào)酬的家務(wù)活的存在,工業(yè)社會依賴的基礎(chǔ)正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和現(xiàn)代性的原則相抵,當(dāng)今市場的普遍主義讓女性不再接受被迫在家庭內(nèi)從事家務(wù)勞動,沖突也必然爆發(fā)。

這種家庭的沖突、性別的沖突由制度而產(chǎn)生,也需要制度性的解決方法。靈活工作制就可以被看作一種緩解兩性沖突的制度性解決方案(同樣包括白天兒童照料、社會保障等等)。彈性工作制能夠改變傳統(tǒng)工業(yè)社會中家庭和勞動分割的狀況,因此讓有酬勞動和無償家務(wù)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因此傳統(tǒng)的“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家庭分工和不可緩和的家庭-工作沖突就有了轉(zhuǎn)變的制度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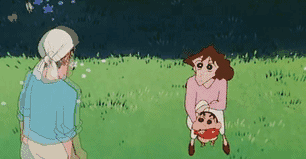
2
能否在勞動市場上減少性別不平等?
《風(fēng)險(xiǎn)社會》中寫到,彈性工作制和不同形式的兼職工作可以讓作為“隱性儲備”的婦女和年輕人涌入勞動力市場,實(shí)現(xiàn)靈活就業(yè)。尤其是對于剛剛生育過后的母親而言,彈性工作制能夠降低兩性在收入、勞動參與方面的不平等。用貝克的原話說,“彈性工作制可以幫助女性自由地過上一種自主的生活,避免一種母性的復(fù)歸”。這說明彈性工作制不僅是一種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工具,而且也是在家庭需求增加時(shí)期提高和保持個(gè)人工作能力的工具(Chung,2018)。
這種正面的影響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中更為突出。因?yàn)閷I(yè)性和管理性強(qiáng)的崗位對工作時(shí)間有著很高的期待,彈性工作制能讓這些女性更靈活地安排工作時(shí)間,兼顧高強(qiáng)度的工作任務(wù)和帶娃需求(Fuller和Hirsh, 2019)。最近也有一些傳統(tǒng)的勞動密集型崗位新設(shè)立了“媽媽?shí)彙保ㄟ^提供靈活的崗位避免了“一刀切”地辭退育兒女性并且減少了企業(yè)的用人成本。此外,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自媒體的興起,也有越多曾經(jīng)的全職太太們涌入了這種新型的勞動力市場,通過在平臺上把家務(wù)或者帶娃的日常生活分享出來,實(shí)現(xiàn)靈活就業(yè)。

但是由于彈性工作制和傳統(tǒng)的工作形式不符,常常被人們認(rèn)為是效率低下、對工作不投入或者表現(xiàn)不佳。而女性相比與男性更容易因此遭受歧視,晉升機(jī)會也會被減少(Kmec等,2014;Chung,2020)。新興的靈活就業(yè)形式也存在著社會保障不完善、收入相對較低、不穩(wěn)定等問題。并且從本質(zhì)上看,許多工作還是在幫助延續(xù)傳統(tǒng)的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家庭分工模式。這些工作形式雖然給女性提供了一種新的職業(yè)發(fā)展路徑,但沒有在根本上改變職業(yè)性別隔離的現(xiàn)狀。選擇彈性工作制對女性在長期的職業(yè)發(fā)展上則可能會遭受負(fù)面損失。
疫情居家辦公中的家庭勞動分工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fā)以來,疫情中學(xué)校和托兒所的關(guān)閉大大增加了家務(wù)勞動和照看孩子的工作量,同時(shí)“居家辦公”也成為了很多人新的工作形式,許多雙職工父母這時(shí)候會面臨著誰承擔(dān)這一責(zé)任的新選擇。疫情不僅影響著夫妻的工作方式,也進(jìn)一步影響著他們在家庭中角色和分工。
從一方面來看,疫情中的居家辦公是一個(gè)提升男性的育兒責(zé)任的好機(jī)會。縱向來比較,如果父親選擇了居家辦公,他們和以前相比就會做更多的家務(wù)和照顧孩子,母親是唯一或主要負(fù)責(zé)家務(wù)和照顧孩子的人的可能性與以前相比也會就大大下降(Chung,2021)。

圖1:新冠封城期間家庭內(nèi)部母親承擔(dān)主要家務(wù)的比例。資料來源:(Chung,2020)
需要承認(rèn)的是,由于母親也增加了他們的勞動參與,母親為主的傳統(tǒng)的家務(wù)勞動分工模式并沒有得到改變(Dunatchik等,2021),但是父親在家務(wù)中“從無到有”的改變也有著積極的意義。
從另一方面來看,彈性工作制可以幫助減少女性回家照料孩子的收入損失。有研究指出,在疫情中面對學(xué)校停課時(shí)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傾向于回家照顧不上課的孩子、減少工作時(shí)間或是退出勞動力市場。在這種背景下,彈性工作制為女性提供了在家中也可以工作的機(jī)會,減少女性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影響,能夠緩解不斷擴(kuò)大的性別收入差距(Tverdostup,2022 ;Foley和 Cooper,2021)。

結(jié)語
彈性工作制是一個(gè)新的制度工具,但它也只是一個(gè)工具。彈性工作制對于性別與家庭有多大的影響歸根結(jié)底還是兩性在各自的天平上給工作和家庭賦予了多少權(quán)重。
因此整個(gè)社會的性別文化對彈性工作制是否能真正促進(jìn)性別平等和家庭工作平衡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性別更為平等的社會中,彈性工作制則能更好發(fā)揮它促進(jìn)工作-家庭平衡等正面作用,而性別文化更傳統(tǒng)的地區(qū),它對家庭和性別帶來的負(fù)面影響則顯著更高(Kurowska, 2020)。如果還是帶著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規(guī)范的眼鏡去看待彈性工作制,它不但不能促進(jìn)家庭和諧和兩性平等,反而加劇了舊有的性別分工。比如有研究指出,男性會利用彈性工作增加了工作強(qiáng)度或時(shí)間,而女性在彈性工作中給家庭花費(fèi)的時(shí)間和精力更多(Lott和Chung,2016)。在這種傳統(tǒng)的“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觀念下,彈性工作制會加重女性的家務(wù)負(fù)擔(dān),彈性工作制還更會加大兩性的性別收入差距。

因此,只有改變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規(guī)范,改變對父職和母職期待的差異,才可以真正讓彈性工作制起到緩解家庭工作矛盾、促進(jìn)兩性平等的作用。
彈性工作制是否能真的緩解家庭和工作的矛盾也和組織文化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如果一個(gè)企業(yè)中有人人爭做“完美打工人”的導(dǎo)向,把加班當(dāng)成努力,把工作帶回家只是為了能晚上做或者周末從而能“卷”過同事,那么彈性工作就會帶來更嚴(yán)重的工作與家庭沖突(van der Lippe和 Lippényi,2018)。

圖2 papi醬 “老板的異想世界——完美上班族-嗶哩嗶哩”。資料來源:https://b23.tv/VOnj7hb。
總之,要想讓彈性工作制度發(fā)揮它能帶來的正面作用,就需要利用這一制度的人們做出積極改變,第一步改變或許可以從消除對彈性工作者的歧視、不再把選擇彈性工作的女性和能力低下劃上等號開始。
參考文獻(xiàn)
Beck, U., Lash, S., & Wynne, B.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Vol.17). sage.
Chung, H., & van der Horst, M. (2018).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s After Childbirth and the Perceived Access to and Use of Flexitime and Teleworking. Human Relations, 71(1), 47–72. https://doi.org/10.1177/0018726717713828
Chung, H. (2020). Gender, Flexibility Stigma and the Perceived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Flexible Working in the UK. Soc Indic Res 151, 521–545.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8-2036-7
Chung, H., Birkett, H., Forbes, S., & Seo, H. (2021). Covid-19, Flexible Work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Gender Equal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Gender & Society, 35(2), 218–232.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2211001304
Dunatchik, A., Gerson, K., Glass, J., Jacobs, J. A., & Stritzel, H. (2021). Gender, Parenting, and The Rise of Remote Work During the Pandemic: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Gender & Society, 35(2), 194–205.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2211001301
Foley, M., & Cooper, R. (2021).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Where to Next?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63(4), 463–476. https://doi.org/10.1177/00221856211035173
Fuller, S., & Hirsh, C. E. (2019). “Family-Friendly” Jobs and Motherhood Pay Penalties: The Impact of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Across the Educational Spectrum. Work and Occupations, 46(1), 3–44. https://doi.org/10.1177/0730888418771116
Kmec, J. A., O’Connor, L. T., & Schieman, S. (2014). Not Ide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orking Anything but Full Time and Perceived Unfair Treatment. Work and Occupations, 41(1), 63–85. https://doi.org/10.1177/0730888413515691
Kurowska, A. (2020). Gendered Effects of Home-Based Work on Parents’ Capability to Balance Work with Non-work: Two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Models of Division of Labour Compared. Soc Indic Res 151, 405–425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8-2034-9
Lott, Y., Chung, H. (2016) Gender Discrepancies in the Outcomes of Schedule Control on Overtime Hours and Income in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6),752–765, https://doi.org/10.1093/esr/jcw032
Noonan, M. C., Estes, S. B., & Glass, J. L. (2007). Do Workplace Flexibility Policies Influence Time Spent in Domestic Labor?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2), 263–288.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06292703
Shockley, K. M., & Allen, T. D. (2007). When Flexibility Helps: Another Look at the Availability of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1(3), 479–493. https://doi.org/10.1016/j.jvb.2007.08.006
Tverdostup, M. (2022). COVID-19 and Gender Gaps in Employment, Wages, and Work Hours: Lower Inequalities and Higher Motherhood Penalt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1-23.
van der Lippe, T., Lippényi, Z. (2020). Beyond Formal Access: Organizational Context, Working From Home,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of Men and Women in European Workplaces. Soc Indic Res 151, 383–402.
原標(biāo)題:《彈性工作制度怎么來的?工作家庭因此更平衡嗎?》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jī)構(gòu)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fā)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jī)構(gòu)觀點(diǎn),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diǎn)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