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世界史學科的反思與前瞻:共商、共建、共享學術共同體
世界史學科自2011年被確立為一級學科以來,經(jīng)過十年的建設,在各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縱向來看,國內(nèi)學者的研究成果涵蓋了古代、中世紀、近代、現(xiàn)當代各歷史階段;從橫向來看,各大高校已經(jīng)成立了如美國史、英國史、日本史、中東史、非洲史等專題研究基地或研究中心。然而,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仍面臨著一些具體的問題。首先,世界史學科的研究力量相對薄弱,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還不夠;其次,世界歷史范圍過大、語言多樣、部分領域的資料匱乏,給世界史專業(yè)學習帶來的難度較大,影響了青年學子對世界史學習與研究的熱情;最后,學科布局不平衡,世界史研究陣地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城市,西北地區(qū)學科發(fā)展較為緩慢。因此,反思世界史學科遇到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zhàn),探尋其未來發(fā)展的出路,就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

線下參會學者合影
針對上述問題,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舉辦了世界史學科建設研討會,其中一個主題是“世界史學科自身的反思與未來出路”,另一個主題是“世界史學科的團隊建設、特色培育及其遇到的挑戰(zhàn)”。特邀南京大學陳曉律教授、北京師范大學郭小凌教授、復旦大學顧云深教授、復旦大學李劍鳴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沐濤教授、上海師范大學陳恒教授、上海社科院郭長剛教授、南開大學趙學功教授、西北大學黃民興教授、復旦大學黃洋教授、暨南大學李云飛教授、陜西師范大學李秉忠教授、西北大學韓志斌教授、上海師范大學洪慶明教授、復旦大學歐陽曉莉教授參加座談。上海大學歷史學系郭丹彤教授和楊長云副教授主持了兩個主題的討論,張勇安院長、王三義教授、柴彬教授、劉義教授、吳浩教授、張琨副教授、以及青年教師王佳尼、謝曉嘯、沐越等參加了討論。

主持人郭丹彤、楊長云
議題之一:“世界史學科自身的反思與未來出路”
圍繞這個主題,有八位專家談了自己的看法。內(nèi)容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從學科本身存在的不足,到高等教育發(fā)展過程中各個學科力量的不均衡,都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

陳曉律
陳曉律教授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世界史學科建設取得了較大的進步。但總的來看,除了上海幾所兄弟院校以外,世界史學科在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并不十分景氣,還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在學科隊伍建設方面,世界史團隊的力量比較單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世界史學科專屬的史學陣地較小。除《世界歷史》外,沒有其他以世界史為主的頂級核心期刊。再次,世界史學科隊伍的后備力量嚴重不足。按照南京大學世界史學科留人的標準,學者必須要發(fā)表頂級刊物若干,還要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才有可能留下,這種壓力也導致世界史研究隊伍萎縮。其次,世界史學科本身的難度較大。無論是在語言學習方面,還是資料搜集方面,抑或是成果產(chǎn)出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困難。這些困難也使世界史學科在與其他學科進行競爭時,容易處在一個不利的位置。最后,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工作者很難擁有話語權(quán)。針對當前世界史學科建設的現(xiàn)狀,陳曉律教授提出幾點建議:一是邀請與會專家多多交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tài)來迎接困難,共同攻關;二是世界史學科建設應列入相關單位負責人的考評指標;三是呼吁各大高校加強世界史學科隊伍的建設,以提高世界史學科的整體水平。

顧云深
顧云深教授根據(jù)自己在復旦大學的工作經(jīng)歷,從“學科焦慮”、理論運用、人才培養(yǎng)三個角度探討了當前世界史學科發(fā)展中的若干問題:第一是世界史的“學科焦慮”問題。由于國家相關部門對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還缺乏足夠的重視和規(guī)劃,社會對世界史學科也缺乏一定的了解和支持,導致部分學者對世界史專業(yè)的發(fā)展前景充滿焦慮。要克服這種“學科焦慮”,學者必須確保其學術研究的連續(xù)性,因為一門學科的發(fā)展最基本的推動力就是一代代的傳承。從事世界史研究的人必須要沉下心來,在自己本領域內(nèi)深耕、積累,不為形勢、潮流所動。第二是世界史的理論運用問題。世界史不同于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等專業(yè),對它的研究是一項傳承的工作,也是一個了解歷史發(fā)展過程的工作。所以世界史的工作者應該與當今一些所謂的“時髦”理論保持距離感,要結(jié)合學科本身進行理論的研究。第三是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由于世界史涉及的范圍太大,對各種語言的要求較高,各方面資料收集的難度也比較大,所以世界史人才的培養(yǎng)難度比一般的學科更大,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學者從總量上看還是太少。如何解決人才培養(yǎng)的難題?顧云深教授主張借鑒首都師范大學的做法,將世界史與其他學科結(jié)合起來,尤其是語言類學科,從而幫助學生克服世界史學習的語言困難。其次要重視導師的作用。導師需要花費精力,引導學生思考,同時對學生們要求嚴格,在論文的規(guī)范性、開題,研究、寫作、論文質(zhì)量把關等方面下功夫。然后要多關注年輕人,多給他們機會,要讓他們有信心,不能讓年輕人覺得沒希望,覺得做世界史一點意思也沒有。只有這樣才能吸引優(yōu)秀的人才來從事世界史研究。最后,世界史工作者要潛心深耕,不能“趕時髦”。世界史本來就是一個小的、后起的學科,它可能永遠成不了顯學,所以我們要有堅韌的耐心讓這個學科成長,同時不斷改進自身的不足,這也是世界史學科建設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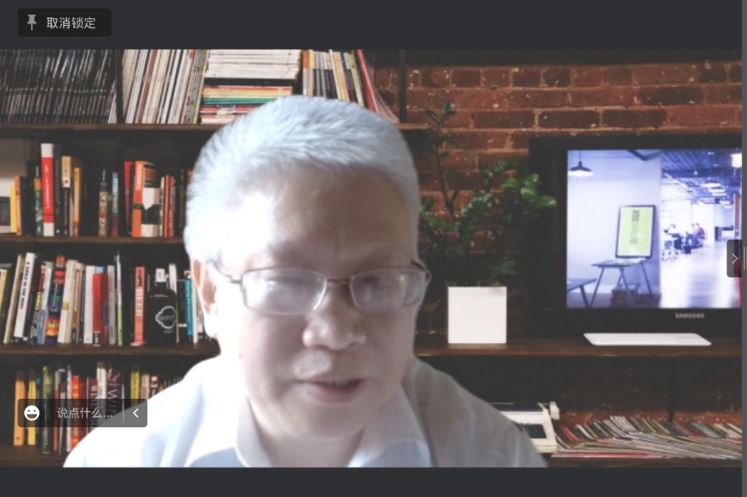
趙學功
趙學功教授則從人才培養(yǎng)、學科發(fā)展、培養(yǎng)模式、資料建設、學術話語權(quán)、學術共同體建設等六個方面討論了世界史學科面臨的一些挑戰(zhàn):第一,人才培養(yǎng)是世界史專業(yè)面臨的重要挑戰(zhàn)。如何吸引更多有天賦、有潛質(zhì)的學生對世界史的研究興趣,如何鼓勵并吸引他們將來從事世界史研究,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也是人才培養(yǎng)的一個重要方面。第二,世界史的整體發(fā)展受到了諸多制約。作為剛設立不久的一級學科,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還處于起步階段,所以在師資隊伍建設、課題申請數(shù)目、學術交流,甚至整個學科的建設方面,面臨的問題還比較多。第三,在培養(yǎng)模式方面,可以借鑒區(qū)域國別學的方法,促使世界史學科與外語學科相結(jié)合。“世界史+小語種”的模式,不僅有助于緩解語言不同的難題,也能夠促進世界史學科的全面均衡發(fā)展。第四,資料建設的問題。總的來看,國內(nèi)只有北京大學對有關世界史的國外數(shù)據(jù)庫的訂購較為齊全,其他學校可能只訂購了其中的一部分,難以滿足教學科研的需要。所以如何加強資料建設、如何提高大學圖書館的數(shù)字化、電子化程度,也是世界史學科面臨的一大難題。第五,學術話語權(quán)的問題。國內(nèi)學者從事世界史研究,一方面是為了增進國人對世界歷史問題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在某些領域提出自己的見解,與國外的同行學者進行平等的對話和交流。根據(jù)個人的一些了解,目前已經(jīng)有一些年輕學者開始在國際學界嶄露頭角,在歐美有影響的期刊如《美國歷史雜志》《外交史》《冷戰(zhàn)研究雜志》等發(fā)表論文,應該還有一些學者在海外高水平的期刊上發(fā)表了論文,中國世界史學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期盼將來能有更多的學者在國際刊物上發(fā)表文章,這對整個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都有很大的幫助,并進一步提升中國學者在國際學界的話語權(quán)和學術影響力。第六,世界史學術共同體的建立和凝聚問題。近年來,世界史學科的學術活動、學術會議、各種研討會舉辦得比較多,但是多數(shù)會議都是各個國家的專題研究,相互之間的交流還是比較少。如果能夠成立一個世界史學術共同體,就包括學科建設、梯隊團隊建設、課程設置、師資需求、論文發(fā)表、人才培養(yǎng)等問題一起展開探討,或許能夠更好地凝聚力量,推進世界史學科更好全面地發(fā)展。

沐濤
沐濤教授結(jié)合自己在華東師范大學的工作經(jīng)驗,就世界史專業(yè)在招生、學生畢業(yè)、學科點設置等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第一,世界史學科從本科生到博士生都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近幾年,華東師范大學世界史專業(yè)博士生導師人均招生數(shù)不到1名,碩士生招生數(shù)在減少,本科生畢業(yè)論文的選題,世界史方向的也比中國史少,這與華東師范大學世界史學科在全國的地位嚴重不匹配。學生們普遍認為世界史比中國史難學,對外語及外國資料的要求較高。招生的不足也給學科的人才培養(yǎng)帶來了難題。第二,世界史專業(yè)的博士生按期畢業(yè)比較難,特別是有發(fā)刊論文數(shù)的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世界史專業(yè)期刊數(shù)量較少,除了《世界歷史》外,缺乏其他以世界史為專題的權(quán)威性雜志。盡管還有一些以書代刊,但是與其他學科相比,被列入核心期刊或評價指標體系內(nèi)的刊物還是太少。再加上近兩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出國交流和留學中斷,打亂了原有的培養(yǎng)計劃,直接影響了論文的質(zhì)量。第三,世界史學科全國的碩士點和博士點數(shù)量太少,每年新增1-2個。從事世界史學科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學者相對集中,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南京這樣一些大城市,分布不太均勻,不利于全國世界史學科的均衡發(fā)展和人才培養(yǎng)。所以他建議,以后在一些項目的評審、論文的發(fā)表方面,適當?shù)叵蛑形鞑繉W校傾斜,擴大學科點的范圍。第四,區(qū)域國別學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世界史工作者可以參與國別區(qū)域?qū)W的研究,提高自身的研究水準和對外交流;另一方面,處理不當?shù)脑挘矔魅鹾头稚⑹澜缡繁旧淼难芯苛α浚彝庹Z、國際問題、國際政治等相關專業(yè)對區(qū)域國別學的建設也非常重視,所以世界史工作者必須要有一種緊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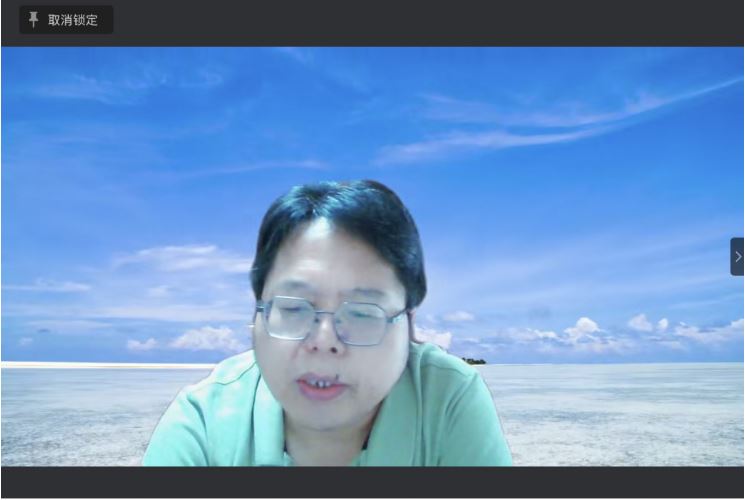
李秉忠
李秉忠教授則以《區(qū)域國別學的西方傳統(tǒng)和中國路徑》為題,對區(qū)域國別學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強調(diào)區(qū)域國別學可以推動世界史的學科建設。區(qū)域國別學從定義上講,是一門跨學科的、對于某一地區(qū)或區(qū)域進行綜合性研究的學科,它在二戰(zhàn)之后,尤其在美國的主導之下發(fā)展比較快。西方的區(qū)域國別學研究主要根據(jù)國家利益需要確定研究的選題,國家提供各種各樣政策和經(jīng)費支持,一些國家還特別注重文明史在區(qū)域國別中的地位。李秉忠教授特別指出,中國的區(qū)域國別研究與西方的區(qū)域國別研究存在著本質(zhì)上的差別。西方區(qū)域國別研究的本質(zhì)是西方對全球統(tǒng)治智識的體現(xiàn),所以西方的區(qū)域國別研究往往被視為大國之學。中國學術界也習慣于認為區(qū)域國別研究是大國之學,但“最大發(fā)展中國家”這一前提決定了我國的區(qū)域國別研究追求的是如何認識自身及其與世界的關系,強調(diào)不同國家平等展開相關研究的合作和對話,進而助力于文明交流和互鑒。因此,簡單地將區(qū)域國別研究視為大國之學并不能準確地對區(qū)域國別研究進行定性,事實上很多國家都在開展著區(qū)域國別的研究。那么如何在國內(nèi)開展區(qū)域國別研究?李秉忠教授談到了以下幾點:首先,國內(nèi)學者不僅要生產(chǎn)有關廣大發(fā)達國家的知識,還要生產(chǎn)有關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知識,并通過對非西方世界的研究生產(chǎn)出關于西方世界的知識。其次,區(qū)域國別學有三種構(gòu)建模式,分別是以外國語言文學、國際關系、世界史為主導的區(qū)域國別研究模式。陜西師范大學致力于以世界史為基礎的區(qū)域國別研究,陜師大世界史傳統(tǒng)的優(yōu)勢方向是蘇聯(lián)東歐史、冷戰(zhàn)史和中亞中東研究,近年來逐漸向黑海地區(qū)發(fā)展,將世界史與區(qū)域研究相結(jié)合。再次,進行跨學科的研究。陜西師范大學開設的世界史班,既學語言,又學歷史學,還增加了一些區(qū)域國別研究理論和方法類課程。跨學科的方法對于世界史的研究無疑具有推動性作用。最后,需要強調(diào)中華文明在區(qū)域國別研究中的獨特地位與特殊經(jīng)驗。另外,學者們也應該做一些長期規(guī)劃,促進世界史和區(qū)域國別研究的發(fā)展。

黃洋
黃洋教授首先回應了顧云深教授的觀點,即世界史這個學科不是一門顯學,所以不要指望它受到特別的重視。當然上海的情況比較特殊,像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大學等高校都比較重視世界史專業(yè)的發(fā)展。但這些學校都是特例,像復旦大學這樣的才是常例。從復旦大學的個案來看,世界史在學校里并不受重視,是邊緣學科,與中國歷史相比,差距還是很明顯的。但世界史學科的這種情況也有好處,一方面來自學術之外的干預較少,學者們可以做自己感興趣的課題;二是世界史學科尚未面臨被“砍掉”的危險,所以暫時還沒有生存的危機。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世界史工作者到底能夠做些什么?黃洋教授談了以下幾方面:首先,在一個大的環(huán)境中,整個社會的支持,我們是左右不了的。但是學者們可以盡自己的一己之力,培養(yǎng)更多優(yōu)秀的學生,發(fā)表更多優(yōu)秀的作品。雖然有時候一個學校的招生指標很有限,但是學者們也有一些可做的工作,比如說現(xiàn)在各個學校都可以轉(zhuǎn)專業(yè)、轉(zhuǎn)方向,所以學者們還面臨著如何將學生吸引到世界史的問題。因此,黃洋教授呼吁同仁們要做一些普及的、面向社會、面向高中生的工作,培養(yǎng)他們對世界史的興趣。同時寫一些有關世界史的通識書籍,面向廣大讀者,包括高中生。以此為基礎,擴大世界史專業(yè)的受眾面,促進其長遠發(fā)展。

洪慶明
洪慶明教授認為,作為一個世界史從業(yè)者,對于世界史學科建設來說,本著“盡人事聽天命”的態(tài)度,也就是說在具體的時代環(huán)境中保持進取。這是因為,人文學科的興盛與國家經(jīng)濟的發(fā)展、社會的繁榮息息相關,對于我們研究外國歷史的尤其如此。只有國家經(jīng)濟繁榮了,才會催生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和放眼世界的姿態(tài);只有國家經(jīng)濟繁榮了,世界史研究才有經(jīng)濟基礎的支撐。以法國史研究為例,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一些學者發(fā)表的文章水平并不高。但是到六十年代,由于美國經(jīng)濟的繁榮,從事法國史的工作者比較容易申請到經(jīng)費,從業(yè)者也方便到國外學習、訪學和查閱資料,所以在這個時期美國的法國史研究才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在中國也是如此,2011年世界史學科能夠升級為一級學科,也是以2000年之后中國的經(jīng)濟起飛為基礎性支撐。世界史學科發(fā)展至今已有十年,十年建設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一些基本的問題也存在,第一個是發(fā)展的不平衡,世界史工作者主要集中在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比如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第二個是增長模式過于粗放。所以世界史的研究必須要包含大量的工作計劃和整合,包括課程體系、基礎理論和基礎知識的系統(tǒng)訓練,因為這些對于史學研究者的邏輯思維訓練至關重要。最后,洪慶明教授談到了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學科的建設現(xiàn)狀。近十年來,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專業(yè)發(fā)展迅速,無論是縱向(古代-中世紀-近現(xiàn)代)還是橫向(國家/區(qū)域)的分布都比較均衡,其中大國史、區(qū)域史和周邊國家研究都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但是從整個大環(huán)境來看,世界史學科的平臺建設還不夠完善,歷史學期刊太少,大多數(shù)雜志都是中國史占據(jù)主流,不利于世界史專業(yè)的長遠發(fā)展。因此,洪慶明教授呼吁必須加強世界史學術期刊平臺建設,世界史學科學生向編輯崗位發(fā)展,以解決學術發(fā)表的瓶頸問題。

張勇安
文學院院長張勇安教授對這個主題的討論作了總結(jié)。世界史學科經(jīng)過十多年的建設,無論是團隊的建設、學科的發(fā)展,還是學術影響力都在提高,這當然跟學界、學科評審的領導們,還有社科基金評審們的努力是離不開的。此外,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也借了一些國際的大勢。近年來,留學歸來的青年學者數(shù)量不斷增加,他們受過系統(tǒng)的教育,為世界史團隊增添了力量。然而,根據(jù)相關數(shù)據(jù),世界史學科在建設過程中也面臨諸多挑戰(zhàn)。以第五輪學科評估為例,當時參與評估的世界史高校大概有58所,而擁有博士點的只有二十多所。在整個學科評估的序列中,躋身A+類學科(排名前5%)的高校只有3家。絕對排名較低也導致了各高校在資源配置上的劣勢。此外,高校的人才培養(yǎng)工作做得還不夠。以上海大學為例,近些年來報考歷史學的學生人數(shù)的確有所增多,但最終選世界史做畢業(yè)論文,或者選世界史來考研的人數(shù)還是較少。在這種大勢之下世界史工作者能做什么?張勇安教授指出,一是要更加重視人才的培養(yǎng),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學生身上。二是需要對評價體系進行調(diào)整。以往對老師們的評價主要是看科研文章的發(fā)表數(shù),或者項目的申請等,如何讓老師們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人才的培養(yǎng)上,這應該是最需回應的一個問題。在會議最后,張勇安院長也呼吁與會學者多多交流,為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貢獻自己的智慧。
議題之二:世界史學科的團隊建設、特色培育及其遇到的挑戰(zhàn)
這個議題涉及高校世界史研究的途徑、目標和任務等,尤其團隊建設和學科特色培育,是一項長期積累之后始有成效的工作。具體應該如何做,十幾位專家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現(xiàn)整理如下:

郭小凌
郭小凌教授從自己擔任史學研究所所長和博物館館長的管理經(jīng)驗談起,認為世界史團隊建設首先需要有優(yōu)秀的學科帶頭人或管理者。上海各院校世界史學科發(fā)展成績喜人,就得益于擁有一批勇于擔當、能力突出的學科帶頭人,這也是任何單位、部門、學科的共性。有了出色的學科管理者或?qū)W術帶頭人,學科的團隊建設、特色培育就迎刃而解了,這就是管理的意義。最后郭小凌教授表達了他對《路易十四時代》中關于世界史上有重大貢獻的大都是藝術家、思想家、文學家這一觀點的不認同,在他看來,治理者在人類歷史舞臺上作用重大,有時甚至起決定性作用。

韓志斌
韓志斌教授從學科建設和團隊建設的角度,結(jié)合自身研究心得,提出建立學術共同體、創(chuàng)辦學術期刊、選好學術帶頭人、營造良性學術競爭環(huán)境等建議。第一,建立學術共同體。世界史學科應該以團結(jié)的精神,成立包括美國史、英國史、歐洲史、中東史、非洲史、拉美史等研究團體的學術共同體,打破區(qū)域國別分割狀態(tài),實現(xiàn)中外古今融通,加強交流,促進世界史學科整體發(fā)展。第二,創(chuàng)辦學術期刊。世界史學科要呼應教育部破“五唯”要求,加強世界史學術評價共同體建設,既要積極創(chuàng)辦新的世界史學術期刊,又要加強現(xiàn)有學術期刊的聯(lián)動,為同行學人提供更多學術成果發(fā)表平臺。上海師范大學陳恒校長創(chuàng)辦的《世界史評論》已作出有益探索,西北大學《中東研究》創(chuàng)刊多年,已進入C刊行列,得到各高校認可,稿源廣泛,目前西北大學又創(chuàng)辦了《南亞史》輯刊。每個學校的世界史學科都要積極創(chuàng)辦專業(yè)期刊雜志,擴大學術陣地。第三,選好學術帶頭人。韓志斌教授認為德高望重、理論獨到的學術帶頭人對學科發(fā)展和團隊建設非常重要,以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為例,彭樹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論奠定了中東研究團隊的基礎,后在王鐵錚老師、黃民興老師帶領下,多年深耕,一脈相承,發(fā)展下來。第四,營造良性學術競爭環(huán)境。團隊建設一定要有良性競爭的學術環(huán)境,不能寡淡,不能急功近利,要勇于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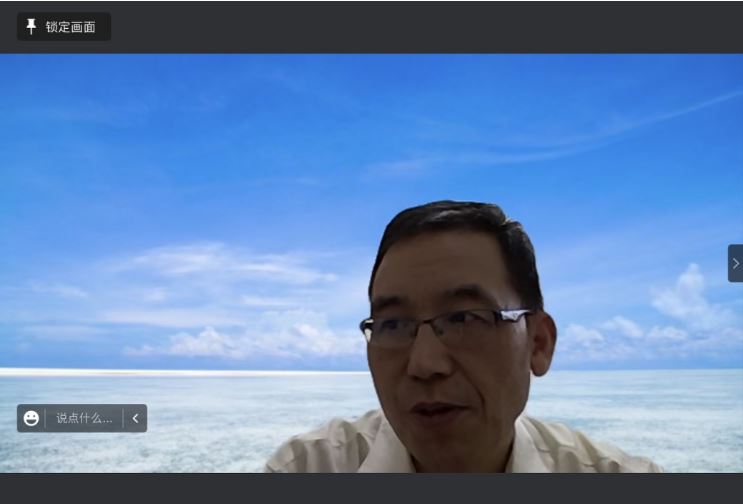
黃民興
黃民興教授結(jié)合自身工作經(jīng)歷和西北大學世界史博士點申報經(jīng)驗,從學科困境、區(qū)域國別研究成就和發(fā)展機遇三個方面分析世界史學科的未來發(fā)展方向,對區(qū)域國別學科對世界史學科發(fā)展的影響表達了看法。第一,學科困境。世界史學科困境早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國家轉(zhuǎn)向經(jīng)濟建設、注重實用學科時就已呈現(xiàn)。歷史學注重基礎研究,不能直接應用于經(jīng)濟、科技發(fā)展,相對而言就不太受重視。隨著歷年來問題的積累和新情況的出現(xiàn),世界史面臨更多困境。英語、日語等通用語言的使用使世界史過分注重歐、美、日等大國史的研究,忽視歐洲小國和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研究。受諸多因素制約,2011年世界史升級為一級學科并沒有改善學科困境,世界史在各個方面仍然面臨很多發(fā)展瓶頸,比如世界史學科點的數(shù)量特別是博士點的數(shù)量和其他學科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第二,區(qū)域國別研究成就。關于區(qū)域國別研究,國內(nèi)的認識存在誤區(qū)。一種觀點認為區(qū)域國別史直到今年才被列入學科目錄,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區(qū)域國別研究機構(gòu)很早就存在,比如1964年西北大學設立了中東研究所,這是國內(nèi)最早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之一,在中東研究方面頗有名氣。此外,隸屬于世界史的區(qū)域國別史研究也已經(jīng)存在很久,比如西北大學世界史下屬的“世界地區(qū)史·國別史”(南亞·中東)學科點1986年就已設立。1986年以印度史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彭樹智先生和中東研究所聯(lián)合申報世界史博士點,本來申報的是世界近現(xiàn)代史,審批下來的學科點是世界地區(qū)史·國別史(南亞·中東),是全國高校中有關方向的第一個,與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其他已經(jīng)擁有同類學科點的老校、名校相比,這突出了西北大學的學術優(yōu)勢,提高了學校地位。因此,區(qū)域國別研究早已名列國家學科目錄,西北大學的世界地區(qū)史·國別史二級學科博士點就是實例。從學科的角度看,是世界史學科最早設立了區(qū)域國別史研究。幾十年來,西北大學在該學科點培養(yǎng)了一百多位博士,發(fā)表出版了很多成果,世界史學人對學科發(fā)展一定要有充足的自信。第三,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機遇。社會對世界史學科有需求,世界史應該向什么方向發(fā)展?創(chuàng)辦刊物、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都值得探討。2022年9月發(fā)布的新學科目錄增設區(qū)域國別學為交叉學科一級學科,可以授予法學、文學、歷史學三個學科學位,這為世界史學科提供了新的發(fā)展機遇。區(qū)域國別的研究重點不是歷史,而是現(xiàn)狀,因此世界史研究的學者和機構(gòu),在立足基礎研究的同時,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課題申報要適當?shù)叵蛑行摇⑾颥F(xiàn)實問題、向應用領域轉(zhuǎn)移,這既是挑戰(zhàn),也是機遇。區(qū)域國別史確實是世界史應注重發(fā)展的新方向,如何去發(fā)展,需要認真地討論和研究。第四,學科評估帶來的沖擊和挑戰(zhàn)。近年來,學科評估日益受到重視,它對評估學科有一定好處,但這個指揮棒被過度重視會沖擊一些小弱學科的生存地位。一些地方高校擁有一些弱勢學科,但這些學科對地方社會發(fā)展經(jīng)濟有用。現(xiàn)在,有的學校為了發(fā)展重點優(yōu)勢學科進入全國前列學科,把一些小的、弱勢學科裁撤,這究竟是不是好事?高等教育終究是服務于國家、地方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如果一切都為了學科評估,高等教育最后會走向何方?只能有待未來的觀察。

李劍鳴
李劍鳴教授首先談及當前世界史學科發(fā)展面臨的不利形勢。不過李劍鳴教授也指出,大的局面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我們能做的事情,一般限于學科自身的范圍。建設好我們的學術共同體,就是當下能做的一件事。我們可以從不同的維度和層次來推進學術共同體的建設。首先,我們要重視學術共同體的國際性和跨國性。世界史研究者一定要有國際主義的情懷和眼界,大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向國際史學尤其是歐美史學取法。在這方面,環(huán)境史、醫(yī)療社會史的學者做出了比較突出的成績,值得其他領域的學者效法。其次,世界史研究要跟整個中國史學一起成長。中國史領域近年有許多出色的成果,比如黃道炫教授的黨史研究,劉永華教授的歷史人類學研究,都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啟發(fā)。世界史學者應當跟中國史同行多溝通,抱著小學生的心態(tài)向他們學習。世界史研究只有跟上中國史研究的步伐,才有更大的希望。最后,同行之間需要互相分享,彼此交流,這是學術共同體的支柱。要帶著欣賞的眼光看待同行的研究,不僅要分享研究資料,而且要相互引用研究成果。費正清當年寫《中國新史》,就引用了近千種同行的論著,幾乎囊括了當時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全部有代表性的文獻。同行之間的討論、批評和引用,有利于增加本土的學術積累。第四,師生關系也是學術共同體的組成部分。老師和學生、特別是導師和研究生的關系,也屬于同行的范疇,而不是“老板”和“打工仔”的關系。老師要跟學生平等地探討問題,學生可以發(fā)問,也可以質(zhì)疑;老師要接受學生的追問,要反思自己的想法。在指導學生寫論文時,最好是采取討論的方式,而不要居高臨下地“指手畫腳”。這有助于激發(fā)學生的靈感,增強他們的自信。總之,世界史學科雖然是一個小學科,似乎也不太受重視,但我們這些世界史研究的“從業(yè)者”,還是要有一點學術上的“貴族氣質(zhì)”,在推進學術共同體建設的同時,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好學者,一個好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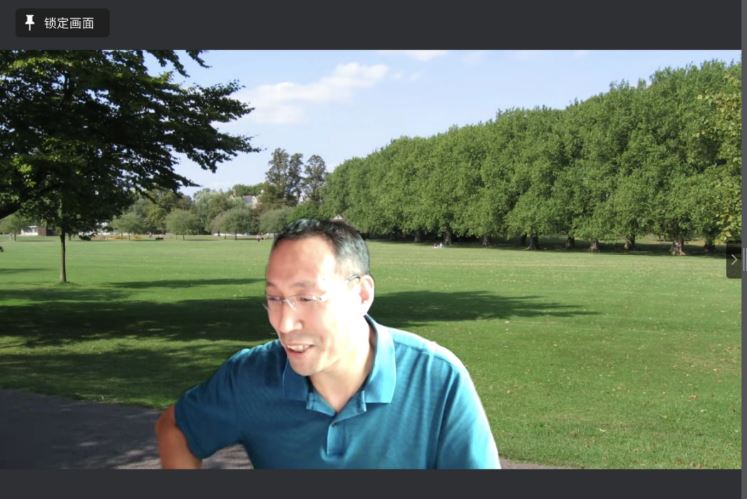
李云飛
李云飛教授結(jié)合自身的工作環(huán)境和研究體會,談了學科方向整合的困境、資政建言和學術研究的關系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構(gòu)建三個問題。第一,學科方向整合的困境。暨南大學基于特殊的辦學使命,歷來重視東南亞史、華人華僑史的研究,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大多聚集到了學校成立的國際關系學院和華僑華人研究院。文學院歷史系世界史學科雖然也有部分教師研究東南亞史,但總體來說,不得不采取與國際關系學院差異化發(fā)展的道路,著力建設古代中世紀史、冷戰(zhàn)國際史、南亞、西亞史。第二,黨和國家在國際新格局下面臨新的挑戰(zhàn)和新的需求,暨南大學的人文社科研究特別重視資政報告的撰寫,并出臺了一系列應用類研究成果的認定和激勵的措施。歷史學尤其是世界史研究確實有資政建言的空間、潛力和責任,但是世界史學者應當如何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平衡和取舍,值得深入思考。第三,學術共同體中同行互相交流和引用。李云飛教授特別認同李劍鳴教授提出的構(gòu)建學術共同體及同行相互交流和引用的觀點。他指出,微觀研究的深入使得中觀、宏觀的理論問題容易被忽視,學者之間彼此自說各話,缺乏共同話題,由此造成學術共同體之間關系松散。結(jié)合自己研究體會,李云飛教授建議學界同仁在開展微觀個案研究時更多關注同行,甚至是中國史同行所關注的話題,比如國家認同、國家構(gòu)建、中央與地方關系、文明互鑒、比較帝國史等。微觀研究如果能與共同話題有勾連或爭鳴,就更有益于活躍學術氛圍,促進學科發(fā)展。

郭長剛
郭長剛教授以樂觀的心態(tài)看待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現(xiàn)狀,從知識生產(chǎn)、歷史理解等角度,探討了世界史學科研究范圍、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特色培育等問題。第一,歷史研究不應期待被高度重視。實際上,世界史學科也沒有被漠視,不然也不會在2011年被升格為一級學科,現(xiàn)在區(qū)域國別學的設立也是對世界史重要性的認可。第二,拓展世界史研究范圍和領域。我們現(xiàn)在的世界史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非常有限的十幾個國家,主要是歐美,現(xiàn)在世界上人口超過一億的國家除了我們還有13個,這13個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只有對美國和日本的研究相對比較多。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突破西方中心論是很難的,所以,世界史的研究任重道遠,必須擴大研究的覆蓋面,為社會提供更為豐富的關于“世界”的知識供給。第三,特色培育。可以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新思考傳統(tǒng)理論的適用性問題,如工業(yè)化問題、全球發(fā)展問題;可以設置更多的議題,如族群沖突問題、宗教沖突問題、地緣競爭問題等。最后,郭長剛教授呼吁上海市世界史學界勇?lián)厝危崆爸\劃,推動世界史研究和區(qū)域國別研究早立潮頭。

陳恒
陳恒教授的發(fā)言體現(xiàn)了資深教育者和專業(yè)學者的憂患意識和現(xiàn)實關懷。他首先肯定了上海市世界史學會是全國最團結(jié)合作的團體,然后話鋒一轉(zhuǎn),拋出了世界史學科及相關討論令人悲觀的境遇。第一,教育的異化。各種討論看似熱鬧,卻是教育的異化,即“見物不見人”,因為所談一切都脫離了教育的本質(zhì)。教育的本質(zhì)是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但很少有人在討論和實踐中考慮這一問題。第二,世界史學科未來前景不容樂觀。世界史本就屬于新興學科,在發(fā)展過程中也面臨著各種問題,所以世界史同仁不能太樂觀。有機會能為這個時代,為世界史學科做出貢獻,實屬時代眷顧。第三,做大世界史學科困難頗多。受大環(huán)境影響,世界史研究隊伍小,基數(shù)不夠。目前全國從幼兒園到大學有1884萬教師,在編在崗全職高校教師256萬,其中專職教師187萬,世界史研究者不足1000人。2011年世界史升級為一級學科后,也只有京津滬、東南沿海的高校世界史發(fā)展較好,很多傳統(tǒng)的世界史強校日益衰落。所以世界學科一定要抓住區(qū)域國別學可以授予歷史學學位點的機會,不要討論可能存在的負面作用,要乘勢壯大學科隊伍,擴大話語權(quán),培養(yǎng)高端應用型人才,提升學科地位。第四,世界史學界現(xiàn)實關懷不足。首先,缺乏面向公眾閱讀的寫作,學識沒有用于服務社會、服務當下;其次,缺乏改革課程體系、課程設置的討論,各學校基本遵循傳統(tǒng),很少思考如何設置應時代之需的課程體系;再次,缺乏優(yōu)秀教材。陳校長提議上海大學、華東師大等上海高校聯(lián)合召開研討會,認真討論課程體系和課程設置改革的問題。關于教材,陳校長極為推崇葛兆光先生講義的寫作模式:熟稔中國傳統(tǒng),敘事能力高超,熟知學術前沿,文筆生動,通俗易懂。法無定法,式無定式,他呼吁專家學者們發(fā)揮聰明才智,為學生為研究者寫好教案,編好教材。第五,學界缺乏三個意識,即問題意識、分享意識、世界意識。克服體制的弊端、改變自娛自樂的治學旨趣、減少內(nèi)卷、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做成世界性學問應該是學界同仁共同努力的方向。

歐陽曉莉
歐陽曉莉教授回應前面幾位嘉賓的話題,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經(jīng)歷和感想。她對李劍鳴教授提到的師生關系、同行對話交流、同行互相贊賞、互相分享感觸頗多,談到碩士期間導師資助電腦,博士畢業(yè)后美國導師幫助修改其即將出版的書稿,感慨指導學生寫出好文章難于自己寫出好文章,并向發(fā)言的各位老師致以敬意。她還通報了復旦大學《西方古典學》和《西方史學史》兩份輯刊的創(chuàng)辦情況,介紹了復旦大學的學程項目,該項目為本科生提供希臘語和拉丁語課程,從而激發(fā)了學生對古典學和古代文明研究的興趣。難能可貴的是歐陽曉莉教授擁有良好的學科知識普及和服務社會的意識,她給小學二年級學生做講座,教他們寫楔形文字,她去博物館開展知識普及活動,她為游戲公司做專業(yè)咨詢,為古代文明學科能夠在中國獲得可持續(xù)發(fā)展貢獻力量。

徐有威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徐有威教授主要研究當代中國史,對世界史頗感興趣。他介紹了自己近年來從事中國小三線研究的經(jīng)歷和感受。第一,要有世界史的視野,擅于從世界史的視角發(fā)現(xiàn)中國史研究的新亮點。當代中國的三線建設是冷戰(zhàn)的產(chǎn)物,搞清楚小三線建設有利于深入理解國際冷戰(zhàn)史,也體現(xiàn)中國史學研究對國際冷戰(zhàn)史的學術貢獻。第二,要有國際主義的情懷,積極向國外宣傳推介中國的學術研究成果,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國學術話語權(quán)。他的小三線口述史著作,已經(jīng)在美國出版。第三,嘗試多元化的歷史知識普及方式。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線研究成果已成為電影、電視、紀錄片和博物館的素材,普及了歷史知識,彰顯了學術研究的現(xiàn)實價值。徐有威教授的研究為中國史研究走向世界提供了成功經(jīng)驗,也為世界史學科探索新的研究方向提供借鑒。

劉義、柴彬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劉義教授和柴彬教授也參與了討論。劉義和柴彬教授結(jié)合工作經(jīng)歷談及寬松的團隊氛圍、協(xié)作團結(jié)的團隊精神和勇于擔當、富有魄力的學科帶頭人對人才培養(yǎng)和學科發(fā)展的作用。
最后,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勇安教授作總結(jié)發(fā)言。張院長衷心感謝線上線下各位前輩、專家及同仁們的支持、指導和真知灼見,也期待各位同仁能夠有機會線下相聚,為世界史學科發(fā)展貢獻智慧,共商、共建世界史學科學術共同體,將來共享這個共同體帶來的收獲。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