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伍爾夫的倫理選擇與中國之道

電影《時時刻刻》劇照
20世紀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構思小說《達洛維夫人》時曾這樣闡明其創作意圖:“我要描寫生命和死亡,健全和瘋狂;我要批判社會體制,以最強烈的形態揭露它的運行。”她在創作意圖中所表明的“雙重性”和她在小說中將主要和次要人物的處世之道和生死之道并置的“雙重性”,表明她的作品隱含著倫理選擇。
近年來,中西學者已開始關注伍爾夫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帕特麗莎·勞倫斯在《伍爾夫與東方》和《麗莉·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中論述了以伍爾夫為核心成員的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與中國“新月派”詩社的文化交往關系。高奮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中國眼睛”》中考證了伍爾夫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指出伍爾夫作品中的三雙“中國眼睛”分別體現了她對“中國式創作心境、人物性格和審美視野的感悟”。若能進一步深入探討中國之“道”在伍爾夫作品中的深層意蘊,就會更有益于更深層次地闡明中西思想的交融。
伍爾夫小說中對中國的描寫體現了由表及里的過程。在小說《遠航》(1915)中,中國作為一個遠東國家被提到;在《夜與日》(1919)和《雅各的房間》(1922)中,出現有關中國瓷器、飾物的描寫;在《達洛維夫人》(1925)和《到燈塔去》(1927)中,兩位重要人物伊麗莎白·達洛維和莉莉·布利斯科都長著一雙“中國眼睛”。從籠統的地理概念到具體的文化物品,再到傳達情感和思想的眼睛,伍爾夫對中國的領悟逐漸進入靈魂層面。《達洛維夫人》是她以中國之“道”為鏡,反觀西方文化,表現其倫理取舍的典型作品。
《達洛維夫人》的顯性和隱性結構均體現“道”(way)的喻義。小說的顯性結構包含兩條平行發展的“倫敦街道行走”的主線:一條表現克拉麗莎·達洛維與親朋好友,從一早上街買花到盛大晚宴結束的一天活動;另一條表現賽普蒂莫斯·沃倫·史密斯與妻子行走在倫敦街道,找醫生看病,直至賽普蒂莫斯傍晚跳樓自殺的一天活動。兩群人互不相識,但他們同一時間在相近的倫敦街道行走,幾次擦肩而過。他們在街道、人群、車輛、鐘聲、天空、陽光所構建的聲光色中觸景生情,腦海中流轉著戀愛、家庭、社交、處世、疾病、困惑等五味雜陳的意識流,突顯他們不同的處世之道和喜怒哀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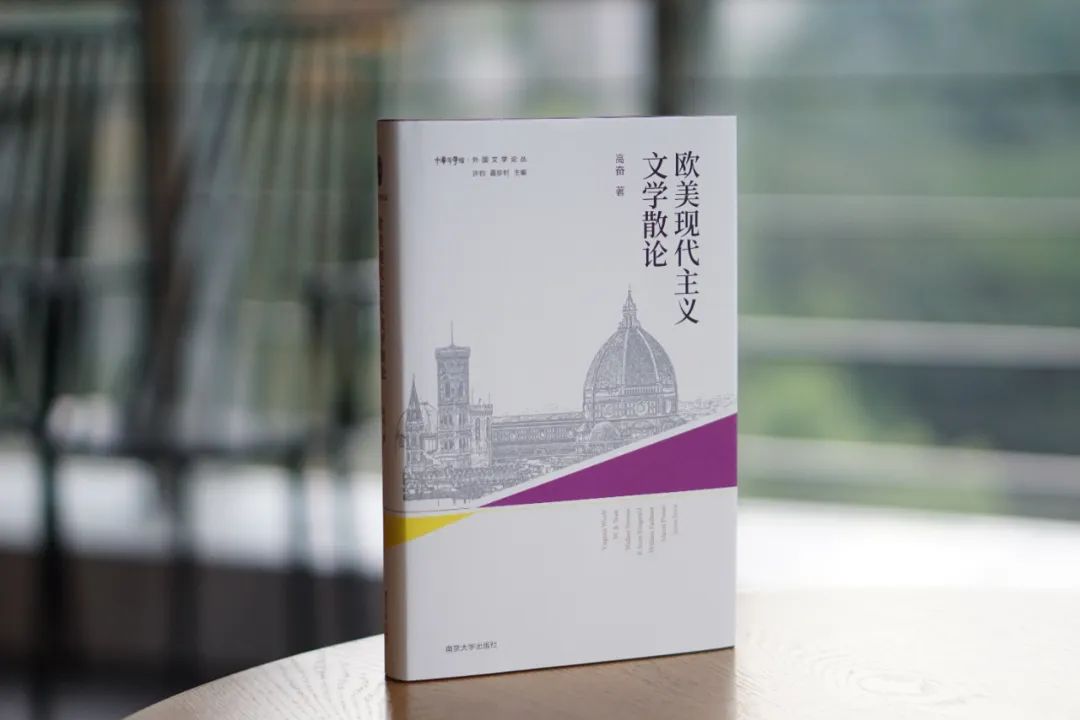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
小說的隱性結構是由“道”(way)這一關鍵詞所編織的網狀結構構成的。小說中“way”這一單詞共出現73次,比較勻稱地用于主、次要人物的性格和言行描寫,也用于描寫社會和大自然的運行之道。這73個“way”就像漂在水面上的浮標,標示出人物的處世方式和生命態度,浮標的下面連接著人物的意識流大網。這是伍爾夫最欣賞的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靈魂描寫模式,她曾這樣概括陀氏作品的隱性結構:它用“海面上的一圈浮標”聯結著“拖在海底的一張大網”,大網中包含著深不可測的靈魂這一巨大的“海怪”。不過《達洛維夫人》中的“way”浮標,所連接的是多人物的意識并置,與陀氏的深度靈魂探測略有不同。
小說的基點是主人公彼得的夢中感悟,他在夢境中將生命視為一種超然物外的心境:“在我們自身以外不存在其他東西,只存在一種心境(a state of mind)……那是一種愿望,尋求慰藉,尋求解脫,尋求在可憐的蕓蕓眾生之外,在脆弱、丑陋、懦弱的男人和女人之外的某種東西。”整部小說就是由多個人物的心境縱橫交叉所構成的巨網,充分展現“生命和死亡,健全和瘋狂”的對抗與連接,但人物的心境各不相同:“人人都有自己的處世方式。”(Every man has his ways.)伍爾夫像羅素、韋利、毛姆等學者作家一樣,“把目光轉向東方,希望在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哲學文化中找尋拯救歐洲文化危機的出路”,伊麗莎白的“中國眼睛”就是顯著的標志。
伍爾夫將人物的倫理道德融入他們的處世方式之中,用并置方式展現,然后從克拉麗莎的視角做出倫理批判。小說無章節,大致可分成12個部分,每個部分聚焦某特定人物的意識流,大體呈現“克拉麗莎·達洛維—賽普蒂莫斯—克拉麗莎—彼得(克拉麗莎的前男友)—彼得—賽普蒂莫斯—賽普蒂莫斯—理查德·達洛維(丈夫)—伊麗莎白·達洛維(女兒)、基爾曼(家庭教師)—彼得—彼得—晚會”這樣的人物交叉并置形態。
以“無為之道”反觀“獨斷之道”
老子《道德經》中的“無為之道”,既是社會治理之道,也是個人處世之道,其主要內涵有二:一是順其自然。老子認為,“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
也就是說,有道之人以“無為”的態度來處理世事,讓萬物興起而不加倡導;生養萬物而不據為己有,作育萬物而不自恃己能,功業成就而不自我夸耀。無為,就是讓萬物自由生長而不加干涉,一切隨順。二是無欲無爭。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就是說,“道”永遠是順其自然的,然而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它所作為的……不起貪欲而歸于安靜,天下自然走上正常的軌道。無為,就是無欲。
伊麗莎白·達洛維、理查德·達洛維和薩利·西頓三個人物均表現出順應天性、無爭無欲的處世之道,體現“無為”之道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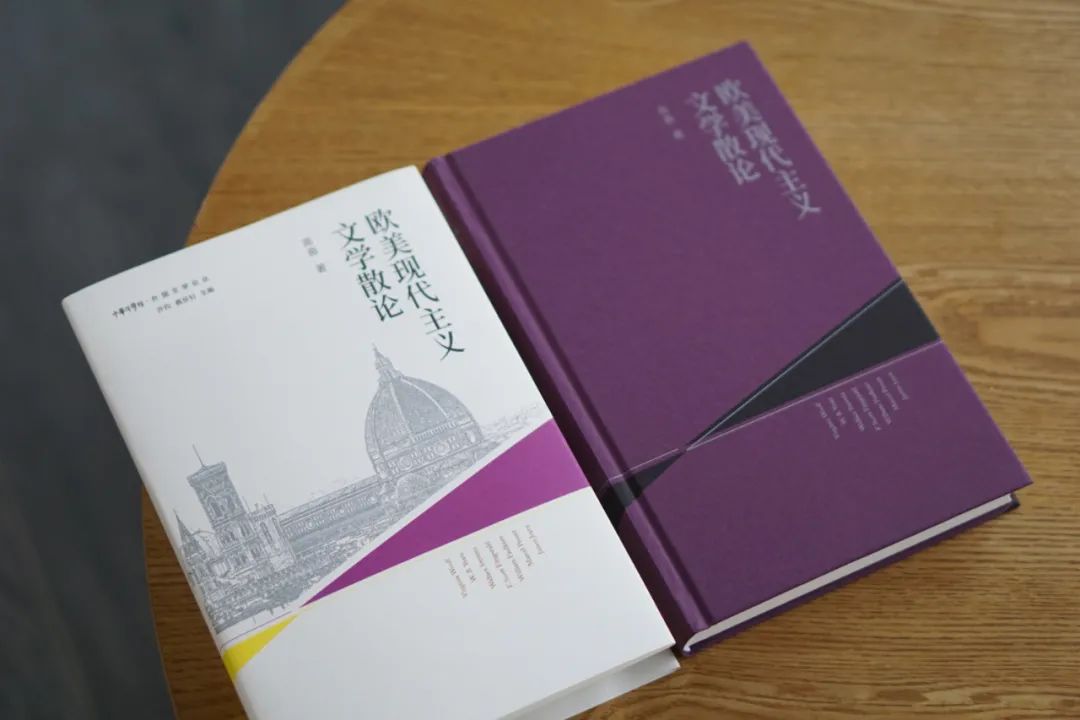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
伊麗莎白,克拉麗莎和理查德的女兒,她的處世方式是“趨向消極”(inclined to be passive)。她不像達洛維家族其他成員一樣金發碧眼,而是一位“黑頭發,白凈的臉上長著一雙中國眼睛,帶著東方人的神秘色彩,個性溫和、寧靜、體貼”的女孩。她的眼睛“淡然而明亮,帶著雕像般凝神注目和不可思議的天真”;她喜歡“自由自在”;喜歡“住在鄉村,做她自己喜歡做的事”,不喜歡倫敦的各類社交活動;她想從事“某種職業”,成為醫生或農場主;她推崇“友善,姐妹之情、母愛之情和兄弟之情”(geniality, sisterhood, motherhood, brotherhood)。伊麗莎白的“消極”處世方式在小說中并無負面含義,而是一種人人喜愛的品性。她母親克拉麗莎覺得伊麗莎白“看上去總是那么有魅力……她幾乎是美麗的,非常莊重,非常安詳”;她的家庭教師基爾曼雖然對世界充滿仇恨,卻“毫無嫉妒地愛她,把她看作露天中的小鹿,林間空地里的月亮”;親朋好友們將她比作“白楊樹、黎明、風信子、幼鹿、流水、百合花”。伊麗莎白自由自在、無欲無爭的性情,體現的正是老子的“無為”之道。老子相信,“無為”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無有入無間”,無形的力量能夠穿透沒有縫隙的東西。這也正是伊麗莎白獲眾人喜愛的原因:她像大自然那樣自在地顯露天性,無爭無欲,盡顯善意。眾人被她的美麗和單純折服,視其為自然之化身,“友善,姐妹之情、母愛之情和兄弟之情”之象征。
理查德·達洛維的處世方式是“客觀明智”,與伊麗莎白一樣展現“無為”的處世方式。“他是一個十足的好人,權力有限,個性敦厚,然而是一個十足的好人。無論他承諾了什么事,他都會以同樣的客觀明智的方法去完成,不摻雜任何想象,也不使用任何心機,只是用他那一類型的人所特有的難以描述的善意去處理它。”“他性情單純,品德高尚……他行事執著頑強,依照自己的天性在下議院中維護受壓迫民眾的權益。”他給予親朋好友支持、關心和尊嚴。達洛維先生“客觀明智”的處世方式的最大亮點在于,他始終用自己的天性去看待事物,保持事物的本真面目,順其自然地處理事物,不摻雜個人的偏見和欲念,具備輕松化解矛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保持自己天性的純真自在,不違心,不委曲求全。他所達到的境界就是老子所說的,“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以無為的態度去作為,以不攪擾的方式去做事,視恬淡無味為味。達洛維處世方式的根基是他單純、善良、寬容、敦厚的“無為”品性,這正是克拉麗莎拒絕前男友彼得而嫁給達洛維的原因,她從他那里獲得真正的幸福。
薩利·西頓的處世方式是“我行我素,絕不屈服”(gallantly taking her way unvanquished)。她作為克拉麗莎的閨蜜,在一次散步中忽然吻了她一下,被彼得看見了,“而薩利(克拉麗莎從未像現在那樣愛慕她)依然我行我素,絕不屈服。她哈哈大笑”。她喜愛花道,頗具超凡脫俗的東方神韻:“薩利有神奇的魅力,有她自己的天賦和秉性。比方說,她懂花道(way with flowers)。在伯頓,人們總是在桌上靜置一排小花瓶。薩利出門去摘些蜀葵、天竺牡丹——各種以前從不會被放在一起的花——她剪下花朵,讓它們漂浮在盛水的碗里。效果極好。”薩利一直以“我行我素”的方式生活著:和父母吵架后,她一文不名地離開家庭,獨立生活;她不喜歡的勢利男人吻了她一下,她抬手就是一記耳光;她嫁給自己喜愛的商人,生了五個孩子,全然不顧世俗的偏見。她熱情、有活力、有思想,生性快活,依循天性自在地生活,大體上屬于老子所說的“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的人,也就是,順其自然而無心作為的有德之人。

電影《時時刻刻》劇照
伊麗莎白、達洛維先生、薩利三人共同的處世原則是依照天性、順其自然、自由自在和無爭無欲。從另一角度看,他們最大的特性是:從不用自己的觀念去強迫和壓制他人;給自己自在空間,決不侵犯他人自由。他們是伍爾夫筆下“健全”(sane)的人。與他們相對的是“瘋狂”(insane)的人,他們試圖以各種名義去壓制和改變他人,不尊重他人,給他人帶來困擾和痛苦。彼得·沃爾什和多麗絲·基爾曼便是這類人物。前者以愛情的名義,用各種方式傷害戀人克拉麗莎,導致戀情破裂;后者以宗教的名義,仇視世界,傷害他人,自己也陷入痛苦深淵。
羅素在《中國問題》中對比中西文化時,曾這樣說:“老子這樣描述‘道’的運作,‘生而弗有(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為而弗恃(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功成而弗居(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人們可以從中獲得關于人生歸宿的觀念,正如善思的中國人獲得的那樣。必須承認,中國人的歸宿與大多數白人所設定的歸宿截然不同。‘占有’(possession)、‘獨斷’(self-assertion)和‘主宰’(domination)是歐美國家和個人趨之若鶩的信念。尼采將它們歸結為一種哲學,而他的信徒并不局限于德國。”如果說伊麗莎白、達洛維、薩利的性情具備“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的中國之道的特性,那么彼得和基爾曼所操持的正是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占有”“獨斷”和“主宰”的信念。
彼得·沃爾什的處世方式是“對抗”(be up against)。他用自己的觀點去對抗社會規則、習俗和所有人,包括戀人,“我知道我對抗的是什么,他一邊用手指撫摸著刀刃一邊想,是克拉麗莎和達洛維以及所有他們這樣的人”。他被牛津大學開除,不斷遭遇各種挫折,一生都很失敗。他與克拉麗莎相愛,情感相通,卻始終只能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去理解她,覺得她“懦弱、無情、傲慢、拘謹”,不斷批評指責她,諷刺她是“完美女主人”,“用一切辦法去傷害她”。克拉麗莎認為他很愚蠢,“他從不遵從社會習俗的愚蠢表現,他的脆弱;他絲毫不理解別人的感受,這一切使她惱火,她一直對此很惱火;他到現在這年齡了還是那樣,真愚蠢”。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很荒謬,“他向克拉麗莎提出的許多要求是荒謬的……他的要求是難以達到的。他帶來許多痛苦。她原本會接納他,如果他不是如此荒謬的話”。彼得體現了西方文化所推崇的“獨斷專行”(self-assertion)信念的某種后果。
基爾曼的處世方式是“自我中心主義”(egotism)。“她知道是自我中心主義導致她一事無成”,但是她覺得“這個世界鄙視她,譏諷她,拋棄她,給了她這種恥辱——它將這具不討人喜歡、慘不忍睹的身體強加給她”。她認為“上帝已經給她指了道,所以現在每當她對達洛維夫人的仇恨,對這世界的仇恨,在心中翻滾時,她就會想到上帝”“她心中激起一種征服的欲望,要戰勝她,撕碎她的假面具”。“控制”和“主宰”(domination)的欲望是她個性中最主要的特征。
伍爾夫通過克拉麗莎的意識流,對彼得和基爾曼以愛情和宗教的名義,獨斷專行地去占有和征服他人的行為做出激烈的倫理批判。“愛情和宗教是世界上最殘忍的東西,她想,看著它們笨拙、激動、專制、虛偽、竊聽、嫉妒、極度殘酷、肆無忌憚,穿著防水布上衣,站在樓梯平臺上。”他們的可怕之處在于,當他們帶著理性的、宗教的觀念去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時候,他們從不尊重生命,從不理會生命的差異,從不知道他們正在毀滅最美好的東西——人的生命本身。
“自我中心”是彼得和基爾曼一葉障目、迷失天性的主要原因。彼得有魅力有才智,“總能看透事物”,但他“生性嫉妒,無法控制自己的嫉妒情緒”,經歷了那么多年的挫折和失敗后,他與克拉麗莎見面時依然只關心“他自己”,克拉麗莎稱之為“可怕的激情,使人墮落的激情”。唯有在睡夢中,他才獲得“平和的心境”(a general peace),仿佛看見大自然用它神奇的雙手向他潑灑“同情、理解和寬恕”(compassion, comprehension, absolution)這些他生命中缺少的、至關重要的東西。他最終明白,“生命本身,它的每一瞬間、每一點滴、此處、此刻、現在、在陽光下、在攝政公園,這就足夠了”。而基爾曼雖然得到了上帝的指引,她內心卻一直在黑暗中苦苦掙扎,期盼自己能夠超越仇恨與痛苦。“她用手指遮住眼睛,努力在這雙重黑暗中(因為教堂里只有虛幻的靈光)祈求超越虛榮、欲望和商品,消除心里的恨與愛。”
正是通過兩組人物的并置,伊麗莎白、達洛維、薩利所代表的“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與彼得和基爾曼所代表的“占有”“獨斷”和“主宰”,兩種處世之道的利弊不言自明。無為之道的根基是善,它的立場是利人利己,因而人人和諧相處,人人各得其所。獨斷之道的根基是一種偏狹的善,它的立場是利己損人,只能導致對立和沖突,結果是害人害己。仇恨、沖突、戰爭是獨斷之道的產物。
本文節選自《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有刪改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
高奮 著
本書從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現代主義作家作品論和現代主義作家論歐美文學三個視角切入,論析歐美現代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威廉·巴特勒·葉芝、華萊士·史蒂文斯、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歐美經典作家作品,探討歐美現代主義文學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并透過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眼睛考察和闡明古希臘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美國文學、俄羅斯文學等歐美國別文學的特性。本書匯集了作者在歐美現代主義文學領域耕耘30余年的部分成果,其中多篇論文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本書的創新特色是探討用中西互鑒方法研究外國文學的立場、導向和特性;提供用中國詩學解讀歐美作家作品的實例;探索中國學者基于本土思維、文化和詩學的跨文化審美批評模式。
你可能還會喜歡:
原標題:《伍爾夫的倫理選擇與中國之道》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