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理論與批評·特輯 | 劉錚×黃德海×金赫楠×王蘇辛:觀察與敘述
原創 劉錚等 上海文學
觀察與敘述
劉 錚×黃德海×金赫楠×王蘇辛
編者按:盧德坤的新作《角色扮演》,并不炫技,卻撬開了一個小說創作的經典問題:小說的敘述者是誰,他或她潛伏在哪個點觀察,我們從他們的視界里又獲得了什么?四位評論者,由此延展,各自發掘出了這篇小說中諸多的對峙:封閉與開放,明與暗,虛和實。于是,這篇具體的作品映射出更寬廣的小說創作形態或是困境,也迫使我們自問,在這世界之中,我們又扮演了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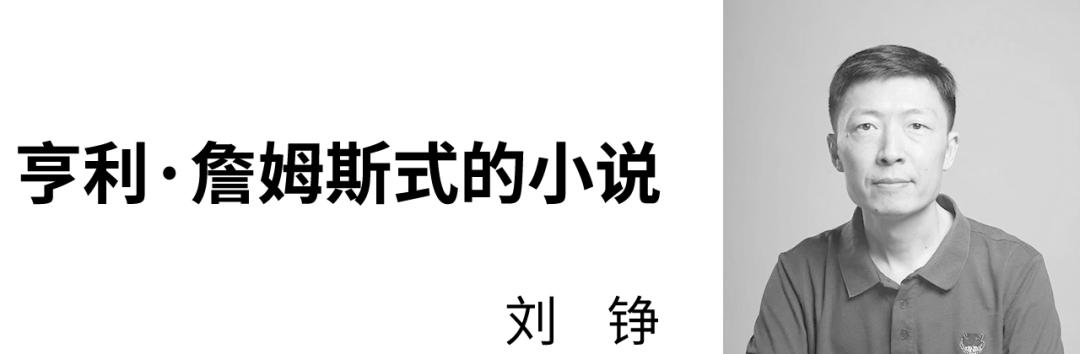
如果大膽一點,我們可以說盧德坤的這篇《角色扮演》是亨利·詹姆斯式的小說,或者至少是朝著亨利·詹姆斯的偉大作品提示的方向努力過了。
我們知道,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說世界里,真正發生過的可稱之為“事件”的事實是非常少的,主要人物之間的關系往往并無進展,而是處于僵持、膠著的狀態,盡管那種僵持、膠著經常比別的作家刻畫的驚險動作更能讓讀者神經繃緊。對于亨利·詹姆斯來說,小說的事件,毋寧是發生在角色心里的。不管是心湖泛起漣漪,還是心潮掀起巨浪,若有一個心不在焉的旁觀者站在故事發生的現場,那他很可能什么跡象也留意不到,因為亨利·詹姆斯筆下的角色斷不會把心事表曝在袖子上(to wear his heart on his sleeve)。在那里,有的是聽不到的轟鳴,看不見的塌陷。
我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角色扮演》是亨利·詹姆斯式的小說的。盧德坤的這部中篇,幾乎沒有什么情節可稱為“事件”。我們不妨試著用一句話概括它的故事:它講的是曾做過“第三者”的女子薛冰因朋友苒苒介紹認識并愛上了一個叫余忠平的未婚男子,但同居一段時間后她發現跟余忠平的感情出現裂痕,瀕于崩解。就這樣一句話,不僅將小說的情節概括了,而且簡直沒遺漏什么關鍵的內容,因為盡管小說似乎在暗示薛冰與余忠平的感情出了問題與苒苒有關,卻也畢竟止于暗示而已,甚或只是薛冰的一種猜度,而無實據。至于小說家把薛冰、苒苒、余忠平安排進娛樂產業的鏈條,讓兩個人作為賣力的編劇為劇本掮客余忠平打工,這種設置,老實講,恐怕不是本質的——它固然使他們之間達生了一種包含經濟關系在內的、合理的關系組合,但是,假如他們事實上的關系換成另一種組合,似乎也不大會影響他們之間情感的拓撲關系,因此,我們不把這種松散的雇傭關系寫進那句情節概述,應該也是無甚問題的。就像之前講過的那樣,《角色扮演》的事件,是發生在角色心里的,更準確一點說,是發生在薛冰心里的。而盧德坤在小說中想成就的,就是讓我們聽到薛冰心里的轟鳴,看見她心里的塌陷。
小說以第三人稱敘述,但視角嚴格限制為女主人公的視角,讀者不知道女主人公不知道的東西,讀者了解的限于女主人公自己觀察、揣測和思考的東西,而且,很自然地,完全不能排除這些東西會誤導讀者的可能。此類手法,恰好是亨利·詹姆斯式的——只要想想《一位女士的畫像》這樣的名著就夠了。薛冰這位女主人公,無疑也具有亨利·詹姆斯筆下某些角色的那種特質:他們不大依靠行動和語言與周遭世界發生關聯,他們寧愿在內心深處對外在世界進行無休止的揣度,偶爾,當世界的棱角規定了揣度的范圍,他們也并不會停止揣度,而是將心靈的指針稍稍轉一個角度,在那個新的方向上繼續思忖下去。他們的希冀是永遠也達成不了的,他們內心的空洞也是永遠填不滿的,因為無論離前定的目標有多近,他們那沒有限度的揣度總會把凡俗的幸福和滿足推得更遠一些。因此,我們既可以承認薛冰對余忠平的猜疑可能并非無的放矢,同時又應該意識到,假如用猜度來審視世界,那就永遠不難找到可供猜度的材料。薛冰手里握著錘子,自然看什么都是釘子。
當然,像一切真正的愛情齟齬那樣,薛冰與余忠平的不能相與,根本原因在于他們不是同一類人。小說以頗為別致的方式提示了這一點,那就是余忠平說的,薛冰“有種特別的表情”。從本質上講,薛冰的精神世界有某種“出世”(other-worldliness)屬性,偶爾形之于外,便是那一恍惚出神的特別表情。而這暗示著薛冰、余忠平的精神是不可能統一到同一個平面上來的。所以,我們會發現,薛冰求之于余忠平的,其實是某種余忠平無論如何不能提供的東西,也正因為如此,薛冰的求索終竟是徒勞的,而余忠平或竟是無辜的。
也許是為了與主人公曲折的心理相適應,小說作者有意采用了一種迂回隱晦、看似大有深意的內心描寫語言。有時候,角色剎那頓悟,讀者卻對她究竟悟出了什么摸不著頭腦。主人公的心理狀態不斷被描述著,但總有那最后一重簾幕,從未為我們升起。這種“疑陣”式的描寫語言,恐怕也很接近亨利·詹姆斯的后期作品所采用的那種語言。
小說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曾在文章里寫過,據說亨利·詹姆斯看了自己不喜歡的稿子,會在退還時習慣性地寫上一句:“您選擇了一個很好的主題,處理得也直來直去。”奧康納說,作者看了這話沒準兒挺樂呵,但亨利·詹姆斯這樣寫其實已經給作品判了死刑,因為他太清楚,比誰都更清楚,直來直去的寫法是無法與好的主題的復雜度相匹配的。“或許我們再也沒有新的內容可講述了,但卻總會有某種新的方式去講述,而在藝術上,講述的方式,已經成為講述的內容的一部分……”當我們回過頭來品味盧德坤的作品,的確也有那種感覺,他講述的方式,已經成為他講述的內容的一部分。甚至于,我們簡直覺得,他講述的方式,就是他要講述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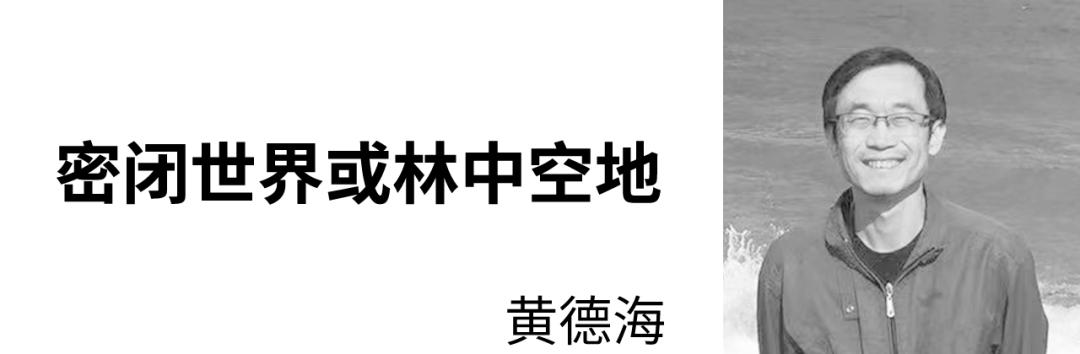
如果“愛”可以拆解成三個部分,無心而生的激情、必然而至的相處、有意而為的扶持,盧德坤《角色扮演》主要致力的,是其中必然而至的相處部分。如果把相處再行拆解,則可以分為恩愛的點點滴滴和排斥的枝枝節節,這小說主要寫的,是后面的枝枝節節。
或許不只是盧德坤如此,凡關涉到“愛”,以至于更廣泛的情感問題,寫作的選擇,很容易就傾向于經常發生矛盾的地方。兩情相悅或傾蓋如故,有多少故事可以寫呢?托爾斯泰不早有明示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角色扮演》中的一男二女,甚或更重要的一男一女,從開頭到結尾,都在相處而排斥的境遇之中。仿佛兩個把自己團抱起來的人,愿意彼此接納,卻每次靠近都反彈了開去。他們似乎在意著自己在對方心目中的形象,也愿意根據對方的愿望做出改變,最終卻是碰撞更有力地塑造了彼此。
這個靠攏又彈開的過程,盧德坤寫得足夠耐心,幾乎每一個細節都經得起認真的審視,可以一小段一小段地推敲其中的轉折和心思。那些一直存在的生疏感覺,時刻能注意到的漠然成分,陡然而生的戒備之心,隱藏在小說的每一個角落,綿密、緊湊、準確,推動著整個故事自然而然地發展。
單純討論小說技藝,可以說,這個作品堪稱出色,甚至是杰出。無論是上面談到的細節,還是沒有言及的章節精心設置,包括作者極力避免的道德判斷,都讓作品運轉如意,從容飽滿,稱得上珠圓玉潤。不過,讀作品的時候,卻也難免會覺得,我不愿意在這個小說的世界里生活,里面的空間有點局促,某些地方壓迫得人喘不上氣來。
用這樣的方式談論一篇小說,有著太多的風險,差不多違背了評價現代小說的鐵律——離開具體的技藝去挖掘作品的潛在內容。當然,鉆探邏輯死角,則任何鐵律背面都樹立著另一條鐵律,比如,什么時候都不應該忽視個人的閱讀感受。更好的談論方式應該是,不過于遵循這些清規戒律,就這樣在對作品和自我的質疑中,慢慢把察覺到的問題說清楚。
想到這一點,回來看這個小說,或許能逐漸發覺,上面提到的局促感,是因為作品給出的是一個密閉世界。造成密閉的原因,正是由于把“愛”的三個相關方面拆分開來,用心于其中的一個部分,而這個部分也只是選取了排斥的側面。抽空了“愛”中無心和有意的部分,只擇取排斥來集中筆墨,當然人人都會成為想要抱團的豪豬,一旦靠近就被對方刺得退遠。
需要考慮的可能是,如果出于各種原因,一個人的世界從開闊走向密閉,就像起始時完整意義上的“愛”最后變成了單一的“愛”,并不屬于上面的情形。密閉世界的說法,只適應于作品落筆時人就已經置身其中的情形。也就是說,密閉世界的情形,并非人物和世界交互發展的結果,而是從開始就是給定的。《角色扮演》里人物的命運,某種程度而言,并未被賦予天然的開闊可能。
小說里的人物一旦被給定了密閉世界,里面就少了人世的天光云影徘徊,密密麻麻擠在一起的全是人事,人們舉手投足都難免成為碰撞或敵意。《角色扮演》里的人物,哪里有片刻的松弛呢?他們要一直挺著腰桿,才不會被這些精心設置的密密麻麻壓垮。
這么說,其實不是很準確,在小說里,起碼薛冰留意到“虛影”的時刻,或者她對“黑化”反思的時候,確乎應該是“什么東西松開了,什么東西又擰緊了”。這個松開又擰緊的瞬間,大概是某種人心深處的片刻松弛,從人事中打撈出一些屬于自我,卻也并不排斥每一個人的空間,可以略微安慰人在世間的塵勞。有點可惜的是,這個瞬間還沒有來得及在小說里充分打開,眾多的煩憂就席卷而來,人只好又一次沉沒在密閉的世界里。
寫到這里,我忽然意識到,前面密閉世界的說法也許并不準確——哪個小說不是一個密閉世界呢?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是,如果你造了一間屋子,不妨開出一扇窗戶;如果你造了一片森林,不妨留下一塊林中空地;如果你造了一個密閉世界,不妨試著讓人物可以摸索出一條更有生機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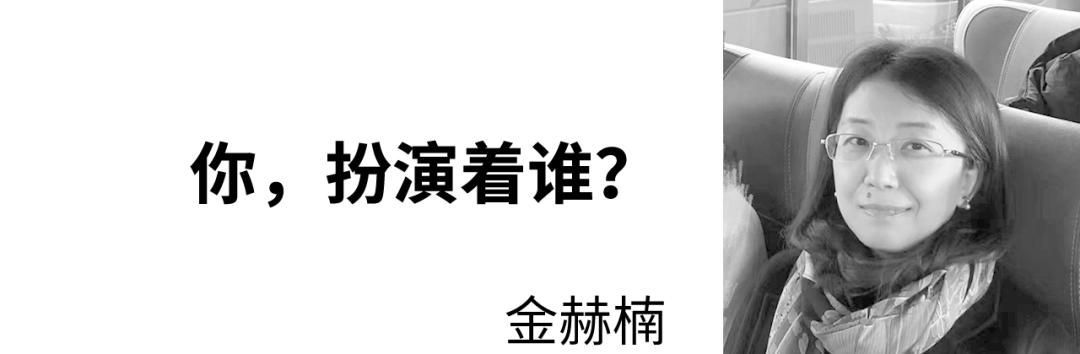
身處一個資訊異常發達的時代,我有時會想,面對浩渺世事及其花樣百出的迅捷傳播盛況,文學講述的獨特價值和必要性,究竟在哪里?當我們以文學的方式來試圖進入一段人生、近身一個人物,在那些看起來清晰明白的戲劇性和因果律之外,那些日常中習焉不察而又真實存在于當代人的生活常態與精神世界中的東西也許才是作家們最大的興致所在,其中所潛藏的諸多奧秘也由此徐徐展開。文學寫作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大背景下,反而更凸顯著自己的獨特使命和魅力所在。
盧德坤的中篇小說《角色扮演》尤其適合拿來佐證文學的這一特質。翻開小說,不過是三個尋常飲食男女,普通甚至多少有點無聊的生活與人生,故事和人物的大致輪廓也不陌生,都還是現實生活和文本講述中早已熟稔的那些心思、情緒和盤點算計。然而這篇小說的妙處就在于它從“角色扮演”這個角度切入了尋常人的普通生活。小說中的三個人物,薛冰、余忠平和苒苒,三個人之間的情愫悄生與暗度陳倉,這些明顯帶有強戲劇性的參差錯落并未成為作者的敘事著力點,他饒有興趣呈現和討論的是他們每個人基于不同場景和心緒之下的“角色”感。二人世界里,買汰燒過程中薛冰自認“家政婦”,不時焦慮著自己的“賢惠值”和“女友力”,而一轉身她又提醒自己須是個“有自己房子的人”,在一段關系中的自我定位和有所依靠與“只是個人的事”在她的意識里來回打轉,相互沖撞又彼此支撐;小說另一位女主角苒苒則在立志和常立志、發愿和常發愿的矛盾反復中樂此不疲地實踐著她的助理編劇角色;而余忠平,三人關系中的男主角,“看上去像個上班族”,轉身又成了薛冰入職的面試官,作為男人又在女人薛冰的回憶中“有滑稽演員的潛質”……同為編劇,三人都試圖清晰厘定自己戲劇內外的生活與人生,卻又往往陷進入戲太深和冷眼旁觀的糾結之中。
小說中有一個饒有意味的情節:余忠平無意中發現和拍下了薛冰的一個表情,而它“十分陌生,與她私有的影像庫里的任何一幀都不相符……畫面里的人,可以說是另一個人;可畫面里的,確是自己啊”。初讀到這里的時候,我理解,作者是在強調薛冰在他人無意中捕捉到自己的表情瞬間中,實現了從一個角度的自我發現和認識。而再往后讀,薛冰翻看苒苒朋友圈時看到一張她的自拍照,照片上的苒苒有“一種明確的似曾相識的感覺”,似乎與自己有些相似,那種不易言明卻能分明感受到的氣息上的相似。“影子或許想否認與本尊的關系,或許不想脫離但又欲脫離,但到底能不能脫離?”——這是小說中薛冰的疑惑,大概也是作者最想要深入探討的命題。
所謂“角色扮演”,其實就是一個人的不同面向。也許,外表看起來再簡單平和的一個人其實也有著豐富和復雜的內心世界,人的不同面向正是這復雜和豐富的不同表現——了然于心和意料之外的、已知和未知的、熟悉的和陌生的。之前的作品中,盧德坤偏愛表達那些時代生活中青年人的內心世界,他們在時光與世事流轉中的難以訴諸言表的孤獨和敏感,以及那些交集在一個人內部的分裂和糾纏。《角色扮演》中,作者延續了這種觀照和講述生活的著力點,薛冰、余忠平和苒苒作為當下城市生活中最尋常又最具時代特征的男男女女,他們內心深處真正的喜嗔哀樂與豐富復雜,既是個體的又是群體的。而文學,作為人類某種意義上的神經末梢,它的功能之一便是感知、勘探和呈現這種豐富與復雜。所以,在文學的意義上,誰又能一口咬定說小龍女和李莫愁就不可能是同一個人的不同角色側面,誰又能確認“謝耳朵”裝(出自美劇《生活大爆炸》,常用來調侃那種有些孩子氣、愛鉆牛角尖的極具個性的人)與福爾摩斯裝之下的男人究竟是不是同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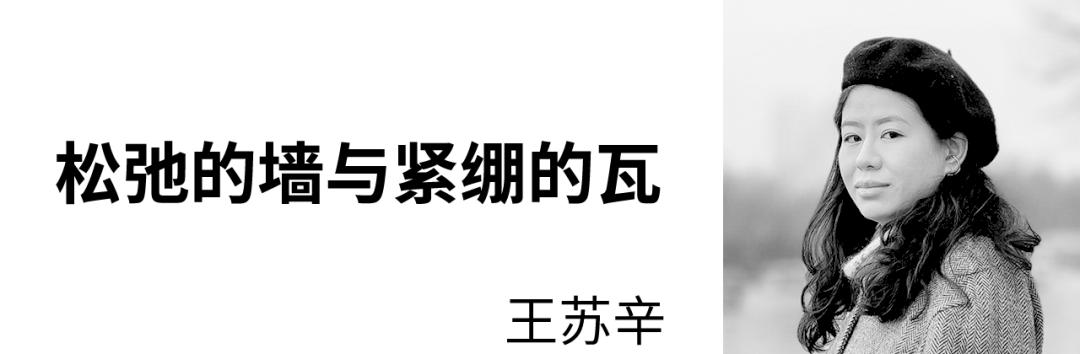
有一段時間,為了糾正自己的坐姿,我在座位的一側擺上一面穿衣鏡。忙碌到想要休息的時候,就瞥一眼鏡中的自己。那鏡中的“我”,不似早晨試穿衣服時的舒展、從容,而總是滿面嚴肅、愁態。總之,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覺得鏡子里的“我”非常古怪。感覺并非自己,而是某個平行世界里的NPC,不知道被誰操縱著。這樣一種感受,和盧德坤中篇小說《角色扮演》里的女主人公薛冰的感受很像。只是薛冰感受到的“不是自己”是從男朋友余忠平的視頻中。很多人或許也都有過這樣的時刻,聽那些自己發出的語音,看每一次他人抓拍的照片、視頻,總覺得那拍的,仿佛不全是自己。有時候甚至與美丑無關,僅僅源自一種陌生。延續到小說中,仿佛是一種不易察覺的差異感通過他人抓拍的形式,被薛冰體察。而男友那仿佛一體、無差別的神色,又因此與她的不同形成一種隱約的較量。
通讀《角色扮演》,這樣的細節很多,盡管張力各有不同。甚至會覺得,這才是盧德坤真正想要寫的。而作為背景的失敗婚姻、茫然前途,或許在別的作家的作品中,往往承載著小說最主要的部分。可在盧德坤這里,它們僅僅只是細節的注腳,閃爍一下,發出含含糊糊的弦音。而小說的弓,真正的核,是薛冰用她的眼,帶我們進入的那些過去與此刻交叉穿梭的神態,仿佛模糊實則清晰的夜晚風物。甚至連薛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或循環或升級中的NPC的某一個環節,那作為密友存在的苒苒也可以是另一個“她”,甚至不管她們到底是誰在“學”誰。如果把作為背景的弦比作“松弛的墻”,那盧德坤真正要寫的,或許是這些“緊繃的瓦”。
很多時候,生活真正的冷酷,不會直接呈現在我們的面前。甚至,人和人之間那最真實以至赤裸的細節,以及與之相應的仿佛屬于生活本身的悲劇感,早就被我們作為常識接受了下來。再去寫,不過是徒勞。盧德坤深諳這一點。所以從一開始,他就把《角色扮演》中,那激情、熱烈的一面,壓實成小說中最不會被提起的暗面。成熟的男女們,以試探性的包容,完善著自己的各種身體與語態反應。那些既自然又克制的表述,既配合又因偶然放肆而流露的真情,及其種種,顯得似乎從未懷疑過那有時堪稱剩余的真情實意。因此,作為閱讀者,雖然難免會覺得這篇小說中的情義過于慘淡——編劇行業的潛規則,人與人之間因為接受的信息不同產生的仿佛無法跨越的鴻溝,情人之間的微微嫉妒和互相審視。可是,虛與委蛇中,撐著的體面中那包含著的一絲真的東西,又足以對人的內心產生一些震蕩,左右著人的一些選擇。好似一個人一邊看到自己赤身裸體,一邊又感受著作者給自己披衣服。松弛的墻似乎隨時可以倒下,可是緊繃的瓦片卻始終緊緊裹著它,因此,生活才一邊慘淡又其實堅不可摧地進行了下去——這,才是真相。
盧德坤這些年的小說并不很多。拿出手的每一篇,卻都足夠細致、綿密,經得起閱讀的審視。究其原因,或許是身為一個成熟的青年作家,下筆都試圖攜帶著一個或許依然有限,卻堅固且成熟的世界觀。小說中所呈現的,是真正獨立者的生活。因此,連那呈現出來的世故也是一種對自我的保護和對世界的理解。于是,盡管作者抓取的敘事空間小如芯片,可這個芯片,卻可以在小說中不斷彈跳,看似輕輕開合,又劇烈抖動著小說所有可能的活力。但作者無意去做生活的探險家或冒險者,他始終小心移動著自己的布局,不讓它進入任何不真實的想象。宛若重影的人,只少量出現的二次元女孩,也有其出路和安排。閱讀者看到的也不是心細如發與抽絲剝繭的破局與入局,而是被內心波段團繞的身體的微微起伏,以及小說形象們仿若照鏡子般試圖捕捉、重新認識和平衡的自我。因此,盧德坤小說中的生活,是在世俗之中卻又破除了世俗偏見的,對底色變化的捕捉。盡管其呈現狀態,都是仿若碎片式的,是和腳步一起行進的地面,是濃和淡的夜色一起捕撈的影像。只要這隱匿的波段一直在發射信號,小說就能延續下去。這樣一種需要耐心才能體會和欣賞的曲線,構成盧德坤小說的情節起伏,也完成著小說人物之間的觀察、試探、猶豫和決絕。
原標題:《理論與批評·特輯 | 劉錚×黃德海×金赫楠×王蘇辛:觀察與敘述》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