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論壇︱生成中的新北京書寫
在中國當代的文學史上,北京文學已經不再是一個地方的概念,作為新中國文學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北京文學涌現出諸多作家、作家,如近些年的《北上》《應物兄》《必須保衛歷史》《世間已無陳金芳》《北京城與年》《小翅膀》《永遠的玩具店》等。在前不久揭曉的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中,北京作協推選申報的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楊慶祥的《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張莉的《小說風景》三部作品分獲短篇小說獎和文學理論評論獎。
新的北京書寫或者說在新的歷史語境里怎么書寫北京,怎樣把此時此刻豐富復雜的北京經驗通過強大的共情力轉化為普遍的人類的經驗?最近,北京十月文學月的重要組成之一、“新時代·新北京·新文學”北京文學高峰論壇舉辦。
論壇共設置三場,第一場是主題演講,嘉賓是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李敬澤,中國作協副主席、北京作協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格非,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第二場是圓桌對談,學術主持人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楊慶祥,與談嘉賓為《人民文學》副主編徐則臣、作家計文君,評論家叢治辰、徐剛;第三場是青年之聲,嘉賓是青年作家馬小淘、李唐和伽藍。

論壇現場
破除繭房,以整全的感受力去表現和書寫世界
主題演講環節,李敬澤分享,自己參評魯迅文學獎時,讀了很多中篇,發現其中有一共同之處:當作家要寫一個異質的、與自己的生活質地不同的現實時,通常會將自己放置于“敘事者”、一個作家這樣一種身份。
由此在面對現實的時候,當一個作家要寫溢出自己邊界之外的那個現實的時候,他本能的一個藝術選擇是,把作家自身的身份派進去作為敘述者。一來保證了心理上的安全,與他的對象、與他的認識、與表現對象之間保持了距離;二來,故事里“作家”與其他人的摩擦、碰撞,不相融,也是小說行進的重要動力,是故事里有戲的部分。
李敬澤認為,這一現象恰可以反映出,文學經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建構,已經逐漸形成文學界的繭房,作家們持有共同的一套言說,來寫作世界、人、人性等等,我們大家都在這套話題里、這個房間里運行,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另一個方面,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進入到一個高度復雜的社會。某種程度上講,無論是經驗上、情感上,還是在理智上,人群和人群之間,人和人之間的阻隔變得更加劇烈,而文學家同樣生活在自己的繭房里,破除這個繭房,這本身就是中國現代文學根本的初心之一。”
回顧之前的作家作品,魯迅的《孔乙己》《在酒樓上》等等,都是魯迅深刻意識到人和人出現了新的阻隔而進行的寫作。“但對魯迅來說、對于那些開啟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驅們來說,這種阻隔不是為了讓我們建立起一個房子自己舒舒服服待著,而是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民主的文學和文化,超越和破除如此眾多的繭房。”李敬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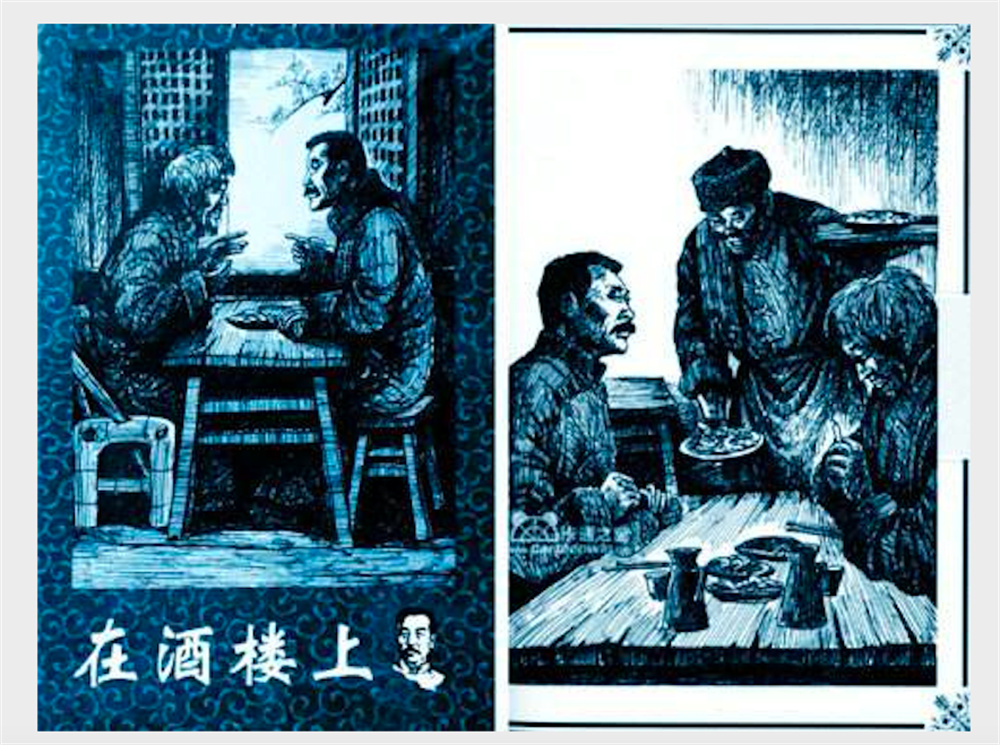
魯迅《在酒樓上》
由此,“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作家們曾經面對廣大的世界,面對不同的人,有信心以無所不知的、整全的感受力去表現和書寫他們,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的限度,同時又樂于在小說中體現和玩味。新時代所召喚的那個新文學,絕不是由于我們的作家年齡新,也不是由于我們的作品在表面風貌上如何新奇和特異,而是我們的作家、我們的文學能不能夠面對正在展開的如此廣大的一個世界,如此復雜的一個生活,有新的態度,有新的方法”。
格非認為,今天這個社會由于社會分工、由于新的產業、新的傳播方式的發展,我們越來越多地進入一個局部的、局部之局部的生存環境當中。現在經常可以看到很多同質化的寫作,跟我們通過資訊、通過朋友圈每天看到的大量的社會新聞、社會事件沒有什么區別,或者說很難做出嚴格的區分。而把熟悉的東西重新變得陌生,這是作家的工作。在寫作中通過語言,通過文學的描繪,我們重新把動詞、名詞、形容詞,把這里面本來就蘊含的巨大力量能夠激發出來,而不是讓它重新變得概念化。這是從技法上、從手法上、從敘事上對作家提出的新挑戰和新任務。
生成過程中的北京文學
張清華以“新時代北京文學的在地書寫與世界眼光”為主題分享道,新時代北京文學還在生成的過程之中,這已是今日文學發展的內在事實,但是關于這一新的文學時段的內在屬性的詮釋,更尚在觀察與探索之中。
北京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活躍與豐收的局面,確乎令人們記憶猶新,且常常懷念。北京從古老的帝都到一座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從傳統的胡同、四合院、大雜院、家屬院這種居住形態,到今天摩天大樓林立的深海一樣的大都會的居住形態,決定北京文學的深刻變化。而且很重要的一點,北京文學既是狹義的行政區塊意義上的地理文學的書寫,同時也是作為中國文學的核心性和標志性的書寫,它不僅僅是其自身,同時也是一個更大的區間和理解的范圍。張清華認為,這也是我們在理解和敘述北京文學的時候所必須面對的一種特殊性和困難。
與時代進程相匹配的,1980年代之初以鄧友梅、劉心武、林斤瀾、王蒙等老一代作家為代表的懷舊式的北京書寫,重新喚回且擦亮北京的傳統形象,把一個有豐富的民間文化、傳統文化、現代歷史的滄桑巨變的記憶重新打撈出來,建立了老舍之后真正具有在地性的北京書寫。

《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照,一種懷舊式的北京書寫
之后一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如王小波、王朔、史鐵生等,以前衛的筆法、戲劇化、戲謔性表現北京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文化與生活形態、生活方式上的新變化,依次展示出開放年代北京的新景觀,他們筆下大量出現改革開放以后以及后革命時代新北京的經驗,這和之前的老舍等老一代作家一起形成北京文學的大傳統和小傳統。
進入到當代,格非在北京居住二十年,鐵凝、閻連科、劉震云、李洱、邱華棟,甚至在北師大工作的莫言、余華等等也都在作品中也相當多地融入北京的文化與形象。
關于新時代的北京書寫,張清華提出,作家們應當自覺聚焦北京歷史文化,凝視當代改革發展經驗,邱華棟的《北京傳》,寧肯的《中關村筆記》《三個三重奏》《北京城與年》等非虛構作品,徐則臣的中關村系列小說等都在這一點上做出開拓;另外,90后青年作家也值得關注,他們的書寫呈現奇幻的、多異的、不同類型風格混合價差的特點,正在為新時代的北京故事增添全新的要素。而且,新一代作家和老一代作家的戀物式寫作不同,更多是轉眼時代的變化,人性的裂變,人心的溫度,著眼于個體的生存際遇,著眼于心靈,著眼于現代生存的壓力與復雜的心理反應,與上一代作家著眼于世事變遷、倫理變化、社會文化價值的更迭、不同話語的激蕩已經幾乎完全不同。
懷著一種“整體性”的野心
圓桌對話環節,計文君首先談道,敘事的邊界在拓展,生活的邊界也在拓展,近些年元宇宙的被關注表明,虛擬世界和我們現實世界不存在二元的對立,它不是科幻,就是現實,它是互相嵌入的,或者說我們某種程度上已經在自我分化。

圓桌對談
“文字的世界基本是成本最低的媒介,它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可能性,作家應該更勇敢一點,有更多的實驗的可能性。對于這種有限性的認知和對于無限邊界的勇敢探索,既敬畏又勇敢的心態可能是每個時代的寫作者應該有的。我們的寫作者在今天也許面臨的任務是重新回歸命名者,我們必須對很多很基本的事物重新進行命名。”計文君認為。
碎片化的確是這個時代的本質,我們如果一直拿著《戰爭與和平》《紅樓夢》的標準要求當下的作家和這個世界,有可能是錯位的。
徐則臣認為,今天接近世界本質的難度是非常大的。“我很喜歡賈樟柯拍的許多素材和畫家劉小東的畫,就是一個場景,我也不賦予這些場景、這些小的紀錄片多少微言大義,他們也不認為能把握這個世界的本質,只是留存這些資料。現在面對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的極其復雜的世界,我有時候想,如果能留下來實實在在的一堆資料,其實已經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楊慶祥同樣認為,世界在當下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流動性:大規模的遷徙、知識在流動、財富和情感都在流動,“所以當下的寫作,寬度并不重要,而深度是最重要的,這個深度直接決定你作品的共情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魯迅不是一個整體的作家,魯迅寫的東西都是幾個點,但那幾個點寫得特別深,你從那一個點能感覺到整個世界。”楊慶祥說。
評論家叢治辰談及,在今天嘗試于寫作中呈現“整體性”,可能是一種幻覺,但是現代文學三十年,當代文學七十年,每一個時期的作家都懷著對整體性的野心和理想,會追逐某種整體性,但是整體性都不可靠。但是,重要的是有一個整體性的野心,并且努力去關照每一個細節。
在青年作家演講環節,馬小淘、李唐和伽藍也分別結合自身的創作,談到了如何在大氣磅礴的時代進行細水微光的寫作,如何寫出動人的嶄新的北京經驗。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