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克萊爾·羅登︱文藝作品中的伊麗莎白二世
依照慣例,大部分媒體訃文的主體內容在傳主過世前早已備好,發表時稍加潤色即可。本文亦不例外,主體在2017年夏天已經完成,彼時女王九十一歲,愛丁堡公爵九十六歲,剛剛退休。《地鐵報》的頭版頭條是“向您脫帽致敬!”,配圖是頭頂日漸稀疏的菲利普王子戴著波樂帽站在雨中。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9日,英國倫敦,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靈柩被安置在倫敦市中心的西敏寺,準備舉行葬禮。
等到女王真的安息時,我至少得看她的葬禮兩次,一次是西敏寺的現場直播,還有一次是2014年在西區舞臺,邁克·巴特利(Mike Bartlett)的話劇《查爾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開頭。巴特利這出無韻詩體的話劇可以視作莎士比亞歷史劇的現代版,2017年5月在電視上播出時,開頭的場景引發了爭議。“最最敏感的問題是如何呈現女王的葬禮,”導演了話劇版和電影版的魯珀特·古爾德(Rupert Goold)說,“以及對在現實生活中要直播葬禮的BBC意味著什么”。
差不多也是那時候,觀眾還可以在網飛平臺一口氣看完彼得·摩根(Peter Morgan)編劇的《王冠》第一季,從伊麗莎白公主和菲利普·蒙巴頓結婚說起。摩根的時間線從中間回到最初再到中間。《王冠》是從他2006年編劇的電影《女王》中衍生出來的,海倫·米倫飾演女王,麥克·辛飾演剛上任的首相托尼·布萊爾,要面對戴安娜王妃去世的棘手局面。這部電影還衍生出了話劇《女王召見》(The Audience),最初也是米倫出演,后來在2015年的重演版中換成了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馬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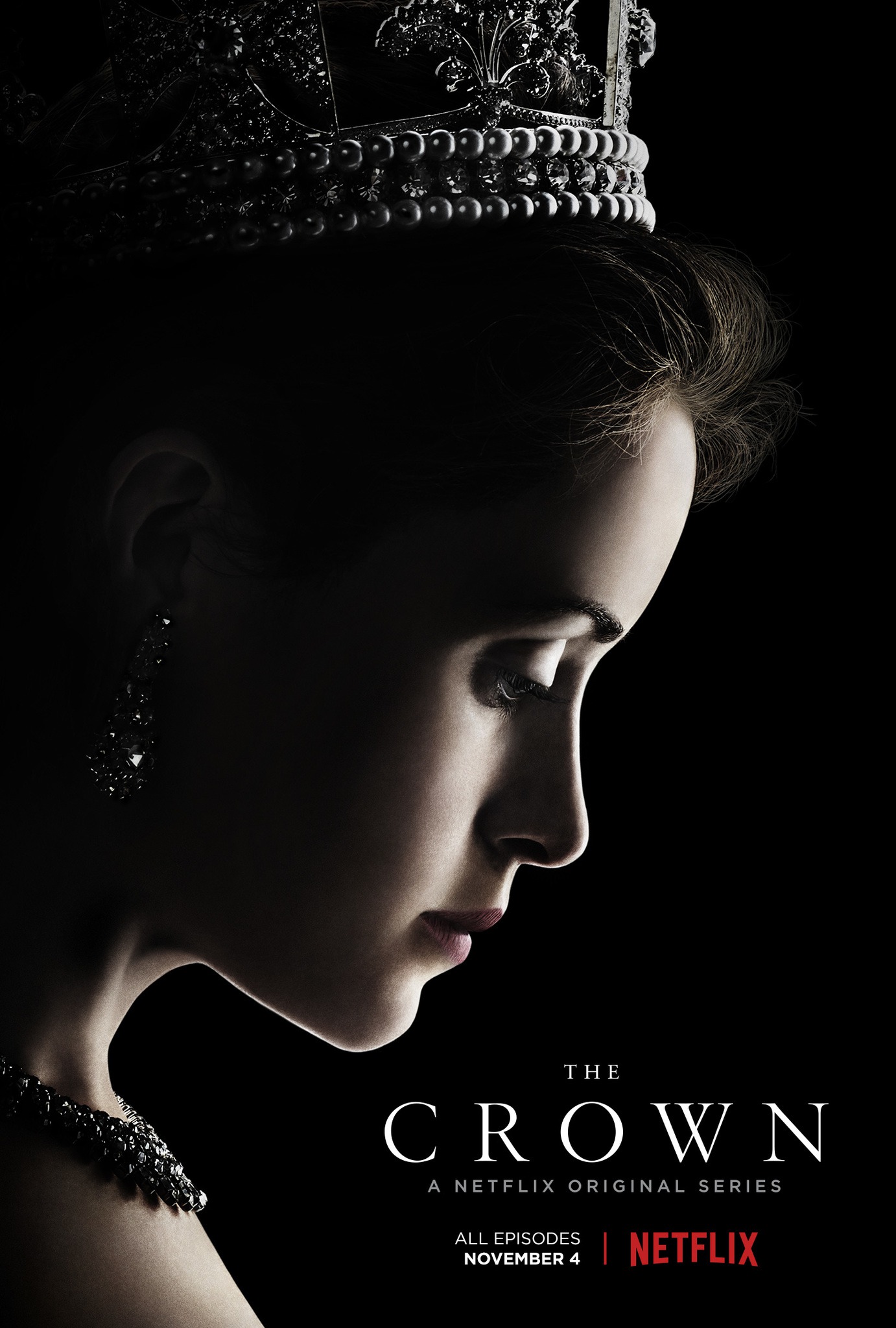
《王冠》第一季海報
我2017年為寫此文做準備時,《王冠》才播出一季,當時尚不清楚是女王的真實人生會先結束還是文藝虛構故事先結束。現在我們知道了。《王冠》第五季將于今年11月播出,講述的是女王六十多歲時的愉快生活,第四季中飾演女王的奧利維婭·科爾曼會交棒給艾美達·斯丹頓。女王真實人生的結局是一個好心腸的編劇不忍心寫下的:她在一場全球疫情中失去了相伴七十三年的丈夫,只能獨自哀悼;她被迫看著愛子當眾出丑;在英國重啟之際感染病毒;九十五歲高齡還要在康復后立刻恢復工作;她沒有等到一場更大更重要的故事收尾(普京的“特別軍事行動”如何收場)就離開了。
那么,在電影里看你自己的死到底是什么感受?不光是你自己的死亡,還有你的童年(2010年的《國王的演講》)、你的少女時代(2015年的《公主夜游記》)、你的垂暮老年(2016年的《圓夢巨人》中,佩內洛普·威爾頓飾演的女王在喝了巨人的自制飲料后放了一個綠色的屁——“噗噗炮”)……所有這些伊麗莎白們在熒幕上飄來蕩去,幾十年的光陰被壓縮在一起。坊間傳聞女王看過電影《女王》和電視劇《王冠》,而且挺喜歡。很顯然,這是坊間傳聞,因為王室的官方立場永遠是無可挑剔地不表達好惡,就連“無可奉告”也不說。“女王陛下是個好姑娘,但她沒什么話要講,”披頭士在《艾比路》專輯的附贈歌曲中唱道,“女王陛下是個好姑娘,但她一天一個樣”。這些特質讓她成為藝術作品無法抗拒的呈現對象:一個活生生的神話,一個可供無限猜想和重釋的公有之謎。
不過伊麗莎白二世應該更傾向于1970年代之后的文藝作品對她的刻畫。熒幕上最早出現的女王形象之一是喜劇短片《翠莎的婚禮》(Tricia’s Wedding)中男扮女裝的斯蒂芬·瓦爾登,該片諷刺了翠莎·尼克松和愛德華·考克斯的婚禮,嘉賓伊麗莎白二世、查爾斯和查爾斯那長得像米克·賈格似的黑人情人都參與了婚禮濫交派對。另一早期“致意”是斯坦利·巴克斯特男扮女裝的系列小品“布蘭達公爵夫人”(靈感可能來自《私家偵探》的布蘭達?譯注:《私家偵探》雜志曾經給英國王室成員起過各種平民名字的外號,諷刺他們努力顯得親民的舉動,女王叫“布蘭達”,威爾士親王叫“布萊恩”,愛丁堡公爵叫“基斯”,瑪格麗特公主叫“伊馮”等等),“她”在“蓋伊·福克斯日的廣播”中發表了惡搞版圣誕祝福:“城堡里的富人、農舍里的佃農、養兔場里的兔女郎都從很久以前的火藥陰謀(譯注:1605年英國天主教徒在國會地下室放置炸藥企圖炸死國王)中獲得了靈感,點燃各自的煙花,享受了一聲巨響的簡單快樂。”

《翠莎的婚禮》
這些還都是無傷大雅的樂子,但在1977年(女王登基的銀禧慶典年),性手槍樂隊發布了真正爆炸性的單曲《天佑女王》:“天佑女王/法西斯政權/他們讓你變成蠢貨/潛在的氫彈/天佑女王/她不是人類/在英格蘭的夢中/沒有未來。”反君主制情緒明顯俘獲了當時的民心,盡管被BBC禁播,該單曲沖上了金曲排行榜的第二位,據說有權勢人物插手,否則本來是要登上榜首的。十年后石玫瑰樂隊的“伊麗莎白我親愛的”化用了中世紀蘇格蘭民歌“斯卡布羅集市”的曲調,詭異地將披頭士“女王陛下”的甜美旋律和性手槍的暴力歌詞融為一體:“撕碎我煮我的骨頭/她不丟王冠我便死不瞑目/我的目標實實在在/我的訊息清清楚楚/你該落幕了/伊麗莎白我親愛的。”
很少有人對伊麗莎白二世登基前的時代還有記憶。她伴隨我們長大,泛泛地說,過去六十年中君主與藝術的關系好比典型的母子模式:從1970年代的青春期叛逆,再到世紀之交十年的溫情和幽默(《王牌大賤諜》《憨豆特工》《辛普森一家》),等到她九十歲以后,人們就只有對曾祖母輩的尊重和奉承了。也許這一軌跡也反映了社會的總體變遷,從為所欲為的無政府傾向、直白的實驗精神轉向了今日以尊重和正確為重的更為小心翼翼的文化。
讓我們比較一下艾倫·貝內特(Alan Bennett)兩次描寫女王的不同——前一次是話劇《歸屬問題》(A Question of Attribution,1988),后一次是喜劇中篇小說《非普通讀者》(The Uncommon Reader,2007)。《歸屬問題》是一次對真與假的相互作用的天才探討,其中涉及表演、藝術、蘇聯間諜安東尼·布朗特的國族忠誠問題,還有女王,作為一個永遠生活在媒體注視下的人物。布朗特的審訊官查布描述了他太太碰上女王巡視薩里:“有人聽到女王陛下說‘多么華麗的購物中心’。我好奇她是真心的么。”話劇毫無疑問地告訴我們,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答案。布朗特在白金漢宮和女王討論假畫和肖像畫,但也許是在討論布朗特本人的“造假”,他對女王說:“它們沒有一個真正捕捉到了您。”針對布朗特對那些肖像畫的評估,女王的回應是:“我不認為人們想被捕捉,不是嗎?至少不是完全捕捉……我不知道人還有秘密的自我,雖然人人都假設人會有。如果能證明人沒有秘密自我,某些報紙就沒啥可做文章的了。”不過她也與其他人的真實自我保持了距離:“麻煩在于,不管我見誰,他們永遠特別有禮貌。一個人特別有禮貌的時刻并不總是他們最好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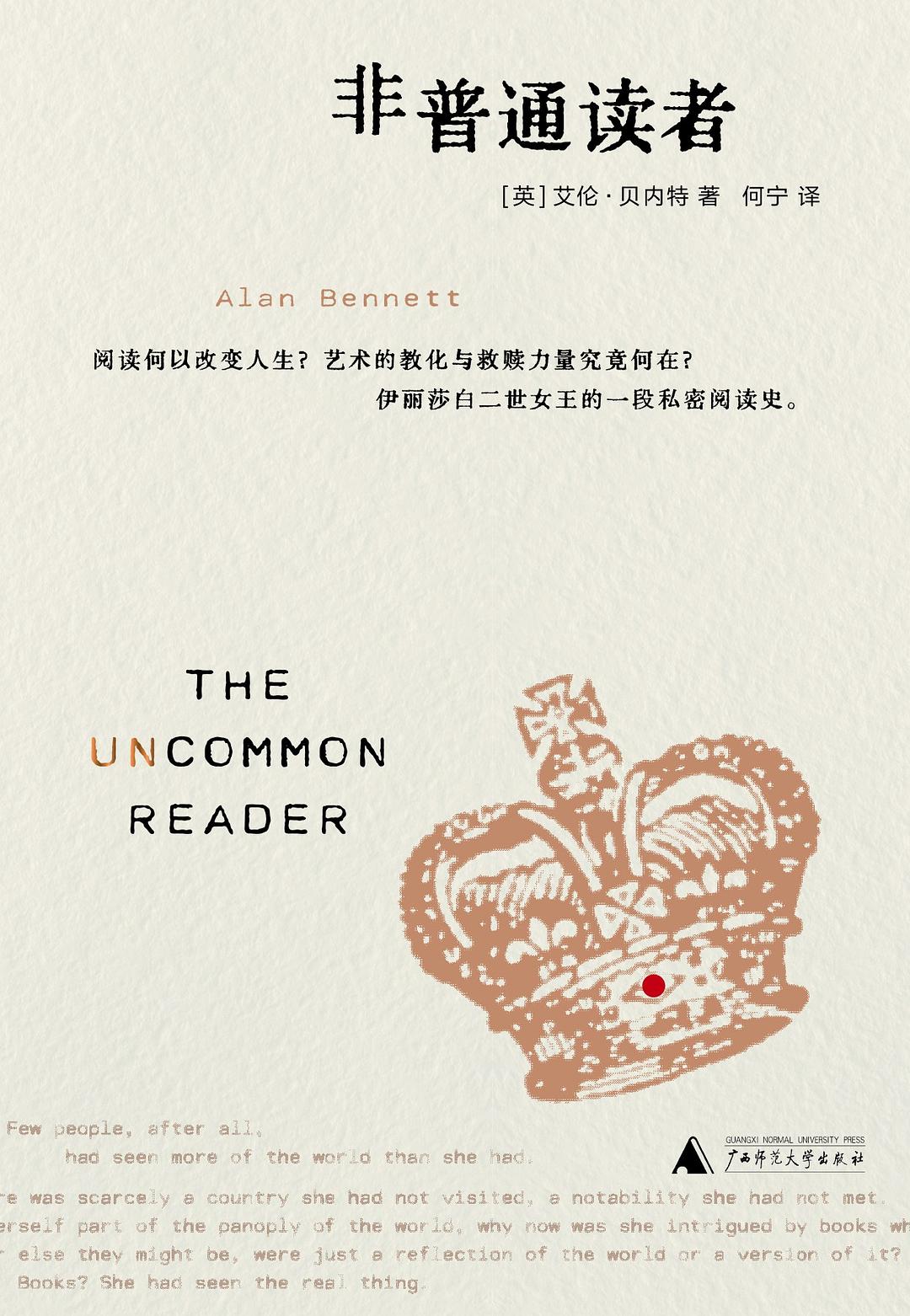
《非普通讀者》中譯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6月版
《非普通讀者》也有相同主題:“她知道自己的約束性,她讓別人害羞,沒有幾個仆人能在她面前表現得自在。”貝內特的再現部絕對是大調的(譯注:古典音樂中大調明朗開闊,小調陰柔沉郁),女王本人并不神秘,甚至像一張白紙:“嗜好隱含了偏向,偏向是必須避免的;偏向會讓一些人感到被排斥。她必須不偏不倚。她的工作是表現出對別人的興趣,而不是讓自己變得有趣。”在這張白紙上,貝內特淡淡地譜寫了自己對女王“真正”自我的狂想曲。一只任性的柯基拖著女王來到王宮里的一間圖書室,她借了一本書,開始成為一個讀者,在大作家的作品中摸索前行,許多作家她都接見過。“她有點兒驚喜地在E.M.福斯特的傳記里讀到他說過如果她是個男人的話,他就會愛上她。”
小說里,不少內廷官員并不鼓勵女王多讀書,但她的新嗜好得到了一個年輕廚子的慫恿,這個叫諾曼的小伙子對她沒有過度的懼怕,令她感到耳目一新。“不過女王如果知道諾曼不怕她的原因是她如此老朽,她的年老已經沖刷掉了王室威嚴,可能就沒那么高興了。”金籠子里的孤老君主被不敬的平民打動的故事套路屢試不爽——朱迪·丹奇和比利·康諾利主演的《布朗夫人》(1997)里的維多利亞女王,還有朱迪·丹奇和阿里·法扎勒主演的《維多利亞與阿卜杜勒》(2017),后者的導演斯蒂芬·弗雷斯也是《女王》的導演。也許《非普通讀者》開啟了終章,伊麗莎白二世尚未離世就已獲得了歷史人物的虛構性。過去十年里文藝作品中的女王形象豐富又舒適,再也沒有性手槍樂隊那種惡意滿滿的政治評論。
蘇·湯森(Sue Townsend)的小說《女王和我》(1992)想象了一個被潛意識操控廣告洗腦的不列顛選出了一個激進的共和政府。新任首相杰克·巴克迅速把女王從白金漢宮搬到諾丁漢Hellebore Close(看上去很像“接近地獄”)的公住房,讓她領養老金過活。王室成員都跟著女王搬了家,湯森大寫特寫他們對改朝換代的反應。戴安娜看到新居所時渾身發抖,“但查爾斯王子笑了。在這里終于可以過上簡單生活了。”愛丁堡公爵臥床不起,女王迎難而上,在“接近地獄”的團體精神中尋找安慰。湯森為笑話留了不少空間,溫莎一家人努力想把價值連城的中國地毯鋪進他們狹小的新公寓里,還有一幕是女王努力趕時間去社會服務部領取一筆緊急救濟金,這樣家人們才能吃上飯用上電。
女王在眾目睽睽之下向人借糖,交流DIY小技巧,這都是絕無可能發生的空想。但在全國范圍內,第四堵墻已經碎了兩次。第一次不是空想而是噩夢,我們這一邊打碎了玻璃,導致了可恥的悲劇后果。馬丁·艾米斯在1997年寫道:“必須承認,是我們把他們逼進了那個隧道,只為滋養我們自己那些偷偷摸摸的需求。”他說的當然是戴安娜之死。當女王照本宣科發表悼詞,公眾不依不饒,直到白金漢宮降了半旗,王室成員回到倫敦公開表達哀悼。《獨立報》的頭條是:女王屈服于臣民的力量。彼得·摩根編劇的《女王》講的就是這一段故事,其公映的2006年距戴妃離世不到十年,以飽受折磨的女王(“我從未被如此仇恨過”)對托尼·布萊爾的警告作結:“你看那些報紙頭條時會想,有一天這也會發生在我身上。的確如此,布萊爾先生。它發生的時候就是如此突然全無預警。”

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由丹尼爾·克雷格飾演的007詹姆斯·邦德護送女王。
接下來是2012年——女王真正的后現代時刻,她走出鏡子,走進了自己的敘事。丹尼爾·克雷格扮演的邦德躲過兩只柯基的夾擊,大步走上紅毯樓梯來到女王住處,女王正坐在書桌邊等待享受五分鐘大名,她轉過身說了臺詞:“晚上好,邦德先生。”當她出現在奧運體育館時,兩千七百萬觀眾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女王的可愛之處在于,在這么多年的歷練后她依然是個糟糕的演員。她聽上去就像在讀臺詞,你還能看出她在努力保持不笑場。然后直升機飛去體育館,女王的替身和克雷格一起乘著降落傘從天而降,而她的真身出現在皇家包廂里,穿著宣傳片拍攝時的那身連衣裙。整個事件如此蠢萌、如此夸張又如此可愛,怪異得恰到好處,仿佛一座雕像朝你眨眼。(今年初為她的鉆禧慶典拍的宣傳片中,她和帕丁頓熊喝茶,立刻被做成了表情包。)
女王的臉是雕像,是象征,勝過千言萬語。《女王和我》中,當她準備離開王宮時問杰克·巴克:“那么您會四下尋找一位新的掛名首腦嘍?一位總統?”杰克回答:“不。英國人民會成為自己的主人,五千七百萬人民。”女王說:“很難給五千七百萬人一起拍照呢。”伊麗莎白二世一生拍過無數照片,但她的姿態有更深的意義。倫敦女王廣場花園里的紀念花壇一面刻著菲利普·拉金為銀禧慶典寫下的詩句:“在萬物無常的時代/事情要么變壞要么變怪/只有一樣恒久美好:/她不會變。”另一面刻的是特德·休斯的詩:“一人即一輪/一國即一人/一王冠換一樞紐/保持其整全。”這比拉金的要晦澀多了,肯定也不如拉金隨詩寄給費伯出版社的打油詩那樣讓人過目不忘。拉金寫道:“特德肯定比我寫得好……天空惡意分成兩半/星星像掛架上的平底鍋般嘎啦作響/烏鴉在白金漢宮頂上拉屎/上帝尿濕了褲子。”
克雷格·布朗(Craig Brown)在八卦書《卿卿夫人:瑪格麗特公主的九十九個瞬間》(Ma’am Darling: 99 Glimpses of Princess Margaret,2017)中說女王“肯定是古往今來見過最多人的人。然而神奇之處在于,女王努力避免對任何人說出任何不同尋常或值得銘記的話。這是一種成就,而非失敗:她的職責和使命就是要沉悶,要像一張郵票一樣有用而不露感情,她一生致力于完成這項幾近不可能的任務:不說有意思的話”。女王如白紙,我們作為讀者就可以任意解釋,不用糾結作者意圖。不過任何過度揣摩她心理的行為都會顯得有些傻——比如馬丁·艾米斯2002年給《紐約客》寫的《伊麗莎白二世的精細情感》。“伊麗莎白知道自己要找個丈夫,找個力量源泉”,艾米斯寫得好像他剛跟伊麗莎白喝過早茶。《王冠》第一季好就好在你很難確認年輕的女王到底在想什么。
艾米斯寫到伊麗莎白公主二十一歲生日在南非的演講(1947年)就好多了。她宣布,“很簡單,我在此鄭重宣布,我的整個人生無論長短都將全心為你們奉獻,為我們的偉大帝國大家庭奉獻”。艾米斯機敏地反駁:“一點兒都不簡單,不是嗎——同意成為一個隱喻?”披頭士唱道:“我想告訴她我很愛她/但我得用酒把肚子填飽/女王陛下是個好姑娘/總有一天我要讓她當我的女人/哦是的,/總有一天我要讓她當我的女人。”當然她一直都是我們所有人的。
她真的是嗎?馬爾科姆·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1955年給《新政治家》寫了一篇引發爭議的檄文,“事實上對王室的無聊吹捧對他們和對公眾都毫無益處,最終會損害君主制本身……當然這不是他們的錯,盡管我懷疑他們漸漸開始喜歡拋頭露面,理論上說他們應該反感才對”。在我看來這錯得離譜。無論我們怎么想象,女王都不會一早起來就在谷歌上搜自己,或是花時間看新一期的八卦雜志。有些公眾人物就是不會讀自己的新聞。
我們的著迷是我們的,不是女王的。有時別人會建議她讀報紙(比如戴安娜去世后),了解國民的情緒。不然,你干嘛要去看你自己被公眾想象的哈哈鏡扭曲成什么樣了呢?在現實中,她的生活和你我一樣,一地雞毛。她身處的世界是真正豐富、多變、有趣的,而她周圍最顯眼的那些元素——子女、孫輩、馬、狗,只是我們對伊麗莎白二世及其無聊工作的扭曲迷戀的道具而已。你我都可以列出一張摯愛之人的名單,我愛的人名對你而言毫無意義但對我卻是一切。現在你試試王室名單,查爾斯、安德魯、愛德華、安妮。聽上去耳熟嗎?我們覺得熟悉,但他們是陌生人。千真萬確的陌生人。
(本文原文發表于2022年9月16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由作者授權翻譯)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