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疑古”更應該是具體的學術實踐
近年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孫慶偉教授在不同場合呼吁通過考古學的手段來重建中國古史,并在北大開設了核心通識課“考古學與古史重建”。現在,他化呼吁為行動,所著《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一書即將在2018年3月由三聯書店出版。在此我們征得孫老師的同意,先期刊發該書后記,借此了解作者重建夏代信史的心路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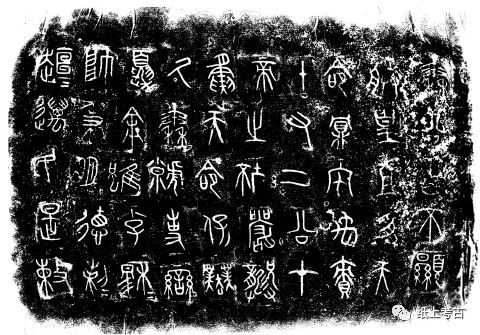
2015年春天,我的那本小書《追跡三代》出版之后,得到很多師友的關注,以至有朋友稱我是“考古學史專家”。這讓我很是難堪,因為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的。我在該書前言中說得很清楚,“正確認識夏商周考古已有的成就,深入了解當前面臨的問題”,是為了“明確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在書的后記里,我更是強調《追跡三代》只是“照著講”前賢的成就,接下來我應該“寫一部闡述自己學術觀點的書”,如此“才算得上是一項完整的研究”。李零先生在看到《追跡三代》之后,就幾次敦促我——表示想聽聽我本人對于這些問題的看法。所以,實際上早在2014年夏天,在《追跡三代》交稿后,我就開始了新的寫作——更準確地說,是繼續我的寫作。
但在過去的三年多時間里,我的想法幾經變化,甚是煎熬。
我最初的設想是,再寫一本《追跡三代》的姊妹篇,把該書重點闡述的三個問題——夏、商、周三族的起源問題做一個通盤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這項研究就算告一段落。但甫一動筆,就意識到自己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這樣的三個重大問題,豈是一本書所能囊括?所以大概在2015年初——也就是《追跡三代》面世之后,我曾暗發一宏愿,立意以十年之功完成“三代五書”——即對夏、商、周、秦、楚各寫一書,將五族的文化來源問題作一徹底的清理。下定決心后,也立即調整了寫作計劃,決定先從夏文化著手,于是才有了眼前的這本《鼏宅禹跡》。但也正是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的想法再一次發生了轉變,深深體會到以考古材料重建古史的局限性以及我本人在研究方法上的窘迫——在沒有很好地解決前述兩個問題之前,我勉為其難地嘗試著重建夏代信史自然是可行、可容許的,但如果將同一研究范式反復操練五次,完成我所謂的“三代五書”——我既擔心自己會產生極大的審美疲勞,更覺得如此做法是對學術研究工作的極不尊重。所以,于我而言,“三代五書”的念頭真可謂是曇花一現,我期盼自己會有重拾這一愿望的那一天。
在三代考古乃至整個中國考古學中,夏文化問題始終占據著特殊的地位,不但考古學者孜孜以求,社會各界也在翹首以盼,希望考古學界能夠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雖然學界同仁對于夏文化的認識眾說紛紜,但就我本人而言,最為服膺的還是鄒衡先生所強調的,“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我始終覺得,在夏文化這個問題上,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材料問題,而是如何理解材料和運用材料去講好夏文化這個故事的問題。從這層意義上講,夏文化探索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研究者對待古史的基本態度。上個世紀初葉以來,學界常有所謂“疑古”、“信古”之分,楊寬先生在他的《中國上古史導論》自序中就有以下的評述:
近人分我國古史學之派別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釋古。主信古者動謂戰國秦漢之書近古,所記傳說必有所本,一切皆為實錄,未可輕疑;主疑古者以古書既有真偽,所傳古史又不免失實,茍無精密之考證批判,未可輕信;主考古者,輒病于傳說之紛繁,莫由遵循,又鑒于近人爭辨古史,立論絕異而均不出故紙堆之范圍,乃謂但有紙上之材料無用,非有待于鋤頭考古學之發掘不為功。主釋古者,則以古人十口之相傳,“事出有因”,必有史實之殘影存乎其間,未容一概抹殺,茍據新史觀加以歸納推理,即為可信之古史。此四說者,除信古一派外,無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具體到每一位學者,其實并不一定就歸屬于某派。就我自己的取向而言,介于楊寬先生所說的“信古”和“釋古”之間。我對于古史的基本態度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堅信以《史記》為代表的古史框架基本是可信的。鄒衡先生所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其實也就是在“信古”的基礎上如何去“釋古”的問題。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最感困惑的也恰恰是論證夏文化的敘述邏輯,在幾經調整之后,才最終選擇了目前這種最為平實的敘事方式,效果如何,當然要由讀者來評判。
除了“釋古”的邏輯,研究中最令我心憂,最感無所適從的則是長期以來考古學界對于考古學文化這一概念的隨意界定和混亂使用。蘇秉琦先生早已強調,考古材料不等同于史料,考古學文化實際上是將考古材料“加工”或“轉化”為史料的關鍵一環。因此,發掘者對于考古學文化的不同理解不僅直接影響到原始材料的刊布,更影響到考古材料向史料的轉化。考古學者對于考古學文化內涵的隨意界定,其結果便是沒有人能夠在一個按照統一標準提供的、客觀的史料平臺上開展后續研究,由此導致學者們在很多問題上進行不必要的反復紛爭,從而極大地影響了考古學研究的科學性,傷害了考古學的學科聲譽。如何準確界定考古學文化這個概念,以及如何區分文化、類型、期、段,建立一套客觀可視的量化標準或操作規范,應是學界同仁所面臨的緊迫任務,也是學科建設的當務之急。
和本書寫作密切相關的教學工作是我自2016年以來主講的北京大學核心通識課“考古學與古史重建”。我在課程大綱中強調,這門課的首要任務是幫助同學建立起“正確的古史觀和古史框架”。因為就一般年輕同學而言,他們天然地相信“疑古”是先進、科學的治史態度,而“信古”則是保守、落后的研究取向。任由李學勤先生有關“對古書的反思”和“走出疑古時代”的吶喊與呼吁,同學們依然是我自巋然不動。我當然不是要否定“古史辨”派學者的先進性和重大貢獻,恰恰相反,我是想提醒同學們讀完了《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和《秦本紀》再來 “疑古”也不遲——“疑古”不僅僅是一種態度,更應該是具體的學術實踐——畢竟不是人人都有資格來“疑古”的。本書附錄中的前兩篇文章,都是配合講課所寫的講義,主旨與本書密切相關,所以一并收入在此。
在過去的幾年中,考古學界最顯著的一個變化是越來越多的同仁關注并投身于公共考古活動中來,我自己也應邀參加過數次公眾考古活動。雖然這些活動已經初見成效,但我始終認為,考古學科和考古知識的普及化其實并不能,或主要不能依靠普通民眾獵奇式的淺嘗輒止的參與,而應該依靠學界同行在社會大眾普遍關注的重大學術問題上能夠拿出直擊人心的學術成果來。考古學科之所以是“小”學科,并不僅僅是因為社會大眾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不夠,而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學科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學者和學術成果太少。換句話說,民眾應該被“打動”,而不是被“引導”。一個學者社會影響力的獲得,既需要深厚的學養,更需要對話題的精準選擇——前者不可一蹴而就,但后者卻可以立竿見影。被余英時先生譽為“樸實楷模”的史學大家嚴耕望先生就以自身治學經歷專門談學術研究“論題選擇”的重要性。嚴先生坦言自己的《唐仆尚丞郎表》一書的“功力之深實遠在”他的另一著作《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之上,但影響力卻遠遜于后者。究其原因,就在于問題的選擇上。因此,嚴先生在《治史經驗談》中告誡后學:
從事文史學科的研究,本不應談實用問題,不過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對于別的研究者有較大用處,并對一般人也有用;換言之,欲有較大影響力,就不能不考慮實用問題。論者本身成就的高低是一回事,對于別人是否有用是一回事,這兩方面往往不能兼顧,但也可以兼顧,關鍵是在問題的選擇。……就實用觀點說,也很難有絕對的標準。不過就目前一般觀點言,國家大計、社會動態、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為大家所關注的問題,在這些方面有了重要的貢獻,較易為大家所注意所看重,可發生較大的影響力。
嚴先生并稱:
講學問誠然不應有功利主義,也不必理會對人是否有用,但若是望辛勤的著作能得到學術界的大反應,就不能不考慮選擇論題的重要性!
嚴先生的這一番肺腑之言可謂是當頭棒喝。我之所以在近年將研究的重點轉移到“古史重建”上來,是因為我相信這是考古學的學科使命,也是社會大眾對于考古學科的主要期盼;而我之所以在“三代五書”中先從夏代著手,并不僅僅因為夏是“三代”之首,更是因為夏代歷史對于社會大眾而言“更為有用”,或者說,社會大眾對于了解夏代歷史的心情“更加急迫”——社會需求,理應成為研究者論題選擇的重大考量。試問,有哪位作者不是期盼自己辛苦寫出的著作能夠得到“學術界的大反應”呢?實際上,社會大眾對本學科的某個學術問題抱有濃厚興趣,這實在是學科之大幸,研究者又豈能熟視無睹,置之于不顧呢?
本書的寫作,得到我的老師李伯謙先生一如既往的關注和支持。李老師是夏商文化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他就提出二里頭文化“既不是夏代晚期的文化,也不是整個夏代的文化,而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國’、‘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這一創造性觀點。在此基礎上,他后來更是率先明確了夏文化的“三段論”——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為早期夏文化、新砦期為“后羿代夏”的夏文化、二里頭文化為“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這些觀點影響深遠,迄今仍是學術界的主流意見。但讀者不難看出,在有關夏文化的認識上,尤其是關于夷夏關系、“新砦期”的有無、二里頭文化的屬性、東下馮類型的歸屬等根本性問題上,本書的觀點均與李老師的持論相左,甚至是針鋒相對的。這些看法我都與李老師反復交流,甚至互相駁難,李老師在堅守自己觀點的同時,更鼓勵和敦促我早日完成書稿。如今我自己在北大任教也超過二十年了,也有了自己獨立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李老師的學術雅量令我認真思考為師之道——言傳與身教缺一不可,道德與文章不可偏廢。
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商周組真是個神奇的團隊——這里有授我學業的劉緒、徐天進和孫華三位老師,有雷興山、董珊、曹大志三位同事,更有一眾朝氣蓬勃的研究生們。三位老師素來謹嚴,當面從無溢美之詞,但從他人處知道老師們對我其實頗多褒獎,天進師更是在《追跡三代》出版之后,用他雋永的書法手書“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八個大字加以獎掖鼓勵。雷、董、曹三兄和我在治學上雖然各有側重,但始終相互激勵,以求共同進步。在此氛圍之下,各位年輕同學也都一心向學,各有專攻,儼然世界一流大學的學術氣象。
早在學生時代,我就夢想有朝一日可以在三聯書店出版自己的學術著作。現在夢想成真,要格外感謝成立不久即享學術盛譽的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衷心感謝鄧小南老師的青睞,允我充任文研院的工作委員,在這里得以和學生時代的朋友李猛、周飛舟等位再續前緣,砥礪學問,并結識渠敬東等一眾新朋友。也是在文研院,結識了同為北大同學的馮金紅,蒙金紅不棄,大力促成這本小書在三聯的出版,并親自為之責編。
本書的寫作始于2014年夏天,三年多來,白天的時間基本上都用在教學和學院的行政事務上,寫書都靠晚上和節假日的零碎時間來進行。這樣的寫作方式既不痛快,也影響敘述的連貫性,但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為了保證必要的寫作時間,這三年中我連最低限度的家務也未承擔,斯皇同學的學習更未顧及,這是我對妻女最感虧欠的地方。此時但求此書能對夏文化探索有所裨益,以稍減我的愧疚之心。
2018年是北大一百二十周年校慶,也是我本人在北大學習和工作三十周年。值此之際,出版這本小書,也算是一個小小的紀念。
(本文原題為《不忘初心——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系作者為即將于今年3月在三聯書店出版的《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一書所作后記,經作者授權,轉載自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圖書館微信公眾號“紙上考古”。)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