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韓潮︱信天翁與不死鳥:如何閱讀《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

《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毫無(wú)疑問(wèn)已是二十世紀(jì)下半葉以來(lái)最為聲名顯赫的歷史著述之一。不過(guò),這本書剛剛面世之初,在中世紀(jì)史學(xué)內(nèi)部其實(shí)并不乏異議,甚至頗有些讓人尷尬的評(píng)論。斯莫利(Beryl Smalley)甚至說(shuō),“讀完此書,就好比品嘗了一頓只有果醬沒(méi)有面包的晚餐一樣讓人感到不適”;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同康托洛維茨交惡的康托爾(Norman Cantor)則在書評(píng)里毫不客氣地指出,作者與其用力在不相干的文本比如莎士比亞的《理查二世》,還不如多去研究研究國(guó)王與國(guó)會(huì)之間的斗爭(zhēng)話語(yǔ);而后來(lái)被康托爾視為中世紀(jì)研究“曾經(jīng)和未來(lái)的國(guó)王”的薩瑟恩(Richard Southern)則說(shuō),“追隨康托洛維茨教授在中世紀(jì)尋找‘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之旅,就好比在黑夜里的陌生國(guó)度里漫步,景觀是時(shí)斷時(shí)續(xù)的,盡管有時(shí)也不乏壯觀瑰麗,但要想憑此辨識(shí)出這個(gè)國(guó)家的樣貌是不大可能的”。這種情況甚至一直延續(xù)到1997年《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四十周年紀(jì)念文集里,盡管此時(shí)《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的地位已經(jīng)得到學(xué)界公認(rèn),但這本紀(jì)念文集里仍舊有一篇文章對(duì)康托洛維茨的研究路徑持強(qiáng)烈的保留態(tài)度,其文頗有些不客氣地揶揄道,雖然康托洛維茨的著作能讓我們學(xué)習(xí)、沉思、想象乃至于“夢(mèng)想”,“但我絕不會(huì)讓我的學(xué)生以此作為歷史寫作的典范”。
類似的“惡評(píng)”最近二十年已不大看到。事實(shí)上,《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此后適逢周年的紀(jì)念幾乎已成了一種固定的儀式:繼1997年的四十周年紀(jì)念文集、2007年由《表象》雜志推出的五十周年紀(jì)念專刊之后,2017年此書出版六十周年之際又至少有兩本紀(jì)念文集和一本紀(jì)念專刊相繼面世。

2017年六十周年紀(jì)念文集《國(guó)王的身體永不毀壞》
不過(guò),成名之作的早期“惡評(píng)”并非全無(wú)意義,由于它們不太可能為縈繞在巨作周邊的神秘性所惑,這些今天看來(lái)大多落空的誤判其實(shí)多多少少能反映成書過(guò)程中原本存在的一些問(wèn)題。更為重要的是,成名之作的早期“惡評(píng)”往往能從側(cè)面昭示學(xué)術(shù)方法和風(fēng)氣的流轉(zhuǎn),大多數(shù)“惡評(píng)”之所以產(chǎn)生,無(wú)非是因?yàn)橄鄬?duì)老派的學(xué)者不能適應(yīng)新的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所致。如果誰(shuí)能有心搜羅今天為學(xué)界公認(rèn)的成名之作的早期“惡評(píng)”,或許能寫成一部頗有意味的邊緣學(xué)術(shù)史也未可知。
就《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而言,首先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這本書的結(jié)構(gòu)的確存在著一些爭(zhēng)議。1953年左右,康托洛維茨的初稿其實(shí)已經(jīng)完成,但其中并沒(méi)有目前定稿本中論述但丁的第八章,這一章很可能也并不在其最初的構(gòu)思之列。全書完成之后,作為此書的評(píng)審人之一斯特雷耶曾建議康托洛維茨將但丁一章刪去。而另一位評(píng)審人波斯特(Gaines Post)則建議,至少應(yīng)再加上一節(jié)五到十頁(yè)左右的結(jié)語(yǔ)。結(jié)果兩位評(píng)審人的建議都被康托洛維茨拒絕了,他在前言里說(shuō),“我只是在極少數(shù)情況下才覺(jué)得有必要得出一些結(jié)論”。雖然最終定稿時(shí)他不得已應(yīng)評(píng)審人的要求在形式上增加了一個(gè)附論,但其討論的毋寧是一個(gè)與全書整體不太相關(guān)的新話題——“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是否僅為獨(dú)屬于中世紀(jì)的歷史現(xiàn)象,抑或是在異教政治傳統(tǒng)里也有類似經(jīng)驗(yàn)存在?——至于全書的結(jié)論,康托洛維茨仍舊付之闕如,按照他在前言里的說(shuō)法,讀者“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結(jié)論,并自行把齒輪組裝起來(lái)”。
我相信,本書的任意一個(gè)讀者都能感受到“自行組裝”的不易,康托洛維茨的謙辭其實(shí)反過(guò)來(lái)看更像是一個(gè)倨傲的作者對(duì)于讀者耐心和智力的要求。康托洛維茨曾經(jīng)有些自負(fù)地稱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為Kabinettstücke(珍玩),換言之,非行家里手不能辨識(shí)其魅力所在。可能也正是這種理智的倨傲讓他拒絕為這部著述給出哪怕一個(gè)簡(jiǎn)短的結(jié)論。

如果說(shuō)結(jié)論的闕如是出于理智的倨傲,那么斯特雷耶關(guān)于但丁的一章的意見(jiàn)則更多牽涉到全書的結(jié)構(gòu)問(wèn)題。我相信,斯特雷耶之所以建議康托洛維茨刪去但丁一章,即便不是因?yàn)樵谒磥?lái)這一章有離題之嫌,也或多或少是因?yàn)榇苏驴瓷先ザ嗌儆行┤哔槪瑒h去但丁一章,或許反倒能讓我們看到一個(gè)構(gòu)思上更為完美的版本。事實(shí)上,如果讀者足夠細(xì)心,應(yīng)當(dāng)能覺(jué)察到在全書倒數(shù)第三章即“國(guó)王永遠(yuǎn)不死”一章的結(jié)束處,康托洛維茨其實(shí)有一段不長(zhǎng)不短的結(jié)語(yǔ),回應(yīng)了全書開篇提出的獨(dú)體法人問(wèn)題。因而,如果沒(méi)有最后加入的兩章,那么《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原本是一個(gè)精巧的回環(huán)結(jié)構(gòu):即以十六世紀(jì)伊麗莎白法學(xué)家那里的獨(dú)體法人問(wèn)題為設(shè)問(wèn),通過(guò)回溯至十一世紀(jì)末諾曼無(wú)名氏的文本和奧托二世的微縮畫,經(jīng)由十三世紀(jì)西西里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和英格蘭的布萊克頓為過(guò)渡,再經(jīng)過(guò)對(duì)十三世紀(jì)之后、中世紀(jì)晚期的政治體延續(xù)性問(wèn)題的解釋,最終回轉(zhuǎn)到對(duì)文初十六世紀(jì)問(wèn)題的回答。我相信,此書原初的構(gòu)思就是這樣一種回環(huán)的結(jié)構(gòu),并且,這個(gè)閱讀的密碼就隱藏在這個(gè)回環(huán)結(jié)構(gòu)的首末兩端:在全書正文的開篇,康托洛維茨使用了一個(gè)鳥類的意象——波德萊爾的“信天翁”,以此形容政治神秘主義一旦喪失其神秘性之后,就好比被剝?nèi)チ松拾邤痰挠鹨硪话悖毞Α⒖蓱z、受人奚落;而在這個(gè)回環(huán)結(jié)構(gòu)的最后一節(jié),康托洛維茨同樣使用了一個(gè)鳥類的意象——傳說(shuō)中神秘的“不死鳥”,毀滅之后總能從灰燼中再次誕生和起飛。二者恰好設(shè)定了一個(gè)相對(duì)照的、說(shuō)明象征性權(quán)力之神秘性或有或無(wú)的意象組合。
對(duì)一部著述而言,這個(gè)回環(huán)結(jié)構(gòu)其實(shí)是近于完美的,如果這部書就到此為止,或許也足以傳世。但大概是五十年代以后對(duì)但丁的重讀使得康托洛維茨改變了原本的寫作計(jì)劃,于是造成了全書結(jié)構(gòu)上憑空多出來(lái)一個(gè)全新的主題,也給讀者帶來(lái)了不小的閱讀挑戰(zhàn)。康托洛維茨的構(gòu)思和成書過(guò)程此前并不為人所了解,至少在2017年康托洛維茨的最新傳記出版之前,學(xué)界并沒(méi)有多少人知道康托洛維茨的運(yùn)思環(huán)節(jié)。不過(guò),若干敏感的讀者如專治政治神學(xué)的卡恩應(yīng)當(dāng)排除在外,她早早便曾斷言,《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事實(shí)上包含著兩個(gè)論證:其一是英格蘭的世俗憲政的基督論起源問(wèn)題;其二則是在但丁一章中得到闡發(fā)的世俗化的人道宗教問(wèn)題。

如果不考慮其雙重論證,從現(xiàn)有文本的結(jié)構(gòu)上來(lái)看,《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以梅特蘭和英格蘭憲政為開始的主題最后看上去的確偏離了它的開端。當(dāng)英格蘭憲政問(wèn)題為發(fā)端、其后不斷延伸的“二元性”主題蔓延、擴(kuò)張至“但丁的兩個(gè)太陽(yáng)”收束時(shí),一個(gè)簇新的問(wèn)題域卻出現(xiàn)了:傳統(tǒng)上被布克哈特視為“文藝復(fù)興宣言”的皮科論人類尊嚴(yán)的命題,此時(shí)被康托洛維茨界定為僅僅是對(duì)但丁的世俗化人性宗教的模仿。《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正文的最后一句話暗示著一個(gè)全新的主題作為全書的結(jié)語(yǔ)——這就是“人道宗教”的到來(lái),因?yàn)椋碎_始要為人性本身加冕。

但丁對(duì)于康托洛維茨有著特殊的意義。在早年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中,但丁就毋寧是這部傳記的另一個(gè)主角,康托洛維茨在此書中不僅將但丁視作弗里德里希二世與圣弗朗西斯、愷撒帝國(guó)與耶穌帝國(guó)、鷹與十字架的折中,而且,在他看來(lái),但丁的《帝制論》在現(xiàn)實(shí)中的原型就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國(guó)家,《帝制論》三卷所描述的三種世界性力量同時(shí)也存在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國(guó)家里。而在五十年代之后,康托洛維茨又開始不斷地重讀但丁,1954年他著手修訂《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時(shí)開設(shè)的一個(gè)討論班課程即為“但丁作品中的王權(quán)與人類自由”,而直到1963年康托洛維茨去世前的最后一個(gè)討論班課程仍舊是但丁的《帝制論》。我相信,正是對(duì)但丁的閱讀將康托洛維茨重新帶回了政治神學(xué)的語(yǔ)境。按照卡恩的看法,康托洛維茨的但丁解讀甚至毋寧就是對(duì)施密特的回應(yīng),通過(guò)但丁的政治神學(xué)所構(gòu)想的人類共同體與人性本身的自主,康托洛維茨最終回應(yīng)了施密特建立在敵友區(qū)分基礎(chǔ)上的國(guó)家神話。
卡恩的觀點(diǎn)能否成立另當(dāng)別論,但無(wú)論如何,康托洛維茨此書在最具克里斯瑪意味的地方,亦即在國(guó)王的榮耀里尋找現(xiàn)代憲政起源的秘密,卻是毋庸置疑的。看上去英格蘭憲政的神學(xué)起源和世俗化的人道宗教,構(gòu)成了此書的政治神學(xué)的兩個(gè)獨(dú)立面相,二者之間確定無(wú)疑存在,卻極難清晰辨明的聯(lián)系,則是這本書的復(fù)雜構(gòu)思留給讀者的一個(gè)極大挑戰(zhàn)。這一點(diǎn),康托洛維茨本人很可能也了然于胸,所以在正文的結(jié)束處,他以特有的曖昧語(yǔ)氣說(shuō)道,現(xiàn)在英國(guó)法學(xué)家關(guān)于政治身體和自然身體的定義,“對(duì)我們來(lái)說(shuō)總算更容易理解了——但或許變得更難理解也未可知”。

總體而言,這兩個(gè)論證應(yīng)當(dāng)可以統(tǒng)攝在政治神學(xué)這個(gè)大命題之下。康托洛維茨使用了施密特的政治神學(xué)一詞,但這本書里卻從沒(méi)有一處出現(xiàn)施密特的名字。他的寫作動(dòng)機(jī)毫無(wú)疑問(wèn)與施密特有關(guān),大體上他也應(yīng)當(dāng)認(rèn)可施密特的斷言,現(xiàn)代國(guó)家的基本概念是中世紀(jì)神學(xué)概念的某種世俗化形式。但與其說(shuō)康托洛維茨的政治神學(xué)直接來(lái)源于施密特的《政治神學(xué)四篇》,還不如說(shuō)來(lái)源于施密特另一部相關(guān)作品《羅馬天主教與政治形式》。因?yàn)椋凇读_馬天主教與政治形式》一文里,施密特已經(jīng)指出,教會(huì)是一個(gè)法人,但不是股份公司意義上的法人,在教會(huì)的法人形式中隱藏著一個(gè)社會(huì)學(xué)的奧秘。因此,我很懷疑《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引言中康托洛維茨本人所講述的那個(gè)關(guān)于此書寫作動(dòng)機(jī)的起源故事是否屬實(shí),或者這個(gè)故事只是一種記憶疊加的產(chǎn)物,否則無(wú)法解釋康托洛維茨和雷丁(Max Radin)教授的談話幾乎重復(fù)了施密特若干年前的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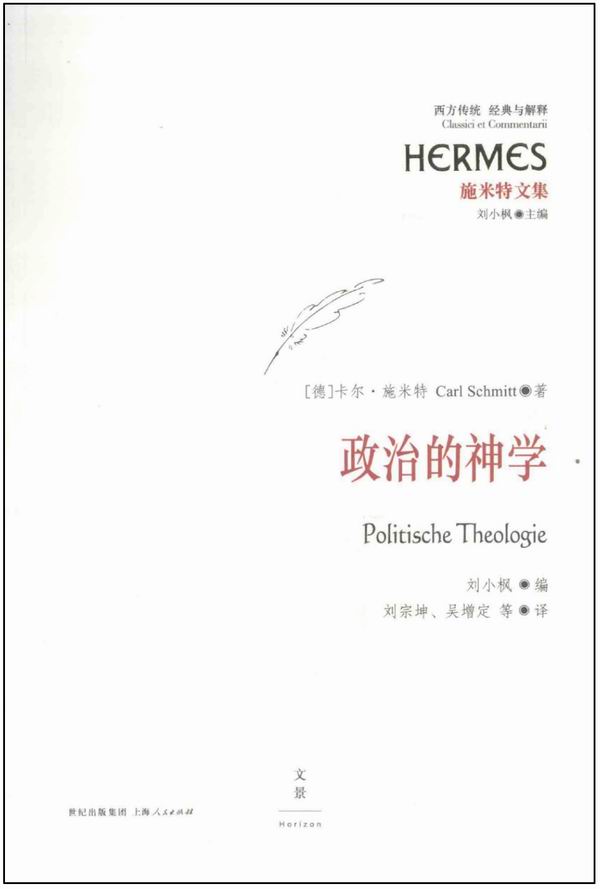
至于《政治神學(xué)四篇》中的例外狀態(tài)和緊急狀態(tài)之類的話語(yǔ),則被康托洛維茨妥帖安排在此書論政治體必然性的章節(jié)里,如果不仔細(xì)閱讀,讀者很難直接從字面上看出此書與施密特的直接聯(lián)系。康托洛維茨更傾向于將施密特的政治論斷融入“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擬制演化的某個(gè)階段里,他本人則非常克制地不對(duì)中世紀(jì)政治神學(xué)的現(xiàn)代對(duì)應(yīng)項(xiàng)做過(guò)多的引申,盡量不在字面上直接指出,現(xiàn)代國(guó)家理論中的某個(gè)概念對(duì)應(yīng)于中世紀(jì)神學(xué)中的某個(gè)概念。而唯獨(dú)只有一次他脫口說(shuō)出,中世紀(jì)晚期的“永久必然性”概念其現(xiàn)代對(duì)應(yīng)項(xiàng)就是現(xiàn)代的“不斷革命論”。
但康托洛維茨對(duì)施密特的推進(jìn),并不是更為精確地找到了現(xiàn)代國(guó)家概念的中世紀(jì)對(duì)應(yīng)項(xiàng),而毋寧是將施密特的政治神學(xué)帶回到中世紀(jì)的世界里,帶回早期現(xiàn)代的世俗化進(jìn)程之前。這必定會(huì)帶來(lái)某種理論困難,如果說(shuō)在施密特那里,現(xiàn)代國(guó)家理論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學(xué)概念,那么這種單向的關(guān)系對(duì)于中世紀(jì)而言卻并不存在。首先,嚴(yán)格來(lái)說(shuō)中世紀(jì)國(guó)家既不是世俗的也不是非世俗的,其次,這也恰恰是因?yàn)椋缈低新寰S茨所言,“教會(huì)與國(guó)家之間無(wú)盡的交互關(guān)系,活躍在中世紀(jì)的每一個(gè)世紀(jì)里,并且在雙方那里都創(chuàng)造了各自混雜的形態(tài),雙方都從對(duì)方那里借用并交換了徽章、政治符號(hào)、特權(quán)以及榮耀的形式”。而在同時(shí)期的一篇論文《國(guó)家的神話》里,康托洛維茨更是明確指出,正是在這種混雜和交互的關(guān)系中才衍生出后世的“國(guó)家的神話”。因此,相對(duì)于施密特的政治神學(xué)而言,康托洛維茨的中世紀(jì)政治神學(xué)不僅僅是回溯性的,而且也是擴(kuò)展性的。
幾乎不可能把施密特的政治神學(xué)照搬進(jìn)中世紀(jì)的政治神學(xué),“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不可能是所謂世俗化的神學(xué)概念,更不可能是神學(xué)化的世俗概念,它只能而且必然只是一種純粹的擬制。畢竟,借用康托洛維茨本人的隱喻來(lái)說(shuō),中世紀(jì)的世界更像是一個(gè)活躍著不死鳥、而未曾一睹信天翁的世界,在這個(gè)世界里,擬制的演化仿佛不死鳥的種種蛻變,而擬制所采取的種種載體形式,就構(gòu)成了《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里的形態(tài)學(xué)。
有學(xué)者嘗論,施密特的政治神學(xué)大體上是獨(dú)斷性的形而上學(xué),而康托洛維茨的政治神學(xué)則是經(jīng)驗(yàn)性的歷史學(xué)。不錯(cuò),康托洛維茨游走于憲政史、儀式史、圖像學(xué)、文學(xué)批評(píng)、政治思想之間,乃至于時(shí)人對(duì)此書有“萬(wàn)花筒”之謂,其思考方式毫無(wú)疑問(wèn)是歷史性的,但其歷史形態(tài)學(xué)一以貫之的中心卻只是一個(gè)神秘的擬制。

不過(guò),對(duì)于老派的中世紀(jì)學(xué)者而言,僅僅憑借一個(gè)含混的象征化表述就能駕馭時(shí)段跨度巨大、材料類型眾多的一段歷史,的確是讓人心生疑慮的。斯莫利之所以說(shuō)《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是“一頓只有果醬沒(méi)有面包的晚餐”,部分的原因就在于她認(rèn)為,沒(méi)有現(xiàn)實(shí)政治相佐佑,僅憑“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的隱喻完全沒(méi)辦法撐起這部書里所有的材料;同樣,康托爾之所以懷疑康托洛維茨莎士比亞研究的價(jià)值,之所以建議康托洛維茨將筆力放在國(guó)王和議會(huì)之間實(shí)際的斗爭(zhēng)話語(yǔ)上,也同樣是因?yàn)椋谒磥?lái),即便我們承認(rèn),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的觀念扎根于教會(huì)和神學(xué)的原則里,但無(wú)論如何也應(yīng)當(dāng)與英格蘭的現(xiàn)實(shí)政治有關(guān),而在《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里恰恰看不到任何現(xiàn)實(shí)政治的要素。我相信,斯莫利和康托爾的意見(jiàn)一定都受到薩瑟恩更早的一篇書評(píng)的影響,薩瑟恩提供了對(duì)《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最初也是最為基本的懷疑,在他看來(lái),康托洛維茨毋寧是將象征置于現(xiàn)實(shí)之前,而且似乎假設(shè)了一個(gè)人類完全沉浸于其中的幽暗的象征世界,在這里,如果沒(méi)有象征,人們既不能把握政治現(xiàn)實(shí),也無(wú)法表達(dá)他們實(shí)際的政治野心。正是基于此,薩瑟恩才有暗夜里行路之喻,意指康托洛維茨此書固然像暗夜里行路那樣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但絕非歷史的本來(lái)面目。
事實(shí)上,更晚近一些的四十周年紀(jì)念文集里對(duì)康托洛維茨的責(zé)難一文,還是與前述批評(píng)如出一轍。此文也還是認(rèn)為康托洛維茨刻意選擇文本、抽離語(yǔ)境以適應(yīng)他的論證,幾乎不涉及其討論文本的政治社會(huì)條件,因此,在他看來(lái),《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從根本上說(shuō)只是一種去語(yǔ)境化的研究,“不應(yīng)被視作歷史研究的典范”。

說(shuō)《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是去語(yǔ)境化的研究,乃至于說(shuō)康托洛維茨的研究與劍橋?qū)W派的旨趣大相徑庭,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康托洛維茨的確從中世紀(jì)盛期到現(xiàn)代早期五百余年的歷史中選擇了若干跳躍的歷史階段,他其實(shí)并不想去論證這若干環(huán)節(jié)的來(lái)龍去脈和因果聯(lián)系。康托洛維茨本人并不關(guān)心,伊麗莎白時(shí)期的法學(xué)家是否借用了福蒂斯丘的理論,或者布萊克頓是否讀過(guò)諾曼無(wú)名氏的著作;而且,此書中的論證推演也完全沒(méi)有借用直接的因果聯(lián)系,比如第三章康托洛維茨的筆觸之所以由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西西里轉(zhuǎn)向同時(shí)期布萊克頓的英格蘭,其實(shí)并非建立在同時(shí)期兩地間頻繁的外交和政治交往之上(盡管康托洛維茨有文專論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臣在英格蘭的經(jīng)歷,但此處卻非常克制地拒絕了以此作為立論根據(jù)的誘惑)。在所有的歷史關(guān)聯(lián)里,對(duì)康托洛維茨來(lái)說(shuō),很可能最不重要的恰恰就是直接的因果性聯(lián)系。

很難為康托洛維茨的研究找到一種明確的方法論定位,頗有些學(xué)者認(rèn)為,康托洛維茨的方法接近于后世的“身體話語(yǔ)分析”“文本考古學(xué)”“新歷史主義”,乃至于科澤勒克式的概念史研究。所有這些后設(shè)的定位,我覺(jué)得都未必那么恰當(dāng)。不錯(cuò),《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偶然闖入了福柯的視野,的確是這部著述成名的意外因素之一。但身體這個(gè)詞在康托洛維茨那里僅僅活在隱喻和象征的世界里,既不見(jiàn)肉也不見(jiàn)血,他的身體概念只是一種象征化的表述,和今天文化史里的“身體史”分支完全不是一碼事。因此,與其說(shuō)這部書的關(guān)鍵詞是身體,還不如說(shuō)是身體的象征化表述。而這種象征化表述與后世的“話語(yǔ)分析”或“文本考古學(xué)”究竟有幾分關(guān)系,也是十分可疑的。
事實(shí)上,康托洛維茨本人偶爾倒是使用過(guò)一個(gè)方法論用語(yǔ)——憲政語(yǔ)義學(xué)(constitutional semantic)。這個(gè)比較罕見(jiàn)的詞匯或許能比較好地體現(xiàn)康托洛維茨的方法論特征。在憲政問(wèn)題上,與其說(shuō)康托洛維茨關(guān)心的是老派的、偏于政治史取向的憲政史問(wèn)題,還不如說(shuō)其關(guān)心的是憲政的語(yǔ)義學(xué)問(wèn)題。但這種語(yǔ)義學(xué)絕非是分析意義上的語(yǔ)義學(xué),康托洛維茨完全不想讓布萊克頓的“國(guó)王在法律之上”與“國(guó)王在法律之下”如何在分析的語(yǔ)法中更加清晰而無(wú)矛盾地呈現(xiàn),相反,從布萊克頓問(wèn)題的學(xué)術(shù)史來(lái)看,康托洛維茨毋寧是刻意強(qiáng)化了其矛盾性,以適應(yīng)全書中一以貫之的如“正義之父與正義之子”“法律之上與法律之下”“大寫的國(guó)王與小寫的國(guó)王”等悖謬式表述。
或許應(yīng)當(dāng)說(shuō),僅就憲政問(wèn)題而論,康托洛維茨的憲政語(yǔ)義學(xué)方法探究的只是使憲政得以可能的符號(hào)性的、觀念性的、禮儀性的和語(yǔ)言性的條件。康托洛維茨并不想得出與老派的憲政史研究學(xué)者類似的結(jié)論,如果你認(rèn)為可以從《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里得出,何以唯獨(dú)在英國(guó)革命才出現(xiàn)了大寫的國(guó)王與小寫的國(guó)王之間的斗爭(zhēng),你恐怕一定會(huì)失望而歸。麥基文、梅特蘭那一代人對(duì)憲政與法律擬制之間關(guān)系的闡釋,從未曾離開對(duì)其現(xiàn)實(shí)政治關(guān)系的分析,而康托洛維茨稱“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為“擬制”(fiction),卻并沒(méi)有明確說(shuō)明,他所討論的究竟是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還是文學(xué)性的虛構(gòu)(literary fiction),大體上研究者認(rèn)為,他其實(shí)刻意模糊這兩個(gè)原本相隔萬(wàn)里、僅有字面關(guān)聯(lián)的用語(yǔ),更有甚者,康托洛維茨還刻意引入了一個(gè)唯名論概念“理智的擬制”(fictiones intellectuals),進(jìn)一步暗示fiction一詞與形而上真實(shí)的曖昧聯(lián)系。這一點(diǎn)是麥基文和梅特蘭那一輩的憲政學(xué)者萬(wàn)萬(wàn)不曾想到的。

2016版
老派的憲政史研究之所以不再受到歡迎,并不僅僅因?yàn)樵诮?jīng)驗(yàn)層面他們忽略了國(guó)家問(wèn)題和憲政問(wèn)題的相關(guān)性,學(xué)界整體風(fēng)氣的流轉(zhuǎn)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gè)因素。“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當(dāng)然不可能是一個(gè)純粹的憲政主義概念,同樣也不可能是一個(gè)純粹的絕對(duì)主義概念,絕對(duì)主義和憲政主義之間的界限在此書中也許會(huì)令人失望地模糊,但真正讓康托洛維茨成為一個(gè)先行者的原因肯定不在于此。康托洛維茨之所以不同于此前的老派憲政史研究,從根本上說(shuō),恰恰在于他采取了實(shí)證史學(xué)家不能接受的、忽視現(xiàn)實(shí)政治語(yǔ)境的研究方法,因?yàn)檫@本書實(shí)際上是在最具克里斯瑪意味的地方、在國(guó)王的榮耀里尋找現(xiàn)代國(guó)家和現(xiàn)代憲政共同的起源秘密。
另一方面,康托洛維茨之所以成為勒福、古謝、阿甘本乃至于布爾迪厄不斷回溯的理論源頭,也并非是由于他在純粹政治理論方面早早洞察到了所謂權(quán)力的象征性維度。康托洛維茨并沒(méi)有多么敏感的歷史方法論的自覺(jué)意識(shí),如果說(shuō)康托洛維茨有什么超出同時(shí)期中世紀(jì)史學(xué)家的視野,那么毫無(wú)疑問(wèn)還應(yīng)當(dāng)是他講述的中世紀(jì)政治神學(xué)的故事。如果這部書分析的僅僅是教會(huì)與國(guó)家之間的交互影響史,那么此前若干學(xué)者的研究已經(jīng)足夠出色了,但是,康托洛維茨在此書中描述的“教會(huì)與國(guó)家之間無(wú)盡的交織狀態(tài)”,最終導(dǎo)向的卻是一個(gè)實(shí)證史學(xué)家殊難理解的、幾乎近于唯名論的擬制概念。
而或許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更容易為我們這個(gè)唯名論時(shí)代而接受。康托洛維茨極具技巧性地一面將法律擬制與文學(xué)虛構(gòu)相勾連,一面轉(zhuǎn)而斷言擬制未必皆虛空、未必不真實(shí),其實(shí)正是我們這個(gè)唯名論時(shí)代的學(xué)術(shù)話語(yǔ)里最為常見(jiàn)的闡釋象征性權(quán)力的路徑。如果再次借用康托洛維茨的隱喻,這就好比,已然在現(xiàn)實(shí)中一睹信天翁的命運(yùn),卻斷言曾經(jīng)存在過(guò)所謂的“不死鳥”。
當(dāng)然,這終究是一個(gè)吊詭。按照康托洛維茨講述的故事模型推演下去,在我們的這個(gè)世界里,一個(gè)弒君者如果要真正殺掉端坐在王位上的國(guó)王,就必須同時(shí)讓國(guó)王的兩個(gè)身體全都?xì)w于寂滅。但是,如何殺掉一個(gè)象征性的身體?誰(shuí)又能夠殺死一個(gè)不存在的擬制物?殺死那只“不死鳥”,難道不是一個(gè)更加荒誕不經(jīng)的故事?再進(jìn)一步,如果你無(wú)法把它真正殺死,那么它是否一定會(huì)換一種形式重新回來(lái)?因此,我并不認(rèn)為,這個(gè)故事與現(xiàn)代國(guó)家的真實(shí)起源有關(guān),從根本上說(shuō),這毋寧揭示的是我們身處的這個(gè)極端唯名論時(shí)代的困境。

但是我相信,康托洛維茨是揭示這個(gè)困境的合適人物。在麥卡錫時(shí)代里,康托洛維茨身處的加州大學(xué)系統(tǒng)曾經(jīng)要求每一位教員簽署一份效忠的誓詞,以表明其身份不是共產(chǎn)黨員。康托洛維茨斷然拒絕了效忠宣誓,并因?yàn)榫芙^宣誓而失去教職、被迫離開伯克利。在他留下的一份關(guān)于伯克利宣誓爭(zhēng)議的文獻(xiàn)里,康托洛維茨這樣寫道,“每一個(gè)誓言,一旦說(shuō)出,都有它自足的生命”。從他對(duì)待誓言的態(tài)度來(lái)看,康托洛維茨配得上是我們這個(gè)唯名論時(shí)代里一位罕見(jiàn)的、視空虛為真實(shí)的捕風(fēng)者。或許也只有這樣視空虛為真實(shí)的捕風(fēng)者才能夠?qū)懗鲞@部關(guān)于fiction的偉大作品。不過(guò),唯一不能確定的是,這位偉大的捕風(fēng)者收回的網(wǎng)里,究竟是垂死的信天翁,抑或是重生的不死鳥?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