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葉樹彬︱又一個巴黎革命日——科林·瓊斯筆下的熱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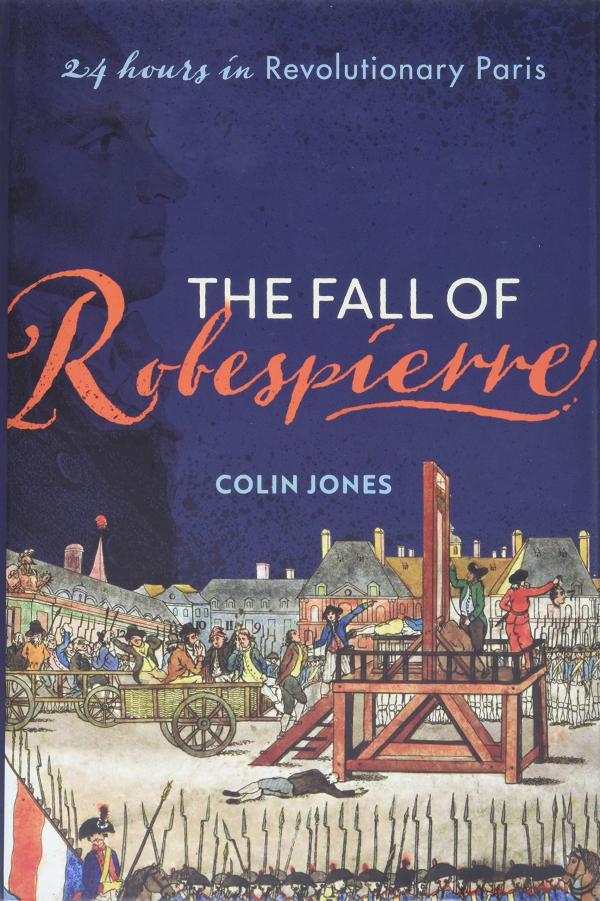
Colin Jones, The Fall of Robespierre: 24 Hour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021, 480pp
共和三年熱月八日(1795年7月26日),負責調查羅伯斯庇爾一派陰謀的國民公會代表庫爾圖瓦(Edme-Bonaventure Courtois),向國民公會提交了長達兩百六十六頁的熱月九日(1794年7月27日)報告,其扉頁寫道:“宣于共和三年熱月八日,暴君倒臺周年的前一天。”在報告中,庫爾圖瓦將前一年的熱月九日定性為國民公會對抗暴政的勝利之日。此后,熱月九日事件作為一場國民公會反抗羅伯斯庇爾恐怖統治的政變,逐漸成為公眾和大部分史家的共識。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熱月九日究竟是一場什么性質的政變?1793至1794年革命政府主政是一場恐怖統治嗎?羅伯斯庇爾是恐怖統治的罪魁禍首還是民主事業的捍衛者?這些問題如同迷霧一般籠罩在羅伯斯庇爾和恐怖統治研究上,這不僅僅是因為研究本身困難,敏感之處還在于回答會牽涉到現實意識形態問題。左派史家與修正學派史家的史觀便截然不同,前者如馬迪厄、索布爾等人秉持環境論,認為恐怖統治是對國家緊急局勢的應對,羅伯斯庇爾是社會正義的捍衛者;后者如孚雷、諾曼·漢普森、帕特里克·葛尼斐等自由派史家,認為恐怖統治是大革命內在意識形態邏輯的產物,羅伯斯庇爾是這一意識形態邏輯“游戲”最高超的玩家。
這一羅伯斯庇爾謎題是如此棘手,以至于在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日(1989)論戰激烈之時,竟絲毫無羅伯斯庇爾研究的身影。在1994年舉行的羅伯斯庇爾研討會上,威廉·多伊爾對此便評道:“在這些情況下,大多數職業史家的困境是可理解的。任何人試圖關注羅伯斯庇爾或其革命生涯的任一階段,都冒著寬恕屠殺者這一指責的風險。”盡管如此,中立地研究羅伯斯庇爾,對于理解異象般的大革命仍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多伊爾看來,這樣的中間立場仍然鮮見。時至今日,多伊爾可以得到寬慰了。許多史家不顧艱辛而投身于此,他們考證和反思相關材料,從不同的視角打開問題思路,試圖真正地理解羅伯斯庇爾和恐怖統治,方法多樣,結果也風采各異。科林·瓊斯出版于2021年11月的《羅伯斯庇爾的倒臺:革命巴黎十二時辰》(The Fall of Robespierre: 24 Hours in Revolutionary Paris)便屬其中之一。
科林·瓊斯是著名的研究法國近代早期歷史的英國史家,向來以長時段的歷史研究見長,但新作《羅伯斯庇爾的倒臺》全然不同。瓊斯另辟蹊徑,爬梳熱月政變后巴拉斯(Paul Barras)下令收集的大量證言,“近焦”(up close)地跟蹤熱月政變這一天巴黎人的經歷,譜寫了一段精彩絕倫的熱月九日微觀史。
充滿變數的熱月九日
作為觀察的視角,“近焦”是瓊斯在書中開篇便強調的研究手法——近距離地觀察革命事件的每一個細節,如此才能得到宏觀視角下不能看到的異質。瓊斯認為,要想穿透大革命千變萬化、難以預料的事件迷宮,就必須近焦地深入革命進程中永無止盡的細枝末節(《羅伯斯庇爾的倒臺》,23頁)。瓊斯采用這樣的觀察手法,并不意外。盡管他擅長研究長時段歷史,但他也是《巴黎傳》和《蓬巴杜夫人及其形象》的作者,對于地點和人物的細致描寫是他的拿手之處。瓊斯也受益于同是巴黎城專家的梅西耶,在觀察革命事件上,二者心有靈犀。正因此,他引言開篇便引用了梅西耶的獄中思考。熱月九日梅西耶正被囚禁在獄中,受著恐怖統治之苦。梅西耶將法國大革命總結為一種光學現象,意指大革命的任何事件從遠處和近處進行觀察將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不僅如此,瓊斯放棄了傳統的學術論述結構,采用了逐小時遞進的敘事安排。該法既緣于瓊斯在觀看電視劇時受妻子建議的啟發,也源出烏力波(Oulipo)文學工坊所實驗的文學手法——“在限制中進行創作”。瓊斯相信,這種按小時分章的敘事結構所帶來的限制,能夠激發想象力和增強表現力(第7頁)。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近焦式的觀察、時序遞進的敘事,熱月九日充滿偶然性和變數的特點得以展現得淋漓盡致,而這正是瓊斯想要的。
在這一研究思路的引領下,瓊斯將熱月九日分成五個部分進行敘述。第一部分“陰謀因素”(從午夜時分到清晨五時),聚焦于巴黎的時況與兩委員會內的騷動。由于前夜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表了威脅性的演講,救國委員會其他成員感到不安。翌日初始,救國委員會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圣鞠斯特屢受攻擊,但仍試圖尋求和解。第二部分“一場戲的背景”(從清晨五時到正午時分),關注的是兩委員會內部達成的協議,該協議商定圣鞠斯特該日將先在救國委員會內、后在國民公會中發表和解演說。與此同時,曾為特派代表的塔利安試圖拉攏、串聯國民公會的溫和派代表,以反對羅伯斯庇爾。第三部分“一場議會政變”(從正午時分到下午五時),熱月政變正式爆發。該日正午,國民公會內部發生的激烈沖突,羅伯斯庇爾一派受到猛烈的指責并遭逮捕。遭到解職的巴黎國民衛隊司令安里諾(Fran?ois Hanriot)不甘屈服,他下令敲響戰鼓(générale),召集巴黎各區的國民衛隊。隨后,安里諾先發制人,率隊前往國民公會所在的杜伊勒里宮劇場大廳(salle des spectacles),試圖解救羅伯斯庇爾一派代表,但遭失敗并被囚禁。第四部分“巴黎革命日”(從下午五時到午夜時分),政變進入高潮。十六個巴黎分區的國民衛隊集結在巴黎公社廣場,巴黎公社也召開了市政大會并組建執行委員會(comité d'exécution),對巴黎各區進行起義動員。巴黎公社一方的科芬阿爾率隊解救了安里諾,但在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并未攻擊國民公會,而是回到了公社廣場。羅伯斯庇爾一派代表也陸續被解救到巴黎公社。處于懈怠之中的國民公會意識到了自己剛剛逃過一劫,開始采取主動措施,任命巴拉斯為巴黎督軍(généralat)組織武裝力量,繼續印刷、派發國民公會的告示。國民公會宣布羅伯斯庇爾一派代表不再受法律保護(hors-la-loi),一經抓捕,不經審訊即可處死,幫助他們也意味著是在對抗國家、法律和國民公會。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巴黎民眾和各區議會選擇了站在國民公會這一方。入夜漸深,巴黎公社廣場的國民衛隊陸續散去,勝利的天平倒向了國民公會。第五部分“午夜、午夜前后及午夜之后”,熱月政變已接近尾聲。巴拉斯率領的國民衛隊攻入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議員四散奔逃,羅伯斯庇爾一派代表——羅伯斯庇爾、圣鞠斯特、庫東、奧古斯丁·羅伯斯庇爾、勒帕,或是奔逃,或是自刎。隨后的熱月十日便是大規模的搜捕和處決。
在瓊斯筆下,熱月九日是偶然性的產物。盡管羅伯斯庇爾一派與兩委員會其他成員——巴雷爾、俾約·瓦萊納、科洛等人的矛盾早已有之,但尚未到須兵戎相見的地步。熱月九日皆不在兩派的預料之中,計劃更是談不上。熱月八日深夜,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表完講話后便坦然睡去,對第二天并無任何策劃。早晨時分,救國委員會內部本來就商定和解,圣鞠斯特也起草好了白天要發表的和解講話,試圖借此緩和昨日羅伯斯庇爾講話帶來的緊張氣氛。瓊斯分析了圣鞠斯特的話稿,發現圣鞠斯特甚至想“自立門戶”,與羅伯斯庇爾保持距離,脫離后者的影子,不再對其亦步亦趨。這些都暗示熱月九日會是一個派系和解、分化的日子,而不是火山爆發的時刻。變數在于圣鞠斯特的失策,他沒有按照原定的計劃在兩委員會中先行講話,而是直接在國民公會發表講話,并派庫東前去兩委員會進行辯解。圣鞠斯特可能想避免兩委員會的“扯皮”和爭執。但此舉讓救國委員會同僚頓感恐慌,他們認為圣鞠斯特沒有按計劃行事是在藐視他們,意在先發制人,爭取國民公會的支持,圖謀發動清洗,而庫東是一個障眼法,旨在讓他們放松警惕(216頁)。救國委員會等人怒火中燒。國民公會開議沒多久,塔利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攻擊正在講話的圣鞠斯特,可謂正中他們的下懷。一場反對羅伯斯庇爾一派的大火便就此燃起,裹挾了絕大多數對羅伯斯庇爾心存不滿的代表。
千鈞一發之際,手握絕對優勢卻未敢直搗黃龍,亦是變數。科芬阿爾率領的營救隊伍在救出安里諾后,人數占優,且有大炮加持,攻下附近僅有護衛隊防守的國民公會劇場大廳綽綽有余。但是,或是懾于國民公會的威望,或是在未收到攻擊命令情況下不敢輕舉妄動,科芬阿爾的隊伍調轉方向,返回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亦是舉措失當。在有先發優勢的情況下,巴黎公社大會宣布了禁出令,防止議員離場,希望以此增加出席率和防止大會信息外露,但此舉使其失去了爭奪事件解釋權和爭取巴黎民心的先機。早已集結在公社廣場的國民衛隊士兵也是群龍無首,始終得不到公社明確的解釋和命令,致其逐漸喪失耐心,離散回家。部分隊伍最終加入了國民公會一方。巴黎民眾和各區議會,在沒有得到清晰命令和權威的解釋前,猶豫不定,未敢先行支持某一方。正因此,擁有獨立印刷所的國民公會從始至終都在堅持編輯、印刷、派發當天的告示,逐漸樹立了自己權威、合法的形象,贏得了巴黎民眾。
這便是科林·瓊斯筆下的熱月九日,國民公會和巴黎公社各自布局,但缺乏全局視野,危險和機遇同在;巴黎謠言遍布,民眾陷于信息迷霧之中。面對傳來的互相對立的信息,核心街區的民眾游移不定,莫敢貿然站隊,與此同時,偏遠街區的民眾則全然不知巴黎中心正在風起云涌的政治風波。瓊斯借此表明,不同于標志著大革命爆發的7月14日和君主制倒臺的8月10日,熱月九日是一場“即興演出”,它的意義不夠明確,仍有待構建(468頁)。由此我們回到了行文初始所引用的庫爾圖瓦報告,它將熱月九日刻畫為一場議會戰勝暴政的政變,這一說法成了之后督政府的官方解釋。瓊斯的認識與之截然相反,他試圖還原真實的熱月九日,賦予該事件以本真意義。

一幅表現熱月政變的繪畫。此圖片中羅伯斯庇爾被一支手槍擊中。
作為民眾運動的熱月九日
在恐怖統治中,革命政府熱衷打壓巴黎民眾運動。1793年末到1794年初革命政府清除了激進的埃貝爾派和忿激派。此后,革命政府也未放松過對巴黎民眾運動的壓制,包括拒絕巴黎各區要求舉辦“人民之友”節和“最高主宰”節的動議,以及取締為了慶祝弗勒里大捷的聯誼宴。1794年春天對民眾社團的打壓便被稱作“芽月慘劇”(drame de germinal)。甚至在熱月九日前夕,巴黎警察局(l'administration de police de Paris)已在密切監管最高工資法將要引起的工人示威,并命令馬爾斯軍事學校(l'école de Mars)的青年士兵駐守熱月十日的巴拉和維亞拉烈士紀念節,以防工人騷亂。布呂奈爾在其篇幅短小但洞見迭出的著作《羅伯斯庇爾的敗亡》中便說道:恐怖統治逐漸形塑了體制主宰的政治文化,革命政府對挑戰政府權威的自發群眾運動抱有深刻的不信任(Fran?oise Brunel, 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Bruxelles: Editions Complexe, 1989, p. 29)。
雖然左右派史家對于“恐怖”的理解截然不同,但在這一恐怖統治實踐觀上,雙方懷有共識。羅伯斯庇爾主政的革命政府剪除了群眾運動,但同時也破壞了自身的執政基礎,最終遭到了反噬。這一最終的節點便是熱月九日,它被看作是恐怖統治的結束、革命政治的“右轉”,或是羅伯斯庇爾革命邏輯的終結、大革命對1789年原則的回歸。總之,大革命被認為完成了“去恐怖化”或“去民眾化”(depopularization)。對于這些解釋,瓊斯深感不滿,并對傳統的歷史事件遭到忽視而感到失望。關于革命政治,他相信熱月九日仍有許多需要解釋(Katlyn Carter, Interview: “24 Hour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An Interview with Colin Jones”, Age of Revolution, March 7, 2022)。在瓊斯看來,熱月九日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群眾運動。早在2014年,瓊斯便在一篇論文中闡明了自己這一史觀。他認為熱月九日的巴黎民眾并非漠不關心政治動向,而是虎視眈眈地觀望政治局勢,隨時做出行動。“‘民眾的漠然’是一個神話。”(Colin Jones, “The Overthrow of Maximilien Robespierre and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Peopl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9, No. 3 [June 2014], pp. 697; 706)此外,瓊斯認為,熱月九日也不是一次政治右轉,因為發起政變的兩委員會委員和國民公會代表幾乎都是山岳派,并且,巴拉斯、瓦迪耶、俾約、科洛都是恐怖政策的主政者,塔利安更是臭名昭著的外省恐怖締造者之一。瓊斯這種對熱月九日事件的理解在很多地方都受益于馬丁·萊昂斯(瓊斯在就讀研究生期間曾聽過萊昂斯的課程),在后者看來,熱月九日是左派內部的一場政變(Martyn Lyons, “The 9 Thermidor: Motives and Effects”,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Vol. 5, Issue 2, 1975, p. 125)。但有一點除外,當萊昂斯認為“要想解釋熱月九日事件,不能不考慮到巴黎各區的消極被動”時,瓊斯則指出,巴黎各區及其民眾是主動熱情地參與到這一事件之中的。
于是我們能看到,瓊斯在此書中花大量篇幅刻畫了一幅巴黎民眾的政治圖景。雖對恐怖修辭和恐怖政策已顯疲態,但巴黎民眾仍熱衷觀看大革命廣場斷頭臺的行刑場景;熱月八日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表的演說,也得到大多數會眾的積極反響;因不滿最高工資法,工人騷亂一觸即發,以至于熱月政變當天行人看到巴黎公社廣場集結了許多國民衛隊士兵,還以為是工人在集會示威;標志著大革命戰爭轉守為攻的弗勒里大捷更是讓巴黎民眾欣喜若狂,使其愛國熱情高漲,由此催生了聯誼宴運動(la campagne des banquets fraternels),并促進了熱月九日各區之間的友善運動(The fraternization movement)。友善運動的形成源自重新恢復活力的巴黎區議會。得益于該運動,熱月九日晚上的政治消息才能迅速傳播,并使得之后國民公會的勝利得到了全面而徹底的宣傳(487頁)。因此,1794年夏天巴黎民眾的政治熱情依然高漲,群眾運動遠遠談不上因為革命政府的鎮壓而偃旗息鼓。
國民衛隊也不容忽視,他們也是巴黎民眾的一部分。國民衛隊士兵之前只能由出身中產階層的積極公民擔任,如今全體男性公民皆能擔任,他們輪值時是民兵,平時則是平民百姓。在熱月九日中,這些國民衛隊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因為他們的參與,巴黎公社才能在初期占據著先發優勢。也正是因為他們的支持,國民公會才能最終占得勝勢。瓊斯對此頗具洞見,他認為,比起已遭政府削弱的巴黎區議會,國民衛隊士兵更能代表巴黎輿論。相比之下,無套褲漢只是巴黎民眾的一小部分(486頁)。
瓊斯非常清楚,雖然熱月九日的巴黎民眾并未像7月14日、8月10日和5月31至6月2日那樣,依據某一具體的訴求而主動發起反叛行動,但這事出有因。熱月政變事出突然,民眾沒有太多的思想和心理準備。并且,國民公會和巴黎公社兩方的民眾動員來得很晚,民眾沒有充足的反應時間(24頁)。事件高潮時段更是正值深夜,此時忙活了一天的民眾亟需休息,無暇他顧。此外,在有限的獲知信息的手段下,巴黎民眾面臨著內容互相沖突的消息,他們不知道該相信哪一方,更不知道哪一方能獲得最終的勝利,殘酷的恐怖統治舉措至少讓他們學會了謹慎行事以盡量站對邊(487頁)。等他們反應過來發生了什么,已是翌日羅伯斯庇爾一行人坐在囚車行往大革命廣場的時候了。盡管如此,在瓊斯看來,巴黎民眾的的確確積極熱情地參與到了熱月九日中:深夜被驚醒的民眾竭力打聽發生了什么;國民衛隊士兵在看到“宣布非法”的告示后,紛紛響應了國民公會的號召;翌日囚車路旁的民眾更是歡慶暴君的倒臺。瓊斯總結道,“熱月九日是最為典型的巴黎革命日(the most Parisian of Revolutionary journée)”(28頁)。科林·瓊斯這一史觀不乏先例,布呂奈爾在《羅伯斯庇爾的敗亡》里便已表明:“事實上,人們不能忽略巴黎民眾在熱月九日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對熱月10日早晨發布的聲明視而不見:‘巴黎各區配享祖國,當之無愧。’”(Fran?oise Brunel, 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p. 74)但瓊斯的獨到之處在于,他通過對熱月九日這一天的細致描繪,讓巴黎民眾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展露無遺,從而為這一史觀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闡釋,幾乎讓人無可辯駁。
瓊斯這種“復民眾化”的熱月九日研究,矛頭直指“熱月神話”所塑造的官方熱月九日。上述布呂奈爾所引用的聲明是巴拉斯在政變翌日作出的,他將熱月九日定性為:在人民的支持下,國民公會對抗暴君的一場勝利。但沒過多久,國民公會丹東派代表勞倫·勒克維特爾(Laurent Lecointre)修改了這一說法,指責將丹東送上斷頭臺的恐怖統治主政者,認為不僅僅是羅伯斯庇爾,還有他在革命政府中的同僚都應當為恐怖統治負責(471頁)。在熱月九日到督政府上臺這一年多的“后熱月”時段里,伴隨著輿論自由的再生,指責革命政府恐怖血債的請愿、書信和獄中回憶錄紛至沓來,革命輿論已悄然發生了轉變。隨后,國民公會中的溫和派逐漸占據了優勢地位,主導外省恐怖的山岳派特派代表紛紛受到指控,如犯下南特屠殺的特派代表讓-巴普蒂斯特·卡里耶就在1794年秋天遭到了審判。1795年春天,曾將無數人送上斷頭臺的革命法庭公共檢察官富基耶·坦維爾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臺。發起熱月政變的山岳派也不免于外,1795年3月22日,巴雷爾、俾約·瓦萊納、科洛遭到逮捕并被流放至圭亞那。1795年4月1日的芽月起義和5月20至23日的牧月起義,巴黎民眾呼吁充足供應面包和實現1793年憲法,但遭到巴拉斯的殘酷鎮壓,熱月政府再也不能容忍又一個革命日的發生,已決心鏟除群眾運動。于是一個多月后,我們便看到了庫爾圖瓦的報告,其中對熱月九日的描述已無巴黎民眾的身影,被妖魔化的羅伯斯庇爾與民眾被捆綁到了一起,該報告完成了對熱月九日的“去民眾化”(472-473頁,科林·瓊斯對此還有專門的研究,參見Colin Jones, “9 Thermidor: Cinderella among Revolutionary Journé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5, pp. 9-31)。
自大革命史修正學派嶄露頭角以來,學界關于熱月神話的研究可謂不知凡幾,科林·瓊斯的研究是其中的佼佼者。恐怖統治一詞是熱月政府時期才發明使用的,1793至1794年的革命政府在熱月時期遭到污名化,“人民”一詞再次回到了舊制度下那種群氓的負面含義,學界對這些事實幾無異議。但有一個歷史人物仍引起許多爭議,對他的研究學界尚無定論。此人也是理解熱月九日的關鍵,是瓊斯此書關注的重中之重。他便是羅伯斯庇爾。

羅伯斯庇爾
羅伯斯庇爾、恐怖統治與大革命
熱月九日正午,在準備打斷圣鞠斯特的講話時,塔利安與頑固的山岳派代表蒙泰居(Goupilleau de Montaigu)說道:“這正是攻擊羅伯斯庇爾及其黨羽的時刻。”(217頁)在開始攻擊后,羅伯斯庇爾一直沒有上臺講話的機會,當時國民公會的輪值主席科洛也在刻意阻止羅伯斯庇爾發言,之后羅伯斯庇爾便遭到逮捕。但在被解救后,躲在市政廳的羅伯斯庇爾顯然有機會發表意見,但他仍沉默不語,他是被突如其來的變故所震懾住了嗎?還是覺得自己已處于非法的地位而多說無益?去到巴黎公社后,羅伯斯庇爾受到熱烈的歡迎,但依然默不作聲,唯一的聲響便是自殺時的槍聲。他并沒有像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政治斗爭那樣振臂一呼而發動叛亂,他不是街頭政治家,更非如巴拉斯那樣的雷厲風行的武裝首領,他無意領導這場公社叛亂。瓊斯非常肯定這一點,他指出,羅伯斯庇爾更多的是一個通過雄辯將政治真理告知民眾的愛國者,而非民粹領袖。讓·馬丁對這點看得也非常透徹,他分析了十月游行事件、8月10日和5月31至6月2日事件中的羅伯斯庇爾,指出,羅伯斯庇爾實際上并未策劃并參與到這些民眾行動中。民眾暴動之時,羅伯斯庇爾往往躲了起來,他并不適應混亂無序的狀況。但在事件發生后,羅伯斯庇爾便會利用他的雄辯,為民眾行動構建合法性。就這點而言,羅伯斯庇爾是一個高超的意識形態政論家(參見Jean-Clément Martin,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aris: Perrin, 2016; Colin Jones, The Fall of Robespierre, p. 27)。
顯然,熱月九日不在羅伯斯庇爾的預想之內,即使是巴黎公社獲勝,那也不是羅伯斯庇爾想要的,因為在1793至1794年山岳派主政的這段時間里,維護國民公會的權威一直是他的目標。但這不表明羅伯斯庇爾與熱月政變的爆發無關,政變的矛頭始終對準的是他。瓊斯在此書中竭力論證這一點。熱月八日晚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表的演說,無疑是在宣揚敵人陰謀論、鼓動清洗國民公會和兩委員會,當晚科洛和俾約便被逐出了雅各賓俱樂部,由此在其對手中造成了恐慌。但瓊斯指出,羅伯斯庇爾并沒有策劃陰謀行動,或許他有意清洗政府中的腐敗者,但這離一場陰謀反叛相去甚遠,更不可能在第二天便有計劃行事,因為八日晚羅伯斯庇爾在俱樂部的講話結束后,便回到杜普萊的家就寢了。更何況,當晚兩委員會的會議主題是和解,公安委員會成員明顯有意與羅伯斯庇爾合作。因此,熱月九日,既無羅伯斯庇爾陰謀,亦無反對羅伯斯庇爾的陰謀。這正是瓊斯通篇都在強調熱月九日是一場即興演出,且很少使用“政變”一詞來形容這一事件的原因。在瓊斯看來,國民公會粉碎了羅伯斯庇爾圖謀登基、實行專制統治的意圖這一說法純粹是熱月神話的產物。
但羅伯斯庇爾確確實實與其山岳派同僚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更多的是雙方在施政理念上的分歧,而不是個人沖突。瓊斯對此談到了不少,但限于主題,并未給予足夠的筆墨,而許多恐怖統治研究則已經對此給出了詳盡的解釋。瓦迪耶一手炮制了卡瑟琳·蒂奧(Catherine théot)丑聞案,指控帝奧以女預言家的角色在寫給羅伯斯庇爾的一封信中,暗自將羅伯斯庇爾支持最高主宰崇拜節與以西結預言新耶路撒冷等同起來。該案體現了兩委員會中的去基督教化支持者對羅伯斯庇爾自然神崇拜的不滿。瓦迪耶也借此暗諷羅伯斯庇爾(關于這一事例,萊昂斯已做出了詳盡的研究,參見Martyn Lyons, “M. -G. -A. Vadier [1736-1828]: The Formation of the Jacobin Mentalit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0, No. 1 [Spring, 1977], pp. 74-100)。卡爾諾(Lazare Carnot)與圣鞠斯特在軍事策略上存在嚴重的分歧,卡爾諾支持征服戰爭,試圖將由公民士兵組成的北方軍轉變成職業軍隊,圣鞠斯特則反對征服、主張嚴格的共和國防衛戰,卡爾諾也與羅伯斯庇爾的和平主義相抵牾。在熱月九日前夕,正是卡爾諾將巴黎的國民衛隊炮隊調往了前線,借此削弱了巴黎公社的力量(瓊斯、布呂奈爾、萊昂斯都談到了這點,詳見Colin Jones, The Fall of Robespierre, p. 326; Fran?oise Brunel, 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pp. 85-86)。牧月二十二日法令(或稱大恐怖法)也分化了兩派,該法規定治安案件可以繞過公安委員會,簡化審判程序,這令公安委員會成員感到不滿(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p. 83)。總之,羅伯斯庇爾與兩委員會另一派的矛盾,主要是治安、宗教和軍事等方面的政見分歧。因此,熱月九日并不是羅伯斯庇爾怪異恐怖的言論導致的,也不是熱月黨所稱的一場終結恐怖統治的政變,熱月九日根植于山岳派內部兩派的觀念和政見分歧。
羅伯斯庇爾也不該被認為是“恐怖”的始作俑者。實際上,1793年山岳派主政后,相比于已經進入救國委員會的丹東,羅伯斯庇爾仍遠離政治事務,此時恐怖統治已然開啟。羅伯斯庇爾那句著名的“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致命的,沒有美德的恐怖則是孱弱的”廣為傳頌,往往被視作羅伯斯庇爾鼓動恐怖的證言,但羅伯斯庇爾意在向無套褲漢表明正義的優先性,而非鼓動殺戮(這一觀點參見Jean-Clément Martin,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 240)。還需注意的是,熱月九日塔利安之所以率先攻擊羅伯斯庇爾,正是因為羅伯斯庇爾收到了塔利安在波爾多的不潔行徑的線報,他將塔利安的情婦卡巴呂投入監獄,并試圖懲戒塔利安。瓊斯在全書開篇便仔細檢視了該案。此外,羅伯斯庇爾也召回了殘酷鎮壓里昂叛亂的富歇(Joseph Fouché),欲指控其反革命。就此而言,羅伯斯庇爾雖然呼吁以“恐怖”來打擊共和國的敵人,但他并未直接參與到恐怖實踐之中。比亞爾的恐怖研究對這點有所呼應,他認為恐怖行徑更多是由當地的緊張局勢和當事人行為導致的,巴黎的中央政府并未組織實施,因而也不負直接的責任(Michael Biard, Pascal Dupuy,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ynamique et ruptures, 1787-1904,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p. 135)。至少羅伯斯庇爾沒有直接的責任,他不應該背負恐怖統治沉重的血債。為此,瓊斯在此書中堅決拒絕使用時代錯置的“恐怖”一詞(469頁)。此外,熱月九日之后,恐怖遠未結束。更甚者,此后暴力成了行使國家權力的一種日常手段,再也不需要羅伯斯庇爾那樣的辯護(Jean-Clément Martin,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 314)。
羅伯斯庇爾究竟是怎么樣的一個人,他是如何走到熱月九日那個地步的?近年來,許多史家都對他做出了新的解讀。大衛·安德列斯依托情感史理論,認為羅伯斯庇爾代表了十八世紀末一種新興的、獨特的自我建構,他將自己代入為情節劇(melodrama)的受害者,最終將自己構想為“護民官”的角色,以致釀成一種走向毀滅的惡性邏輯(David Andress, “Living the Revolutionary Melodrama: Robespierre's Sensi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s, Vol. 114, No. 1 [Spring 2011], p. 124)。瑪麗薩·林敦認為羅伯斯庇爾以政治美德為政治信條,成了大革命“本真”政治競爭的勝者,但最終亦遭懷疑,為之反噬(Marisa Linton, “Robespierre et l'authenticité révolutionnair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No. 371, 2013, pp.153-173)。奧利維耶·貢當蘇認為隨著革命的發展,羅伯斯庇爾逐漸扮演了一個負責在民主原則與革命現實間搭建橋梁的角色,它是由大革命機制造就的(Olivier Contensou, “Robespierre: La cause du peuple”, Cahiers Verbatim, Vol. VII [Automne 2019], pp. 15-37)。馬塞爾·戈肖區分了“政治原則”(le politique)和政治實踐(la politique),認為羅伯斯庇爾混淆了這兩者,造成了“原則的專制”(Marcel Gauchet, Robespierre: The Man Who Divides Us the Most, translated by Malcolm DeBevoi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238)。馬丁的研究則與眾不同,他對羅伯斯庇爾進行了“祛魅化”,認為羅伯斯庇爾并無異常之處,他的獨特性是建構出來的,馬丁最后對熱月九日進行了一種“去羅伯斯庇爾化”的解讀(Jean-Clément Martin,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 pp. 321-324)。相比于這些研究,瓊斯對羅伯斯庇爾的解讀并無太大創新。他認為,羅伯斯庇爾不是一個野心家,至少不是他的“熱月敵人”所說的那種帶有舊制度政治烙印的宮廷野心家,反之,他稱得上是正直如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者。
但是,瓊斯的解讀也有獨到之處,他結合了“名望”研究,讀出了熱月九日的另一面。名望是十八世紀新興的文化現象,十八世紀大眾傳媒的發展縮短了人們相識的距離,民眾對于他們素未謀面的人物會產生喜好情緒,由此賦予一個人物以巨大聲望,使其成為名人。1793至1794年,羅伯斯庇爾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聲望,仿佛革命之初的米拉波那樣。但羅伯斯庇爾從未締造過個人政治崇拜,其聲望遠未達到后來拿破侖的卡里斯瑪的程度,而大革命也有堅固的反崇拜文化(Antoine Lilti, Figures publiques: l'invention de la célébrité 1750-1850, Paris: Fayard, 2014, pp. 238; 247)。因此,巴黎民眾才會在一夜之間拋棄了羅伯斯庇爾。瓊斯借此指出,熱月九日亦是一場民眾維護大革命體制、反對威權獨裁的政變事件。在這一天,巴黎民眾選擇了共和體制,保護他們自1789年以來獲得的、極為珍貴的民主,而非追隨政治偶像(489頁)。
小結
自共和二年熱月九日到現在,已過去了兩百多年。材料稀少、個人喜好和政治偏見,都為這段歷史鋪上了層層迷霧,我們投身或觀望于此,是否注定會陷入無盡的歷史迷宮?即使我們相信存在歷史真相,也難以企及其本來面目。在巴黎公社內自殺失敗后,羅伯斯庇爾因下顎嚴重損毀,無法說話。他被帶到巴黎公社廳區的民事委員會進行審訊,后被轉到公安委員會,其間不被允許寫字。整個熱月九日,羅伯斯庇爾唯一留下的文字材料是午夜時分起義宣言中的簽字,其中只有兩個字母“Ro”。無從確證其中的含義,只知羅伯斯庇爾的猶豫。如若他能留下更多材料,這層層迷霧或許就能散開幾許。但迷宮依舊。熱月政府塑造的羅伯斯庇爾專制、殘暴、嗜血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縱使許多史家努力剔除政治偏見,中立地進行研究,以探尋更為真實的羅伯斯庇爾,也難改這一根深蒂固的窠臼。
科林·瓊斯的熱月九日劍指這一窠臼。瓊斯該書的文學創作手法,既旨在更貼近事實原貌,也意在吸引更多的讀者,試圖將一個更為本真的羅伯斯庇爾和熱月九日傳遞給公眾。在他的熱月九日,羅伯斯庇爾沒有登基稱王的野心,更無主動發起政治清洗的計劃,恐怖血債亦與其沒有直接的關聯。熱月政變,純粹是民眾忠誠于民主機制,拋棄了羅伯斯庇爾。就連羅伯斯庇爾自己也無法走到國民公會的對立面,在為巴黎公社起義號召書簽名時的猶豫,或許表明了他拒絕充當僭主。以羅伯斯庇爾為例,以自然權利之名追尋民主,必然會導致恐怖嗎?必然會導向戈肖所說的“原則的專制”嗎?這是每一個了解過大革命的人都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對此,科林·瓊斯該書的價值之一,便是告訴我們:“烏托邦之路”并沒有走向極權,熱月九日的巴黎民眾和羅伯斯庇爾都依舊選擇了民主。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