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石一楓:這些想法的深入與否決定了小說的復雜程度 | 寫作課
小說創作中的幾組概念
——從《漂洋過海來送你》說開去
文 | 石一楓
說實在的,我不是很喜歡“創作談”這個說法,總覺得那有“教人怎么讀自己的小說”之嫌,而小說一旦淪落到需要教人怎么讀,已經落了下乘,也喪失了這個大眾文體的本意。大眾文體不同于精英文體,門檻低是它的天然要求,權力歸于讀者,作者蹦出來指手畫腳,透著越俎代庖的自戀。然而小說這門藝術門檻雖低,門道卻深,我想我也應該把自己的想法進行一下梳理,一來是和朋友們交流,再者也能幫助自己提高。總歸是個自我反思和自我鞭策的過程。
在某種意義上,《漂洋過海來送你》以及我近些年來的創作,其實是伴隨著幾組概念或云幾組關鍵詞進行的。對于那些概念或云關鍵詞,朋友們的討論多有涉及,各自談的想法也很深入,從作者的角度來說,那些想法的深入也決定了小說的復雜程度。當然作者在動筆的過程中,往往也會有些不可控的情況,有時想到了卻沒寫到,有時寫到了卻沒想到,或許也正因為此,和大家一起復盤才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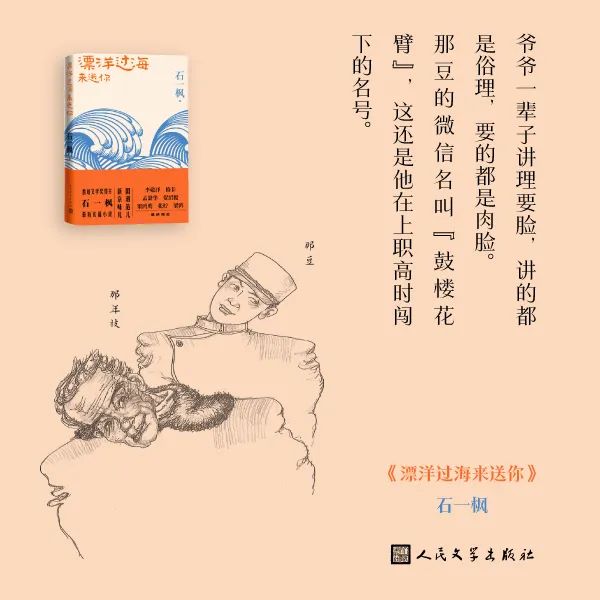
第一組概念應該是“故事”和“現實”。假如小說是講故事,那么現實題材的小說就是講那些來自現實、與現實高度相關的故事,這是字面上的粗陋理解。有時也會想,故事多了,干嗎一定要講現實的故事呢?干嗎一定要講現實中的小人物的故事呢?大人物的故事、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故事不是講起來更加信馬由韁,聽起來更加驚心動魄嗎?事實上我們古典小說中的故事總是離現實、尤其是離普通人的現實距離很遠。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的是英雄而不是我們這些凡人。我們連淘都不配被淘。但這又涉及意義的問題了: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了,動物也不被允許修煉成精了,恰恰只有現世凡人的生活才是最值得關注和反思的。原來我們就是那淘人的浪。過去學歷史,還知道有個年鑒學派,不大看重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而是把貿易規模、交通方式和食譜構成當作決定歷史發展的動力,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歷史學多少還是有點兒明確的目的,它想要探究真相。而對寫小說的,真相好像也無所謂,關鍵在于我們認同什么,把什么看作是有價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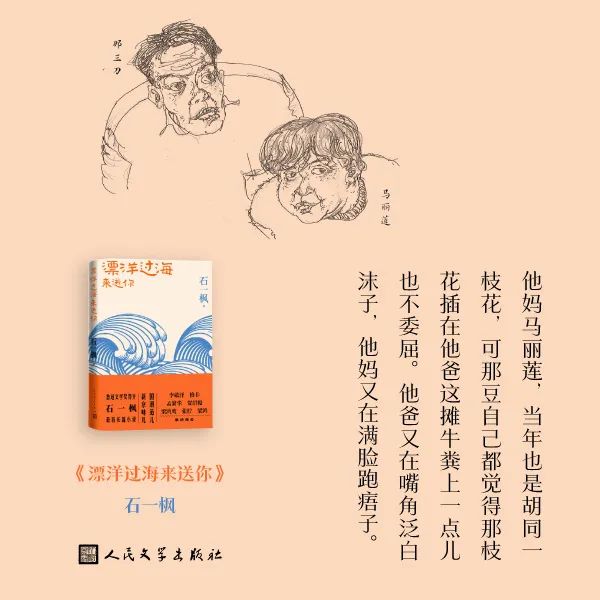
但又面臨一個問題:什么樣的故事是對我們現實生活的恰當反映呢?這也關乎真實,因為故事本身就是對現實的提煉和改編,那么又要怎樣提煉和改編才不至于失真呢?另外還有個說法,現實永遠比小說精彩,媒介的發達讓現實膨脹了,撲面而來,假如突然發現編的都不如真的有意思,你編它干嗎呢?這時候好像就有必要讓“現實”跟“主義”發生一點兒聯系了。我在《當代》雜志當過一些年的文學編輯,看稿子最怕看到有“現實”沒“主義”的,那感覺就跟《舌尖上的中國》里混進一個差勁的廚子似的——天蒙蒙亮,這哥們兒就“開始了一天的勞作”,可惜上好的食材會收集不會收拾,干脆來個亂燉吧,多放味精。還是說得粗陋點兒,現實主義需要寫作的人對現實有看法,關鍵不在現實,而在那點兒看法。而在小說里,什么是看法?故事本身就是看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故事寫的還真未見得是現實,而是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我們總在找尋著一個故事,它能夠自我生長,也能夠帶領我們生長,每一次生長的結果,都讓我們眼中的世界不復是它原有的模樣了。看法貴在有穿透力,因而故事也貴在有穿透力,只不過獲得穿透力的途徑又各有不同。對于我目前而言,似乎那些強烈的、有著一定程度戲劇性的故事更能穿透現實的表象,幫助我找到它層層外殼之下的內在機理,或許因為這個原因,我并不排斥那些有著傳奇甚至極端色彩的故事。前兩年寫的《心靈外史》和《借命而生》如此,這次的《漂洋過海來送你》也有這樣的特質。故事大量地使用了“無巧不成書”和“說時遲那時快”的演進方法,寫的時候我自己也會心虛:這太“過”了吧?然而再一琢磨,為了讓我的看法在故事中成立,似乎也只能如此。為了表面的、掩飾出來的圓熟而犧牲故事的力度,在我看來是不值當的。當然得承認,一旦只能如此,也恰恰暴露了我作為作家的火候不到,而繼續追尋“那一個”完美的故事,似乎也是我這種職業的本分了。這是令人沮喪的,也是令人振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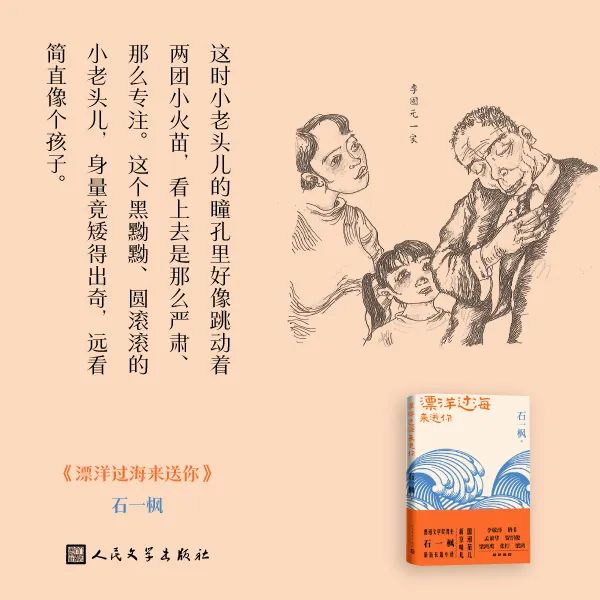
以上大約泛泛而論,或許還涉及了“寫小說”這件事情的本源意義。我可能屬于那種有點兒溯源癖的作家,對小說里的事兒不溯清源流就沒法兒寫,對寫小說這事本身不溯清源流好像也干不下去。也有作家更加本能一些,不用考慮這樣的問題也能寫作,對人家我只有羨慕的份兒。而此后還想討論一對概念,就是“熟悉”與“陌生”。
這里的“熟悉”與“陌生”又分成兩個層面來說,有淺有深。淺的層面在于你“能寫什么”和“寫什么才像”。我們說廣闊的現實、無邊的生活,歸根結底都是屬于別人的,是屬于人類這個群體的,而個人的經歷與感受其實很有限。我們看似一群到處亂竄的蟑螂,其實各在各的地盤上竄,廚房的不去衛生間,衛生間的不去儲物間,一不留神還被粘板給粘住了。但寫小說和寫統計表、寫報告、寫新聞稿都不一樣,它得在一定程度上還原現實,起碼讓讀者“相信它是真的”,所以只有熟悉的東西才能下筆,不熟悉的沒準兒寫著寫著自個兒先吐了。在某些文學理念中,“經歷豐富”是創作的先決條件之一,確實也有作家當過兵,種過地,打過鐵,沒準兒還坐過牢呢,這肯定是寫作上的優勢——不過隨著社會分工對人的固化越來越嚴重,大部分人經年累月從事的營生也變得越來越有限了,最后很可能會變成當兵的羨慕種地的,種地的羨慕打鐵的,大家一起羨慕坐牢的。作家協會就組織大家“采風”,“體驗生活”,所針對的想來也是這個問題,不過多少又有點兒急就章的意思。既然我們時代已經不大可能產生海明威那樣的作家,那么比來比去,沒準兒倒是最不值得羨慕的“作家”或者“文化人”反而值得羨慕——因為他閑,閑得沒事兒就會操心人家的事兒,操心來操心去,陌生就變得熟悉起來了。當然,真能做到替別人操心,可能也是一種職業素養。再具體到《漂洋過海來送你》,小說是從我耳熟不能詳的因素入手,牽扯到耳不熟更不能詳的因素,最后盡量達到耳熟能詳的效果。我在北京生活,不過一直住在機關家屬院,要不就住小區,這些地方都和胡同區別很大,但我上班又在二環路里,挨著東四一片兒碩果僅存的胡同,沒事兒老在里面溜達,溜達了些年頭就有點兒感覺了。后面寫到殯儀館里的情況,則需要查一查資料,好在現在查資料也方便,在網上看也能看熟了,不必“此事要躬行”。寫到國外反而簡單了,我在美國東海岸待過點兒日子,芝加哥是現成的,至于寫到去埃及、去阿爾巴尼亞的海外勞工人群,又得感謝作家協會——有次去那邊參加活動,給我一人扔到經濟艙里睡了兩夜,發現身邊乘客和以往不同,全是南腔北調的工人師傅,所以何大梁那條線索也可以說是坐飛機的收獲。過去聽老編輯聊天,說中國的作家大部分屬于“自傳型”的,所以好多人寫著寫著也就覺得沒意思了,我當然也不覺得“筆耕不輟”是個多大的美德,不過一直避免當個自戀的人,所以心里想,以后寫東西得寫別人的故事,不要以自我為中心。而別人的故事,也得從自己熟悉的地方出發,一點兒一點兒地把陌生變成熟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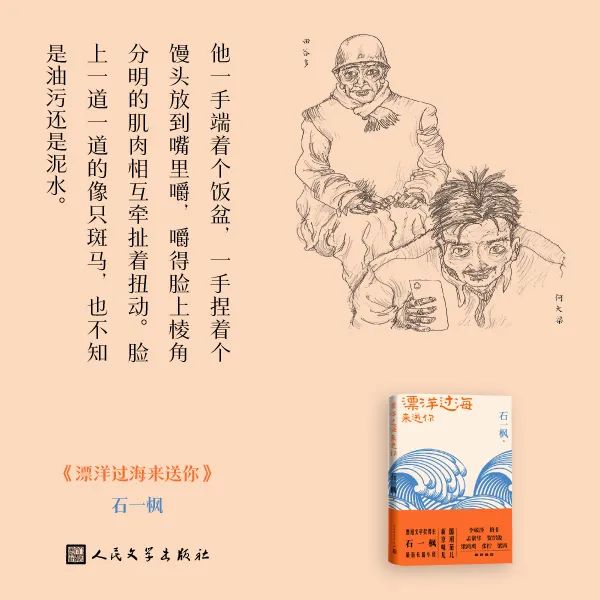
而“熟悉”和“陌生”的第二個層面,在我看來可能是深一點的層面,恐怕仍然和意義有些關系。有時候也想,就算寫的都是熟悉的事兒,就算把陌生的也變成熟悉的了,到頭來又有什么意思呢?就像從電線桿子上摘下一塊口香糖放嘴里,還對人顯擺,你看,我從來不挑食。在這個角度上考量寫小說這件事情,它固然是個手藝活,語言的鑄煉、結構的安排之類都很重要,但終歸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個熟能生巧的功夫。題中沒有之義就不是手藝活了,有時越熟越不巧,它需要我們把熟悉的東西再變得陌生。有了陌生,也就有了新知,純然陌生的新知是學習,熟悉中得來的陌生是發現。當然不只文學如此,人文社科的學問很多也如此,比如還是看歷史,很多國家天經地義的事情在其他國家就像行為藝術一樣。就連自然科學好像也如此,所以牛頓是在蘋果樹下發現了萬有引力。就小說而言,假如一個作品中的場景看似熟得不能再熟,都是從生活中來的,但又總能讓讀者看出未曾有過的新鮮氣象,那就是把熟悉變回陌生了。熟悉和陌生的兩個層面,從陌生到熟悉,再從熟悉到陌生,有點兒像前人的看山看云之說,只不過順序變了,在我這兒是先“看山還是山”,然后才“看山不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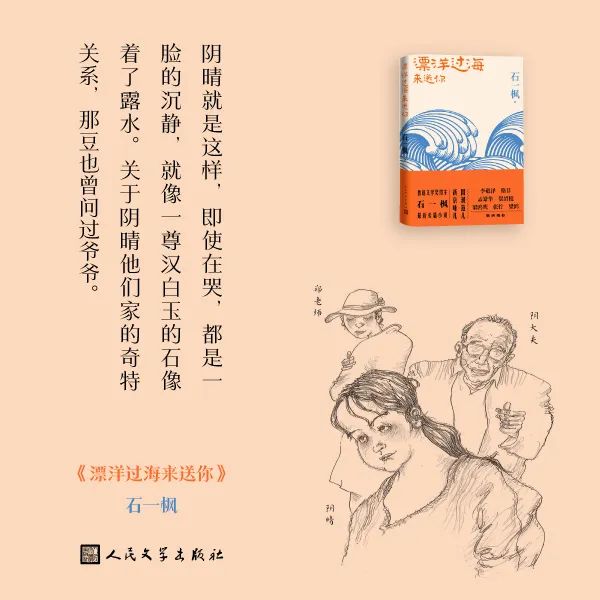
而將熟悉變回陌生,似乎又有兩條路徑,一是在舊題材上有觀念上的突破,二是在新題材上有觀念上的發現——就我而言,好像更喜歡也更適應后者。前輩作家經常寫到晚清或者民國,有開創性的比如《白鹿原》,是在政治的線索之外重書了一條宗族的線索,以此看待中國人的歷史與生活,欠缺開創性的就有點兒像翻烙餅了,一會兒這面朝上,一會兒那面朝上,頭一次翻驚天動地,但翻多了卻不免讓人懷疑他是為了翻而翻。這種題材我讀過很多,但實踐的興趣一直不大。我希望能從大家都已熟悉的當下生活中找到一點新的發現,并且我想,我們所經歷的“當下”也在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延長,開始具有了它獨特的歷史價值。我是改革開放造就的一代人,而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了,長度上已經超過了現代文學史。《漂洋過海來送你》當然也是在這種興趣的影響下寫出的東西,比較著力的有兩點:一是全球化對中國人生活的影響,過去說世界是普遍聯系的,這是個哲學命題,現在就是個日常狀態;二是價值觀上的“隔輩兒親”,幾十年來的中國人好像都在反對他們的父輩,但祖輩信奉的東西,是否會以變形的樣貌重現在孫輩身上?當歷史重演兩次,究竟是悲劇還是喜劇?而對“北京”這個概念的發掘,好像倒在其次了。在我看來老舍之所以了不起,也不在于寫了北京,而在于通過北京寫了他那個時代中國最迫切也最重大的問題,譬如啟蒙,譬如救亡,譬如革命。北京就是個背景,說得損點兒,對于我們這種離不開北京的人,無非是粘蟑螂的那塊板。當然求新也會伴隨著一些取舍,比如塑造人物的筆墨,那豆的父輩和“貧嘴張大民”等形象有所重合,其他民俗意義上的“老北京”更是很多前輩寫過的,我沒有更新的看法就少寫點兒,那豆和陰晴那代人,尤其是他們對祖輩的再認識是新鮮一些的元素,我需要著重塑造。這和老先生說的“有話則短,無話則長”也是一個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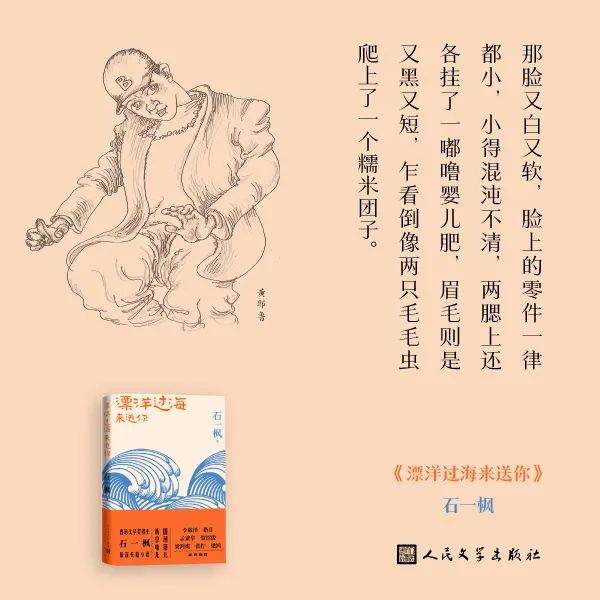
此外再說說另一對概念,“復雜”和“單純”,這好像又與寫作的心態有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小說當然是復雜的好,因為現實生活本來就很復雜,如果看不到那些復雜,那么可能不太適合寫小說。當然也得恭喜這樣的人,因為他沒準兒生活得很幸福。但僅僅復雜就夠了嗎?小說中的人物自然有復雜的,也有單純的,他們有他們的自我邏輯,然而我們這些身在小說之外又與小說密切關聯的人,又應該以怎樣的狀態去面對小說所呈現、提煉甚至夸張了的生活的復雜?這個問題也關乎我們閱讀、寫作小說時的底色。作家的本質不同,也許正是在小說中流露出來的底色不同。我所喜愛、佩服的作家,好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能看到生活的復雜,但又不畏懼或屈服于那種復雜,而是能以盡可能單純的目光去審視復雜。他們泛舟海上卻能錨定自身,這近乎一種修為。又當然,那種復雜與單純的關系似乎也在人類進入現代以后變得越來越復雜了,羅曼·羅蘭還能直說“認清生活真相之后還能熱愛生活”,我們卻要首鼠兩端地考慮是否認清,是否熱愛。和《地球之眼》《玫瑰開滿了麥子店》等作品一樣,《漂洋過海來送你》也觸及了道德甚而信仰的問題,雖然體現在人物身上可能是變形的道德和變味的信仰,但在很大的維度上問題還在。既然問題成立,也就沒必要回避,答案本身有沒有價值另說,但不放棄解答我想還是有價值的。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認識到問題的復雜與迫切,最后歸結為人物的一個單純選擇,這可能又是“故事”層面的衍生邏輯,在幾篇小說里面多有暗合。只不過我在找到了故事的內在動力之余,也在懷疑這種動力體現得是否有點兒一廂情愿了?換句話說,可貴的單純是否傷害了可貴的復雜?和前面的幾個概念一樣,這對關系也值得我在以后的寫作中去認識和深化。
以上拉拉雜雜,是我對《漂洋過海來送你》這部作品,以及近年來對寫小說的一點想法。總而言之,可能并未跳脫出前人智慧,尤其是“現實主義”寫作的基本原則。原則都在書本上寫著,不過不在一時一地,考量與運用也就是另一回事。而我還想保持一個看待自己作品的原則,就是當著內行不要自作聰明,將自己的想法盡可能地呈現出來加以審視,以期能在日后寫出更好的作品而非更好的“創作談”。
文章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8期
本期微信編輯:于文舲
相關閱讀
《漂洋過海來送你》 石一楓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漂洋過海來送你》的構思過程,統言之,想講講人和歷史、世界的關系。我喜歡看的一些前輩自有一套話術,愛把天下事說成他們村的事。吃碗看鍋,胸懷世界。而對我這個年紀的人而言,還有一種潛意識,那就是我們的生活早已被整個兒地球所裹挾,你愿意也罷不愿意也罷,都沒有了吃碗看鍋的距離感。這種裹挾有時令我們幻覺登上天下之巔,有時又讓我們自怨自艾地舔舐傷口,而我們也需要將其過程與機理呈現出來。
——石一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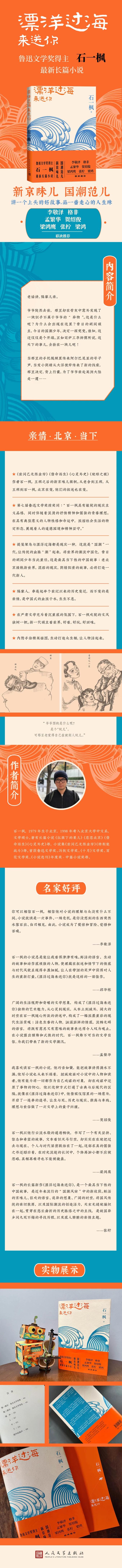
原標題:《石一楓:這些想法的深入與否決定了小說的復雜程度 | 寫作課》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