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年度書單︱解璽璋:轉(zhuǎn)型時代的歷史思辨和國際視野
清末民初的歷史具有持久魅力的原因,除了其豐富性、復(fù)雜性,以及呈現(xiàn)出多種可能性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它與當(dāng)下斬不斷、理還亂的關(guān)聯(lián)。這種關(guān)聯(lián)不僅是時間上的,更是歷史演化的和社會心理上的。故近年來關(guān)于清末民初這段歷史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僅2017年所見并讀過而有所感的便有:許紀(jì)霖的《家國天下:現(xiàn)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rèn)同》、李禮的《轉(zhuǎn)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zhuǎn)變》、唐啟華的《洪憲帝制外交》、瞿駿的《天下為學(xué)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黃興濤的《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陸建德的《海潮大聲起木鐸》。下面我分別談?wù)勱P(guān)于這幾本書的讀后感。
《家國天下:現(xiàn)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rèn)同》延續(xù)了從現(xiàn)實問題出發(fā),進(jìn)行學(xué)術(shù)研究和理論探討的習(xí)慣做法。在這里,作者所面對的問題大約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無所不在的國家意志;二是民眾中的大多數(shù)國家意識、公民意識薄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盛行;三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乃至軍國主義囂張,深刻影響輿論。當(dāng)然還有其他問題,但突出表現(xiàn)在這幾個方面,它們互相糾纏,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沖突中共生,在撕裂中相處,構(gòu)成了當(dāng)代中國的社會政治圖景。
這本書試圖提供一種政治解決方案,以回應(yīng)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他以“現(xiàn)代國家認(rèn)同”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為切入點,上溯中國古代“家國天下”的傳統(tǒng),指出傳統(tǒng)社會中的“家國一體”是以倫理性的禮樂制度為其基礎(chǔ),即使大一統(tǒng)的秦漢體制亦不能有所改變。個人的自我認(rèn)同只能通過在家族、王朝公共事務(wù)中的道德實踐來實現(xiàn),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種家國天下共同體在近代以來受到了挑戰(zhàn),隨著西學(xué)新知的大量涌入,有先知先覺者開始重新思考“我”與“家國天下”的關(guān)系,譚嗣同的“沖決網(wǎng)羅”,就是要沖破儒家三綱所編織的家國天下共同體的束縛,從而獲得解放了的、獨立個體的身份認(rèn)同,不再通過家族或“國家”這個中介構(gòu)建人生意義。但同時也要看到,甲午之后不斷加深的亡國滅種的壓力,使得其中一些人為國家的渙散和民族的蒙昧而擔(dān)憂,從而在舊的“家國天下”解體之后,建立新的國家、民族認(rèn)同。對中國來說,這是百余年來曾以各種方式不斷被提起而至今尚未完成的任務(wù),中國亦因此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由于失去了社會和天下的制約,國家權(quán)威至高無上”;另一方面,“由于從家國天下共同體‘脫嵌’,現(xiàn)代的自我成為一個無所依傍的原子化個人,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如何走出困境呢?作者主張重建一個“既劃清各自的疆域,同時又相互制衡”的“家國天下新秩序”。這個“新秩序”“必須補充社群主義以建立社會的自我,引入共和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以重新理解個人與國家的關(guān)系,強(qiáng)化世界主義來讓個人從普世文明中獲得真正的自我”。這種新的認(rèn)同模式,雖不乏理想主義的嫌疑,卻總是對當(dāng)下國族社會嚴(yán)重分裂的一種回應(yīng)。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來傳統(tǒng)家國天下的解體與社會轉(zhuǎn)型,固有其歷史演化的自身邏輯與來自西方的外部刺激,而新興報刊的興起,以及公共“輿論場”的形成,亦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禮對晚清報人群體的研究,則再現(xiàn)了那個時代自由言說、眾聲喧嘩的生動局面。他仔細(xì)考察了這個群體的構(gòu)成及其社會身份,作為新型“意見領(lǐng)袖”和社會精英,他們是如何利用報刊“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以培養(yǎng)民眾的“國民”意識,乃至“公民”意識,并積極介入政治,影響晚清政治走向的。他們制造了“民意”,以“民意”取代“公意”乃至“公理”,最終,自己也被“民意”裹脅,成為這種“民意”的受害者。
這個群體大致包括這樣幾類人,一類是從傳統(tǒng)知識體系中游離出來的士大夫,其中多數(shù)為主動選擇,欲以言論參與政治;一類是科舉廢除后進(jìn)入城市尋找新的機(jī)會和出路的地方讀書人,其中多數(shù)是被動的,因上升通道被阻斷,只得借“文字”以謀生;還有一類是海外留學(xué)的學(xué)生(主要在日本)和畢業(yè)回國的留學(xué)生,他們中多為具有反抗精神的激進(jìn)青年,自己被輿論所鼓動,亦以輿論鼓動別人。這些人放棄科舉致仕的“正途”,參與公共輿論的建構(gòu),對社會大眾進(jìn)行思想啟蒙,催生社會政治變革乃至革命,形成對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認(rèn)同,是清末民初異常活躍的政治勢力。不過,他們的思想及身份是如何轉(zhuǎn)變的,在這個過程中發(fā)生了什么,歷史敘事一直語焉不詳。李禮的《轉(zhuǎn)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zhuǎn)變》一書,對此做了詳實的描述和透徹的分析,是一部頗有新意的著述。

瞿駿《天下為學(xué)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也是一本很有意味,又很有思想深度的書。作者抓住近代中國轉(zhuǎn)型過程中思想與文化被賦予特殊意義的現(xiàn)象,探討其中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的獨特性及復(fù)雜性,揭示近代讀書人對變革、進(jìn)步的渴求,以及如何通過思想文化革命影響促進(jìn)社會政治革命。作者注意到,中國近代發(fā)生的國變背后總是伴隨著影響更加深遠(yuǎn)的天下之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與政治秩序解體相伴而來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機(jī)”。而這種文化危機(jī)或曰政教危機(jī),恰恰又是知識群體被革命裹脅的社會政治土壤。
瞿駿把目光投向傳統(tǒng)精英群體之外的青年學(xué)生和地方讀書人,以及轉(zhuǎn)型時代“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得以展開的重要載體——教科書,細(xì)致入微地描述了在新舊交替、“交互激蕩”的歷史情境中,他們是如何塑造思想文化革命的形態(tài),同時又被思想文化革命所塑造的。在這里,瞿駿獨辟蹊徑,以“再歷史化”、“去熟悉化”的勇氣和態(tài)度,深入探究歷史的多種可能性,進(jìn)而呈現(xiàn)出近現(xiàn)代中國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多重復(fù)雜的面相。進(jìn)一步拓展了討論空間,使得長期以來被遮蔽的歷史真相從已經(jīng)板結(jié)的歷史敘事中脫穎而出。我們看到,歷史不再是一條線性發(fā)展的不歸路,而是一幕山重水復(fù)、柳暗花明、歧路亡羊、曲徑通幽、方生方死、福禍相倚的活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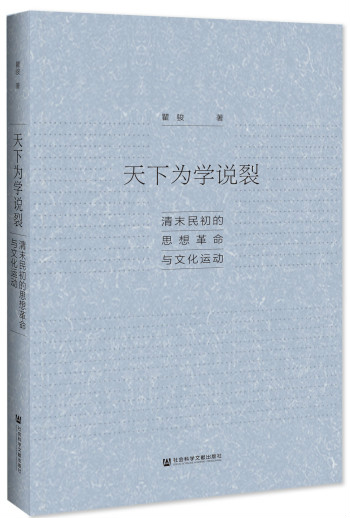
傳統(tǒng)的家國天下解體之后,中國面臨著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被列強(qiáng)瓜分的危險亦始終存在著,在此之際,國族認(rèn)同就顯得尤為緊迫。這個問題許紀(jì)霖、瞿駿在書中都有所論及,而黃興濤對“中華民族”這一觀念的深入考察,更觸及到清末民國以來中國人現(xiàn)代族群認(rèn)同及其觀念變遷史的核心部分。在他的《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一書中,關(guān)于中華民族作為“自覺的民族實體”的研究,尤為引人矚目,恰如鄧正來先生所言:“這一研究對于中華民族的獨立、統(tǒng)一和復(fù)興具有重要的意義。”這里所謂“自覺”,源于費孝通先生在上個世紀(jì)80年代提出的“從’自在’到‘自覺’的中華民族認(rèn)識論”。他將中華民族分述為“自覺的民族實體”和“自在的民族實體”,前者指近百年來民族自覺對中華民族的“重塑”或“再造”,而后者則指幾千年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實際狀況。
黃興濤的研究固然有對前現(xiàn)代民族融合史的梳理,但重點還在探討從長期歷史積淀而形成的“自在”的中國人,到清末民國“自覺”的中華民族的演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觀念的、邏輯的、思辨的,更是實踐的。也就是說,黃興濤更注重先知先覺的精英觀念是如何轉(zhuǎn)化為普通民眾的社會文化意識,并為這種社會文化意識所制約、所規(guī)范的?在這個上下互動的過程中,那些政黨意識形態(tài)、政治符號和文化媒介又是怎樣發(fā)揮作用的?由此想到瞿駿的《天下為學(xué)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他對清末“排滿”思潮的梳理,以及對轉(zhuǎn)型時代學(xué)生生活史的論述,對清末江浙地方讀書人和新文化運動中“失語者”的研究,對清末民國教科書多重面相的悉心發(fā)掘,在一定意義上,是將這個過程形象化和具體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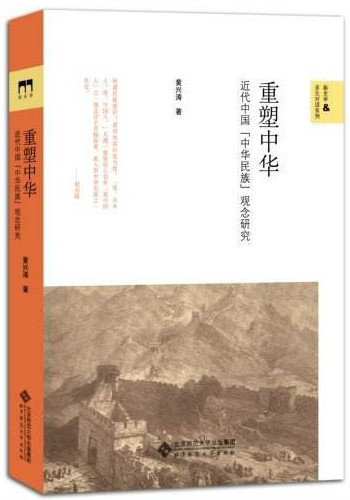
陸建德的《海潮大聲起木鐸》涉及清末民初兩個時有爭議的人物,即林紓與嚴(yán)復(fù)。前者不認(rèn)可辛亥革命,自稱“清室遺民”,新文化運動中,激烈反對以白話替代古文,對鄙薄綱常名教的言行亦深惡痛絕,時人稱作頑固的封建復(fù)古派的代表。后者晚年趨于保守,列籌安會六君子之名,人稱“帝制余孽”。但他們二人都是清末最早的新知識、新文化的輸入者,可謂功莫大焉。無論林譯小說,還是嚴(yán)譯學(xué)術(shù)名著,都曾深刻地影響清末的思想文化革命,是溝通中外文化的翻譯家和思想家。而以往加諸他們的“惡謚”,其實是有失公正、公道的。
陸先生所作,不止于要為二公翻案,而是提出了評判晚清人物的重要原則,即“應(yīng)該意識到他們身邊的濃霧”,這樣,或許可以“同情地理解林紓和嚴(yán)復(fù)的難處”。陸先生既以研究歐美文學(xué)為志業(yè),對“西學(xué)”在中國的傳播與吸收,固有不同于庸常的認(rèn)識。他特別提醒人們注意,林紓與嚴(yán)復(fù)的“西學(xué)”,是以“本國文化傳統(tǒng)有著深刻反省意識”為基礎(chǔ)的,所以,“絕非個別自以為明了世界大勢、心醉于幾個抽象名詞而又’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新派人物能比”。亦或如嚴(yán)復(fù)所言:“其人雖皆具新識,然皆游于舊法之中,行檢一無可議。”觀其言,或是夫子自道,而加諸林紓亦未嘗不可。他們行走在歷史的迷霧之中,未能預(yù)見到政治上的成敗,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的譯述和漸進(jìn)改良思想,為轉(zhuǎn)型時代貢獻(xiàn)全然不同于激進(jìn)的西學(xué)“譊譊者”的新價值。

與林紓和嚴(yán)復(fù)相比,袁世凱更是一個被傳統(tǒng)歷史敘事嚴(yán)重污名化的人物。他為了達(dá)到稱帝之目的而向日本出賣國權(quán),在主流歷史敘事中似乎已成定論。但唐啟華的研究則表明,歷史真相也許并非如此。他在《洪憲帝制外交》一書中,充分利用了目前所能找到的中、日、英外交檔案及三方研究成果,為研究洪憲帝制提供了不同于中國內(nèi)部視角的外部視角,使得突破百年來史料與詮釋框架的限制成為可能。
在這里,唐啟華不僅著眼于洪憲帝制時期的中國外交,而且深入探討了歐戰(zhàn)前期遠(yuǎn)東的國際關(guān)系,以及英、日、美、俄等國與中國外交之互動,將中國外交與東亞及全球外交聯(lián)結(jié),探討洪憲帝制外交的復(fù)雜面向及其相互影響,從而使洪憲帝制的歷史敘事超越革命史觀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之束縛,回歸到歷史學(xué)術(shù)本身。依據(jù)史實而不是想象,唐啟華得出結(jié)論:中國在“二十一條”交涉中外交失敗之說,不能成立;而袁世凱以出賣國權(quán)換取日本對稱帝的支持一說,應(yīng)該只是當(dāng)年革命黨的政治宣傳。事實上,洪憲帝制失敗,正與日本軍方及右翼勢力的全力倒袁有所關(guān)聯(lián)。這或許也是“再歷史化”、“去熟悉化”的例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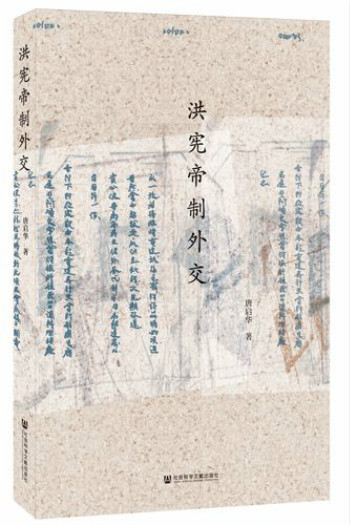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