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讀她的小說,即使最虛無的心也會愛上生活
小說《鯊齒蟹》選自新世代海外華語文學作家王梆的首部小說集《假裝在西貢》,講述了一個青春與謀生混雜的水涔涔的南方故事,銀春發廊的一對雙生姐妹花,她們野蠻生長、苦中求樂,絕不甘心生命像商品一樣被交易。開篇第一段“我媽死了,我自由了”,乍泄出令人心驚的叛逆。。

紅紅將濕漉漉的緊身裙一把扒下來,扔到臉盤里,然后俯身沖著賴在草席上的我說,我媽死了,我自由了!那是1991年的盛夏,天空突然被人割開了一個大口。暴雨不斷,建筑廢料堵住了下水道,洪水迅速地把廣州,那個正在淪陷為工地的城市囚禁了起來。腐爛的西瓜和瘟雞從上流漂到下流,尿黃色的積水底下,蠕動著形形色色的蟲豸。
當紅紅發梢上的雨水滴到我的臉上時,我正在一場關于鯊齒蟹的記憶里游蕩著。鯊齒蟹、鱷魚、山魈……在所有這些和洪水相關的食人獸中,我最怕的就是鯊齒蟹了。鯊齒蟹不像鱷魚,它們體積微小,繁殖速度像球菌一樣,顏色和洪水一致。吃人后腳跟時,小卒先上,趁人不備,冷不丁啄出一粒腳皮肉,血滲出后形成咸腥的紅色信號,大軍們再追風逐電,聚攏而來,不出半炷香,被抬出水面的人就只剩半截腳了。泡過水的皮肉煞白無血,看起來就像被削掉了軟骨的豬蹄。每次發大水,街道變成河流,小孩們全副出動,把桌子掀翻過來當船筏,踢水皮球,或者用曬衣桿打水仗,只有我縮在陽臺的欄桿后面,疑神疑鬼,心神不定,和此刻這個“鳥樣子”一模一樣。

我媽死了,我不干了,我自由了!紅紅扳著我的肩膀,把我立了起來,水淋淋的頭發粘了我一臉,這下我才徹底蘇醒過來。
在銀春發廊里,我是小雞,紅紅是我的母雞,老板娘是老鷹。紅紅自由了,那我怎么辦?
從我進入銀春發廊的第一天起,老板娘就一直處心積慮地要把我趕走。有天晚上,她突然披上了一條嶄新的花披肩,說要帶我去白宮喝夜茶。老板娘平日連包子都不肯多施舍半個,怎會披條披肩就變得綽闊起來?果然,一個顱骨凸出,重心不穩的印尼老華僑,從滿堂蒸籠包的白氣里冒了出來。
這妹仔太小,放在我們那里不合適,你帶她走啦,她可以在你的士多店里,幫你賣賣嘢……吃飽喝足,老板娘邊用牙簽捅著滿嘴的牙縫,邊漫不經心地對印尼老華僑說道。冇問題,冇問題,我會看住她的啦!為了使兩邊的口輪匝肌對稱,印尼老華僑費勁地笑著。
我才不要去,我說。你不去?哪個養你啊?你要不要去站街?你要站街,我就給你留下……老板娘說。我不要站街!我噘起嘴。不站?那你帶她走,即刻就帶她走,快快催催,免得阿Sir找上門來說我窩藏幼女!老板娘朝印尼老華僑努了努嘴。

那我的行李呢?我的衣服呢?還沒有告訴紅紅……我央求。紅你媽個黑!她邊有得閑理你啊?她客那么多。你咁中意她,你同她做啊,你們一對姊妹花,不如一起做雙飛,我同你們四六開,好唔好?老板娘抬高嗓門。哎呀,你對小妹仔說這些干什么?印尼老華僑黏在老板娘的肥臂上,伸手夾起一只鳳爪,話咗她也不明嘛!放心啦,我會好好照顧你的,你那些舊衣服扔掉就算啦,我已經買咗新的給你,牙膏牙擦,都是新的……
上了最后一班開往黃埔港的渡輪,我就開始后悔,但顯然已經來不及了。渡輪很小,甲板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每個人的臉看上去都是陰沉沉的。當船頭淌過污濁的珠江水,朝一個更寬廣更昏暗的航向邁進時,印尼老華僑用他那夾著卷煙的黃手指,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掐了一下——隔著二十多年的時光,那塊被掐陷的部位仍保留著清晰的身體記憶,就像讓一個有潔癖的人去淘糞,指縫里因此便染上了糞便的記憶一樣。

我想給紅紅打電話,渡輪上似乎沒有電話亭。我想起來紅紅也沒有電話,只有老板娘有電話,白天象征性地擱在收銀臺上,打烊后鎖在柜臺里。那一年我只有十五歲,十五歲的肉聯廠職工的女兒,全副身家不到十元五角錢,胳膊被人拽得死死的,目光所到之處只有一頂頂破草帽、一只只破網兜和一雙雙沾滿污泥的腳。黑色的波濤正一刻不停地吞吐著白色的唾沫,紅紅,我的母雞你在哪?
一進士多店,我就開始琢磨逃跑的路徑。士多店是間青磚房,看起來年代久遠。汽水、廉價香煙和水果糖堆在售賣架上,角落里一把竹梯通往閣樓。閣樓昏暗狹窄,站起來得貓腰。沒有床,雜木地板上平行地鋪著兩張麻將竹席,一張看起來汗跡斑斑,另一張攤放著一條加小碼的喬其紗連衣裙,價碼還沒剪掉。一股被風干的鼠尸味,侵蝕著樓閣里的所有物件,從吃剩半碟的粉餃,到掛在墻上的夏威夷花襯衫,再到衣櫥上的蛤蟆太陽鏡和假牙……
閣樓沒有廁所,只有一只搪瓷尿壺,大便得去后院。后院是個天井,四周是與士多店相連的青磚樓,模樣看起來像家茶餐廳。夜深人靜,通往茶餐廳的鐵門已經鎖上了。兩只潲水桶發著惡臭,一塊巨大的砧板橫在院子中央,上面的內臟和積血足以喂飽一個蒼蠅王國。不遠處有一口八角井,井邊爬滿了濕漉漉的水蛇。用磚砌成凹形,頂上鋪了半塊石棉瓦的,就是印尼老華僑的蹲廁了。發現了這個藏身之地后,我就二話不說,拉上門鉤,將自己反鎖了起來,任憑印尼老華僑如何軟硬兼施,任憑蚊蟲如何叮咬,也無動于衷。那晚的月亮銳不可當,像一把剃刀。我從少女變成了貓頭鷹,睜著橙黃色的眼睛,站在陡峭的巖石上,隔著一大碗漆黑的江水,向紅紅頻頻發射著求救信號。

凌晨時分,我終于聽到了腳步聲,接著是霹靂哐啷的鐵門聲,然后是茶餐廳勤雜工疲憊不堪的哈欠聲……我沖出茅廁,穿過鐵門,邁過茶餐廳的門檻,不顧一切地往碼頭上跑去。當第一班渡輪移近時,紅紅果然屹立在甲板上,像一個信心十足的狙擊手,無情地掃射著對岸的一切。她那發育未全的乳房,被清晨的陽光鍍上了一層結實的金。從那以后,紅紅和我做回了銀春發廊的一對姊妹花。
我的鋪蓋緊挨著紅紅的鋪蓋,盡管我倆在一起睡的機會實在不多。有時候我起床時,紅紅還沒有回來。不過只要她在,我們就有說不完的話。她如果天亮前下班,還會附在我的耳邊說早安。
我們的臥室是一個熱鬧非凡的通鋪。到處都堆滿了發亮的裙子,廉價香水,開裂的粉餅以及莫名其妙的笑話。每到清晨,姐姐們就會從黑夜的內臟里鉆回來,脫掉香臭難辨的連衣裙,敞開汗淋淋的肚皮和大腿,四腳朝天地倒下去,仿佛重力并不存在,身后的空隙布滿了繁星。有個姐姐,長得不算好看,但只要笑一笑就能讓自己光芒閃耀,有段時間她一躺下就笑,仿佛草席上藏了兩個胳肢鬼。連體人姬無雙被砍成兩半,各自平躺在地上時,也曾竊笑不已,但那是武俠故事,現實中能笑著躺下的人實在不多。紅紅私下告訴我,那小騷精愛上了一個修手表的,也是外地人。能笑趕緊笑吧,以后有得他倆哭,紅紅說。一個月總有三到四天,紅紅鬧痛經。不開工,她便把雙腳架在低矮的窗臺上,說抬高腳踝對痛經有利。騎樓上只有硬邦邦的雜木地板,象征性地掃了幾抹朱紅色的劣質油漆,幾床破棉胎和幾張褪色的草席,占據著紅蟻、蛀蟲和蟑螂的領地。

窗臺底下放著一只蚊香式電爐,我們用它來開小灶。紅紅的小灶總是雞蛋。雞蛋用處可多了,紅紅說,能補血、補鈣,還能用來穿耳洞。紅紅總想趕在天氣還不算太熱的時候,給自己穿上耳洞,盡管她每次穿完都發炎。這是我媽傳給我的祖傳秘方,不會有錯,她說,邊遞給我一只在生姜里消過毒的銀耳針。這秘方聽起來似乎也有些科學道理,蛋煮熟后,連殼帶皮在耳垂上滾,待耳垂通紅發熱,像水煮過的橡木那樣綿軟而麻木時,就用針扎進去,只要足夠狠,一針便可通過,若稍有遲疑,就得補針……說起來很輕松,紅紅卻總是疼得淚腺充盈。
那還要不要穿另一邊?我問,手中的銀耳針微微顫抖。當然要啊,不然好運通!紅紅說,看你這個屎樣,針拿來,我自己穿!然后紅紅就會咬著厚嘴唇,對著鏡子,掉著眼淚,扯著紅腫的耳垂,沖著已經長合的洞眼,一針又一針地扎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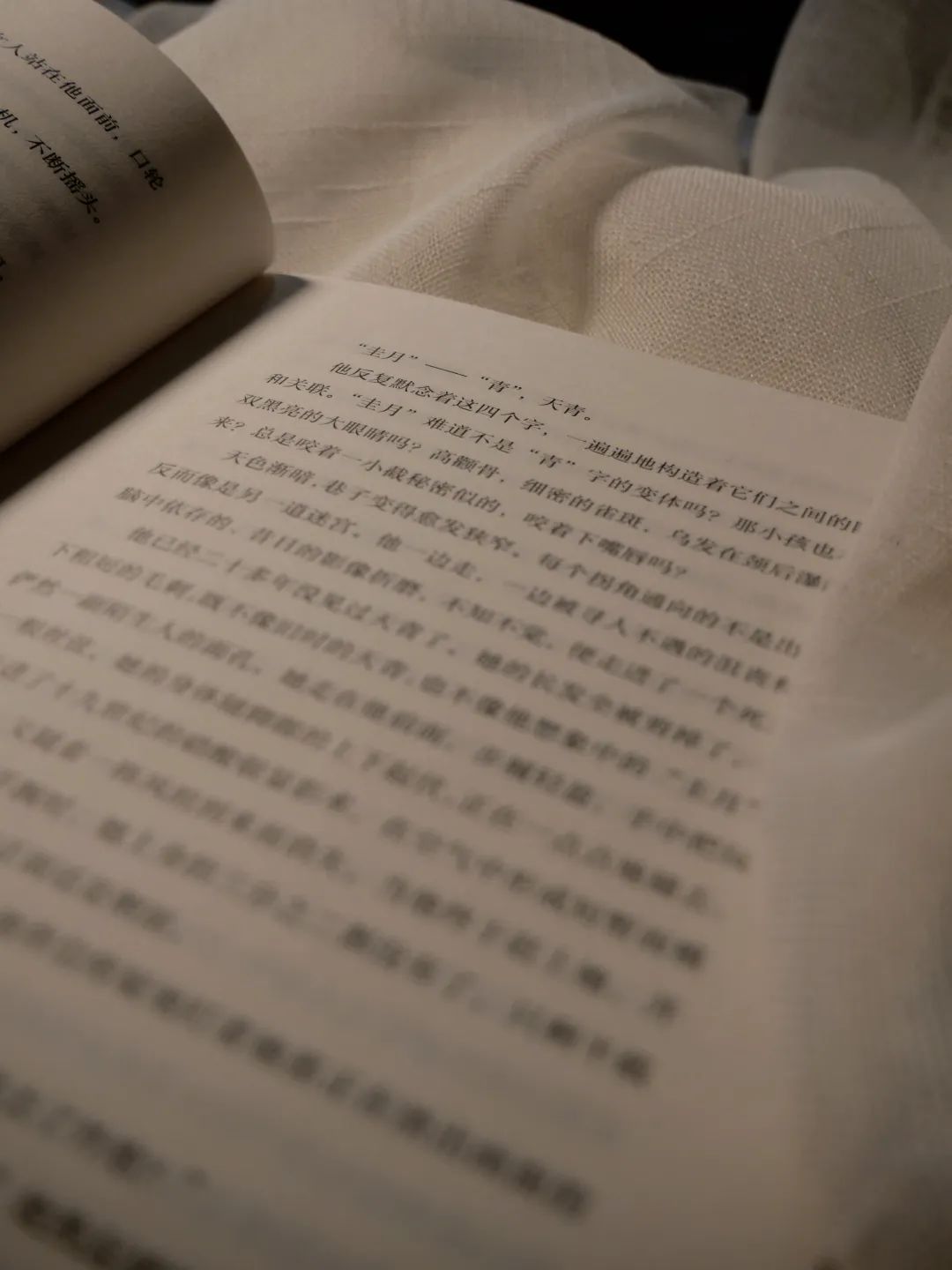
紅紅原本在東莞一家賣假飄柔的地下工廠里做工。一年前,紅紅的母親患了子宮癌,家里的豬全賣了,也不夠換一次化療錢。紅紅不單要付哥哥在技校的伙食費,還要給母親治病,于是她便給自己定下了每天只吃三個榨菜包的規定,結果在一次痛經后染上了突發性貧血,被兩個工頭一頭一尾地抬到了廠區外的一棟爛尾樓里。到了廣州之后,她就變成了“紅紅”。十九歲的紅紅長著一對丹鳳眼,嘴唇豐厚倔強,不開工的時候,喜歡在長發上插一朵絹紅花,對著鏡子沒完沒了地端詳自己。
紅紅和姐姐們開工的地方,在銀春發廊附近一棟隱蔽的出租屋里。一樓住著兩個馬仔,房間里終日煙熏火燎。二樓住著一個老太,據說是老板娘的表姨,也是絕世煙鬼,吸煙時手指上還戴著兩只慈禧太后式的銅指套。三樓是七個板間。板間不算太小,能塞進一張雙人席夢思和一個床頭柜,床頭柜上還有一臺不時骨折的鉆石牌風扇。有時候發廊里沒閑手,我就得把剛剃完頭的客人領到那里去。抱著一沓干硬的舊毛巾,走過煙雨凄迷的小巷,眺望著不知誰家的溫馨燈火,看墻頭上的牽牛花和衣而臥,用眼神問候路燈下偶爾閃過的折耳貓……整個路程既寧靜,又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感,一點都不像去逛窯子,反倒像去墓地憑吊。

當然大多數時候,我哪也去不了,只能待在發廊里,一邊做這做那,一邊斜眼望著那些脖子上滿是碎頭屑,不安地打著腳震,把煙抽得像蚊子吸血似的男人。他們會用怎樣的方式對待紅紅呢?聽說這條街上有個姐姐,意外咬傷了某個客人,就被打掉了半排牙齒。
你別瞎操心,客人們不都是這樣的啦……紅紅邊涂著胭脂,邊從鏡中拋出一個媚眼,他們只是腦袋不夠靈光,靈光的人就不會上我們這了。金子又不是沙子,能隨便淘?搬一箱馬賽克才兩塊錢,月底還得把錢寄回老家給老婆小孩花,夠可憐的,就這樣還要從飯盅里慳下十塊二十塊,滿足一下皮膚饑渴……
立夏一過,陽光便如同砂紙,被它摩擦之后,就會掉一層皮。烈陽隱去便是暴雨,伴隨著攝氏三十四度的高溫,城市變成了一只巨大的蒸籠,蒸籠里是一具具黏糊的皮肉和一條條遲鈍的神經。那幾天,紅紅經常夢見她做工的床底下有只手,時不時地,尤其在客人快要“到”的時候,就冷不防伸上來,一把掐住她的咽喉,往死里掐,不死就不罷休。一個月以后,紅紅就接到了她母親去世的消息。紅紅說,那一定是她母親的手,要她置于死地而后生。

你自由了,我怎么辦?我用指甲摳著地板,一籌莫展。暴雨稍歇,暮色漸涼,我們一整天都沒吃什么東西。經過漫長的討論,紅紅得出了我應該回家的結論,因為我是“什么時候都可以回家的”,在這里待著只是“尚有可浪費的青春”。她說的也許對,我從印尼老華僑那逃跑回來以后,老板娘不但繼續不付我的工錢,連我的伙食也從一日包三餐降到了一日兩餐,即午飯和晚飯。午飯通常要等到下午三點左右才有得吃,因為那是姐姐們睡醒之后的時間。每天早上,我都得七點起床,打掃碎發,擦亮鏡子和剃刀,洗凈姐姐們的衣服,澆富貴竹,開門迎客,為客人洗頭,為理發師遞發卷,澆冷燙精,冒著暴雨或烈陽走三里路到那一區最便宜的農貿市場買菜。回來后一毛五分地和老板娘報賬,完了還得用累得幾乎報廢的雙腳,撐著合頁形的身板淘米做飯……要不是紅紅常給我五毛錢讓我去換包子,我早就餓死了。
你回去吧,好好聽你爸媽的話,別和他們吵了,不值得。上個補習班,再進一家好學校,說不定以后還能考上大學。你比我幸運一萬倍你知道嗎?你不像我,我已經是不干凈的人了,有家也回不了了……紅紅一邊喋喋不休地為我打著氣,一邊翻來覆去地查看我的掌紋,試圖找出她認為我定有作為的證據。

至于我么,我已經想好啦,先去深圳看看。有個老鄉在那里的一個染織廠,掙的錢肯定沒這多,但干凈!紅紅邊說邊微微昂起了腦袋,一刻鐘前凝聚在空中的烏云,仿佛真的被一塊巨大的抹布擦掉了。
我終于答應回家,紅紅如釋重負。她掏出鑰匙,打開行李箱,取出一件厚棉襖,用剪刀拆開衣角的縫線,在棉絮里掏出了幾捆皮筋扎好的錢。她把錢攤開,分成兩份,將其中的一份裝進一只繡著粉荷的針線包,然后連同針線包一起送給了我。那是五元和十元一張的、分量十足的八十元。接著我們趁老板娘不在,到火車站分別買了次日回家的硬座票。
在回程的公共汽車上,紅紅突然決定要請我去看花燈。滿世界都是洪水,哪有花燈?我遲疑。紅紅堅信工人文化宮有個花燈展,她說她在一張包著富貴竹的報紙上看到的,我們便在中途下了車。水還沒退,天色卻已經有些暗了。我們蹚著鯊齒蟹色的臟水穿街過巷,我感覺自己的后腳跟在漸漸變涼,仿佛被吸入了一具行尸的口腔。

工人文化宮是五十年代在一座孔子學堂的遺址上建造的,學堂里陰魂不見,只剩幾只金魚在深褐色的池子里有氣無力地吐著氣泡。我們繞過漂浮在水面的殘枝敗葉,踏上了總算有點干燥的大理石臺階。那里大門緊閉,別說花燈,就連屋檐下掛著的兩只紅燈籠,也被狂風吹癟了。這里真涼快啊!紅紅噘起她的厚嘴唇,干吹了幾聲口哨,絲毫沒有悔意。啊,好久沒吹過風了,我們去找風口吧,這附近肯定有風口的!她是那種只要起了念,就馬上要付諸實踐的人。我們總算在兩堵高墻之間找到了一個風口,那里的風很大,在風口里我第一次向紅紅袒露了我對鯊齒蟹的恐懼。那怪物有多大?紅紅問。我將兩片指甲尖夾在一起打了個比畫。紅紅笑了,別怕,針孔那么點大的玩意,有啥好怕的?它敢咬你,你就一針扎死它!
風更大了,我們的頭發被吹成了兩條又長又黑的“斜坡”。
乜嘢?奔喪后就不回來了?聽紅紅說要走,老板娘的表情顯得極富戲劇性,不過似乎很快也就接受了。你想要返你的身份證?得啊,不過,你點都要做完今晚再走吧?老板娘說。我媽死了!我媽等著在火化前見我一面呢,你也是當媽的,你他媽的不懂嗎?紅紅說。倆人為此僵持不下,紅紅氣得全身的骨頭都要暴出來了,在發廊里大吼大叫起來。你今晚不放我走,我就把這里一把火燒了!我說得到做得到!紅紅邊說邊抓起了掛在鏡子上的一把假發,舉到了吱吱燃燒的香爐上。老板娘每逢初一十五必為菩薩燒香,為此,還專門請人定做了一座齊人高的紅木神龕。
啊呀呀,你同我過不去就算啦,你和菩薩過不去做乜嘢?快點將它拿開,燒咗神龕,在陰間有得你受的……老板娘邊勸,邊悄悄拿起電話,看樣子是要叫她的馬仔。紅紅用眼神暗示我去搶電話,我一不做二不休,把端在手中的一碗滾燙的稀飯,朝電話上潑去。哇有冇搞錯啊,你們……你們兩個食碗面反碗底……老板娘帶著哭腔干號起來。這場斗爭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終于以三個馬仔把我和紅紅分別用人字拖狂扁一頓而告終。

今晚是禮拜六,一定很多客,人死不能復生,有錢總是要賺的,賺咗錢俾你媽買靚香燒,我話得不對咩?又話了,你在我這里住咗這么久,好吃好穿的我都省省的,留一份給你,我幾時有虧待過你?你要這個賤人留下,老板娘斜瞥了我一眼,繼續往下說,我都應承咗你,不是咩?就當我求你啦,好唔好?!你做完今晚,我明日一早就還你身份證……老板娘邊說,邊抱著紅紅那青一塊紫一塊的胳膊,不停地抹清涼膏。
紅紅終于妥協了。她爬上閣樓,將身體埋入一堆眼看就要扔掉的纖維里。開工之前,她吸了半包香煙,然后才跟在一個肥胖的客人后面,走出了銀春發廊的門。今晚早點睡啊,不要等我,別耽誤了明天上午的火車。如果明天早上我還沒有回來,你就自己走吧,給你的錢收好了?她鼓起腮幫,吹了吹我的肩膀,上面有些香灰。

那朵她沒戴走的娟紅花,被窗外的霓虹燈照射著,一會變藍,一會變紫,在濃重的陰影里,怎么看都不再像一朵花。
那天夜里,我仿佛躺在不斷浸水的甲板上,一身大汗卻感覺冰涼刺骨。將近凌晨的時候,我被阿Sir的吆喝聲震醒了,他們以老板娘“涉嫌教唆未成年少女賣淫罪”為由,用手銬把我銬上,將我作為“人證”帶回了派出所。在遭到我的堅決否認后,一位女警把我關進了一間單人牢房。牢房里只有一張鐵床和一條毛巾被,飛蛾們在一盞瓦數極低的吊燈底下亡命撲飛。進了牢房之后,我就開始大哭不止,用手銬上的鐵鏈反復擊打床架,上廁所也不停歇,電棍唬嚇也不頂用。我哭了兩天兩夜,直到我那在肉聯廠殺豬的父親突然像一堵肉泥做的墻,面色鐵青地出現在牢房門口為止。為了對他那隱藏在體內的突發性暴力有所準備,我擦干眼淚,拉直四肢,豎起耳朵,拾起渙散的視線,準備隨時還擊。然而我的父親并沒有像往常一樣揚起頭,相反,他一反常態,情緒穩定。在離我不遠處的一炷蚊香旁,我看到他用配合的食指,在一沓文件的最下方,按下了一個紅印,然后我們就被帶上了一輛警車。大約兩個小時之后,車開到了一棟辦公大樓底下。父親問是否可以讓他留在外面,請示獲準。父親掏出香煙,殷勤地給司機遞了上去。
脫掉褲子,內褲也要脫,在一間寬敞明亮的體檢室里,女醫生下著命令。鐵床是一只折疊的金屬托架,上面鋪著一塊白布,我把瑟瑟發抖的上半身放了上去。他整天就知道吃,才94.9厘米,卻已經有17.8千克了!女醫生說,邊戴上一副乳白色的橡膠手套。17.8千克挺正常的,不用擔心,女助手說……對話聲漸漸遠去,我聽到陰道內傳來薄冰碎裂的聲音,我感到自己體積正在不斷縮小,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流質在我的身邊蕩漾開來,黏稠,溫暖,比洪水還要漫無邊際,比落日還要昏黃。二十多年來,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返這片神秘的水域,我告訴自己不要害怕,就算水里真有鯊齒蟹,針孔那么點大的玩意,沒啥好怕的。想到這里,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變成了鯨魚,擺動著巨大的尾鰭,奮力向前游去。

▲ 王梆,旅英作家,著有非虛構作品集《貧窮的質感》、電影文集《映城志》、法文版漫畫故事《伢三》以及數本短篇小說繪本集。作品散見于《花城》《單讀》等,入選美國“文字無邊界”文學網站,2016年秋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故事新編”中國當代藝術展等。曾入圍2019年第四屆華語青年作家獎,收獲文學排行榜。英國國家寫作中心2022才華扶梯計劃唯一非母語入選者。
文字丨選自《假裝在西貢》,王梆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8月
圖片丨選自電影《燕尾蝶》(1996)劇照
編輯丨曼旎
原標題:《讀她的小說,即使最虛無的心也會愛上生活》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