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爾德的毒舌金句,誰還沒引用過幾句呢?
1881年,王爾德坐船橫跨大洋來到美利堅,進關的時候驕傲地對海關官員說:“我沒有什么可以申報的,除了我的才華。”當然這只是一段野史,但即便是偽造,這句話也完全符合王爾德的身份、性格和氣質,因為王爾德就是如此恃才傲物的毒舌天才。
在王爾德短短46年的傳奇人生里,他留下了無數意味深長的“金句”,其中不少是通過作品中人物對話表達出來的。王爾德筆下的某些金句甚至曾在牛津某報紙上刊行過,為的是以“對年輕人有用的格言和哲理”,給讀者提供生活上的指導。
在意大利作家翁貝托·埃科看來,王爾德利用警句作為元素來寫作小說、喜劇或者隨筆的作者,所展現的是一種“修辭上難以克制的樂趣”,而不是真的想用來訓誡或警示世人,他認為王爾德創作這些警句,除了批評與諷刺當時的社會風氣,其“目的是文體上的高貴與優雅”。
本文選摘自《文學這回事》,經出版社授權推送。
王爾德:悖論與警句
文 | 翁貝托·埃科
什么是警句?什么是格言?
沒有什么東西比警句(aforisma)更難定義的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源自希臘文的字眼從原始涵義“為獻祭而儲備的東西”演變成“定義,諺語,簡潔語句”。這也正是希波克拉底所言。因此,根據津加雷利字典的定義,警句是“表達一個生活準則或是哲理的簡短格言(massima)”。
那么,警句和格言這兩個詞有何不同?并沒有不同,只是長短稍有出入而已。
很少有事情能夠安慰我們,因為很少有事情能令我們傷悲。(帕斯卡《思想錄》,136)
假設我們沒有任何缺點,我們也不會如此興味盎然地去注意別人的缺點。(拉羅什富科《箴言錄》,31)
記憶是我們永遠隨身攜帶的私密日記。(王爾德《不可兒戲》)
某些我自己沒有的思想,或者我自己無法形諸文字的思想,我便從語言里汲取。(卡爾·克勞斯《論家及世界》)
以上句子可以稱為格言或者警句,但是接下來的段落就是格言,因為太長,所以稱為警句就不合適了:
貴族身份為人大開方便之門,凡是擁有它的,從十八歲開始便處處吃得開、名聲響亮且受人尊敬,換成別人,得要等到五十歲才有此等待遇。這是毫不費力就賺得三十年。(帕斯卡《思想錄》,322)
沒有哪位藝術家會有倫理道德上的顧忌。對一位藝術家而言,任何形式的倫理道德上的顧忌都是不可寬恕的矯揉造作。(王爾德《道林·格雷的畫像》前言)
在意大利文版的王爾德《箴言集》中,亞歷克斯·法爾宗將警句定義成形式簡短的格言,此外,他還認為它的內涵該表現出智慧。明確這項特色之后,他還觀察到現今的趨勢,警句旨在凸顯優雅和生動,卻犧牲掉了它原本在表達真理上的果斷立場。當然,不管是格言還是警句,其真理觀和發表者的意圖是息息相關的:如果說一個警句表示一個真理,那就意味著它傳達出了發表者認為是真理的東西,希望聽到的人能夠認同。可是一般來講,格言或警句并不一定要展現高人一等的智慧或故意冒犯挑戰一般人的意見:格言警句旨在從一般意見看來似乎淺薄的地方加以深入,以期修正那個意見,讓它更趨完善。

《輕松自由》
這里舉出尚福爾的一句格言:“最富的人就是儉省的人,最窮的人就是吝嗇的人。”(《格言與沉思》)這句話精妙的地方在于:一般人都認為儉省的人通常是一個不隨便浪費自己有限資源的人,對于自己日常的生活開銷都會精打細算,而所謂吝嗇的人通常指那些累積財富超過自己日常所需的人。這句格言對應的正是上述一般人的看法,所謂“富裕”是從資源的角度來看,而“窮困”,除了倫理道德上的意義之外,還加上一層對于需求的滿足。
一旦修辭上的游戲厘清,那么格言也就不再是為了反駁一般意見,而是證實并強化它。
相反地,當警句和一般人的意見起強烈沖突的時候,乍看之下顯得悖情違理,令人難以接受,而且大家需要先將那修辭夸大的形式明智地減縮才能撥云見日,明白這種警句其實包藏了很難讓人接受的真理,于是,我們進入了悖論(paradoxos)的畛域。
從詞源學的角度考查,所謂的悖論是由parà、ten和doxan等字所構成,意即“超越一般意見”。因此,這一字詞最早系指一個偏離大眾輿論的斷言,令人感到怪異、陌生、出乎意料,而這正是中世紀作家圣伊西多爾使用該詞時所要表達的概念。如果這一令人驚訝的斷言得以被人看出負載著真理價值,那也是要在漫長的時間道路上行進后才能成功。
因此,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有個在當時被視為謬誤的悖論,時至今日卻成為真理。請參考《哈姆雷特》:
奧菲莉亞:殿下是什么意思?
哈姆雷特:如果你貞潔又美麗,那么最好不要讓你的貞潔跟美麗來往。
奧菲莉亞:殿下,美麗跟貞潔相交,不是再好不過嗎?
哈姆雷特:嗯,的確,因為美麗可使貞潔變成淫蕩,貞潔卻未必能使美麗受自己的感化;這句話從前是怪誕之談,可如今已經得到證實了。
悖論的邏輯是自成一格的,都是一些大家既無法證明真偽,內部又自相矛盾的斷言,比方說謊的人提出的悖論。不過漸漸地,超越修辭的意義也嶄露頭角了,因為這個緣故,我還是執著于巴塔利亞《意大利語大辭典》里的定義:
命題、概念、陳述、結論、雋語,通常以純理論式或道德倫理式的論述呈現,并和廣泛傳播或者大家都接受的意見相左,同時也和經驗及常識相悖,更和它涉及的信仰系統,和大家認為天經地義的知識元素大相徑庭。(而且通常不具備真理的力量,只是被貶到詭辯的層次,它被幻想出來只是因為有人性好偏激或喜愛賣弄辯論技巧,但在似乎不合邏輯和不協調的形式里它也有可能包含一絲主觀上的效力,而這種效力最后會扎穩根基,對抗那些不加鑒別就人云亦云的人,對抗他們的無知以及過于簡單的判斷。)
因此,警句似乎是被視為真相的格言,它有意呈現雋言妙語的外貌,而悖論所顯露出來的原始面目似乎是謬誤的,只不過經聽者的一番深思熟慮之后,便能明白它揭示了作者認為是對的東西。悖論在輿論的期待以及它那驚世駭俗的形式之間存有一道鴻溝,因此讓人覺得機智。
文學史上多的是警句,但說到悖論就寥寥無幾了。警句的藝術是容易的(諺語也可視為警句:滾石不生苔;狗吠比狗咬更糟糕),而悖論的藝術是艱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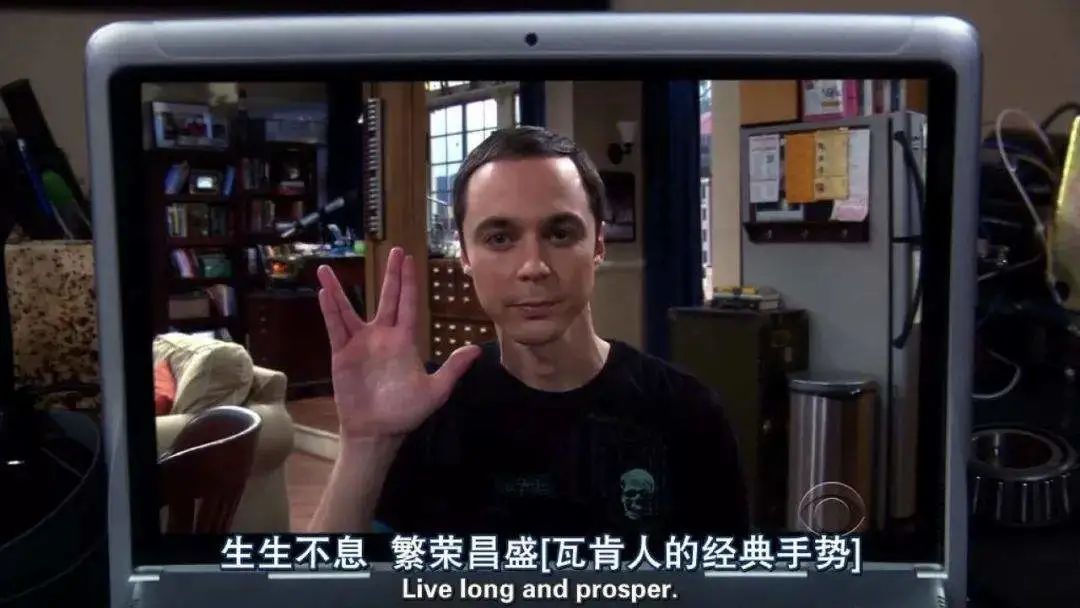
《生活大爆炸》
不久以前我研究過一位警句大師:皮提格里黎。下面列出他最精彩的作品;其中幾條極富哲理,所斷定的真理卻和一般人的意見南轅北轍:
美食家:上過高中的廚師。
語法:教你語言卻妨礙你說出口的復雜工具。
片段:對于不知如何構思書寫一整本書的作者而言不啻是天賜良方。
酗酒病:如此美的一個醫學詞匯,看了真叫肚里的酒蟲蠢蠢欲動。
以下幾條比較像是經推定的真理,肯定了某個道德倫理上的決定或行為準則:
我明白為什么要吻麻風病人,但不了解為什么要握笨蛋的手。
寬容對待對不起你的人,因為你不知道他人腦中有多少對付你的方法。
不過,在《反胡扯詞典》(Dizionario antiballistico)中,作者收集了諺語、格言和警句,有些是他編的,有些則是借別人的。他無論如何要人家始終注意到他的犬儒式人生觀,也就直言不諱自己粗俗不風雅的意見,而且讓人感受到警句的文字游戲可以狡詐到什么程度:
既然大家彼此在交心的道路上努力,我就承認自己助長了讀者性格里小流氓的那一面。讓我把話說明白些:如果街上有人廝打起來或者發生交通事故,就會不知從哪里冒出一個家伙,試著用雨傘去打吵嘴雙方中的一位,挨打的通常是那個開車的。這個沒人認識的小流氓因此便可以痛快地發泄原先隱藏起來的怒氣。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書里面:一個思想未成形或未組織的讀者,一旦讓他找到一個饒富滋味、閃耀奪目或者具爆炸性的句子,便與這個句子談起戀愛,不但接納它,而且還以驚嘆號收尾來評論它,比如“真棒!”、“沒錯!”等等,仿佛這個句子在他腦際縈繞已久,仿佛這個句子凝聚了他思考模式的精華、他哲學體系的膏腴。他“采取了立場”,就像墨索里尼經常掛在嘴邊的一樣。我為讀者提供一個采取立場的機會,卻不用他們深入文學的叢林里。
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警句就是用別出心裁的方法表達人盡皆知的道理。如果把風琴稱為“鋼琴受夠了塵世的生活所以投身教會去了”,那只是把一項我們已經知曉而且也相信的事情用一個強有力的意象重新陳述一遍,換句話說,風琴是教堂樂器。把酒精稱為“一種害死活人卻可保護死人的液體”,并無法讓我們更進一步理解酗酒的害處或是發生在解剖學博物館里的事。
當皮提格里黎讓他那本《波特的實驗》(Esperimento di Pott)里的主人翁說出“有智慧的女人是一種我們偶爾會碰上的不正常現象,好比白子、左撇子和陰陽人或者生來具有十多只手指或腳趾的人”這句話時,他正好投一九二九年男性讀者(或許也包括女性讀者)所好,說出他們想聽的話。
皮提格里黎在評論自己對于警句的見解時,也曾告訴我們,有許多精彩的警句反過來讀也不會減損絲毫的威力。讓我們看看幾個皮提格里黎在《詞典》里所提出來的反讀實例:
許多人輕視財富,卻很少人知道如何慷慨運用財富。
許多人知道如何慷慨運用財富,卻很少人輕視它。
我們根據自己的懼怕而做出允諾,并且根據我們心存的希望去保守這些允諾。
我們根據自己的希望而做出允諾,并且根據我們心存的懼怕去保守這些允諾。
歷史除了是自由的遭遇以外,其余什么都不是。
自由除了是歷史的遭遇以外,其余什么都不是。
幸福存在于事物中,而不是我們的品位里。
幸福存在于我們的品位中,而不是事物里。
除此之外,他還臚列了一張由不同作者寫出的格言。這些格言看起來彼此矛盾,可是似乎各自代表了為人接受的真理:
只有出于樂觀,人才會欺騙自己。(埃爾維厄)
怯懦的人通常比充滿自信的人更善于欺騙。(里瓦羅爾)
假設國王是哲學家,而哲學家是國王,人民會更快樂。(普魯塔克)
如果哪天我準備懲罰某個行省,就會派哲學家去統治那里的人。(腓特烈二世)
我建議使用“可置換警句”一詞來稱呼那些可以反讀的警句。一個可置換警句是它的作者嘗試賣弄機智時所經歷的不舒服感覺,換句話說,只要這個警句顯得妙趣橫生,那么“它的相反說法也為真理”這項事實就不會干擾到它了。可是悖論正是大家習以為常觀點的顛倒,它呈現了一個不能被接受的世界,只會引起抗拒和排斥。然而,如果我們花費心思去了解它,那么它就產生知識;到最后,它看起來妙趣橫生,那是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它是對的。可置換警句包含的真理是片面的,而且經常要等到反讀以后,才透露出真理來,它的兩種陳述沒有一個是真的:只因為它詼諧雋永,所以看起來似乎是真的。
悖論并不是“世界秩序大亂”的古典命題,因為后者是機械式地預言一個怪象紛呈的世界:動物像人一樣說話而人卻發出動物叫聲,魚飛上天而鳥游水中,猴子主持彌撒而主教從一棵樹跳到另一棵樹。后者并沒有遵循任何邏輯,而是將一些雜七雜八或者不可能的事拼湊起來,只是嘉年華式的文字游戲罷了。
如果要踏入悖論的境界,那么邏輯便不可或缺,而且它還只能局限于世界的某個部分。一位波斯人來到巴黎,他描述的法國,好比一位巴黎人描述的波斯。它的效果是悖論式的,因為它逼著讀者超越根深蒂固的成見去觀照大家習以為常的事物。

《打工狂想曲》
區分什么是悖論,什么又是可置換警句的一種方法,就是試試看能否將悖論加以反讀。皮提格里黎援引特里斯坦·貝爾納對于“猶太復國運動”一詞的定義并且將它稍加改動,當然,這個定義只在以色列建國之前方才適用:猶太人某甲向猶太人某乙借錢,為的是要送猶太人某丙回巴勒斯坦。
我們試試能否將它反讀:沒有辦法。這說明了:正確的形式包含了真理,或者至少是特里斯坦·貝爾納要我們當真理加以接受的觀念。
下面幾條是卡爾·克勞斯筆下有名的悖論。我沒有嘗試將這幾條加以反讀,因為只要稍加檢視便知道絕不可能。這些語句都和一般人的觀念背道而馳,所包藏的真理并不是因襲傳統的,而且不能為了表達相反的真理而拿它們來扭曲加工。
當警方將一項丑聞結案時,丑聞才真正開始。
為達到完美,她缺少的只是一個缺陷。
處女情結就是想要玷污處女的人的情結。獸奸非法,而屠宰合法。可是大家難道沒注意到,屠宰這一行為可能就是虐待狂的殺戮?
懲罰只能用來威嚇那些根本無意犯罪的人。
地球上有一個黑暗的所在,探險者從那里被派遣到世界上來。
小孩愛扮軍人。這倒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可是為什么軍人蠻干起來竟像小孩?
精神科醫師總是能診斷出精神病,因為住院之后,那些病人總會出現焦躁的行為。
當然,即使是克勞斯本人也會掉進可置換警句的陷阱里,下面我就舉出幾個輕而易舉便可加以反駁,也就是說,可以被反讀的例子(反讀部分當然是我加上去的):
沒有任何事物比起女人的膚淺更深不可測。
沒有任何事物比起女人的深不可測更膚淺。
寧可原諒丑腳也不原諒丑襪!
寧可原諒丑襪也不原諒丑腳!
有些女人不算漂亮,但有美的韻味。
有些女人算是漂亮,但無美的韻味。
超人是想象凡人時的早熟理想。
凡人是想象超人時的早熟理想。
百分之百的女人為了享樂而欺騙,其他女人為了欺騙而享樂。
百分之百的女人為了欺騙而享樂,其他女人為了享樂而欺騙。
僅有的幾條似乎絕無辦法反讀的悖論則出自斯坦尼斯瓦夫·耶日·雷克之手。下面我摘錄了他在《紛亂思緒》里的幾句妙語:
唉,要是我們能借睡眠分期抵償死亡的債該有多好!
今晚我夢見現實,還好我醒了過來,真險!
芝麻開門,我要出去!
要是美洲沒有擋住哥倫布的探險路徑,天曉得他會發現什么。
恐怖就是在言論鉗制上涂上蜂蜜。
蝦死了才會變紅。對犧牲者而言,這是多么具鑒戒性的精妙比喻!
如果你要摧毀塑像,那么請保留基座,終有一天它又能夠派上用場。
他非常謙遜地認為自己是個只愛涂涂寫寫的人,事實上他是個專門告密的人。
他娶來知識卻無法使她懷孕。
火刑的柴堆不能照亮黑暗。
不是拿破侖也可以死在圣赫勒拿島。
他們彼此緊緊相擁,以至于再也沒有空間留給他們的感情。
他在頭上撲粉,但用的是犧牲者的骨灰。
我夢見弗洛伊德,這是什么意思?
若和侏儒來往,你的脊椎從此再也直不起來。
他有的是誠心善意,只是很少用到。
即便靜默不語,他還是犯了拼字錯誤。
我坦誠自己對雷克的作品愛不釋手,不過雞蛋里挑骨頭,我還是找到一條可以反讀的例子:
表達意見前要思考!
思考前要表達意見!
王爾德的警句格言
現在讓我們把話題轉到奧斯卡·王爾德身上。縱觀他在作品中到處留下的警句格言,我們可能要認清,這位自命不凡的紈绔作家其實只要能讓布爾喬亞階級覺得驚世駭俗,他才不去細分什么是警句、可置換警句或是悖論。相反的,他有足夠勇氣讓雋言妙語披上警句的外衣,除了那股機智勁兒,剩下的就變成低俗可鄙的陳腐言語,或者至少對于維多利亞時期的布爾喬亞階級和貴族階級只是老生常談。
不過,如果我們對這種文類稍加鉆研就可知道,利用警句作為元素來寫作小說、喜劇或者隨筆的作者,終究是個振聾發聵的悖論大家或者只是收集機智文字的老手而已。另外,如果屬于前者,那么他的功力又到何種程度?當然,我的經驗也還處于摸索階段,希望能鼓勵哪個學者出來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最好還能寫成一篇論文。

這里我先列舉一些貨真價實的悖論,我敢保證誰都無法加以反讀(在明理機智的人眼中,充其量只能說它沒有意義,或是錯誤的格言):
生命不過是蹩腳的一刻鐘,人在其中能夠品嘗短暫的暢美時光。
自私并不意味著按照我們的意愿生活,而是要求他人也按照我們愿意的方式生活。
或許比較謹慎的做法是先認定人性本惡,直到哪天你發現人其實是有道德的才終止這種想法。只是今天此舉需要很深入的檢視方能成功。(我們注意到,這個陳述是可以反讀的:“或許比較謹慎的做法是先認定人性本善,直到哪天你發現人其實是無惡不作的才終止這種想法。”然而結果顯然是錯誤的。)
在這世上贏得勝利的盡是丑人和傻子。他們好整以暇地、以沾沾自喜的態度環顧四周。假如他們從來不曾嘗過勝利的滋味,至少失敗的苦楚也會饒過他們。
一個敏感易受傷害的人經常借口腳底長了厚繭,毫不客氣地踩在別人的腳趾上。
當人無法再繼續學習時,就開始教別人了。
每當別人同意我的看法時,我總是感覺自己的看法似乎是不對的。
一位大家喜歡談論的人總是很有魅力。于是后來大家就下結論,說他這個人一定具有什么給人好感的東西。
今天,所有的偉人都有門徒,可是為這些偉人執筆作傳的一定都是猶大。
我能抗拒一切,唯獨不能抗拒誘惑。
謊言是他人的真理。
我們對歷史的唯一責任就是重新改寫歷史。
如果要讓一個理念成為必然不可的真理,那么甘心為它赴死還不足夠。
所謂家庭就是一堆令人生厭的人,渾然不知如何去過生活,而碰到死亡的時刻連一點微知略覺都沒有。
然而,那些似乎很容易就可加以反讀的警句格言就多得不可勝數(當然,反讀是我加上去的):
生活是世界上最罕見的東西。絕大多數的人只是活著,沒有別的。
活著是世界上最罕見的東西。絕大多數的人只是生活,沒有別的。
凡是看出靈魂和肉體之間有所不同的人,即便只是看出一絲不同,那他兩者都不能擁有。
凡是看不出靈魂和肉體有任何一絲不同的人,那他兩者都不能擁有。
生命是件太重要的事,以至于無法嚴肅談論它。
生命是件不太重要的事,以至于無法嚴肅談論它。
世人可以簡單分成兩類:相信難以置信事物的人,比方普羅大眾,以及創造似不可信事物的人,像我就是。
世人可以簡單分成兩類:相信似不可信事物的人,比方普羅大眾,以及創造難以置信事物的人,像我就是。/世人可以簡單分成兩類:創造似不可信事物的人,比方普羅大眾,以及相信難以置信事物的人,像我就是。
中庸之道是個要命的東西。沒有什么會比過度更容易成功。
過度是個要命的東西,沒有什么會比中庸之道更容易成功。
好的決定總有一個命數——它們總是下得太早。
好的決定總有一個命數——它們總是下得太晚。/壞的決定總有一個命數——它們總是下在適當的時刻。
所謂不成熟就是完美。
所謂不成熟就是不完美。/所謂完美就是不成熟。/所謂不完美就是成熟。
無知好比一種外國來的稀罕水果,要是你伸手去碰,它的花朵便會掉盡。
知識好比一種外國來的稀罕水果,要是你伸手去碰,它的花朵便會掉盡。
鉆研藝術愈深,對自然就愈沒興趣。
鉆研自然愈深,對藝術就愈沒興趣。
繪畫里夕陽的風景已經退出流行了。在前代藝術家中最后對它詮釋得最好的人是透納。今天如果崇拜他,那么就是鄉下人的品位了。
繪畫里夕陽的風景再度具有現代感。在前代藝術家中最后對它詮釋得最好的人是透納。今天如果崇拜他,那么就是最時髦的品位了。
美揭示一切,因為它什么也不表達。
美什么也不揭示,因為它表達一切。
所有的已婚男人只能吸引自己的妻子,而且經常連她都不動心。
所有的已婚男人只能吸引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人,而且經常連她也會動心。
就時髦這件事本身而言,就是嘗試宣稱美的絕對現代性。
就時髦這件事本身而言,就是嘗試宣稱美的絕對非現代性。
交際談天的內容應該觸及一切但什么也不必深入。
交際談天不該觸及一切但需深入每件事。
我喜歡言不及義。那是唯一我知道一切的領域。
我喜歡言之有物。那是唯一我一無所知的領域。
只有一流的文體大師才能達到晦澀的境界。
只有一流的文體大師才能達到清晰的境界。
任誰都能創造歷史。可是只有一個偉大人物能夠將它記錄下來。
任誰都能記錄歷史。可是只有一個偉大人物能夠創造歷史。
今天再也沒有什么可資區別英國和美國。當然,語言是個例外。
今天一切事物都可用來區別英國和美國。當然,語言是個例外。
只有現代的東西才會退出流行。
只有退出流行的東西才具現代感。
如果我們對于奧斯卡·王爾德的評斷到此為止,那未免不夠厚道。他是紈绔子弟這個形象的化身,可是布呂梅爾爵士或者他中意的德塞森特都是他的先驅。他在悖論(包藏激怒人的真理)、警句(包藏可接受的真理)和可置換警句(對真理無所謂的心靈機智游戲)三者之間不做任何區分。此外,王爾德對于藝術的諸多理念也容許他采取這種立場,既然一個警句不應該把實用性、真理或者道德教訓當作目的。它的目的是文體上的高貴與優雅。
話說回來,這種追求美學及文體風格上的激怒人的挑釁并不足以令王爾德脫罪,因為他將混淆悖論式的挑釁以及自命不凡的招搖。不過,大家知道,根據他的原則,他鋃鐺入獄的原因本來不應該是因為他愛上道格拉斯爵士,而是因為他給后者寄發了內容如下的一封信:“真是奇跡,你那兩片如玫瑰花瓣般紅艷的嘴唇,不論唱歌或是激吻都同樣合用。”而在法庭上受審的時候,他還辯稱這封信只是文體風格的練習,好比一首散文式的十四行詩。
《道林·格雷的畫像》被倫敦法院的法官認定是傷風敗俗的作品,理由當然蠢得可以,不過,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盡管這本小說具有引人入勝之處,它在本質上卻模仿了巴爾扎克的《驢皮記》并且大篇幅抄襲于斯曼的《逆流》(盡管他只是間接承認這個事實)。普拉茲也注意到,《道林·格雷的畫像》受到洛蘭《福卡斯先生》的影響甚巨,甚至王爾德作為審美專家所提出的諸多格言里有一條:“沒有哪種罪是粗鄙的,但粗鄙卻是罪”,明顯出自波德萊爾筆下一句雋語:“紈绔子弟從不會是粗鄙的人。假設他犯了罪,也許還不至于身敗名裂。不過,如果這罪的緣起是個瑣屑無趣的動機,那么對他的榮譽所造成的損害就無法彌補了。”

《道林·格雷》
然而,如同亞歷克斯·法爾宗在上述那本意大利文版王爾德警句里所評論的:一般來講,如果一位作家從來沒有寫過警句集,那么很難搜集他散見在各作品里的警句,也就是說,我們在這類作家的作品中所看到的警句,并不是寫來只為展現光芒、架空在語境之外的,而是插在一件敘事或者戲劇作品里面,因此也就是在特定語境里由某某人說出口的。
比方,如果作者借由筆下一個荒誕可笑的人物說出一個警句,那么這個警句的力量會因此而削弱嗎?
在《不可兒戲》里,巴拉克諾太太說過:“失去父親或母親可以視為不幸,但若失去雙親那就像是疏忽!”這是一句格言嗎?所以有人推測,王爾德根本不相信他自己所寫出來的格言警句,乃至那些最享盛名的悖論。而這推測倒也合情合理:他在乎的,是描寫一個欣賞這類格言警句的社會罷了。
對此,他本人也證實過。讓我們檢視《不可兒戲》里的一段對話:
亞吉能:“所有的女人都會變成她母親的樣子。這是女人的悲劇。這種事絕不會發生在男人身上,這是男人的悲劇。”
杰克:“你認為這句話言之有理?”
亞吉能:“不管如何,至少措辭精彩絕頂,這和人家對于我們文明生活所做的評論一樣真實。”
因此,王爾德也許不應該被看成生活糜爛的作家,而是當時社會風氣的批評家和諷刺者。至于他活在這種社會風氣里是否悠游自在,那是另一回事,而這也是他的不幸。
讓我們重讀《道林·格雷的畫像》。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言警句總是由像沃登爵士這類淺薄而且自命不凡的角色說出來的。王爾德并不是在做保證,提供我們可以安身立命的準則。
沃登以發表雋言妙語的方式說出一系列的陳詞濫調,都是當時社會里流行的話(正因如此,王爾德的讀者讀起這些錯的悖論反而覺得津津有味):
某主教到了八十歲,嘴里念叨的還是他十八歲時人家教他說的那一套話。只要人們將之隱藏起來,那么最平庸、最俗不可耐的事也會變得饒富滋味。婚姻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讓男女雙方把幻滅的生活變得絕對不可或缺(可是在下文中,沃登爵士又說婚姻真正的缺點在于它讓人變成利他主義者)。我并不相信百分之十的勞動階級生活還過得去。今天,要是誰心碎了,那么好幾家出版社就有生意了。年輕人在情感上想要忠實但忠實不了,而老頭子想出軌,卻無計可施。我不缺錢,得自己付賬的人才有需要,而我從不自己付賬。我不認為英國國內需要任何改變,氣候是唯一的例外。若要重拾青春,那就重蹈覆轍,干些當年的蠢事。男人因為倦怠而娶妻,而女人則出于好奇而嫁人。女人沒有一個是天才,她們不過是裝飾用的性別。女人的現實精神令人衷心折服:我們老是忘了觸及結婚這個話題,而她們一定會提醒我們。當我們快樂的時候,總是善良有德,可是當我們善良有德的時候卻未必快樂。窮人最大的不幸在于,除了自我犧牲什么都做不了。(天曉得沃登爵士是否讀過《共產黨宣言》,因此知道“無產階級除了身上的鎖鏈之外再無長物”的道理?)寧可愛人也不要被愛,被愛實在無聊。每次我們造就一件事跡就會多攬一個敵人,如果你想普受歡迎那就得平庸一些。鄉下人誰都能夠善良有德,因為那里沒有誘惑。婚姻生活就是一種習慣。犯罪是下層社會的專利品,犯罪之于他們好比藝術之于我們,都是一種睥睨同儕的陶醉感覺。謀殺說什么都是錯的:我們也許不應該做出一些茶余飯后無法拿來談論的事……
上述言語盡是些堆砌起來的陳腐言語,這一大篇之所以顯得出色僅僅因為是連珠炮似的傾巢而出而已。(就好像枚舉的手法,最平庸的字眼只因為跟同樣平庸的字眼并陳排列,只因為這種并陳排列如此怪誕不協調,所以令人心生驚嘆。)沃登爵士有種特殊天分,那就是將拿來包巧克力都不配的陳腐言語揀選出來,然后加以顛倒:
所謂自然而不造作其實只是一種姿態,而且是我所知道最教人惱怒的姿態。
擺脫誘惑的唯一方法就是屈從于它。
我酷嗜簡單的樂趣,那是復雜的人最后的避風港。
我所要的只有訊息;不是有用的訊息,而是無用的訊息。
我敢打賭,美國人從來不開玩笑。多嚇人哪!
我同情一切,除了受苦一事。
今天,大多數人……發現下面這件事的時候都太晚了:我們過去所犯的錯其實才是我們永遠不會懊悔的事。
我想對我來說結婚是極不可能的。我在愛里涉足太深(這是道林說的,不過他的思想受他老師的影響甚巨)。
親愛的孩子,膚淺的人說穿了就是一輩子只愛一次的人。
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慘事總包藏一件窮極猥瑣的事。
不論何時,當一個人做出一件徹底愚蠢的事時,背后的動機總是高尚的。
當你不得不和別人和諧共處的時候,總會出現不和諧的事。
男人可以和隨便哪個女人愉快相處,一旦他不再愛她的時候。
我和行動不會失和,我只在面對字詞的時候才有那種現象。
善良有德比不上俊俏美麗。
丑陋是七大美德其中一項。
所有飛短流長的根基都確定是不道德的。
今天我還會懷著敬意傾聽他們意見的人,都是年紀比我小很多的人。
只有膚淺的心靈才拒絕以貌取人。
時下大家待人處事的方法實在恐怖:他們在你背后說話反對你,而反對的事都是絕對而且完全屬實的。
一時興起隨便玩玩和作為一生志向的興趣有點不同,前者比后者持續的時間稍微長一點。
我們必須承認,沃登爵士口中的確說出過幾條挺有效的悖論,比方:
我選擇俊美的人當朋友,聲譽良好的人我才和他們來往,但是只有聰明的人才配當我的敵人。
年輕的美國女子善于隱藏自己的父母,一如年輕的英國女子善于隱藏自己的過去。
慈善家喪失掉對人道的意識,這是他們的共同特點。
我可以忍受粗暴的力量,可是粗暴的理智是完全無法忍受的。
我喜歡瓦格納的音樂勝過其他人的音樂,因為它夠大聲,大到就算有人整場都在說話,其他人也聽不到。
我們談戀愛的時候,起先是欺騙自己,最后總是變成欺騙別人。
所謂的極度熱忱是那些無所事事者的專利特權。
女人喚醒我們想要成就杰作的欲望,但總又妨礙我們達到那個境界。
稱貓為貓的人有義務豢養一只。
然后,沃登爵士的悖論通常不過是可置換警句而已(當然,下面的反讀部分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現代生活中唯一存留的顏色便是罪惡。
現代生活中唯一存留的顏色便是美德。
我們以太過嚴肅的態度看待人道主義,這是世界的原罪。假設山頂洞人懂得笑,那么歷史將會截然不同。
我們以不夠嚴肅的態度看待人道主義,這是世界的原罪。假設山頂洞人可以忍住不笑,那么歷史將會截然不同。
女人代表物質戰勝精神,而男人代表精神戰勝道德。
男人代表物質戰勝精神,而女人代表精神戰勝道德。
事實上,《道林·格雷的畫像》呈現了沃登爵士的自命不凡和愚蠢可笑,同時也對此加以批判。談到他,另一位角色會說:“親愛的……別聽他胡謅。他從不說正經話的。”談到他,作者則說:“他玩弄這個意念,并且任性地變本加厲;沃登將它丟到空中,把它加以轉換;沃登放它逃跑,接著又將它捕捉回來;他讓這個意念發出奇幻的誘人閃光,并且讓它背上悖論的雙翼……他發現道林·格雷將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于是知道,在聽眾當中有一位他想吸引住的人,而這個人的心性使他的機智鋒利起來,為他的想象力增添色彩。”
沃登爵士對于自認為是悖論的說法沾沾自喜,可是他認識的人卻不頂看重悖論:
“人家說好的美國人要死的時候會去巴黎。”托馬斯爵士笑著說道。這位大人擁有一個巨大的衣柜,里面盡是幽默的破舊衣物。
而男爵又補充道:“悖論肯定是有趣的,自成一格的有趣……”
艾斯金爵士的確說過:“所以那是一項悖論?我不這么認為。不過也許是。好吧,悖論之道乃是真理之道。為了檢驗真理,你得把它拿到繃緊的繩索上試試。唯有真理搖身一變成為走繩索的特技表演者時,我們才可以加以判斷。”艾斯金爵士沒有搞錯,可是沃登爵士(不相信任何東西)對于悖論用得十分儉省,而走上那條繃緊繩索上的只是陳詞濫調而不是什么真理。可是沃登爵士他在乎嗎?
“現在,我年輕的朋友,如果你容許我這樣稱呼你,我想請教你,剛才吃飯的時候你說的那些話自己全部都相信嗎?”
沃登爵士面帶微笑回道:“剛才說過什么我已忘得一干二凈。你從頭聽到尾難道發現有什么不道德的嗎?”
在《道林·格雷的畫像》中,真正不道德的事大家說得少但做得多。追根究底,道林會干那些事是因為朋友們用他們那些虛假的悖論誤導了他。到頭來,這是我們可以從這本小說里獲致的結論。可是甚至這項結論王爾德也予以否定,因為他在小說的序言里就已經表達清楚:“沒有哪個藝術家該有道德倫理上的顧忌。對任何一位真正的藝術家而言,一切倫理道德上的顧忌都是不可原諒的矯揉造作。”
而道林·格雷的風格則是對自命不凡、滑稽可笑人格的描述。因此,就算王爾德本人正是自己愛好炫耀犬儒主義的受害者,就算他老是喜歡用譏諷來宴饗讀者和觀眾,我們也不應該錯怪他,硬把他筆下的格言警句孤立起來,仿佛他想要而且能夠教導我們什么。

《道林·格雷》
當然,王爾德筆下某些最好的悖論曾在牛津某報紙上刊行過,為的是以“對年輕人有用的格言和哲理”,給讀者提供生活上的指導:
所謂的不道德只是那些正直清白人士發明出來的神話,為的是要解釋其他人散發出來的獨特吸引力。
當你證明宗教的真相時,宗教就非死不可。從死去的宗教灰燼里便生出科學。
有教養的人會反駁別人的話。有智慧的人會反駁他們自己的話。
野心是失敗者最后的避風港。
考試的時候,總是一些蠢蛋提出一些聰明人沒辦法回答的問題。
只有文體大師才懂得晦澀的藝術。
生命的首要義務在于盡可能地矯揉造作,至于第二項任務直到今天還未被發現。
真正發生的事其實一點也不重要。
人到了成熟的年紀,嚴肅反倒成為心智呆滯的標記。
如果你說真理,那么遲早有一天會被拆穿。
只有膚淺的人才會彼此成為知音。
可是王爾德在何種程度上把這些句子看作真正的知識?我們找到的答案有時是矛盾的、值得懷疑的:“我很少認為自己所寫的是真實的。”或者:“這是一句好玩的悖論,可是作為格言,我不能說自己賦予它什么太大的價值。”
另一方面,如果說“真理如果多過一個人相信,那就不再是真理了”,我們對王爾德筆下的真理要如何判定才能讓大家同意呢?既然他也說過,“在一切不重要的事情中,風格才是基本必要的,而非真誠,反過來說,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中,風格也是基本必要的,而非真誠”。
所以,不必要求王爾德嚴格區分悖論(真理)、警句(顯而易懂)或者可置換警句(虛假,或者缺乏真理上面的價值)。王爾德所展現的是一種“修辭上難以克制的樂趣”,而不是什么哲學上的熱忱。
或許唯一被王爾德發誓為真的格言警句只有一條,而實際上也是他畢生奉行不悖的:“所有的藝術都是徹底無用的。”
本文摘選自

《文學這回事》
作者:[意] 翁貝托·埃科
譯者:翁德明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原標題:《王爾德的毒舌金句,誰還沒引用過幾句呢?》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