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瞿駿:現代中國是“舊有”與“新來”的共存
淡淡煙盡活,疏密雨俱香。
鶴避何嫌緩?鳩呼未覺忙。
峰鬟添隱約,水面總文章。
玉氣浮時暖,珠痕滴處涼。
白描煩畫手,紅瘦助吟腸。
深護薔薇架,斜侵薜荔墻。
此中涵帝澤,豈僅賦山莊。
據說此詩曾得到曾國藩激賞,此試自然也成了俞樾最刻骨銘心之科場一役,他憑此成了“殿元”,遂命名自家書齋為“春在堂”。而此句在今天看來正成為一個巨大的隱喻,提示我們如何來看現代中國的歷史。

現代中國的歷史以“變”著稱,但如何“察變”卻是個到今日仍頗費人思量的問題。在既有的歷史敘述中我們多看到的是變化后了的模樣(當然是否真是這等模樣也依然可以存疑),而不太清楚變化的過程,更模糊的是變化之前的模樣。馬克思曾說:“人類創造著自己的歷史, 但是他們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 他們自己不能選擇創造的條件, 而是只能在直接面對的、已成事實的、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而我們恰恰對這些“直接面對的、已成事實的、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條件重視不夠,以致常常只看到了落花飄零于泥塵的“近代中國屈辱史”,而看不到“春天”究竟是在還是不在。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既有“春天”在與不在變得無關緊要(同時事實上依然還在),國人特別是讀書人的心目中徑自發展出了各自想象的“春天”與自以為的“春天”,并為了他們的想象和自以為而努力、奮斗,直到互博與廝殺。
于是,落花、新枝、仍在發展的卻不被人重視的既有“春天”和想象與自以為的未來“春天”就這樣在現代中國交織孱雜在了一起,這種因交織孱雜而互滲聯動的狀態既引發了現代中國歷史的困境,也開拓了現代中國歷史的新路。
從困境這一面來說,“落花飄零”即現代中國的“黑暗沉淪”確乎是每個中國人所經歷的生存狀態,但對于此種基本生存狀態的回應方式,各人卻有所不同,遂有中體西用、全盤西化、革命、改良、接續、調和等多種方案和主義。1935年陶希圣曾把中國之思想界分為三大陣營:“封建社會的回想的陣營,資本主義的模仿的壁壘和社會主義懸想的陣線”。陶氏的說法與前些年流行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三分法有一些相似,但所見更深,且其立場不在任何一方,因此也就不能引起各家“教主”的注意。在這些陣營、壁壘和陣線之中有堅持中國既有“春天”仍在且相當重要的,亦有篤信“落花飄零”之后必定會有另一個不同“春天”的,所以看上去針鋒相對,彼此對立,但其實它們大多都共享著同一個預設即張灝所說的“前瞻意識”。這種“前瞻意識”讓人對現實有強烈的沉淪感和疏離感,同時對縹緲的未來有無與倫比的熱切盼望。我將其稱為“一種近于無可救藥的未來樂觀主義”。

而之所以為“共享”,是因為不僅我們常稱之為“激進”的那些主義有這種“前瞻意識”。那些曾幾何時遭無數人激賞追捧的改良主義等也一樣有這樣的意識。這從廖平、康有為、梁啟超的著述中可以看得特別明白,其“革命”的目標之遠、范圍之廣和著力之深常令人感嘆和咂舌,讓人不禁要問,真的有改良派嗎?究竟誰是革命派?
現代中國的三重連續性困境困窘由此產生:第一,“新社會總是從舊社會脫胎而出的”,因此現代中國在如何“變”,總有事實上仍在的“春天”,同時又有讀書人想象中的和自以為的未來“春天”,這常使時人產生一個基本的困惑即如果自己“既不贊成復古,又不愿意完全把西洋的整個搬過來”該怎么辦?
第二,正因為有此困惑,從中體西用開始,到調和新舊與接續中西,再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之說,它們雖有各自立說的理據,但體現的都是一種以“新舊雜存”的方式來通向光明未來的嘗試。張東蓀對這種“新舊雜存”的思路做過有力的挑戰,其挑戰的意義并不僅止于指出所謂“新舊雜存”很多時候不過是新舊“共存”,更重要的是點明了無論是“雜存”還是“共存”大概都是長期性的,“新的增加一分,舊的便汰去一分”。這種對“時間”力量的期待會讓“前瞻意識”強烈的國人急迫而躁切。他們一方面覺得這樣的期待是一種惰性,是“人類本能上一種惡德,是人類文明進化上一種障礙”,另一方面則無奈地發現現實就是“新的不可以一天長大,舊的不可以立刻消滅”,走向光明未來的路漫漫又長遠。
第三,光明未來的遙遠而不可得,讓現代轉型中的部分讀書人一邊經歷著“落花飄零”的苦痛現實,一邊愈發覺得我們無法依靠“時間”的力量來再獲春天。郭沫若就警醒眾人說“不要以為春天去了,永遠會要再來”!因此他們從盼望新的春天轉換成了要主動創造新的春天,要一換而過的是種子,是土壤,甚至是氣候。在這樣的氛圍里,人們對那些正在養花以收獲春天之人的努力,常抱以有意忽視或無意忽略的態度,進而常常期盼調換一批更善于養花,乃至能呼風喚雨,創造春天之人。但歷史常常是不如意的,調換了未必更好(但也不一定更壞)。可是這樣一來,現代中國的歷史敘述卻演化成為一個循環路徑:在北洋追慕晚清,在國民黨統治下懷念北洋,時至今日則有晚清風度、北洋精神和民國范兒等林林總總的“舊日重現”,其實質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借助談歷史而對現實形成一種批判。但這些批判常常忽視了一個基本邏輯:若對舊日的懷念成為了循環和常態,那么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
從新路這一面來說,盡管近代中國有如此多的“困境”,但一個主權完整,疆域范圍基本保持,人口、民族依然眾多,文化有“一線之續”且有進一步復蘇跡象的中國仍在那里,這對一個經歷過“民族帝國主義”時代的古老國家來說實在是一個奇跡。
從這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奇跡里顯示出我們一定有新路可走。這條路不是簡單的“脫亞入歐”或者是成為被東西洋列強標準所規定的“民族國家”,因為歷史和現實已經說明“脫亞入歐”或是成為“民族國家”的短暫成功與長期虛妄,而且在追尋這虛妄的過程中,對自身和對它國都有無窮的流弊。中國的新路某種意義上正蘊藏在她的困境之中,即楊國強教授說的“中國人不能不背負著舊有的歷史以因應新來的震蕩”。
這句話洞穿了百多年的中國近代歷史!“不能不”表明“舊有”與“新來”的共存很多時候不是能夠人為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從世界上一切可能的事物中精心搜集起的一堆‘好的方面’,稍一碰撞就會化為灰燼”!這種共存是我們脫不開的“既存狀態”,其有弊亦有利,有危亦有機。對歷史長河來說,百年不過一瞬!仍在的“春天”一方面或許是造成我們無窮困惑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卻也是我們獲得生機的源泉。中國“舊有的歷史”在今日決不只是我們要卸之而后快的包袱。相反的,它能為我們已經貧乏至極的政治、社會想象提供鮮活的養分。康有為、錢穆、章太炎、陳嘉異、聞一多、陳寅恪等近代思想大家的論述尤能說明這一點。他們的價值既在今朝,更在未來。
1907年魯迅曾說:“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放在清末的歷史環境看,此說無疑比那些東京、上海之“仁人志士”跳踉輕發的高蹈言論深刻得多。但110年過去,中國似并未“沉淪”到底。在此前提下,我國本體自發究竟為何?中西交通傳來的是否僅是“新疫”?特別是二者究竟如何“交伐”,“交伐”產出何物等都仍是一個個“進行中的問題”,值得治史者用心去追尋與討論。這里我們不妨再讀一讀1919年時周作人寫下的一段話:“為鄰國人民的利益計,為本國人民的利益計,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信任能夠向和平正當的路走去。第三個師傅當能引導人類建造‘第三國土’——地上的天國,——實現人間的生活。”
這個尋找“和平正當”的路的過程是一場長程競賽,且經常不以成敗來論英雄!
(本文摘自《花落春仍在:近代中國的困窘和新路》自序,瞿駿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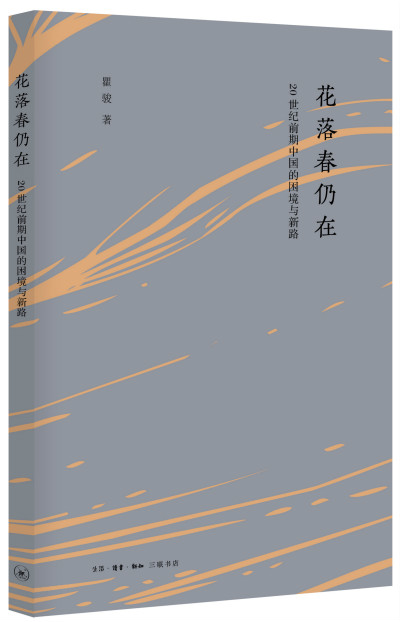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