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Beyond是所有跟青春有關的記憶
原創 南大出版社整理 群學書院

2022年6月10日,適逢黃家駒誕辰六十周年紀念日。南京大學出版社聯合先鋒書店,舉辦《海闊天空:Beyond與我的人生故事》新書全國首發式暨唱談沙龍。主編許金晶來到南京先鋒書店五臺山總店,與詩人黃梵、南京大學教師陸遠和獨立音樂人菠蘿大哥(本書作者之一)暢聊家駒與Beyond音樂在中國內地的巨大影響,并演唱了Beyond的代表性作品,以示紀念。以下是現場發言精選,由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整理并經各位發言者修訂確認后授權刊發,以饗讀者及廣大Beyond歌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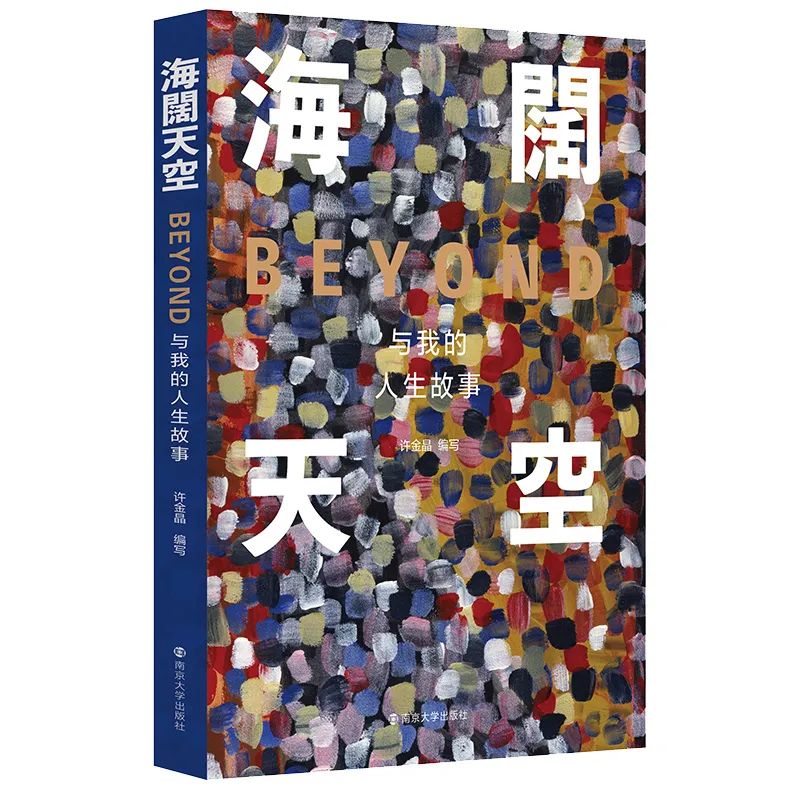
Beyond是所有跟青春有關的記憶
文字整理 | 南京大學出版社

活動現場
陸遠:在所有熱愛Beyond和黃家駒的聽眾心中,家駒和Beyond的生命永遠是年輕的,永遠停留在30歲。我們今天借由黃家駒這個華語樂壇符號來共同閱讀、探討一本別開生面的小書,同時也借用這樣一本小書共同追憶、探索一個時代和一代人的心靈歷程。我相信,這將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夜晚。既然是暢談沙龍,那么在開始之前,先讓我們伴隨著Beyond音樂,回顧一下三十多年前的一首至今依然動人心弦的老歌——《Amani》。
一位去世已將近30年的音樂人,為什么還受到這么多人的關注和喜愛?在今天這樣一個特別的日子,許金晶老師帶著他的這本《海闊天空》來到現場。這本書和市面上常見的那些講述黃家駒生平或Beyond經歷的書都不一樣,收錄的是跟你我一樣熱愛家駒,熱愛Beyond,熱愛那一段光輝歲月,熱愛海闊天空精神的普通樂迷的人生故事。所以,這本書很像一代人的心靈史。
通過家駒,通過Beyond,我們仿佛打開了一扇窗,又仿佛在我們面前放了一面鏡子,成為我們凝視自己、回憶自己,重新發現自己的一種符號。
首先我想請黃梵老師聊聊他眼中的Beyond及流行音樂。黃老師是這本書中第一篇文章的作者,也是非常資深的作家和詩人。

陸遠
黃梵:今天坐在臺上的都是音樂人士。關于音樂這一部分,我在書中已經講的比較詳細了。今天想談一談由家駒的音樂所牽扯出來的兩個很重要的文化問題。如果能認真思考這兩個問題,它可能會加深我們對其他音樂(也包括Beyond音樂)的理解。
第一個問題,流行與先鋒。我們大部分人對于流行與先鋒的理解,還持有一種古老的過時觀念:把它和階層聯系起來。實際上,流行與先鋒的關系在今天已經發生巨變。我們思考一下便知,流行依賴的是慣例。我聽到某種音樂的時候,能夠辨識出它,這中間憑借的就是慣例。因為一般的聽眾,沒有時間先去揣摩、去理解,然后再感受;大眾一定是先有感受,有共情,而只有慣例才能做到這一點。其實,慣例在它發生之初,也是以先鋒的面目出現的。比如說,柯南道爾寫的《福爾摩斯探案集》,永遠是一個私家偵探配一個愚蠢的警長,這一慣例沿襲了一百多年。可是它的源頭,是作家愛倫·坡寫的偵探小說,而這在愛倫·坡創作的那個時代是屬于先鋒的。所以我們知道,現在流行的慣例,它的源頭在當時都是先鋒,不過時間長了,它對我們來說慢慢變得熟悉,成了可以即時消費的慣例。

黃梵
我來舉一個日常的例子。比如說,各位到商店去買一套茶具。店員取一個茶壺,帶著四個杯子。如果是普通的四個杯子,我們都很熟悉,一看就明白是什么。但如果店員拿來一個茶壺,配四個微型的收音機放在一旁,這時你就瞢了,不知道這是要做什么。這就屬于先鋒了。
當然,流行與先鋒這兩種類型,不同階層的人對它們的理解有差別。精英更理解先鋒,大眾更理解流行。但是,現代社會所教養的人群,是要即時消費,還是要先鋒文化所要求的延時消費?大家捫心自問就會發現,我們既要即時消費,又要延時消費。換句不太中聽的話,人們既要享受共情,還要顯露格調。這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特點。也就是說,現代社會塑造的人群,是有史以來最貪婪的人群:我什么都要。雖說如此,我們也無法排斥、蔑視這一人群,因為我們便置身其中。
二戰以后,全世界的藝術都發生了改變。既要把流行的東西留住,又要把先鋒的東西留住。比如說,杜尚,掛杯子的瓶架,這是一個現成的商品,它代表流行、慣例。可是杜尚卻把瓶架當作藝術品,帶到美術館展覽。后來策展人一想,它做的有道理,確實是一個藝術品。為什么呢?他給瓶架取了一個名字,這就讓瓶架有了先鋒的意味。我這樣說,可能大家沒有感覺。再舉一個簡單一些的例子。大家拿一張照片,自己或親人的照片,如果光看這照片,就只是慣例。可如果在照片上寫一行字,那么這照片馬上就變了。如“生病之前”,這行字寫上之后,照片就被灌注了某種觀念。這就是先鋒:它不再是習慣意義上的照片,而已經成了藝術品。
店員放一個茶壺和四個微型收音機,這是先鋒。但是,當店員讓你把微型收音機的底朝天翻過來,你發現里邊是空的,可以倒茶用,你就恍然大悟,原來這是茶具。這個例子展示了流行和先鋒可以結合得密不可分。我們在博爾赫斯的小說中可以發現,這么學究氣的作品居然也使用偵探小說的構造。實際上,二戰以來的繪畫、音樂、小說、詩歌,都發生了類似的巨變。
我們就能理解,家駒當年何以有這樣的困惑。今天看來,他還有一些古典的意味:音樂—精英,不能向流行屈服。在那個年代,家駒做的是非常先驅的事情,他把流行和先鋒結合起來了,這也是二戰之后世界上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只不過香港這個地方商業氣氛太濃,家駒這樣做的時候內心是惶恐不安的。其實,他在做的時候已經引領了潮流。
所以,我覺得流行和先鋒的關系,可以按照上面講的這樣來看待。

黃梵(左)與陸遠
第二個問題,是音樂的抽象概括力。一開始我們放歌的時候,大家盯著歌詞看。陸遠也介紹了,這首歌是家駒去過非洲之后寫的。其實,我不太愿意大家把音樂文字化、說明化。因為音樂是我們所有藝術之中最寶貴的、極少數還保留抽象概括力的藝術門類;而其他藝術全部被形象化了。我們在聽音樂時,本來是看不到形象的,只是自行想象畫面。當音樂直接作用于我們的感官時,它激起的人的概括力是極強的。在所有藝術中,只有兩門藝術的概括力能達到這一程度:音樂和建筑。
我們在裝修房子的過程中會發現,所有的心情都可以放在裝修風格里。因為建筑的裝修風格,本身沒有一個具體的形象。音樂也是這樣。音樂的具體形象如何誕生?這有賴于歌詞、標題和各種各樣的暗示。我們不要把家駒的音樂變窄了,好像它就是寫非洲那一群苦難的人。它為什么不能代表其他國家人的苦難?為什么不能代表個人的苦難?所以說,音樂有它的抽象性,這是高度概括力的體現,一定不能把它變窄了。
也有人說,我聽完家駒的音樂,有一種獨特的感受,所以我是聽懂了家駒的,你們都不懂他。這一做法就把藝術變得很具象化。詩壇也有人做這樣的努力。上海有位詩人,想寫抽象詩。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不啻要讓文字離開字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這是不可能的。除非描繪形象,如此才能繞過理性,作用于人的感官。你想要文字繞開理性,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又不依賴具體的字義——只有一種情況,就和達達主義當年做過的一樣:用象聲詞寫詩,只有聲音,沒有意義。
要在文字里做這種抽象的實驗,是不會成功的。但是音樂天然地就能成功。我們應該保護音樂的這一強大力量,千萬不能把它徹底文字化、說明書化。我時常碰到一些發燒友,聽貝多芬或者別的人,覺得自己特別懂他(音樂的作者)。我有時就說,您把音樂聽得太懂了,反而就不懂了。真的是這樣。
再回到家駒的音樂。開場放《Amani》時,大家都聽了。我特別迷戀家駒的嗓音,他的那種顫音。到“三子時期”,其他人再來唱,雖然歌詞、旋律都一樣,但我們會發現,沒有了家駒的獨特顫音,感覺完全不一樣了。這相當于家駒在音樂中添入了自己獨有的、別人不可替代的部分。我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比如九十年代)聽到家駒的顫音時,特別能受到感染。因為它可以發生轉化,與我生命中的某一瞬間共情。在我心情不好時,他的顫音對我來說就是一種精神依托。現在,我再聽這個顫音時,感受就不一樣了,更多的是從審美的角度聽:如果沒有顫音,歌曲的力量就減少了一半。就像剛才菠蘿大哥講的,“四子時期”是不可替代的,因為貫注了家駒的嗓音和天賦。
詩歌可以被稱為文字里的音樂。我寫詩的時候,會聽里邊的音樂,就像是在作曲。有時也會想:作品的廣度、受眾范圍,和它本身具備的探索性之間,是不是也有一種矛盾?在我看來,這不是簡單地說,你的詩歌越是偏重探索,你的受眾就越少,你越是放棄探索,你的受眾就越多。

活動現場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當年,長三角地區有很多書商,每個書商都想出全世界最暢銷的書。可是人們發現,書商做了十本書,結果這十本都不暢銷。您怎么知道什么會暢銷?暢銷是要引起共鳴,但您怎么知道哪個東西會引起共鳴呢?
其實,每個人的精神取向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每個人只是在盡可能地探索自己。很多詩人、作家,他們首先探索自己的情感,在探索過程中歷練出一些東西,其中有些就具備了共情的基礎。由此,就產生了“10萬+”這樣的現象。但有一些產出,可能永遠只是冷僻的。依我看,家駒的音樂在香港走紅,不完全是他的音樂故意向流行靠攏造成的,這和香港當時的社會轉型有關系。商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公眾對于先鋒的東西就容易有了解的興味,就容易成為什么都要的貪婪人群。此時,人們渴望先鋒,需要先鋒的東西以大家熟悉的面貌出現。家駒他們正好做了這樣一些探索。我覺得,這是時代的際遇。有些時候,時代的際遇是不可模仿的。

活動現場
陸遠:臺上的另一位嘉賓菠蘿大哥,本職是一位醫生,他和許金晶一樣是“理科男”,他們喜愛黃家駒,喜愛Beyond,卻不僅僅是坐而論道,還做了很多原創音樂作品,也曾聯袂演出,他們還給自己的音樂組合起了個諢名,叫“江海一菠蘿”。前幾天我還問過菠蘿大哥,你在手術臺上會不會放Beyond音樂?菠蘿大哥也是這本書的受訪者之一。下面就請他從多重身份的角度談談對Beyond音樂的理解。
菠蘿大哥:我是第一次參與一本書的創作,現在又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1993年,我上初一,在《音樂畫報》上看到家駒逝世的消息。當時就和喜歡音樂的小伙伴一起花了九塊八,買到一張Beyond磁帶,《樂與怒》。在這張專輯里,我聽的第一首歌就是《我是憤怒》;而那個年代周圍人聽的多是《同桌的你》之類。后來,我也弄了一把吉他,跟隨其后。
突然聽到《我是憤怒》,怎么這歌和小虎隊不一樣,和四大天王也不太一樣,和校園民謠更不一樣,感覺很有力量。可能這一點也會遺傳,后來我兒子聽這張專輯時,最喜歡的也是《我是憤怒》。接著聽《情人》和《海闊天空》,印象都很深刻。我后來能夠從事一點兒與音樂有關的事情,有組樂隊的意識,都要追溯到這個時候。

菠蘿大哥
前面黃老師講的內容,太觸動我的內心了。最開始寫歌的時候,我是想好一個旋律,然后硬填詞進去。過了一些時日,我就先寫詞,再找旋律,把它們嵌進去。今天聽完黃老師講的,我就明白了:其實無論是先寫詞,還是先寫曲,都是要在心中存有一個概念。有了這個概念,不管是用先鋒的手法,還是借助別的途徑,都可以把它表達出來。
我對Beyond的感覺,主要還是停留在四子時期。只要用心聽,我們都能從Beyond音樂中獲得一種振奮人心的力量。我的職業是醫生,但同時我也是一個病人。十年前,我大病一場,病隙聽聽Beyond,能夠感受到活下去的動力。
陸遠:金晶,你如何編了這樣一部書?Beyond在你心中又有怎樣的地位?它對你有些什么影響?
許金晶:這是我自己第四本書的首發式,此刻我的心情是極不平靜的。為什么會這樣?這要說回我和陸遠老師的緣分。2015年到2020年,我和陸遠老師的導師周曉虹教授,以及他們的讀書會,一起學習了四五年社會學課程,閱讀了一些經典作品。其中最讓我震撼的一部作品是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這也是我隔一段時間會再讀的書。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成伯清教授圍繞《社會學的想象力》做過一篇大文章,很精彩。這篇文章認為,所有的學術研究(特別是與人有關的學科,如社會學),最終都與研究者個人的生命體驗緊密關聯,只有這樣,研究才能具備生命力。
人們會喜歡各式各樣的歌手,甚至有的聽者對歌手崇拜到狂熱的地步。但是,我們聽音樂、欣賞歌手,最終不是為了成為他們,而是因為他們在作品中表達的某種思想力量,與我們個體的生命體驗和心路歷程發生了強有力的對話,讓我們的生命變得更豐富更多元。
最開始,我想過給Beyond寫一部傳記。但是囿于個人的精力和條件,無法實現這一預期。后來轉念一想,如果關注Beyond音樂的社會傳播狀況,恰好合乎文化社會學、傳播學的一大主潮。也就是說,不僅要研究作者和作品本身,而且要注意這些作品在傳遞給每一個受眾時,在他們那邊引起的反響。
這也啟發我從身邊的朋友那里挖掘故事:他們的生命怎樣與Beyond及其音樂發生了勾連。《海闊天空》這本書并沒有做成純粹文人雅集的面貌,這里面既有楊早、鄭嘉勵等知名學者的作品,也有美發師、小店店主的文字。在編選的時候,我也受到了周曉虹教授和陸遠老師的影響,即要盡可能涵蓋最廣泛的人群,以展示Beyond這一華語樂隊是怎樣觸及每個人的內心,并切切實實改變普通人的生命的。

許金晶
我可以把自己作為例子稍微談談。我現在生活在南京,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比較豐富的業余生活。然而,十五年前,也就是Beyond樂隊最后一次演出之后不久,我待在老家,是一個一無所有的失業人員。我在那段時間注冊了豆瓣,瀏覽音樂條目,關注樂隊動態。當時,我和《海闊天空》這本書的作者之一吳曉斌,也就是我的表哥,我們經常到KTV唱Beyond,他唱《無悔這一生》,我給表哥唱《祝你愉快》。表哥當時在我們小鎮上換過多種工作。在那樣灰暗的日子里,正是Beyond的音樂,支撐我們走下去,尋找更廣闊的未來。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書友都和我一樣,對我們所在的南京文化地標先鋒書店滿懷憧憬之情。其實十年前,我也是經常來先鋒書店聽講座的普通聽眾,喜歡在沙龍上提問;而十年之后,通過持續的積累和堅持,我有幸成為了先鋒書店沙龍的臺上嘉賓。在面對各種外部困難和逆境的時候,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堅持自我,最終把夢想變成現實——這就是我做這本《海闊天空》的初衷,也是Beyond音樂這些年來帶給我的最大感動。

菠蘿大哥(左)與許金晶
陸遠:我覺得應該有無數的樂迷和金晶的情況一樣,家駒和Beyond的歌聲,伴隨他們走過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溝溝坎坎,然后迎來一波又一波的挑戰,達到一個又一個的高峰。我覺得,他們兩位其實是配合得非常好的資深音樂人,而且都有獨立原創能力,所以我們今天不會放過他們,一會要讓他們為大家獻唱幾首歌。

菠蘿大哥(左)與許金晶演唱Beyond曲目
剛才黃老師講道,對于一個好的樂隊來說,它應該是能夠在像我這樣只會在KTV里面唱那幾首歌的普羅大眾,和像金晶、菠蘿大哥這樣比較深入地受到Beyond影響的發燒友之間,或者說,是能夠在音樂理想和商業生產之間游走的。我覺得,無論家駒還是他的另外三位同仁,他們也許經歷過很多妥協,有時必須向市場妥協,但是他們也愿意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因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不知能不能請你們從一個音樂人的角度,或者黃梵老師從詩人、寫作者的角度,就這個問題給大家做一些分享。
菠蘿大哥:我先拋磚引玉。Beyond以前給我的印象,在四子時期是非常深刻的,包括我學電吉他時的solo,練的最多的也是這個。大學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們樂隊演出,第一首歌是《真的愛你》,最后一首歌是《海闊天空》,因為《海闊天空》尾奏足夠精彩,然后我還設計了自己的pose,下腰之類。我相信,每一個吉他手心中Beyond都有一定的地位。現在B站上有一些小朋友,跟著他們的爸爸,兩個人彈《灰色軌跡》,用雙吉他對飆。其實,我很遺憾讓兒子學了鋼琴,不過現在我已經給他報了吉他班,我希望我們父子也能對飆起來。
我看過一個視頻,講Beyond有一首歌叫《遙望》。這是Beyond一首相對柔和的歌。我看到了家駒是怎樣把它寫出來的。他坐在一個餐桌前,拿著吉他,開始掃旋律。對面的人是他弟弟家強,就在那邊講,剛才不太好啦,然后家駒再做調整。我之前看過一些資料,說家駒識譜能力不太行,如果給他一個簡譜或者一個五線譜,要讓他把這首歌唱出來,他是沒有這種能力的。可以說,他就是天才,就是憑借一種感覺創作。他一邊彈,覺得這樣好聽一些,旋律就出來了,這首歌也就完成了。然后有人專門幫他記錄,把譜記下來,再做編曲。
所以說,不可否認,在音樂和眾多的藝術方面,包括其他學科,都有天才。我覺得家駒就是音樂方面的天才。非說他是刻意迎合市場,或是刻意表達他的音樂態度,我覺得他可能未必考慮得那么深刻;他只是想把旋律做得優美一點,讓大家覺得好聽一些。或者說,家強就充當了他的聽眾,講講這個不好啦,那個好一些啦,這個哪里不對啦。就像剛才我的朋友,骨科的鵬哥(今天由他提供設備),我們兩個人的合作其實就是這樣子。出了一個旋律,我說,這個旋律要調整修改,大家磨合,最后就出來一首好歌。

現場讀者
許金晶:雖然我現在也出了三張原創民謠專輯,但我在作曲時,基本上是自己先哼出一個旋律,再填詞。接下來就是由菠蘿大哥上陣,幫我記譜,再幫我編曲。或者我找其他音樂人幫忙做好小樣,再請菠蘿大哥給我把關。
大概六七年前,我做第二張專輯的時候,下班后我就到菠蘿大哥家里,兩個人圍繞歌詞,圍繞現有的旋律,一點一點摳,看哪個旋律更好一些,歌詞也是慢慢地一起商量。一轉眼的功夫,六七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真是非常令人難忘。
至于陸遠老師提出的這個問題,這樣的一種矛盾和沖突,其實從Beyond樂隊成立到他們最后的告別,自始至終都存在。而且對于每一個創作者來說,這樣的問題也是長存的。比如說菠蘿大哥的第二張專輯,我一直認為是他的三張專輯里藝術水準和思想性最高的一張。但是人們可以看到,第二張專輯在網易云和QQ音樂里的收聽量遠遠不如他根據自己本職工作去寫的那些科普歌曲,比如說與急救有關的《黃金十分鐘》等歌曲,這些歌曲的收聽數量是他第二張專輯的幾百倍甚至上千倍。

活動現場
這一點我其實也一樣。我的第二張專輯出來后,給《海闊天空》這本書寫推薦語的著名樂評人李皖老師聽了,說這張專輯非常好。但是在網易云和QQ音樂上發布后,到現在為止,收聽量仍然少到可以忽略。我在網易云的粉絲是281個,我記得很清楚,但這也很正常。你想想我第二張專輯里面寫的是什么?寫的是阿倫特。能有多少受眾自然可想而知了。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阿倫特》這首歌在網易云音樂上發出來后,第一個評論的人好像是個90后的小姑娘。她給我回了一個:“怎么不是特侖蘇?”
當然,我們要明白一點,Beyond跟我和菠蘿大哥最大的不同在于,對于他們來說,音樂既是理想,又是生活,還是他們安身立命的職業。而我跟菠蘿大哥不一樣,我們的本職工作都不是做音樂。我經常跟朋友說,我個人的物質欲望比較低,單位給我開的這份工資已經足夠讓我過上一種相對小康的生活。我用業余時間讀書寫作,創作民謠,看電影,這都是一種從心所欲的狀態。我只會寫我想寫的東西,只會讀我想讀的書,只會推薦我真正認可的東西,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已經有了一個相對不錯的工作的基礎之上。但是在Beyond那里不一樣,音樂對他們來說既是理想,又是職業,所以他們必然面向龐雜的公眾,這與他們堅持自身的音樂理想之間就有了張力。

黃梵(左)與陸遠
黃梵:南京這個城市有三百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其實這當中很多人是了解詩歌的,已經不滿足于時流所見的那些詩人詩作。大家更想讀到探索性的東西:它能給人以精神上的引領,同時以為人熟知的面貌出現。我在社會上做了一些推廣現代詩的工作。也就是說,把現代詩介紹給普通人。那些探索性的詩歌,有沒有可能以大家熟悉的方式呈現,讓它在此時此刻引發共情?我不能保證這樣做就一定會有共情,但我愿意往這方面努力。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所以在年輕的時候完整地走過了八十年代。那時,接受大學教育的人比例其實很低,而且喜歡詩歌的人,確實局限在精英階層。我當時念的是理工科,全班四十人中有二十多位都在寫小說,屬于癮大水平低。一些重要的著作,像加繆的作品之類,他們大都沒有讀過。當然,那時很多東西也沒有翻譯進來。
我如今在南理工教書,有一次問班上的學生,知道《第二十二條軍規》的請舉手。結果班上近三分之一的人都舉手了。再問多少人喜歡詩歌,也有不少人舉手。現代的年輕人,伴隨著許多小眾的文化成為亞文化,他們也聚合成了小眾的群體,總體數量比八十年代要多。
八十年代的文化從整體上看,保持著很強烈的先鋒色彩,這一先鋒性甚至走到了死胡同。比如,在八十年代末期,很多詩歌已經變成天書,沒有人能看懂,業內的人也看不懂,詩歌變成了個人密碼的收容所。但是,現在我們都已經不這么做了。大家逐漸意識到語言本身,包括音樂語言的交流性質。語言是溝通個人和作品、個人和社會的橋梁。所以,在語言傳遞的時候,一定要讓“密碼”保持部分的公共性。關于這個問題,我想大家都已經達成共識。未來還會產生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并成為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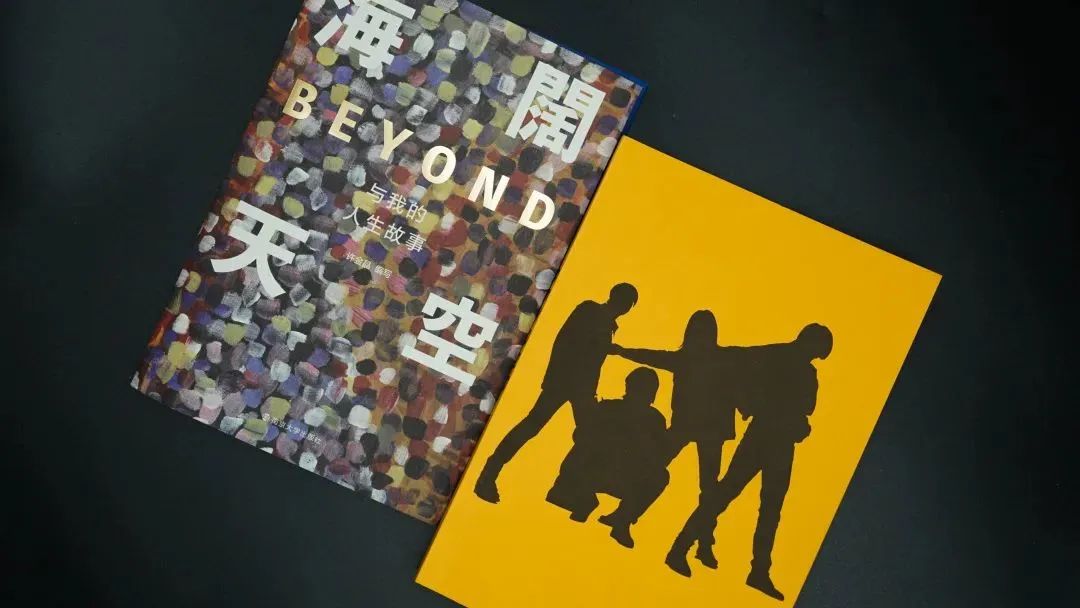
陸遠:最后,讓我們把交流和發言的機會留給讀者。記得開場時開始我問大家,有多少人是1995年以后出生。我們知道,隨著家駒的去世,實際上Beyond在大眾當中的影響力就慢慢式微了。我想說的是,95年之后出生的人與我們這些80后70后還不太一樣。他們到了可以獨立聽歌的那個年代,已經是2005年甚至2010年之后了,那時的整個文化生態,已經和八九十年代完全不一樣了。
前段時間大家都注意到,60歲的崔健開演唱會,70歲的羅大佑開演唱會,實際上,崔健也好,羅大佑也好,Beyond也好,就像我一開始說的,是要拿他們做一面鏡子或一把鑰匙,借以打開我們自己的心靈世界。但我覺得很難再回到八九十年代的那種文化氛圍了。剛剛黃老師也說了,Beyond可能是一個很特殊的歷史時代的產物。
我也特別想聽聽年輕朋友的看法,不知道你們現在聽Beyond的感覺是怎么的。像許金晶,當時他是一個小鎮青年,又處在人生極為灰暗的時刻,這樣的歌能帶給他力量。我們這本書里也寫了很多這樣的人,有的甚至靠聽Beyond來對抗輕度抑郁癥。像這樣的一些例子,我覺得和今天的年輕人不大一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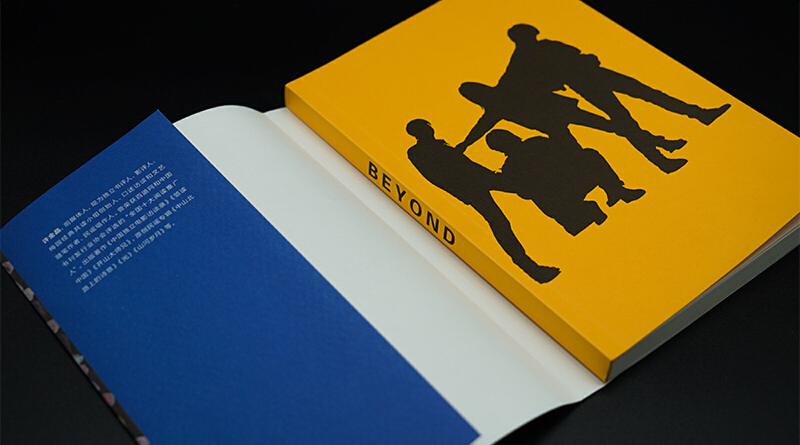
現場觀眾一:我今年上大三,是00后。我們上小學時聽MP3,有一次我去朋友家拷貝,他給了我Beyond的歌。后來我在別的地方又聽見了Beyond,我有點聽不懂,但覺得很好聽。Beyond給了我很多力量,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起于草莽的一個樂隊,來自香港九龍的一個貧民區。據說當時那邊很多人都沒上過學,他們一無所有,擁擠在鐵皮房里,但每天都想要打破自己的命運,打破生活的某種束縛,然后挑戰出來。就是那樣一種感覺,這樣的精神最打動我。人生路上經歷的那些苦痛也好,不幸也好,最終都會變成自己的一些經歷,讓你頑強生長。一直以來,我第一次因為聽一首歌感動到哭。就是這首Beyond的歌詞:只有淡忘/從前話說要如何/其實你與昨日的我/活到今天變化甚多/只有頑強/明日路縱會更彷徨/疲倦慣了再沒感覺/別再可惜計較什么……

互動讀者
現場觀眾二(張娟老師):我上大學時黃家駒已經去世了,我聽beyond,是我們的一個校園樂隊唱的。現在我已記不得樂隊的名字,但就像剛才菠蘿大哥所講,那個樂隊每次演出的時候,必少不了《真的愛你》和《海闊天空》,特別適合開場和結尾的兩首歌。這在當時很吸引我,其實最早我甚至都聽不懂他們的粵語在唱什么,但他的歌聲里就是有那么一種力量,它是一種青春,一種熱情,一種宣泄。所以我覺得,Beyond是所有跟青春有關的記憶。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每次在樂隊演出結束后,我們一起走回宿舍。樂隊的樂手帶著他心愛的姑娘,特別青春,會在圖書館前喝啤酒,聊音樂。后來我在讀博的時候,在做港澳臺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時候,都在想:為什么在那個時候,這樣的樂隊能夠成為一種時代的情緒?
其實,在很漫長的時期里,我們的成長環境都是比較閉塞的,我們這一代人早期接觸流行文化的機會是很少的。但是Beyond出現的那個時代,他們是在一個開放的、迅速發展的香港城市社會里面生長起來的。這樣一個樂隊,在它成長過程中,如果去探究他們到底是專業的還是商業的,我覺得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在一個城市生長的過程中,商業也是有意義的,商業其實在跟那個時代對話,在跟他的觀眾和讀者對話。這個過程特別好的一點在于,它其實也是借助文學(歌詞)走近了我們,是用文學的力量打動了我們。Beyond有社會關懷,是關注當下現實的。所以我后來重新去看歌詞的時候,就深受感動。
我們的社會其實有一個變遷的過程。在上世紀80年代,可能我們看到那些談論情愛的歌會很感動,會覺得我們獲得了某種自由。我去年看到作家唐穎寫的一篇小說,講那時候她為什么要到美國?因為到美國可以自由穿紅色的裙子。在80年代,我們需要的自由就這么多,但是后來人們發現我們需要的其實更多。這些更多的東西是什么?就是要敞開我們自己的心靈,去關注外面的世界。

張娟老師
說回Beyond,他們其實并沒有那么多表現愛情的歌,而是表達對大地、對父親、對母親的深情,他有著海外游子一樣的漂泊感,命運感。今天早些時候我還是很掙扎的,我到底要不要來這個發布會?因為晚上已經有約,而且趕過來還蠻遠的。但在最后那一刻,我就在想今天是家駒的生日,有這一點就足夠了。所以我覺得,我今天能在家駒的生日,在家駒誕辰60周年的日子里,和諸位共同享受這個時刻,就足夠了。

THE END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