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藝術開卷|考古文物串起的楚國八百年
關于楚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較為系統,然而由于文獻本身所限,楚國尤其早期的歷史和文化仍存在記載缺失或語焉不詳的情況。從1932年安徽楚幽王墓開始,楚墓、楚城和其它楚遺址發掘的數量以萬計,出土的楚國陶器、青銅器、漆木器等蔚為大觀,數量龐大的出土楚簡和出版的考古學報告,對研究楚國歷史和文化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利用這100年的豐富考古成果,從考古學的視角來探討一下楚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成為可能并仍有必要。
由湖北省博物館編著、文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楚國八百年》以文物為基礎,展示楚人在八百年歷史長河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化風貌。《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經授權選刊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方勤所撰文章。
關于楚國歷史與楚文化的研究,無論是歷史學、考古學還是文獻學,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在歷史研究的角度,漢代以前的《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以及漢代以后的《資治通鑒》等史籍,包括《楚辭》等文獻均有記載或涉及,當代以《楚學文庫》等為代表著作亦頗豐;在考古學研究角度,從1932年安徽楚幽王墓開始,楚墓、楚城和其它楚遺址發掘的數量以萬計,出土的楚國陶器、青銅器、漆木器等蔚為大觀,數量龐大的出土楚簡和出版的考古學報告,對研究楚國歷史和文化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關于楚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較為系統,然而由于文獻本身所限,楚國尤其早期的歷史和文化仍存在記載缺失或語焉不詳的情況。在中國現代考古學走過100年的今天,利用這100年的豐富考古成果,我們從考古學的視角來探討一下楚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成為可能并仍有必要。
一.關于楚國的歷史
結合《史記》等文獻,楚國自周成王時受封立國,至楚國末代楚王負芻于公元前223年滅國,歷四十多位楚君、八百多年歷史當無誤。周成王公元前1043年至1021年在位,具體是哪一年受封,根據《竹書紀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和《國語·晉語》“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與鮮卑守燎”的記載,結合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的犁子鼎(馮時先生認為犁子即指曾侯諫)也記載了岐陽會盟此事,我們認為楚當在周成王六年與曾國同時受封,即公元前1037年。于是,楚國立國自公元前1037年至公元前223年滅國,共815年,周原出土的三片甲骨上的文字“今秋楚子來告”等記載,也進一步證實楚在周初受封立國,爵位當為“子”,地位卑微,與《國語》“守燎”記載亦相互佐證。

與岐陽之盟有關的青銅鼎
《史記·楚世家》等文獻記載了楚世系,楚國第一位國君為“熊繹”,而清華簡《楚居》中也記載了楚肅王之前的楚君世系,與文獻第一位楚君對應的也稱“熊繹”,關于熊繹之后至楚肅王之前的歷代楚君,《史記》《楚居》基本對應。《楚居》簡記載的楚君,明確叫王的有如武王、文王、成王等共13位,第一個稱“王”始于楚武王;文獻記載熊渠開始稱王,后又畏于周厲王“伐楚”自去“王”號,而出土的熊渠戈,其上銘文“楚公家”,可見熊渠稱“公”而不敢稱“王”符合史實。時代可至西周早中期的宜昌萬福垴遺址出土的楚季編鐘上“公”銘文,以及西周晚期的“楚公逆”(即文獻記載的熊鄂)鐘,均可證西周時期楚國尚未自稱“王”。

楚季寶鐘及鐘上的銘文
《楚居》之外其它出土的如葛陵楚簡、包山楚簡等諸多簡,以及如曾侯乙镈鐘、楚王熊悍鼎等青銅銘文中亦有關于楚君的記載,均可應證《史記》等文獻記載關于楚君世系的不誤。如是,自熊繹至最后滅于秦的最后一位楚君負芻,共41位。在楚國立國國君熊繹之前,清華簡《楚居》、包山簡等楚簡和《史記》等文獻都有關于楚國世系的記載,當是對楚國立國之前祖先的追述,正如包山簡所言“楚先老僮、祝融、鬻熊”,這些只是對楚國立國國君熊繹的祖先的記載,自然不乏傳說因素,結合《史記》等文獻,楚國的祖先當為:黃帝——顓頊高陽——卷章(老僮)——重黎、吳回(祝融)——季連——鬻熊——熊繹”。
楚國都城考古與文獻互相確證的有季家湖、紀南城、河南陳郢、安徽壽郢,時代從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楚滅于秦,而早期都城的尋找仍是目前面臨的主要課題。清華簡《楚居》的出現,似乎可一下子解決楚都和楚文化起源的問題,楚早期都城在丹淅之會幾成定論。但是,我們認為,《楚居》本身所言大體無誤,然而我們怎么解讀它,仍存在誤區:以熊繹立國的都城居“夷屯”為界,《楚居》是把立國之前楚祖先曾經居住過的地方,以及立國之后楚君作為都城均當成“楚居”講述的;而楚祖先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有時候是一群人有時候可能就是幾個人,能一一對應到相應的考古遺址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正確的方法是從《楚居》記載熊繹居夷屯(即《史記》所言之丹陽)之后,才可以依據《楚居》所記載地點尋找,而此前的地點是祖先甚至是傳說時代的追憶,是不能作為尋找都城具體地點的參考,類似就封齊國的姜子牙,他個人就封之前及其祖先的足跡與齊國都城并無關聯。宜昌萬福垴遺址因出土“楚季”銘文編鐘可定位為楚國遺址無異議。而其測年可早到西周早期,遺址本體的年代也當到西周早期;出土了“西周早期的觚形尊和豆的陶片”,部分陶器特征亦可到西周早期;出土的兩件粗柄寬盤豆“屬于西周早期偏晚”。萬福垴遺址本體不是楚國早期的都城,但是結合西周早期分封之初的諸侯國如曾、晉的疆域都不大的現狀,西周早期的楚國都城當只能在漢水之南、沮漳河流域,而不可能遠至丹淅之會一帶。置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之間,根據楚國遺址及出土如“蔡侯朱之缶”等文物綜合判斷,當在襄荊平原一帶。
二.關于楚國的文化
楚國立國時國力弱小,后成長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國力強盛時,西至巴蜀,東至大海,“地方五千里”,占據著幾乎整個南中國。楚國有長達八百年的漫長歷史,同時具有高度發達、風格獨特的地域文化,既有“一鳴驚人”“問鼎中原”等傳奇故事,又有屈原《離騷》、老子《太一生水》這樣神奇爛漫的文化。這些在考古中得到充分體現:

出土的吳王夫差劍(左)和吳王夫差矛(右)

出土的甲胄

出土的弩機
江陵馬山楚墓出土的吳王夫差矛、吳王夫差劍等戰利品,及體現軍事實力的車馬器、弩機和甲胄,反映了楚國的逐漸壯大過程。荊州熊家冢楚惠王墓的盛大規格及復原的“天子駕六”宏大車馬陣場景,更代表了楚國成為大國之后的恢宏氣度。

彩繪鳳紋石編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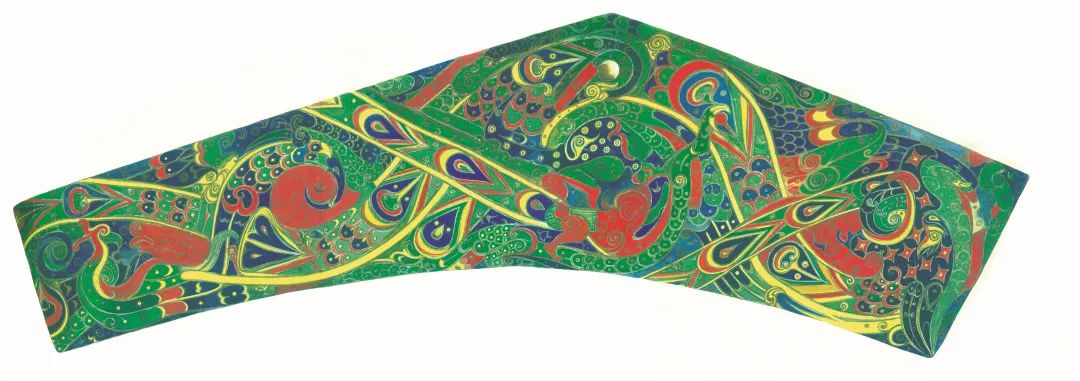
編磬修復后的圖像效果

虎座鳥架鼓
紀南城出土的楚王祭天所用的彩繪編磬的艷麗色彩,虎座鳥架鼓的綺麗構思,以及湖北荊門包山2號楚墓出土的彩繪漆奩圖像,一幅完整的車馬出行圖,所繪圖像包括26人、4乘馬車、10匹馬、9只鳥等,通過5棵柳樹分隔成互有關聯的畫面,首尾連貫而過渡自然,被稱為中國現存最早的“連環畫”。

包山二號楚墓出土彩繪漆奩

湖北荊門包山2號楚墓出土的彩繪漆奩圖像(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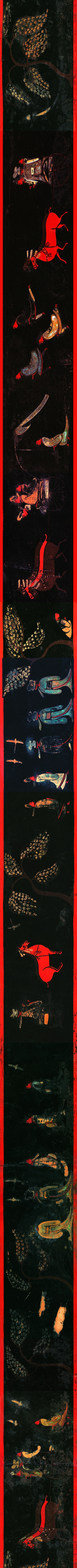
湖北荊門包山2號楚墓出土的彩繪漆奩圖像
荊門嚴倉漆畫,巨幅畫面上的楚式建筑、樂舞等內容,色彩鮮艷,藝術感十足,總之,以紅色、褐色、草綠色、金黃色、藍色等明快、鮮艷色調是楚文化的主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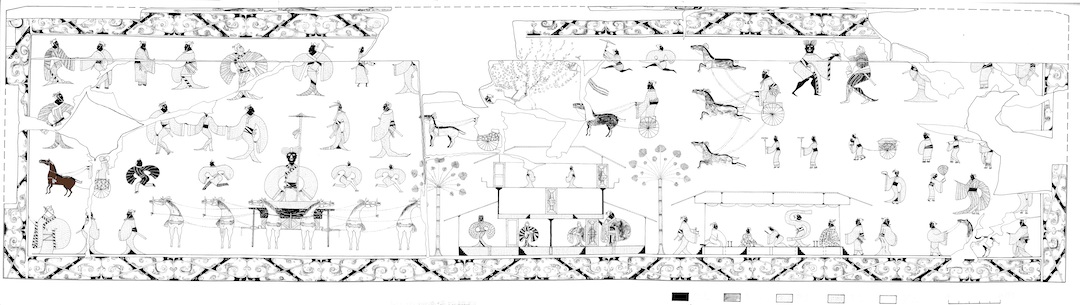
荊門嚴倉漆畫線圖
楚國的發展壯大離不開農業、工業和商業的發達,文物同樣可以展現其發達程度。楚國境內產黃金、白銀和青銅,因而金幣、銀幣和銅幣都曾在楚國鑄行。其中金、銀幣用于楚國境內的大額支付和賞賜,額度較小的交易多使用蟻鼻錢。楚金幣是以龜甲形為主的版形金幣,幣面多有文字,其中又以“郢爯”為主。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是迄今為止已發現的保存最完好、冶煉水平最高、規模最大的古銅礦遺址,古代工匠為掘取銅礦石,開鑿豎井、平巷與盲井等,還采用了提升、通風、排水等技術,以及銅斧、船形木斗、木鏟、繩索等采冶工具,說明那時的冶銅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有“郢爯”字樣的金幣
楚國繁盛時期的郢都紀南城,出土的陶水井圈、筒板瓦、排水管,以及規劃嚴整的宮殿、手工作坊、居民區等布局以及8處城門,其中含3處水門,水運可直通長江,使總面積約16平方公里、作為我國同時期南方最大的一座古城的郢都“號為朝衣鮮而暮衣敝”繁華景象油然可見。2000多年前腌制的干鳊魚,以及水稻、麥、粟、板栗、姜、花椒等,讓人感覺煙火味十足。漆木折疊床、座枕、銅薰杯、銅燈、竹席等日用品,是楚人精致日常生活的寫照;九連墩楚墓出土的假發,裝有銅鏡、木梳、胭脂、油彩等物品的便攜式彩繪漆木梳妝盒,反映出當時貴族對美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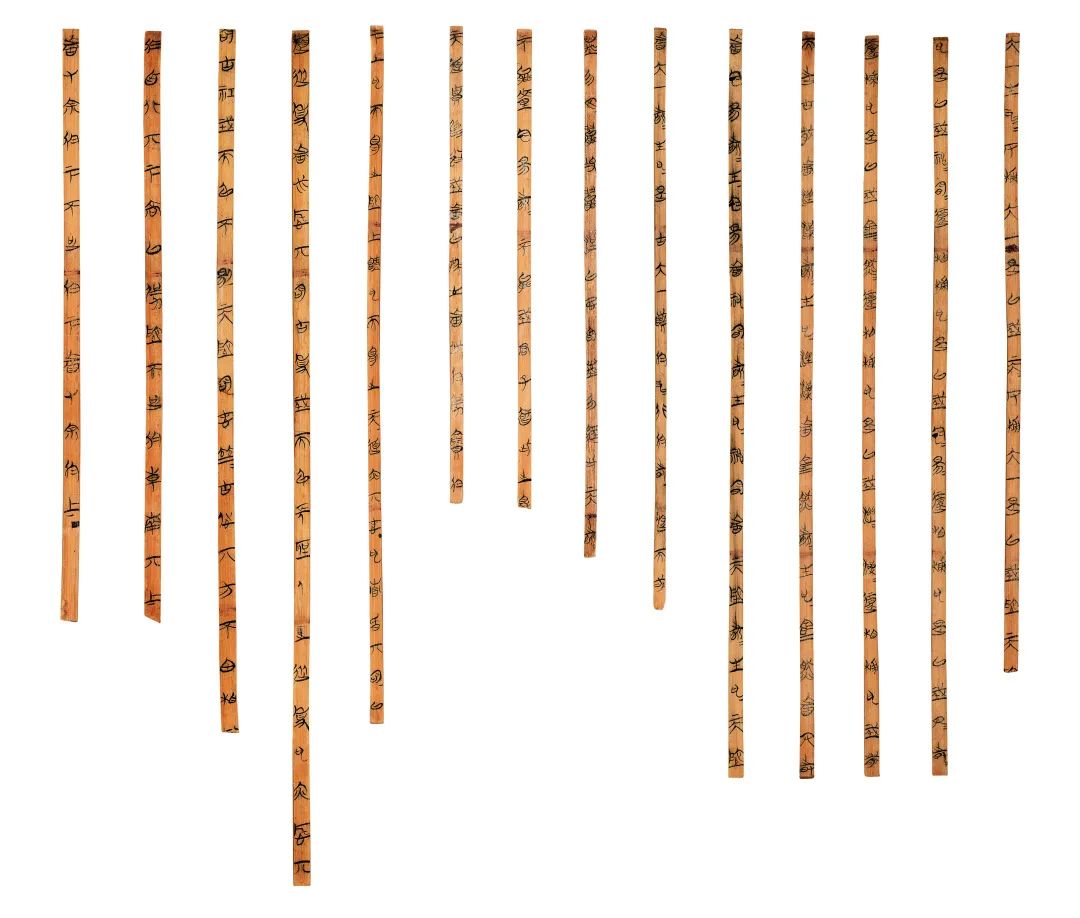
郭店竹簡《太一生水》

郭店楚簡《老子》乙(局部)
據不完全統計,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楚地簡牘已發現30多批、10萬字以上,內容涉及典籍文獻和司法行政文書等。荊門郭店楚墓出土竹簡730枚,包括18篇先秦典籍,其中15篇是失傳文獻。尤其是反映戰國時期深奧宇宙觀的《太一生水》和目前最早的抄寫于戰國中期的《老子》乙種,令人驚嘆。郭店楚簡的發現使楚簡研究成為國際顯學,被譽為是改寫了世界思想史的大發現。楚辭一改《詩經》四字一句、工整對仗的限制,開辟了文學新風氣,為漢賦新文學的到來打下了基石。楚國800年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青銅、漆器、竹簡、絲綢、玉器等精彩絕艷的物質寶庫,也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楚文化最終融入悠久的中華文明,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原標題為《考古學視角下的楚國歷史與文化》)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