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黑陶:在盛夏廣闊墨綠的玉米林中,倉頡墓地,寧靜安詳 | 純粹訪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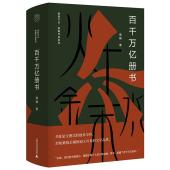
百千萬億冊書
作者:黑陶 著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2021-12
如果對作家黑陶的寫作進行描畫、賦形,必然會發現他寫作的幾個關鍵詞,南方、行走、個人漢語。某種意義上說,黑陶發現,繼而用自己的行走、燒制的個人漢語創造了另一個意義上的南方,這個“南方”代指著廣義的江南,有別于以往所認知的母性特質,它是激烈的、昂揚的、粗壯的,甚至是鋒利的、詭秘的,這是一個父性的南方。為南方命名,是黑陶個人文學的堅實依托,南方這個原初的地理概念,在他的寫作中也在掙脫原初,慢慢成為一個生長著的精神性概念。
黑陶散文新著《百千萬億冊書》,現實、幻象、史料、囈語、想象——地理、人物、民間傳說、歷史、神話——詩歌、日記、摘錄、文學史補遺……這些斷片式的篇章,共同形成了一個“嶄新的,文學與其他學科、與自我生命、與他者生命混雜的散文空間”。
——《文學報》
用燒制的個人漢語,命名父性南方
記者:以一個關鍵詞開啟這個訪談,或許是一種有效途徑。這個關鍵詞是“南方”,或者是“江南”,從《泥與焰》《漆藍書簡》《中國冊頁》再至最新的《百千萬億冊書》,你不斷重復并深入著一項工作:對于“南方”的命名。這種命名是個人生命體驗式的,它依托于大地、依托于行走、依托于自我生命與更大的生命體的連結。這種命名,必然有著至為復雜的內核,而且殊為不易。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指向一個最為表層的問題:為什么要進行命名?于你而言這種命名有何意味?
黑陶:“這種命名是個人生命體驗式的”,謝謝這種珍貴的理解。確實,不是為命名而命名,南方,是在自己寫作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的一個概念,它逐漸成為了個人文學的堅實依托,成為寫作能量的不竭提供場。
我的南方概念,實際是指廣義的江南。但江南這個詞現在已經被用俗,所以我不用江南而用南方。個人的南方,或廣義江南,有其具體范圍,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百千萬億冊書》的序文中,我作過介紹:“這個地域,北際長江,南抵大庾,西溯湘楚,東迄于海。”如果進一步詳察,這個區域又可再細分成五個文化專區:江南水鄉文化區、徽文化區、楚文化區、贛文化區、東部沿海文化區,涉及中國東南八個省區。
這個南方并不空泛,因為,它擁有一個堅硬、灼燙的個人內核。這個內核,就是我的出生地:江蘇宜興丁蜀鎮。江西景德鎮是瓷都,江蘇宜興是陶都,而處于蘇、浙、皖三省交界地區的宜興丁蜀鎮,則是陶都之源地。燃燒的火焰和堅硬閃亮的陶器,是它最為顯著的代表物。如果說個人南方是一棵巨樹,那么,這棵巨樹深扎、有力、強韌的根,就是丁蜀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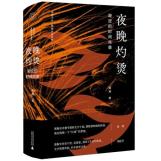
夜晚灼燙: 凝定的時間肖像
作者: 黑陶 著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 2021-07
任何寫作者,也許,都需要一塊地理意義的個人根據地。對南方的命名和擁有,讓我的寫作漸趨自覺,并且不飄。憑此立足所在,我眺望世界和人類。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現實的南方,伴隨著寫作,同時也一直在被我構建甚至創造。因此,南方這個原初的地理概念,在我的寫作中,也在掙脫原初,慢慢成為一個生長著的精神性概念。
我與南方,“自我生命”與南方這種“更大的生命體”,確實有奇妙的連結。比如,在南方無數個具體地點,我注視過長江。在《廣州文藝》今年7月號發表的一組札記中,我曾這樣記錄:“在長久的注視中,長江恍惚經由我的血管,流過我的身軀。長江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總在無數個瞬間,連接融合。”類似這樣的緊密連結,讓我慢慢在個人的寫作之途上,生出定力,獲得內心的強大。
當然,我也時時提醒自己不要陷入狹隘。個人有一個觀點:你的能量多大,你的故鄉多大,你的立足地多大。
生命能量小的人,他的故鄉,只限于是他出生的那個村莊或城鎮;能量稍大,故鄉可以是所在的市、省;能量再大,他的故鄉,就可以是他的國家,甚至地球。比如無錫的盲人音樂家阿炳,當他的《二泉映月》,作為人類的聲音代表,在外太空響起時,我們就可以說:阿炳,對,他的故鄉在地球。
記者:切入你命名的“南方”的內里,是泥土、火焰、大海、父性容器,不難發現,后兩者在你看來往往是被遮蔽的,也正是它們,確證著另一個意義上的江南。某種意義上,這是你對于江南的一種發現或者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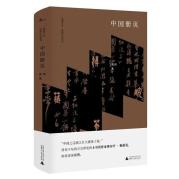
中國冊頁
作者: 黑陶 著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 2020-02
黑陶:寫作者最重要的品質,是不從眾,不受限于公共或流行的觀念與意識,是始終用自我的內心、自我的眼睛,去體會,去看見。
我的出生地丁蜀鎮,就在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太湖的西岸,它實際是處在狹義江南(蘇南、浙北和上海)的腹心。在一般人心中,狹義江南的特征,可以用兩個元代人的著名話語來概括:一句是馬致遠的“小橋流水人家”,一句是虞集的“杏花春雨江南”。
如果偷懶,完全可以按照這個傳統的江南意境方向,進行寫作。但寫作的人要尊重自己,我個人感受到的家鄉、感受到的南方,最重要、最鮮明的元素,卻是另外的,正如你所解剖的我的“南方”內里,是泥土、火焰、大海、父性容器。
因為家里窮,母親是在家里生的我。那是一間非常簡陋的、租居的披屋,這間披屋的幾十米之外,就是日夜在燒制陶器的熊熊窯火。所以,我來到世上呼吸的第一口空氣,就飽含了火焰的質感。我早期的一冊散文集,書名就是《泥與焰》,泥土和火焰,家鄉制陶必備的兩種物質。
大海,也是長久以來被嚴重忽略、嚴重遮蔽的江南元素。從地圖上能夠清晰看到,江南的東緣,就是無垠波涌的太平洋。但是大海,這個獨特的江南元素,它那超級巨大的包容力與蠻荒力,長久以來,被鶯燕的曲聲給遮擋掉了。
火焰和大海,外在示柔,集結以后的內里,卻擁有可以消化、改造一切的洪荒巨力。個人感知的南方,在我內心,幾乎等同于中國文化的某種本質特征。
而且,除了上述種種,幾乎是出于生理性的直接感受,我首先是發現,然后確實是用漢字,創造了“另一個意義上的江南”,這就是:父性的南方。
這種創造的動力,來源于自我生命對所處環境的內在理解,來源于表達自我生命的強烈意愿。
巨型容器般的這個父性南方,是活著的,始終在發展、生長。他的不確定的遠方,也讓個人的文學,充滿了可能。
二泉映月: 十六位親見者憶阿炳
作者: 黑陶 著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 2018-08
記者:在這個“南方”里,蘊藏著一種力量,它是激烈的、昂揚的、粗壯的,甚至是鋒利的、詭秘的。正如上述所言,它與你的個體生命有一種內在的關聯,也就是說,以丁蜀鎮輻射開去的廣大南方鑲嵌在你的生命之中,它的特質與你的生命特質相近,你的書寫必然以此為依據、而展開。
黑陶:在力量強大的寫作者那里,人與所在地域的關系,是這樣的:他就是地域,地域就是他。
當代漢語作家中早已有了這種示范,如張承志的蒼茫西北,畢飛宇的蘇北平原,阿來的四川藏區,莫言的山東高粱田野,賈平凹的神秘秦嶺,王以培的三峽庫區等等。
在我的想象里,存在一幅個人秘藏的地圖,像一幅暗夜里閃亮的地鐵線路圖:繁密的線條,通往世界的四面八方,而每一根線的起始,都是那個火焰灼燙的微小之點:丁蜀鎮。
這個微小的、火焰灼燙的堅實基點,即使我走得再遠,都會、都在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我以核動力,讓我持續獲得繼續走向世界遠處的足夠能量。
記者:以你所言,在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慢慢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私人的‘南方文學’傳統”,在不斷進入南方內部之時,你所依靠的一種方式是“行走”。我以為,這可算作你寫作的另一個關鍵詞。你曾說“潛游于中國深處。沉醉,感受,汲取。甚至,不需要人知”,這意味著你的行走,往往是縱深的,專注的,凝視的,在古老與現代之間來回打量,在鄉鎮和城市之間駐足,那些人們習見與陌生的,在你這里都有了獨特的呈現。“行走”于寫作何以重要,它們如何相連?
黑陶:這里的“行走”,不是普通旅行的“行走”,而是在“自己家里”的一種散步。因為,在個人感受中,南方,就是承載我的一只巨大容器,就是我的家。李白以天地為萬物的旅館,視光陰為各個朝代的匆匆過客(“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與格局更大的李白相比,我略顯狹隘。
泥與焰: 南方筆記
作者: 黑陶 著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 2017-11
在南方行走或散步,我思慕于拜訪前輩。一個人存在于世,有兩個基本維度: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古人對于我們來說,時間維度雖然已經過去,但空間維度仍在。兩個維度中仍存一個,所以氣息仍然是強烈的。若干年來,我熱愛踏訪瞻仰南方容器中我們的文學、文化史現場。我到過老子的誕生地(河南鹿邑)、屈原的誕生地(秭歸樂平里)、李白的安歇地(安徽當涂)、蘇東坡的誕生、流放、逝世地(四川眉山、湖北黃州、海南儋州、江蘇常州)、辛棄疾的瓢泉(江西鉛山)等等,親沐過他們強勁的氣息。
在現場,你就會發現,傳統離我們原來并不遙遠,反而甚至可以說切近。文化前輩在現實空間里存留了眾多具體的東西,最典型的,就是他們的手植之樹。在安徽當涂,有唐代李陽冰手植的構骨冬青;在安徽滁州,有北宋歐陽修手植的“歐梅”;在江蘇宜興,有北宋蘇東坡手植的海棠(年年春分時節繁花盛放,回老家時總不忘去看);在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鎮,有南宋朱熹手植的偉岸樟樹;在江蘇江陰,有明代徐霞客手植的羅漢松;在江蘇蘇州,有明代文征明手植的紫藤……當你的手觸碰到這些仍在生長著的古老植物時,你便是與文化前輩們在間接握手,你會瞬間感受得到辨認的不語溫暖。
這樣的行走,會讓自己對流傳下來的紙上經典產生更親切的情感、有更深的領悟,讓個人的寫作獲得巨大教益,當然,也會收獲巨量的寫作內容。但是,行走的目的并不是唯一為了寫,就像導演費里尼在拍完電影《羅馬》之后說:我放棄的東西不計其數。同樣,在南方的觀感體驗,與呈現于作品中的相比,我放棄未寫的內容也是不計其數。
記者:以我的閱讀感受,你的行走是有意卻又無預設目的的,仿若是隨時進行的,也不講求交通住宿,但“在場”與深入是你所追求的,在很多篇目中幾近一臺照相機和收錄機,卻自有視角,自有感受。這些“行走書”記錄的是時間與空間的一個橫截面,但又是歷史的變遷、人的變遷、世界的變遷,它們呈現的是中國的深部。
黑陶:我喜歡以“萬人如海一身藏”的極簡方式,漫游于南方深處、中國深處。那些莽蒼的鄉野、幽暗的城鎮、卑微淳樸如父母的底層勞動者,常常讓我久久注視,無言感動。
我的純粹個人化的現實或超現實的文字筆記,雖然感性,但假如某個年代的后人讀到,我相信,它們除了文學價值,也是觸及本質的、對我所處時代的某種歷史記錄。它們從一個側面,提供了“歷史的變遷、人的變遷、世界的變遷”的文字證據。
上面說到,行走的目的并不是唯一為了寫,通過行走,我更想獲得的,是自我的充實,是對自我生命的建設。
獨自站在分開粵贛兩省的大庾嶺頭,南眺,是嶺南的珠江水系,北望,是從小滋養我的長江水系。想到這條狹窄的山道上,六祖慧能走過,蘇東坡走過,文天祥走過,湯顯祖走過,便有一種奇異的心情。
夜宿于樂平里一對年輕夫妻空空的磚樓上,打開的窗戶,深夜彌漫進來的,是濃郁如云的橘子花香,“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我所置身的,是現實中異常真實的楚辭之夜。

漆藍書簡: 被遮蔽的江南
作者: 黑陶 著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 2019-03
還有清澈的溪澗,還有波浪般起伏又凝固的青色群山,還有曠野上緩慢壯偉的落日,所見所遇如此,人便不會再注目于日常之營營。
行走,不僅讓我獲得自我的成長和完善,也對腳下的土地,有了漸漸深刻的體認。在《中國冊頁》的跋中我曾說,通過行走,“我已經懂得并且領受:無論遭遇何種戕害,東方大地所獨有的充沛精神、強勁元氣,始終不渝,始終護佑并滋養著她所心知的默默追尋者”。
記者:不斷縱深的行走,敏銳的感知,向內的個人沉思,最終形成你行文的一種氣息。如有評論所說的,你注重的不是記錄的事物本身,而是物質所散發出來的氣息、光影、喻意、鏡像和玄機,借助現象的描寫來傳達一種人類共有的氣息,這種氣息不斷疊加深厚而至一種氣質,它們或承繼于你所因循的那些前人,如屈原、莊子、李白、蘇東坡、辛棄疾、魯迅、廢名……“安靜卻近乎噴涌的野蠻力量”,用最新散文集《百千萬億冊書》中的這個小標題來形容或許也是恰切的,事實如此嗎?
黑陶:漢語中已經誕生過這些光輝的名字。偉大的漢語養育了他們,他們又以自身熱切的生命,反哺漢語,并給漢語增添榮光。這些是如此令人激動!
這些光輝的名字太過炫目,但并不妨礙他們成為每個人的夢想和目標。
記者:來到另一個關鍵詞,“燒制漢語”。在《百千萬億冊書》中,現實、幻象、史料、囈語、想象——地理、人物、民間傳說、歷史、神話——詩歌、日記、摘錄、文學史補遺……這些共同形成了一個你所期冀的“嶄新的,文學與其他學科、與自我生命、與他者生命混雜的散文空間”。“燒制漢語”,這是你發明的個人語詞,它帶著一種強烈的、噴涌而出的冀望,對古老文字的敬畏、對自身漢語寫作的探求。
黑陶:我對祖國的漢字,充滿了感激感恩之心。漢字,人類偉大的發明。可以看、可以聽的漢字,既是中華文明之載體,又是中華文明之本身。
我父親生前是陶瓷工人,他用松枝燒過古老的龍窯。我的生存和勞動方式,實際也是燒制,不同的是,父親是燒制陶器,而我,是燒制漢語。一己的野心是,通過燒制,讓公共性質的漢語,轉化成一套獨屬于我個人的漢語系統。
敬惜字紙,是南方傳統。寫有漢字的紙張是神圣的,在南方,特別是在徽州,即使是十分偏僻的鄉野,也隨處可見石砌的“敬惜字紙”的爐或小塔。有字之紙,須在爐塔內燒化而不能隨意處置。
我還特別尋訪過中國字神,古老的倉頡之墓。在河南商丘虞城縣,在中原盛夏廣闊墨綠的玉米林中,倉頡墓地,寧靜安詳。
在寫作中,漢字之于我,既是一眾供我驅策、英勇搏殺的將士,同時,又是我心中一尊尊虔誠敬崇的神。
以漢字為載體的漢語,在我的理解中,它的功能分為三個層面:記錄交流層面,審美層面,創造層面。
漢語的創造層面,讓我無比向往,這也是漢字、漢語的根本神性所在。
在家鄉丁蜀鎮,河流是銀色之龍,龍窯內燃燒的烈烈火焰,是金色之龍。寂靜午夜,在人類全部睡著之后,銀色之龍和金色之龍,便共同遨翔嬉游于墨藍的家鄉夜空之中——這超現實的畫面,是我的創造,更是漢語的創造。
在閣樓獨聽萬物密語: 布魯諾·舒爾茨詩篇
作者: 黑陶 著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 2020-06
記者:這也涉及到一個或許寬泛但必然橫亙在寫作之前的問題:你如何理解散文這一文體?在對散文空間、邊界擴容之時,你是否也有著對散文某一種特質的堅持、或者說限制?
黑陶:按照我的文學分類法,中國散文,是除韻文之外的一切漢語文章。
我目前的寫作,其實更激進一層:我個人實踐的,是一種“漢語文本”。
漢語文本,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用漢字書寫的任何話語片斷;狹義:用漢字寫成的文學作品。
我實踐的漢語文本,它奉行的理想是:從內容上,世間萬物皆為我備,皆任我而取;從形式上,任何傳統的文學文體,都可納入其中。《百千萬億冊書》,就是呈現的樣本之一。
因為只有弱者,才屈服于規矩,才會自我層層設限。
我很清楚,文本形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綜合的、復雜的手段,它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好地創造屬于你的文學王國,只是為了更深刻地表達你,表達生命最深處的一腔至情。
漢語文本,這是一個足夠浩瀚的疆域,它召喚繼承者、反叛者、探求者和無畏者,它需要被召喚者擁有足夠的生命熱情和生命能量。
最近讀到的作家張煒的一句話,觸動我心:“事實上,文學之路和生存之路在今天變得如此地一致,這就是獨立思考,全面激活生命的勇敢。”在未來的寫作中,如果要有堅持,我們需要堅持的,也許就是始終“獨立思考”,就是“全面激活生命的勇敢”。
延伸閱讀

杏花村
文/黑陶
清明雨,又稱“潑火雨”。寒食禁火,其時之雨,稱為“潑火”。北宋宣城人梅堯臣有詩:“年年潑火雨,苦作清明寒。”在中國人的認知中,與清明關聯度最高的詩,應是唐代杜牧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首詩中的核心地點,是杏花村。
杏花村在中國何處?20世紀80年代,“杏花村”商標被各地爭奪。安徽貴池、山西汾陽、湖北麻城、江蘇南京等二十多地,紛紛參戰。幾番論證淘汰,最后唯剩安徽貴池和山西汾陽。兩家仍各不相讓,不惜對簿公堂。2006年9月13日,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發布第02795號《杏花村及圖商標異議裁定書》,就山西杏花村提出的異議案,國家商標局予以裁定如下:異議人所提異議理由不成立,安徽省杏花村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杏花村及圖”商標予以核準注冊。于是,現在的格局是:“杏花村”酒的商標權屬于山西汾陽,“杏花村”旅游的商標權屬于安徽貴池。
燒制漢語
作者: 黑陶 著
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6-04
在安徽池州人心中,杏花村,杏花深處的村莊,確定在現池州市貴池區秀山門外。他們認為,唐代西安人杜牧(803—約852),42歲時由黃州刺史移任池州刺史,在池州兩年,治所在當時的秋浦縣(今貴池),他的《清明》詩,就寫在池州任上。池州杏花村同樣有酒,目前正在打造的杏花村遺址處,仍存千年古井黃公井。據說該井為唐代杏花村黃公酒壚的酒主黃廣潤釀酒所用,此井:“香泉似酒,汲之不竭”。杏花爛漫的荒煙茅舍酒肆,依賴杜牧一詩而名垂千古。明代池州太守顧元鏡:“牧童遙指處,杜老舊題詩,紅杏添新色,黃壚憶舊時。”明人張邦教:“勝地已無沽酒肆,荒村忽有惜花人。”都是指此。杜姓,現在是貴池大姓,當地的杜氏宗祠,在貴池區茅坦鄉茅坦村,是杜姓遷居貴池的祖祠。2012年4月1日,“首屆2012清明公祭杜牧大典”活動在杏花村吟詩臺隆重舉行,當地媒體新聞:“杜氏后裔、池州大中小學校學生、景區游客及社會各界人士共3000余人參加了這次公祭杜牧大典。杏花村景區吟詩臺廣場豎起了4米高的杜牧像,擺起了香案、貢品。在莊嚴肅穆的氛圍中,公祭活動拉開帷幕,池州杜氏后裔、池州學院代表先后上臺發言和朗誦《清明》詩,社會各界代表分別向杜公像敬香。”
綠晝
作者: 黑陶 著
出版社: 鷺江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6-12
黃昏的池州城邊杏花村遺址文化旅游區內,有人氣很旺的“鵲橋會”飯店。店內宮燈亮彩,黃梅戲悠揚,中年婦女服務員一式古裝打扮,店堂還展示著昔日的花轎婚床。擁擠的一樓大堂邊側看實物點菜,賣相絕佳的紅燒肉已經賣光。點的菜中有特色“殺豬湯”和“糖炒糯米粑”。旁邊數桌正在辦升學酒,祝賀孩子考取“東湖學院”。夜晚和燈彩混雜的空間內,人聲菜香鼎沸。
(本文節選自《百千萬億冊書》,黑陶著,純粹pura出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12月)

黑陶,中國詩人、散文家,1968年出生于蘇、浙、皖三省交界處的一座陶瓷古鎮。母親是農民,父親是燒陶工人。在故鄉的火焰與大海之間,呼吸獨異的江南空氣。個人作品主要有“江南三書”:《泥與焰:南方筆記》《漆藍書簡:被遮蔽的江南》《二泉映月:十六位親見者憶阿炳》,以及散文集《夜晚灼燙》《中國冊頁》《燒制漢語》、詩集《在閣樓獨聽萬物密語:布魯諾?舒爾茨詩篇》《寂火》等。
原標題:《黑陶:在盛夏廣闊墨綠的玉米林中,倉頡墓地,寧靜安詳 | 純粹訪談》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