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劉慶邦散文集《到處有道》推出:用腳步丈量世界土地,用心靈譜寫生命贊歌

從河南到北京再到世界,行過很多地方的路,賞過很多地方的景,見過很多地方的人……作家劉慶邦用腳步丈量世界的土地,也用心靈譜寫生命的贊歌。
風景中蘊藏著天道、人道與心道,刻印在生命里,提供安穩、寧靜與滋養。“到處”是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道”是這每一個角落里不可言說又不言自明的情感與參悟。
正如作家韓浩月評論的那樣:“身為小說家的劉慶邦,和作為散文家的他,還是有不小區別的。劉慶邦的小說作品,有著專屬于他自己的腔調,他的小說時常通體散發著煤塊般的樸素之光,有著苦難的基調,但也有著樂觀主義的明亮。讀多了他的小說,再進入他的散文世界,于是便有了同老朋友對談般的親切,在《到處有道》中,讀者可以看到一個愛喝酒、愛旅行、愛談天,同時又低調、內斂的老頭兒。”“今年71歲的劉慶邦,把這本書當成了一杯酒,這杯酒的百般滋味,他分享了出來,希望‘飲酒者’,能借此酒杯,澆滅內心一二塊壘,得到‘到處有道理’‘到處有道路’‘到處有道義’的精神收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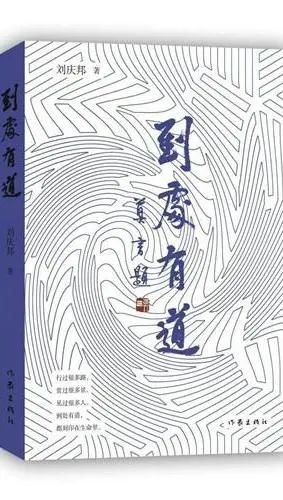
《到處有道》
作者:劉慶邦
作家出版社
在夜晚的麥田里獨行
已經是后半夜,我一個人在向麥田深處走。
人在沉睡,值夜的狗在沉睡,整個村莊也在沉睡,仿佛一切都歸于沉靜狀態。麥田上空偶爾響起布谷鳥的叫聲,遠處的水塘間或傳來一兩聲蛙鳴,在我聽來,它們迷迷糊糊,也不清醒,像是在發癔癥,說夢話。它們的“夢話”不但絲毫不能打破夜晚的沉靜,反而對沉靜有所點化似的,使沉靜顯得更加深邃,更加邈遠。
剛圓又缺的月亮悄悄升了起來。月亮的亮度與我的期望相差甚遠,它看上去有些發黃,還有些發紅,一點兒都不清朗。我留意觀察過各個季節的月亮,秋天和冬天的月亮是亮的,夏天的月亮質量總是不盡如人意。這樣的月亮也不能說沒有月光,只不過它散發的月光是慵懶的、朦朧的,灑到哪里都如同罩上了一層薄霧。比如月光灑在此時的麥田里,它使麥田變成白色的模糊,我可以看到密匝匝的麥穗,但看不到麥芒。這樣的月光談不上有什么穿透力,它只灑在麥穗表面就完了,麥穗下方都是黑色的暗影。
我沿著一條田間小路,自東向西,慢慢向里邊走。說是小路,在夜色里幾乎看不到有什么路徑。小路兩側成熟的麥子呈夾岸之勢,差不多把小路占嚴了。我每往里走一步,不是左腿碰到了麥子,就是右腿碰到了麥子,麥子對我深夜造訪似乎并不是很歡迎,它們一再阻攔我,仿佛在說:深更半夜的,你不好好睡覺,到我們這里來干什么!窄窄的小路上長滿了野草,隨著麥子成熟,野草有的長了毛穗,有的結了漿果,也在迅速生長、成熟。我能感覺到野草埋住了我的腳,并對我的腳有所糾纏,我等于蹚著野草,不斷擺脫羈絆才能前行。面前的草叢里陡地飛起一只大鳥,在寂靜的夜晚,大鳥拍打翅膀的聲音顯得有些響,幾乎嚇了我一跳,我不知不覺站立下來。我不知道大鳥飛向了何方,一道黑影一閃,不知名的大鳥就不見了。我隨身帶的有一支袖珍式的手電筒,我沒有把手電筒打開。在夜晚的麥田里,打手電是突兀的,我不愿用電光打破麥田的寧靜。
我們家的墓園就在村南的這塊麥田里,白天我已經到這塊麥田里看過,而且在沒腰深的麥田里佇立了好長時間。自從1970年參加工作離開老家,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在麥子成熟的季節回過老家,再也沒有看到過大面積金黃的麥田。放眼望去,金色的麥田向天邊鋪展,天有多遠,麥田就有多遠,怎么也望不到邊。一陣風吹過,麥浪翻成一陣白金,一陣黃金,白金和黃金在交替波涌。陽光似乎也被染成了金色,麥田和陽光在交相輝映。請原諒我反復使用金這個字眼來形容麥田,因為我想不出還有哪個高貴的字眼可以代替它。然而,如果地里真的鋪滿黃金的話,我不一定那么感動,恰恰是黃土地里長出來的成熟的麥子,才使我心潮澎湃,感動不已。那是一種生命的感動,深度的感動,源自人類原始的感動。它的美是自然之美,是壯美、大美和無言之美。它給予人的美感是詩歌、繪畫、音樂等藝術形式所不能比擬的。

白天看麥田沒有看夠,所以在夜深人靜時我還要來看。白天為實,夜晚為虛,陽光為實,月光為虛,我想看看虛幻環境中的麥田是什么樣子。站在田間,我明顯感覺到了麥田的呼吸。這種呼吸在白天是感覺不到的。麥田的呼吸與我們人類的呼吸相反,我們吸的是涼氣,呼的是熱氣,而麥田吸進去的是熱氣,呼出來的是涼氣。一呼一吸之間,麥子的香氣就散發出來。麥子濃郁的香氣是原香,也是毛香,吸進肺腑里讓人有些微醉。晚上沒有風,不見麥浪翻滾,也不見麥田上方掠來掠去的燕子和翩翩起舞的蝴蝶。仰頭往天上找,月亮升高一些,還是暗淡的輪廓。月亮灑在麥田里的不像是月光,滿地的麥子像是鋪滿了灰白的云彩。一時間,我產生了錯覺,以為自己站在云彩里,在隨著云彩移動。又以為自己也變成了一棵小麥,正幽幽地融入麥田。為了證明自己沒變成小麥,我掐了一枝麥穗兒在手心里搓揉。麥穗兒濕漉漉的,表明露水下來了。露水濕了麥田,也濕了我這個從遠方歸來的游子的衣衫。我免不了向墓園注目,看到栽在母親墳側的柏樹變成了黑色,墓碑樓子的剪影也是黑色。
從麥田深處退出,我仍沒有進村,沒有回到我一個人所住的我家的老屋,而是沿著河邊的一條小路,向鄰村走去。在路上,我想我也許會遇到人。夜行的人有時還是有的。然而,我跟著自己的影子,自己的影子跟著我,我連一個人都沒遇到。河上有一座橋,我在那座橋上站下了。橋的位置沒變,只是由磚橋變成了水泥橋。橋下還有水,只是由活水變成了死水。映在水里的紅月亮被拉成紅色的長條,并斷斷續續。青蛙在浮萍上追逐,激起一些細碎的水花兒。
到周口市乘火車返京前,我和作家協會的朋友們一塊兒喝了酒。火車開動了,我還醉眼蒙眬。列車在豫東大平原的麥海里穿行,車窗外金色的麥田無邊無際,壯觀無比。我禁不住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說大平原上成熟的麥子是全世界美的景觀,你想象不到有多么好看,多么震撼……我沒有再說下去,我的喉嚨有些哽咽。

打麥場的夜晚
別看我離開農村幾十年了,每到初夏麥收時節,我似乎都能從徐徐吹來的南風里聞到麥子成熟的氣息。特別是近幾年,我在北京城里還聽到了布谷鳥的叫聲。布谷鳥季節性的鳴叫,沒有口音上的差別,與我們老家被稱為“麥秸垛垛”的布谷鳥的叫聲是一樣的。我想這些布谷鳥或許正是從我們老家河南日夜兼程飛過來的,它們仿佛在提醒我:麥子熟了,快下地收麥去吧,老坐在屋里發呆干什么!
今年芒種前,我真的找機會繞道回老家去了,在二姐家住了好幾天。我沒有參與收麥,只是在時隔四十多年后,再次看到了收麥的過程。一種大型的聯合收割機,在金黃的麥田里來來回回穿那么一會兒“梭”,一大塊麥子眼看著就被收割機剃成了平地。收麥過程大大簡化,勞動量大大減輕,這是農業機械化帶來的好處,當然值得稱道。回想當年我在生產隊里參加收麥時,從造場、割麥、運麥,再到曬場、碾場、揚場、看場,直到垛住麥秸垛,差不多需要一個月的時間。且不說人們每天頭頂炎炎烈日,忙得跟打仗一樣,到了夜晚,男人們也紛紛走出家門,到打麥場里去睡。正是夜晚睡在打麥場的經歷,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初中畢業回鄉當農民期間,麥收一旦開始,我就不在家里睡了,天天晚上到打麥場里去看場。夏天農村的晚飯,那是真正的晚飯,每天吃過晚飯,差不多到了十來點,天早就黑透了。我每天都是摸黑往場院里走。我家沒席子可帶,我也不帶被子,只帶一條粗布床單。場院在村外的村子南面,兩面臨水,一面連接官路,還有一面挨著莊稼地。場院是長方形,面積差不多有一個足球場那么大,看上去十分開闊。一來到場院,我就脫掉鞋,把鞋提溜在手里,光著腳往場院中央走。此時的場面子已打掃得干干凈凈,似乎連白天的熱氣也一掃而光,腳板踩上去涼涼的,感覺十分舒服。我給自己選定的睡覺的地方,是在臨時堆成的麥秸垛旁邊。我把碾扁的、變得光滑的麥秸往地上攤了攤,攤得有一張床那么大,把床單鋪在麥秸上面。新麥秸是白色,跟月光的顏色有一比。而我的床單是深色,深色一把“月光”覆蓋,表明這塊地方已被我占住。
占好了睡覺的位置,我并沒有急著馬上躺下睡覺,還要到旁邊的水塘里撲騰一陣,洗一個澡。白天在打麥場上忙了,渾身沾滿了麥銹和碾碎的麥芒,毛毛糙糙,刺刺撓撓,清洗一下是必要的。我脫光衣服,一下子撲進水里去了,雙腳砰砰地打著水花,向對岸游去。白天在烈日的烤曬下,上面一層塘水會變成熱水。到了晚上,隨著陽光的退場,塘水很快變涼。我不喜歡熱水,喜歡涼水,夜晚的涼水帶給我的是一種透心透肺的涼爽,還有一種莫測的神秘感。到水塘里洗澡的不是我一個,每個在場院里睡覺的男人幾乎都會下水。有的人一下進水里,就興奮得啊啊直叫,好像被水鬼拉住了腳脖子一樣。還有人以掌擊水,互相打起水仗來。在我們沒下水之前,水面靜靜的,看上去是黑色的。天上的星星映在水里,它們東一個西一個,零零星星,誰都不挨誰。我們一下進水里就不一樣了,星星被激蕩得亂碰亂撞,有的變大,有的變長,仿佛伸手就能撈出一個兩個。

洗完了澡,我四仰八叉躺在鋪了床單的麥秸上,即刻被新麥秸所特有的香氣所包圍。那種香氣很難形容,它清清涼涼,又轟轟烈烈;它滑溜溜的,又毛茸茸的。它不是撲進肺腑里就完了,似乎每個汗毛孔里都充滿著香氣。它不是食物的香氣,只是打場期間麥草散發的氣息。但它的香氣好像比任何食物的香氣都更原始、更醇厚,也更具穿透力,讓人沉醉其中,并深深保留在生命的記憶里。
還有夜晚吹拂在打麥場里的風。初夏晝夜的溫差是明顯的,如同水塘里的水,白天的風是熱風,到夜晚就變成了涼風。風是看不見的,可場院旁邊的玉米葉子會向我們報告風的消息。玉米是春玉米,長得已過了一人高。寬展的葉子唰唰地響上一陣,我們一聽就知道風來了。當徐徐的涼風掠過我剛洗過的身體時,我能感覺到我的汗毛在風中起伏搖曳,洋溢的是一種酥酥的快意。因打麥場無遮無攔,風行暢通無阻,細腿蚊子在我們身上很難站住腳。我要是睡在家里就不行了,因家里的環境幾乎是封閉的,無風無息,很利于蚊子在夜間活動。善于團隊作戰的蚊子那是相當地猖獗,一到夜間就在人們耳邊輪番呼嘯,任你在自己臉上抽多少個巴掌都擋不住蚊子的進攻。我之所以愿意天天夜間到打麥場里去睡,除了為享受長風的吹拂,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為了躲避蚊子。

沒有蚊子的騷擾,那就趕快睡覺吧,一覺睡到大天光。然而,滿天的星星又碰到我眼上了。是的,我是仰面朝天而睡,星星像是紛紛往我眼上碰,那樣子不像是我在看星星,而是星星在主動看我。星星的眼睛多得鋪天蓋地,誰都數不清。看著看著,我恍惚覺得自己的身體在往上升,升得離星星很近,很近,似乎一伸手就能把星星摘下一顆兩顆。我剛要伸手,眨眼之間,星星卻離我而去。有流星從夜空中劃過,一條白色的軌跡瞬間消失。天邊突然打了一個露水閃,閃過一道像是長滿枝杈的電光。露水閃打來時,群星像是隱退了一會兒。電光剛消失,群星復聚攏而來。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時候睡著的,在睡夢里,腦子里仿佛裝滿了星星。
現在不用打場了,與打麥場相關的一切活動都沒有了,人們再也不會在夜晚到打麥場里去睡。以前我對“時過境遷”這個詞不是很理解,以為境只是一個地方,是物質性的東西。如今想來,境指的主要是心境,是精神性的東西。時間過去了,失去的心境很難再找回。
原標題:《劉慶邦散文集《到處有道》推出:用腳步丈量世界土地,用心靈譜寫生命贊歌》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