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卡爾·雅斯貝爾斯:用生存哲學探求生命的真諦
存在主義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雖然當前已漸式微,但依然是西方哲學的主流,也正是這一點,了解存在主義也更有助于了解當今世界的主要精神狀況。
不過,鑒于被奉為存在主義代表的海德格爾在行文上的晦澀,以及前存在主義的代表克爾凱郭爾的神秘、尼采的癲狂,存在主義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都是難以理解的。

同時,也正是由于這種難以理解,會讓諸多的各種觀念頂著存在主義的帽子、以其鮮艷的觀感,沖擊著人們的思想。存在主義既像是個萬花筒,看進去會折射出不同的光彩,又像是一個世界郵筒,被塞進去五花八門的新鮮理念供人取用。
在存在主義的陣營里,卡爾·雅斯貝爾斯承襲克爾凱郭爾和尼采,并在海德格爾之前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生存哲學”,相對來說,雅斯貝爾斯的思想更貼近現實并更容易理解,所以從對他的理念的理解中,也能夠一窺存在主義的究竟。
存在主義:從神到人的回家之路
即便是在今日,每一個生活在現代世界中的人,依然會不時產生一種虛無、無家可歸的感受。在高速發展的科技和物質文明之下,狂奔的人們總會在偶爾的喘息時間里去思索人生的意義。這仿佛是華麗的現代世界的一道舊時的傷疤,哪怕是如今文明社會極力的用某些眼花繚亂的裝飾將其掩蓋,也無法真正徹底的解決這個問題。
將時間倒回百余年,也就是這個傷疤剛剛形成的階段,在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之后,伴隨著一戰的全球化發展,帶來了世界性的繁榮,也同時絞碎了宗教這一人類依存了上千年的精神寄托。

現代世界的人,被逐出神的伊甸園,被迫在世俗的世界里尋找人生的終極意義。但面對工業革命后平均化、機械化、大眾化的時代,任何人似乎都可以由其他人完全替代的時代,人能作為獨特的自身實際存在。
也正是這樣的背景下,存在主義,作為迎合當時大眾的心理需求,在神被祛魅之后,承擔起了為人們尋找破碎現代世界中的精神家園的作用,畢竟在失去了神的庇護后,人生的意義就無法寄托在來世或者天堂之中,而深陷于瑣碎的日常生活的人們,面對注定的有限生命時,虛無感必然會在反思中占據上風,這時就需要一種能夠在塵世獲得對人生超越的智慧和理論。
生存哲學:探索人存在可能性的交流之道
雅斯貝爾斯在《時代的精神狀況》中對其生存哲學做了最廣義的定義:“生存哲學是利用一切事實的知識的、然而又是超越性的思維,由于此,人想要成為他自己。這種思維不認識對象,而是同時澄明和獲得如此思維的人的存在,由于它超越了一切確定存在的世界知識,因而(作為哲學關于世界的態度)它是飄忽不定的;然而也因為此,它(作為存在的澄明)呼喚著自由,并且(作為形而上學)通過召喚超越而創造它無條件行動的空間。”
這似乎很難讓人理解,實際上,雅斯貝爾斯的“生存哲學”就是“關于生存的惡哲學”。作為關于生存的哲學他構建了兩個空間:其一是廣闊的空間,在此間雅斯貝爾斯追問的是一切現實對于生存的意義;而還有一個狹隘的空間,在此間,他探索什么是生存,生存是如何生成的以及人是如何體驗到生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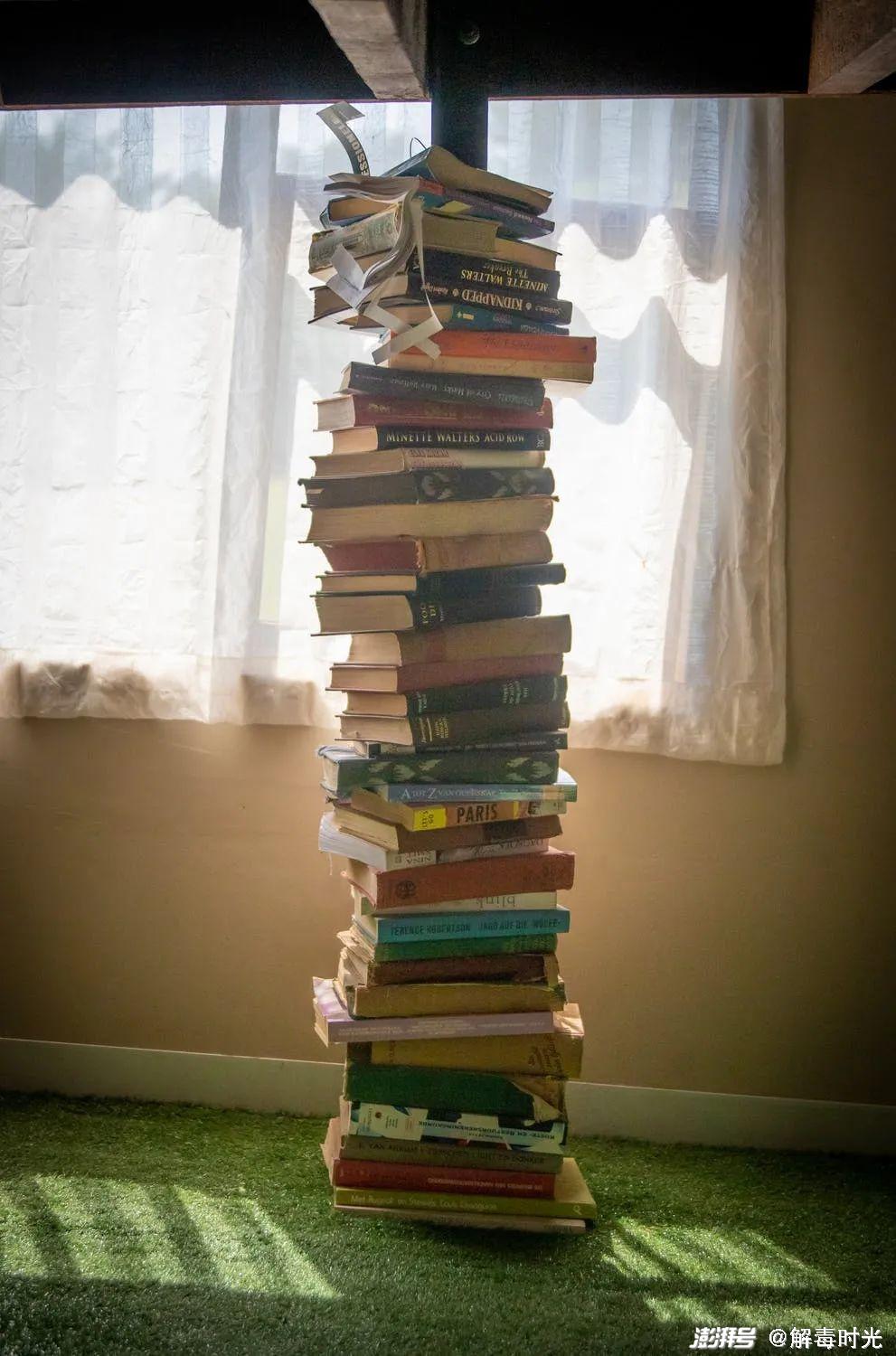
基于此目標,雅斯貝爾斯從最基本的人生體驗中,將人的存在方式劃分出四個層級,分別是此在、一般意識、精神和生存。
此在是人的肉體存在,即生物學意義上的人的生命,包括人的本能和沖動,是最低一級的人的存在方式;一般意識是知性,是人進行認識和邏輯思考的能力與可能性,是一切個別意識現象中的同一意識;精神是人在此在和一般意識的基礎上達到的理念和價值觀之總體;生存是人最高一級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真存在。
與前三個層級不同,它無法從經驗的角度進行把握。雅斯貝爾斯將人的自我存在稱之為生存,“不是如是存在,而是能存在,即,我不是生存,而是可能的生存,我不擁有自身,而是趨向自身。”關于這種無法把握,后文會詳細展開,這關聯到雅斯貝爾斯的一個重要概念“統攝”。

在《生存哲學》中,雅斯貝爾斯,這樣說明其哲學“在本源中洞察現實,通過我如何在思想中與我自身相關的方式,亦即在內在行為中把握(理解)現實。從關于什么的單純知識、從語言風格或說話方式、從各種風俗常規和魚線設定,總而言之,哲思要從所有的表面現象回到現實。”
對于這樣的目標,克爾凱郭爾指出了重點:一切本質上是現實的東西,它對我而言存在,只因我是我自身。我們不僅在此實際存在,我們的實存作為我們的本源得以實現的地方、作為身體,已經被給定我們,并為我們所熟悉。
19世紀,上述意義的思想運動已經反復出現。人們想要“生活”、意求“體驗”。人們要求“實在論”,要求親身經驗,而非單純的認識。人們處處追求“真切”、尋求“各種本源”,想要向人自身推進。
雅斯貝爾斯明確的說,二十世紀是一個覺醒的時代,能夠自身存在的人們已經覺醒。他們想要重視自己、認真坦誠自身,他們尋求已被遮蔽了的現實,他們想要認識可以被認識的東西,他們以其自身理解來思考,從而達到他們的根據所在。
總的來說,生存是雅斯貝爾斯生存哲學的核心,它是開放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以自由為基礎,其本身也象征著自由。而那些覺醒的人如何才能實現生存,實現自我存在?雅斯貝爾斯認為,自我存在展現在交流之中,只有與他人一同處于交流之中,我才能意識到自我存在,如果我是孤立存在的,那么我的自我存在就會終止。生存在交流中實現自身,因此,雅斯貝爾斯的生存哲學也是關于交流的哲學。

雅斯貝爾斯認為,哲學起源雖然是在自我驚異、懷疑以及對臨界情況的體驗中,但最終包括這一切的在于尋求真正交流的意志里。這一點從一開始就看得出來,因為一切哲學都急于傳達、訴說自己,以及讓自己被傾聽,其本質便是可傳達性本身,而這一可傳達性又是與真理的存在不可分的。
“唯有在交流中,哲學的目的才能實現,所有目的之意義最終都根植于交流:對存在的領悟,對愛的澄明,寧靜的完美境界。”
“統攝”概念:為生存開創可能的空間
在雅斯貝爾斯的“生存哲學”中,有一個必須理解但卻對每一個正常的思維來說都異常困難的概念——“統攝”(das Umgreifende)。在德語中,這個詞的意思是“主客體之大全”,所以在中文翻譯中,也被稱為“大全”或“成全”。
首先看看雅斯貝爾斯是如何解釋這個概念的,他利用人思維經驗中可以確認的共同的東西,去探索這個世界真實的存在狀況。他認為我們所思考和所談及的事物是跟我們自身不同的,他們是作為主體自身的對象:客體。
如果我們把自己作為思想對象來看待的話,那我們就會變成其他了,但同時作為一個正在思考的我也一直存在,這個正在指使著這一思考的我,是不可以等同于一般的客體的,因為他是決定其他之所以成為客體之前提。
雅斯貝爾斯把我們思維著的此在的基本狀況稱為“主客體分裂”,也就是起初為一體的東西被撕裂開來的情形,在這里他強調的是起初未分裂的狀況,而這一起初未分裂的東西就被雅斯貝爾斯稱作統攝。
由于認識的對象是在主體客體分裂之中被構成的,那么一切的認識也只有在這一分裂后才能成為可能,這一認識的領域便是存在物的領域。而存在卻超越了這所有的存在物,它既非主體亦非客體,是分裂前的統一狀態。雅斯貝爾斯曾說“存在就是統攝”。

《雅斯貝爾斯傳》的作者漢斯·薩尼爾認為“統攝”至少有兩種含義:
其一,“統攝”完全是對無形物形象生動的描述詞匯,我們不可以把它誤解為有限的存在物。譬如把它想象成某種圓形的、隱匿狀的或有某種外殼狀的東西,進而形成有限的、包容性的想象,這一切必須由無限統攝的抽象思想予以取代。
其二,由于統攝不在分裂狀態之中,故而它是不可認識的。它是未被確定之議題。那么我們應當對其保持沉默嗎?如此絕望之結論雅斯貝爾斯并未得出,而是說:如果人們同樣不能認識統攝的話,卻能澄明它,澄明是一種無需解釋之清晰,是一種無需用規定性進而到達被思物之思忖,是一種無需去知道之證實。
即便是經過如此多的解釋,“統攝”到底是什么,以及提出這個概念究竟對于現實有什么意義?

如果對于康德哲學有所了解的話,就會發現,雅斯貝爾斯的“統攝”跟康德的“物自體”非常像,不過用康德來去解釋雅斯貝爾斯,就仿佛用一個更難的體系來去替換了需要解釋的體系,所以以下就嘗試用一些通俗簡單的語言,對統攝的概念內涵以及作用做出解讀。
科學強大之后,人們常常會產生一個直觀的想法,這世界是可以被完全認識的、被完全理解的,以至于在此基礎上,可以被完全操縱。如果說在蒙昧時代,人的思想是信仰占據主導地位,那么在科學時代,就是認識占了主導地位。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會逐漸出現極端的狀況,人將全部的信仰驅逐出了頭腦,并產生一種狂妄的自大——人必然會駕馭自然,并以替代對神的崇拜。但如此一來,人就會陷入一種對認識的無限追逐中,同時由于自身生命的有限性,這二者之間就會形成一股漩渦,把人吸引進虛無的深淵,因為一旦意識到在有限的生命中要完成一個認識到無限自然的不可能的任務時,人難免會瀕臨絕望。
與此同時,純粹的科學式的思維,會帶來直接的因果觀念,并把道德等精神內涵驅逐出人的思維體系,極端的情況下,就會讓人變成一個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機器,而失去了自身更高、更具超越性的思想。
康德的“物自體”的概念,強調的就是我們所認識到的客體,并不是真實的客體,而是我們感官對“物自體”的反應,物自體是無法被真正認識到的。借此,康德在認識當中為信仰留出了一個空間,當我們知道認識是有界限有效力的情況下,就會保持對自然、對人類社會的敬畏,用信仰、道德來去填補那些無法認識到的地方。
同樣,雅斯貝爾斯的“統攝”,也是指“存在”是主體和客體的統一,我們認識到的客體,只是被主體客體化了的存在,比如我們看到的花,只不過是人的眼睛所感受到的一種現象,如果用現代科技,換成在X射線下,鮮花就會變成了另一個樣子。
但雅斯貝爾斯與康德不同的地方在于,物自體強調的是認識的局限,認為有很多是人的認識無法達到的。統攝則強調人是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去看待存在,存在就是所有這些角度的綜合,就像盲人摸象,最終那個象雖然不能被完全的真實的認識到,但只要摸的人足夠多,那么就會更接近“真相”。

基本上,這就是統攝概念的通俗含義。那么這個概念提出來又有什么用呢?
這時就要把黑格爾拉出來,在黑格爾的歷史觀中,世界是有一種明確的動力和目標的,最終會朝向一個明確的方向。馬克思正是借鑒了這個思路,得出了他獨特的結論,一種必然的、注定的歷史方向。
而雅斯貝爾斯的“統攝”則會給我們帶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強調了事物的多種可能性,倡導在多元化的視角下,對存在的多重理解的綜合。這樣的觀念里,歷史就不會是一個循著某一個必然的方向前進的事件集合,而是能夠被無限打開的存在空間。歷史失去了其明確的方向,而換來了無限的可能。
正如薩特對存在主義的總結——存在先于本質,即對人存在的頌揚背后的對自由的肯定,雅斯貝爾斯的生存哲學,不僅把自由賦予了個體,也把自由賦予了人類的整體。

個人的經歷,可以由自我來創造,面向個體展開一個生存的可能性空間。而全體的經歷,也就是歷史,也同樣是群體共同創造的,它并不會注定朝著某一個方向發展,未來的歷史,也是一個面向所有人開放的可能性空間,在那里,人把對自由的承諾,兌換成現實的存在。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