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錢一棟讀《不正義的多重面孔》|不正義感與哲學的限度

《不正義的多重面孔》,[美]朱迪絲·N.施克萊著,錢一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233頁,40.00元
在正義理論的巔峰年代思考不正義
施克萊的學術研究一向反潮流。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意識形態終結論在西方學界甚囂塵上。施克萊獨辟蹊徑,以意識形態專家的身份寫了一本“法學書”(《守法主義》,1964),不僅嘲諷哈耶克,點破法哲學中的世紀爭論“哈特-富勒之爭”只是同個屋檐下的小打小鬧,還超越這些法學個案,作了一項極具洞察力的時代診斷:以法治為代表的去道德化、去政治化話語,只是一種“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是冷戰語境下西方的特定意識形態反應。1981年,麥金太爾的《追尋美德》出版,美德倫理學復興浪潮走向頂峰。施克萊依然不走尋常路,寫了《平常的惡》(1984)這樣一本怎么看都不像政治理論的政治理論著作,從惡習性(vices)入手來思考自由主義社會的公民品格問題。
《不正義的多重面孔》(1990)也是一本反潮流之作。上世紀八十年代,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獨步學林,社群主義思潮也如日中天。社群主義基本靠批判羅爾斯起家,因此也免不了把正義作為最重要的研究主題。除了查爾斯·泰勒,其他幾位社群主義巨匠的政治哲學代表作,名字里都帶著正義:桑德爾的“出道即巔峰”之作《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1982),沃爾澤致力于將正義“化一為多”的《正義諸領域》(1983),以及麥金太爾那本名字被套用濫了的《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1989)。
1986年,施克萊在一本名家薈萃的文集上發表長文《不正義、傷害與不平等:一個導論》(“Injustice, Injury, and Inequ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Justice and Equality Here and Now, edited by Frank Lucas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引來時任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圭多·卡拉布雷西的講座邀請。施克萊于1988年作了斯托爾斯法理學講座,這是耶魯法學院最古老也是最富盛名的講座,本杰明·卡多佐的《司法過程的性質》、羅斯科·龐德的《法哲學導論》以及朗·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等法理學名作都源自斯托爾斯講座講稿。《不正義的多重面孔》便是以這次講座為基礎,吸收了昆廷·斯金納、斯坦利·霍夫曼以及沃爾澤等人的意見后修改而成的。

《正義與平等——此時此地》
施克萊絕不是簡單在羅爾斯和社群主義者之間選邊站。相反,她把他們放在同一個標簽下進行批判。她認為,一直存在一種思考正義的主流模式,它以亞里士多德的相關論述為典范,綿延兩千年,直至當代的羅爾斯與沃爾澤。她將這種思考模式稱為“常規正義模式”(《不正義的多重面孔》中譯本,34頁),認為其低估了不正義的復雜性和重要性。她把自己歸入以柏拉圖、奧古斯丁和蒙田為代表的懷疑主義傳統,致力于揭示主流正義理論的傲慢無知。書名“不正義的多重面孔”想要表達的便是,常規模式對不正義的理解太過簡單,必須以一種“更直接、更深入、更關注細節”(33頁)的方式,重啟對不正義現象的思考。

朱迪絲·N. 施克萊(Judith N. Shklar, 1928-1992),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歷任美國政治學與法哲學協會主席、美國政治科學協會主席。圖為1966年《哈佛年鑒》所刊施克萊照片。
區分不幸與不正義
“在什么時候,一場災難只是一件不幸之事,什么時候它是不正義之事?”(第1頁)施克萊以這樣一個問句開啟了全書的討論。
按一般看法,答案顯而易見:“如果這一可怕事件是由外在的自然力量導致的,那它就是不幸之事,我們必須忍受自己的苦難。假若它是居心不良的行動者——無論是人還是超自然的存在者——引發的,則它屬于不正義之事,我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憤慨與怒火。”(同前引)這種普通人略加思索就會得出的觀點可被稱為“起因模式”,它根據災難的起因是自然事件還是社會事件來區分不幸與不正義。
“起因模式”顯然是個非常粗陋的答案,施克萊對它的批評大致可歸結為這樣一個命題:自然不一定必然,相反,許多自然災害是事先可防、事后可控的。這個道理不難理解。臺風、洪水等自然災害已經可以準確預報。即便是地震這類尚難及時預測的災難,也可以通過各種措施來減輕其災害程度。此外她也提到,文化或者說社會因素不見得完全人為可控,但對此并未多作展開。因此,自然和人為的區分并沒有太大意義。科技的發展打破了“自然”與“必然”之間的牢固關聯,社會科學的進步則讓我們看到了,人難以徹底走出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化的控制力也許比自然更強。
這個問題還與意識形態立場相關。鼓吹小政府的經濟學家大概會把大量源于政府不作為的災難界定為不幸。因為按他們的看法,政府本就沒有,也不應該承擔這樣那樣的義務。
“起因模式”僅僅將行動者直接施加的傷害看作不正義,因此會把大量不正義行為界定為不幸,進而引發消極不正義現象。
消極不正義是施克萊濃墨重彩渲染的一個概念,是她在“不正義的多重面孔”中最關注的一個面孔。什么是消極不正義呢?它區別于積極主動施加的傷害,表現為面對他人的苦難,站在一邊什么都不做。消極不正義者往往會訴諸必然性話語,表示“這也沒什么辦法”“這就是生活”,非常心安理得。真的“沒什么辦法”嗎?施克萊不這么認為。她在書中專門用了一節篇幅檢討各種必然性話語,特別是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理論。
施克萊把消極不正義概念追溯至西塞羅,后者的相關討論發生在羅馬共和國的語境中。施克萊承接西塞羅的思考,將消極不正義限定為一種“公民觀念”(76頁),亦即將其視作公民品質的缺陷,而非某種普遍的人性惡。因此和許多道德概念不同,不是隨便哪個人都會遭受“消極不正義”指控。它專門適用于那些生活在比較理想的社會之中的公民。這道理也不難理解:在某些社會,人們時刻生活于恐懼之中,我們不能苛求他們站出來幫助別人;不同流合污積極施加傷害就算不錯了。簡言之,生活在不同社會的人,站出來為自己的公民同伴主持公道、排憂解難的“道德成本”不同。理想社會的一個關鍵標志便是,不會讓人頻繁陷入道德困境,能夠比較輕松地做一個好人。
施克萊這本書談的主要是美國(12頁)。就消極不正義而言,施克萊認為美國人最大的問題是在發生災難后,熱衷于追責/甩鍋,忽視善后工作。這一指控可能僅適用于美國等少數國家。在其他國家,防止消極不正義的關鍵也許恰恰是積極批評追責。
三個模式
拜施克萊有意追求的松散文風所賜,此書沒能明確區分“起因模式”和“常規正義模式”。根據其論述,我們大致可以這樣理解兩者的區別:“起因模式”基于未經深入反思的常識觀念,給出了區分不幸與不正義的一組具體標準,“常規正義模式”則是思考正義/不正義問題的一般方式、標準步驟。許多人對具體的區分標準可能看法不同,但他們的思考都遵循這一模式。因此可以認為,“起因模式”只是“常規模式”的一個具體版本。
“常規模式”是如何思考正義/不正義的呢?它專注于正義,認為不正義只是正義的缺席。按亞里士多德的經典論述,正義的核心表現是遵守規則,特別是法律規則,以確保每個人獲得、保有其應享份額。羅爾斯說得透徹:“亞里士多德的定義顯然預先假定了什么是應屬于誰的,什么是他應得的份額的解釋。”([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簡言之,“常規模式” 預設了應得觀念。所謂正義,就是在假定現有規則符合合理應得觀念的前提下堅守規則,違背規則即不正義。
除了“起因模式”,我們還可以從施克萊的散亂論述中提煉出“常規模式”的另一特殊版本,將其命名為“共識模式”。“共識模式”用社會共識來為規則奠基,主張某些規則體現了“我們”——特定歷史文化共同體成員——最深刻的信念,因此是“我們”真正認同也真正可取的。“共識模式”的有效運作因此依賴于社會的高度同質性:在“誰應得什么”這一根本問題上,整個社會擁有共識,雖然可能是有待詮釋的共識。
施克萊在書中著重批判了自己的親密好友沃爾澤的共識觀,認為所謂共識,只是社群主義理論家在自身意識形態立場的引導下,通過隨意解釋社會成員的想法創造出來的幻象。相比各路乍看高深莫測的理論,施克萊的批評平白直接,但卻極具力度:
民族精神的先知式化身或傳統主義化身領悟到了共享意義的諸種意涵,他們從不會拿這些意涵去和實際存在的看法——尤其最不利者和遭受恐嚇者的看法——進行比對。將共有文化與和諧一致的政治利益相混淆只是一種障眼法。通常來說,文化共享的是語言,除了表達別的東西,如果我們敢于表達的話,語言還可以使我們表達對彼此的厭惡和鄙視以及不正義感。如果處于社會中最不利地位的成員無法清晰、自由地說明他們的感受,那么我們應該假定他們怨恨自己的處境,哪怕他們——就像許多黑奴那樣——又笑又唱顯得心滿意足。(206-207頁,更詳細的論證參見Judith Shklar, “Squaring the Hermeneutic Circle,” and “The Work of Michael Walzer,” in Stanley Hoffmann ed.,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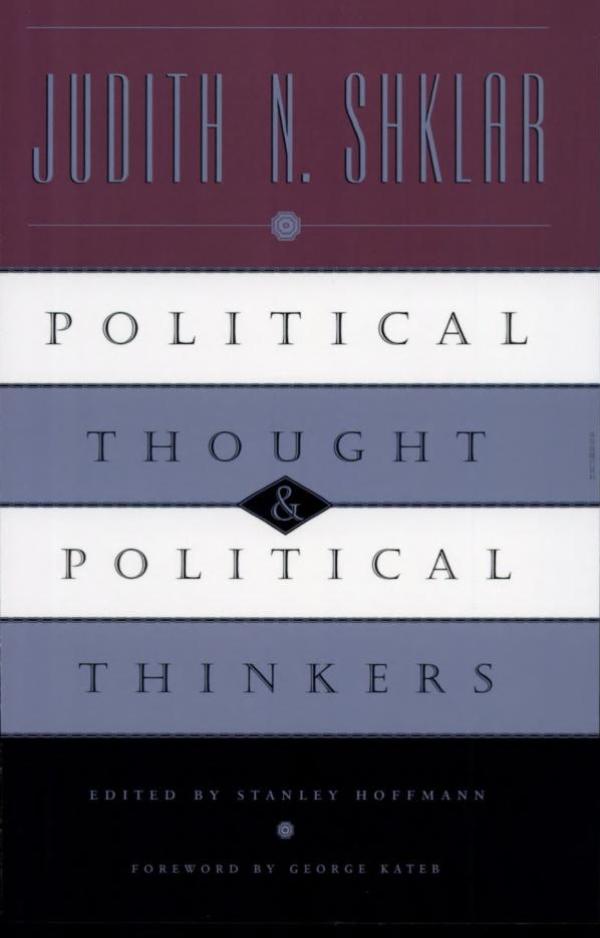
《政治思想與政治思想家》
順便一提,施克萊還對羅爾斯作過類似批評。眾所周知,羅爾斯的前期理論有較為明顯的普遍主義色彩,后期理論則限縮為一種地方性辯護方案,即在西方現代民主社會的語境下,力圖說服觀念各異的人們接受同一套稀薄的政治正義觀念。可以不太嚴謹地說,羅爾斯的后期理論是在提煉宗教改革以來西方社會的政治道德經驗。在一封寫給羅爾斯的信中,施克萊指出,羅爾斯的后期理論依賴于這樣一個假設:這樣的社會中存在價值共識(雖然只是非常稀薄的重疊共識)。她認為,羅爾斯需要給出歷史證據來證明這一點,而這一任務無比艱巨(Hannes Bajohr, “The Sources of Liberal Normativity,” in Samantha Ashenden and Andreas Hess ed., Between Utopian and Realis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udith N. Shkl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9, p. 166)。施克萊總是對共識的虛假性、壓迫性格外敏感,哪怕是具有自由主義屬性的共識。
常規模式的問題及施克萊的開放性方案
“常規模式”有鮮明的司法化特征,其基本邏輯可以這樣拆解:公認的規則規定誰對誰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于是相關主體有了義務,有了正當期待:做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所謂不正義,便是不該做的做了,或該做的沒做。據此,受害人的主觀感受(不正義感)并不重要,正如在司法審判中當事人的感受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規則和事實。
問題是,誰來制定規則?誰來判定規則是否被違反了?
施克萊特別關注第一個問題。她認為,在多元社會堅持要找到“一套”規則體系是不可取的。她說,“……我們還是那么無知且多樣,不適合任何單一的規范體系”(50頁),“昨日堅如磐石之規則如今只顯得愚頑”(16頁)。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主流規則體系帶有壓迫性和欺騙性。所謂的正確規則,往往只是符合強者利益的規則,是對強凌弱的意識形態包裝。施克萊引用了蒙田的一句話來說明這一點:“當女人拒絕這些世上通行的生活規則時,絕不該去責備她們,因為是男人在未經她們同意的情況下制定了這些規則。”(194-195頁)因此,按施克萊的看法,常規模式不僅無法消解不正義感,還會否認不正義感的存在,乃至否認其正當性,進而助長消極不正義。
任何通情達理的人都會承認,有一些主流規則體系,特別是已經被歷史淘汰的規則體系,確實帶有壓迫性和欺騙性。但問題是,一切規則體系都如此嗎?多大程度上如此呢?誠然,無論適用何種規則體系,都會有人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受害者”的不正義感會不會只是一種無根無據的主觀感受,是遇事習慣抱怨者的無聊牢騷?
約翰·密爾便認為,不正義感只是一種情緒反應,在未經仔細考察之前不能判定其道德屬性(170頁)。而在尼采眼里,不正義感更是一種“群畜的怨恨”(184頁),完全不足掛齒。
施克萊以“不是民主思想家,輕視沒受過教育的大多數人”“庸俗的歷史神話”(170、185頁)等大而化之的評判,輕易打發了密爾和尼采對不正義感的質疑。她幾乎是不加論證地認可了她眼中“民主理論最偉大的代表”(160頁)盧梭的立場。盧梭認為,受害者的不正義感“內在、自然地就是準確的”(167頁)。施克萊雖然要比盧梭節制一些,沒有天真地相信心懷不正義感的人必然占理,但她愿意推定這一點,優先聽取受害者的聲音。她寫道:
如果說民主確有道德含義的話,那就是下面這些:民主意味著所有公民的生活都很重要,意味著他們的權利感必須被認可。最不濟每個人也都得有表達觀點的機會,公民們感知自己所在社會中的和個人生活中的不平之事的方式不能被忽視。(66頁)
積極聆聽受害者的聲音是一個涉及民主原則的大問題。民主的價值根基是平等尊嚴觀念,這一觀念使普通人的不正義感覺變得敏銳、不正義感受變得重要。而在等級制時代,被壓迫者相對“安分守己”“樂天知命”,其不正義感既沒那么容易被觸發,也不會被嚴肅對待——在“統治階級”思想家眼中,這雖是一種值得關注的政治風險,但并沒有道德層面的重要性。
和施克萊的其他作品一樣,《不正義的多重面孔》也是一本沒有明確結論的書。施克萊并未給出自己的標準,來區分不幸與不正義,她說:“我的目的不是在它們之間劃出一條分界線,因為本書的論點就是,我們無法在一般層面或者說抽象層面劃出這樣一條分界線。”(236頁)這和她對常規模式的批評相一致。施克萊對常規模式的批評絕不是“既有的一切區分標準都有問題,真正可靠的標準尚待探索”,她的觀點比這徹底得多:任何試圖一勞永逸找出區分標準的做法都是誤入歧途的,它們都不恰當地忽視了不正義感。
施克萊拒絕給出區分不幸和不正義的精確標準,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她打算給出什么樣的方案,來處理這個問題。
施克萊高度肯定法治,認為相比個人復仇,法治是一種進步,可以更可靠地實現正義。這道理也不難理解:許多人并沒有足夠的能力進行報復,報復行為往往會陷入癲狂。但法治畢竟是常規模式的最大典型,它的基本邏輯就是依據既定的抽象規則,來安撫在具體多樣、無法預料的個人經歷中產生的不正義感。因此,它無法完全消除人們心中的不正義感和報復欲。
施克萊主張,“不僅要根據現行規則公平對待一切不正義感的表達,還要以更好的、可能更為平等的規則為目標,來聆聽不正義感的聲音”(195-196頁)。這引出了民主政治。法治必須輔以民主,才能較為妥當地減輕人們心目中的不正義感。
在民主政治中,人們可以有效表達自己的不正義感,不正義的規則于是有機會被改變。不同群體在政治論壇上相互競爭,彼此有輸有贏。因此,通過持續的民主過程,個人心中的不正義感與法治之間的沖突可以得到有效調和。
總之,施克萊關注的不是給出結論,而是不要輕易下結論。保持開放的政治空間,讓憤懣委屈者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是她心目中應對不正義感的最佳方式。
懷疑主義與政治理論的未完成性
前面講到,施克萊對常規模式的批評能否成立,關鍵要看如何評價受害者的不正義感,特別是,這是否可能只是一種無根無據的抱怨?在這一問題上,她幾乎是不加論證地選擇了自己的立場,一種盧梭式的民主立場,懷疑哲學,信賴大眾。那么施克萊如何能說服那些對民主不抱同情的讀者呢?他們大概只會覺得這種圣母心態膚淺且天真。我們可以聯系施克萊的懷疑主義立場,努力幫她填補這一論證空白。
雖然對亞里士多德、羅爾斯這樣的大思想家,施克萊也免不了說幾句客氣話,但她顯然認為,常規模式是誤入歧途的。原因在于,這一模式缺乏懷疑主義精神,對人的能力過分樂觀。
施克萊追隨蒙田的懷疑主義精神,認為之所以不可能找到終局性的規則體系,歸根到底是因為人在認知和心理層面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認知局限性即是客觀上的認知能力欠缺,心理局限性則呈現為種種心理弱點:容易被個例引導;面對不利信息不愿改變自己的看法;慣于用內在動機解釋他人行為,用外在因素為自己開脫……這些心理弱點最終也會影響我們的認知判斷。
這里需要區分下常規模式的發明者和生活在常規模式下的人,施克萊同時懷疑這兩類人的認知和心理能力。施克萊說,“常規正義模式也許完全無可非議,問題只是,它不適合我們。它并無錯謬之處,只是在實踐中行不通、靠不住,因為它所預設的心理和智識品質我們并不具備”(51頁)。這話懷疑的自然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她似乎并不懷疑理論家能給出一套盡善盡美的正義觀念,問題只是,它脫離了現實。不過所謂“脫離現實的盡善盡美”本身就是個無足輕重且含糊不清的概念,我們不如繞過施克萊的修辭性表述,直接認定她對理論家構造常規正義模式的能力抱有深刻懷疑。
但施克萊絕不是徹頭徹尾的懷疑主義者。相反,在根本問題上,她的觀點無比堅定:視殘忍為首惡,認為人最恐懼的莫過于恐懼本身;自由主義的要義就是讓人擺脫殘忍和恐懼,自主且不受偏袒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過對于體系化政治方案,她總是充滿懷疑。她認為,由于認知和心理層面的缺陷,我們對世界、對他人的內心乃至對自己總是缺乏足夠的了解。特別是,理論家總是容易低估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經歷感受的復雜性。這種無知的自信不僅會導致那些抽象系統的理論脫離現實,更重要的是,理論家往往還意識不到這一點,從而走向危險的改天換地式(transformative)烏托邦信念。因此,施克萊的懷疑主義是一種以非常具體、非常克制的認知和心理懷疑主義為基礎的政治懷疑主義,懷疑各種體系化政治觀念,懷疑學者、官員相較于普通人的認知優越性(213-214頁)。相應地,她的自由主義是一種骨感自由主義(barebones liberalism),沒有遠大抱負,僅致力于守護自由,捍衛多元性,寬容邊緣群體(Judith N. Shklar, Legalism: Law, Morals, and Political Trial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5)。
施克萊格外著迷于人心的復雜性。她把對人的動機、情感和欲求的探索稱為道德心理學。這種心理學絕沒什么科學主義色彩,相反,它是非常人文化的。施克萊主要借助各種小說戲劇、社會事件來體察、展現人心的復雜性。她并不覺得人心有多么玄奧離奇,一直拒斥那種脫離文本、脫離語境、鑿之過深的解讀。但她確實認為,理解人心是再難不過的事情。最大的障礙是經驗的匱乏,即沒見識過、難以想象、難以理解一些人物類型、情理邏輯、習俗規矩。
施克萊將道德心理學視為政治理論的核心,而道德心理學遠不夠完備。她說:
社會說明都不可避免地依賴于心理學。除非我們真的知道社會主體的動機是什么,否則我們不可能完全正確。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必須知道的就只是心理學。關鍵是群體而非個體的行為和變化,但如果沒有科學上恰當的心理學,就無法回答“為什么”這個問題。正如朗西曼所知,現在還沒有這樣的東西。我們甚至不知道這種心理學可能會是什么樣的。(Judith Shklar, “Squaring the Hermeneutic Circle,” p. 89)
道德心理學遠不夠完備,因此,政治理論也要保持一種未完成狀態。這種“心理學現實主義”是她拒斥體系化理論的最大原因。重視不正義感、拒絕給出區分不幸與不正義的終局性標準是她的這一立場在不正義問題上的具體表現。
她時常將自己這種側重道德心理學的政治理論路數區別于熱衷體系化、抽象化的哲學路數(她有時會謹慎地說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大致意思是,柏拉圖、蒙田、盧梭這種都是非典型哲學家,典型的則是亞里士多德、康德以及當代的分析哲學家,他們追求清晰的定義、嚴格的論證,致力于構造體系化理論),后者在她看來就是一些“為了避免矛盾和例外,為了超越前哲學形態而設計出來的論證和反駁”(《平常的惡》,第9頁)。
確實,很多理論乍看系統嚴密,但細究之下,不過是作者帶入一大堆未經反思的預設,借助自己非常有限、非常單調的生活塑造的零散直覺,在非常技術化地處理問題,猶如沙灘上建大廈。正是因為意識不到自己的經驗、自己所依賴的理論脈絡的有限性,看不到無法被套入學院理論條條框框的生活現象、人心感受,這種系統精密的分析才得以展開。以這種方式得出來的系統化理論,面對實際生活自然毫無說服力:它本就缺乏對生活的理解力。熱衷于這類研究風格的學者普遍不讀文學、不關心歷史和其他各類經驗研究,在人際交往中呆板拘謹,聽不懂玩笑接不住梗,和施克萊確確實實是兩類人。《平常的惡》《不正義的多重面孔》與分析風格的倫理學、政治哲學著作也確確實實是兩類書。它們立足于歷史經驗、日常生活,選擇以講故事的方式來捕捉那些“逃離了理性化”(同前引),但對我們的政治生活又無比重要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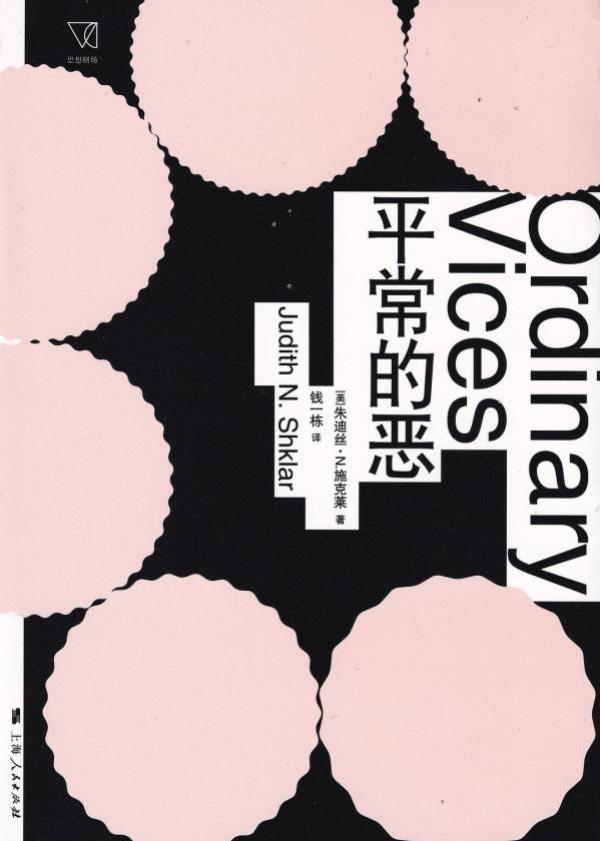
《平常的惡》
與施克萊風格最相似的當代名家大概要數伯納德·威廉斯(對兩人的細致比較參見Katrina Forrester, “Judith Shklar, Bernard Williams and Political Re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2012, 11[3]:247-272)。威廉斯終生關注“倫理學與哲學的限度”,認為現代道德哲學一直在逃避真實的道德生活,無法應對其復雜性特別是悲劇性;體系化的道德理論不僅注定失敗,還會歪曲我們對倫理生活的理解。施克萊的思想主題也可以被非常貼切地概括為“政治理論與哲學的限度”。她著迷于社會生活的“單純表面”(《平常的惡》,135頁),警惕體系化理論,拒絕透過現象看到所謂的本質,喜歡通過講故事來幫助讀者找回對政治道德經驗的感受力。
但施克萊似乎過分輕易地拒絕了體系化努力。體系化有助于暴露我們思想中的不融貫、不一致處,逼迫我們頭腦中的各種觀念相互碰撞纏斗,從而使我們想得更為細密周全。確實有不少哲學家狹隘無知,缺乏感受力,熱衷于自欺式的理性化。但也有足夠多的哲學家務實而誠懇,努力將我們的零散直覺以一種盡可能清晰系統的方式梳理出來,從而深化、細化我們那些模模糊糊的觀念和感受。拒絕體系化只能是誠實面對具體現象的體系化努力失敗后得出的結論,而不應成為在進行具體研究之前便已設定好的思想姿態。否則,它很容易變成抗拒艱苦思想勞作的漂亮說辭。僅就我閱讀施克萊的體會而言,很多問題她完全應該想得更系統、更精確一些(對施克萊的理論貢獻不抱同情但又頗為公允的評論參見Will Kymlicka,“Reviewed Work: Liberalism without Illusions: Essays on Liber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Vision of Judith N. Shklar,” Ethics, Vol. 107, No. 3 [Apr., 1997], pp. 513-514)。
具體到不正義這個問題,硬要給出一套終局性的判斷標準確實是荒謬的(可以停下來問一句:真的有誰試圖這樣做嗎?)。但除了給出標準并接受批評、不斷修正外,我們還能做些什么呢?像施克萊那樣停留于空泛的思想史點評和零散的個例解讀嗎?開放的政治空間確實很重要,但這個空間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為它能夠讓不同的標準、讓抽象的標準和具體的感受相互對話,彼此修正,從而不斷提升其合理性(施克萊可能會說,她也正有此意,參見《平常的惡》349頁,反正她從來沒把話說明白過,因此什么批評都可以圓過來)。如果不能具體指出現實生活的復雜肌理在哪一點上挑戰了某套規則體系,那么我們必須說,這種以“復雜/具體”為名的批評本身卻是空疏抽象的。相比空洞地告誡理論家“不要傲慢”,更重要的也許是具體分析那些傲慢的理論到底錯在哪里。否則,這種告誡姿態只會體現出告誡者本人的傲慢乃至無知。
順著這一話題,我們還可以談談《不正義的多重面孔》頗受詬病的一項主張。
施克萊的一些論述暗示,把不正義理解為正義的缺席是錯誤的,應該拋開正義,獨立地研究不正義。例如她說:“它們(指哲學和藝術)視下述觀點為理所當然:不正義只是正義的缺席,一旦明白了何為正義,我們就會了解所需了解的一切。不過,這一信念也許并不正確。如果只盯著正義,我們會錯失許多東西。”(31-32頁)她主張,應該“直接將我們眼中的不正義經驗視作獨立現象”(32頁)。
問題在于,不正義就是“不”正義,不正義即正義的缺席,這是一個概念真理。將不正義視作獨立于正義的現象顯然是荒謬的,深入思考不正義本身就意味著反思既有的正義觀,兩者在概念上必然關聯。因此如果咬文嚼字的話,我們只能說,獨立于正義來理解不正義是不可能的。真正的關鍵在于,要擺脫追求普遍性與確定性、拒絕矛盾和例外的哲學認知模式,轉而關注具體的、個人化的受害者視角。因此,施克萊真正想要打破的思想桎梏并非正義本身,而是對正義的一種哲學化認識模式,即她所說的常規正義模式。之所以要“獨立于正義”,僅僅是因為一談正義便容易陷入常規正義模式。總之,從不正義入手僅僅是策略性的,方便我們調換視角,從抽象思維轉換成更貼近具體經驗的思想焦距。
對這個小問題的分析既展現了施克萊的反體系化、反哲學立場,同時也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施克萊對精確嚴密的思考方式可能偏見過深。至少對她而言,這種思考方式并不會構成什么“認識論障礙”,沒有這種思考習慣才是她許多問題的根源。
《不正義的多重面孔》的四種讀法
《不正義的多重面孔》是一本典型的施克萊作品。它不作精確的概念分析,沒有嚴密的謀篇布局,顯得非常松散,甚至有些前言不搭后語。這是她有意追求的蒙田式隨筆風格。很大程度上,這樣的作品是難以分析的。它只有模糊的總體立場和諸多零散的閃光點,很難概括出明確的論點、論據、論證結構。
因此,在努力做出體系化分析后,我們還得嘗試捕捉那些被遺漏的側面,盡量還原這本書的多重面孔。一個有效的辦法是梳理它和施克萊其他著作之間絲絲縷縷的思想關聯。
這本書是施克萊的晚年著作,和《平常的惡》《美國公民身份》同屬一個研究序列:美國政治思想研究。我們可以先從這個角度來閱讀這本書。
《平常的惡》探討了美國社會中尋常可見的五種惡習性。但為什么是五種而非四種或三種惡呢?為什么是這五種而非另外五種惡呢?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施克萊并未給出明確說法。她似乎就是順著蒙田的一句話想到了這樣一些惡習性(《平常的惡》,第3頁)。因此我們也許可以把不正義特別是消極不正義算作第六種平常的惡。
“美國公民身份”原文是American Citizenship。在施克萊的論述中,citizenship的含義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公民身份(她談的是基于復雜多元的社會認可而獲得的政治體成員身份,而非國籍這一法律身份),另一類是公民品質,主要關注公民能否做出符合公民身份的行為,是否盡了公民義務(相關討論參見Judith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我們可以說,施克萊晚年的兩本小書都是在談American Citizenship,這本談美國公民品質,那本談美國公民身份。

《美國公民身份》
第二種讀法是把這本書和《守法主義》放到一起,將其看作“永恒少數派的自由主義”這一思想母題在不同理論語境下的具體演繹。和《守法主義》一樣,這本書也有極強的法學色彩,連批判對象——守法主義和常規正義模式——也可以說是換湯不換藥,是同一種思維模式在不同時代、不同學科中的具體呈現。它們的主題都是反對以法治話語為代表的形式主義、規則本位思維模式,后者意味著不再關注實質爭議,認為一切問題都可以按既有規則處理(此即法學、道德哲學中所說的“形式主義”)。施克萊雖然高度認可法治乃至形式主義思維的實踐價值,但反復強調其局限性,努力讓湮沒于主流規則體系之下的少數派聲音(準確講來是弱者的聲音)、讓實質爭議出現在政治舞臺上。因此有學者給施克萊這種獨特的自由主義立場貼上了競爭性自由主義(agonistic liberalism)的標簽(Giunia Gatta, Rethinking Lib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Skeptical Radicalism of Judith Shklar, Routledge Press, 2018, esp. pp. 2, 13, 127-128)。

《守法主義》
《不正義的多重面孔》時不時會討論必然性話語,反對宿命論觀念。這又把我們引向了施克萊的第一本著作:《烏托邦之后》(1957)。這本書細致描繪了啟蒙時代的政治樂觀主義如何一步步走向衰敗。啟蒙哲人和十九世紀的宏大理論家有一點非常不同:他們并不認為有什么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結構性因素,對理性的力量、對人的能動性充滿信心。這也許是施克萊想要找回的政治觀念,一種反宿命論的政治觀念。施克萊政治理論的規范性基礎可能是最稀薄的(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90),但正因如此,它對政治的期許也是最大的。
最后,這本書顯然有極強的盧梭色彩,免不了讓人想起她那本大名鼎鼎的《人與公民:盧梭社會理論研究》(1969)。施克萊認為,不正義感是盧梭政治理論的論證主線。對于盧梭給出的方案,她沒有照單全收:那太斯巴達了,不可能在現代社會實現(194頁)。但她青睞的依然是一種盧梭式的方案,一種適合美國國情的民主政治(她晚年經常批評時興的共和主義理論不切實際)。

《人與公民:盧梭社會理論研究》
話說回來,最適合這本書的讀法也許就是不刻意追求什么讀法,拿起來讀,讀不下去便放下。施克萊更接近博雅文人而非現代學者。追求干貨的專業讀者讀她的書也許會感到失望,甚至覺得名不副實。她的作品本質上都是蒙田式的散文集,而非現代學術工業制品,分析論證也非她所長。一門心思提煉干貨的讀者只會錯失書中最有價值的那些閑筆,那些脫離論證主線的枝枝蔓蔓。施克萊總是能寫出那種洞察世事人心的句子,照亮蔭蔽在日常生活中的諸多微妙感受,而讀者不斷加深的閱世經驗也會在不經意間點亮書中那些原本一掃而過的句子。因此,讀這種書很考驗緣分,需要和生活相互印證才能讀出味道,才能慢慢凝結為我們的智慧和教養。這是老派的書,能長進人心里去的書。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