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與神對話的人:射手座文學大咖TOP10
射手座也叫人馬座,就是希臘神話中那個人頭馬身的怪物。由于有四個蹄子,所以他們喜歡不受拘束地“跑野馬”,以志存高遠、不講道理和運氣極好而著稱。但有知識有教養的射手,則是神話中英雄們的導師:大概只有神人雜交的英雄們才能跟上他們雙倍的步伐。
射手和雙子都盛產詩人,但他們有著完全不同的詩人稟賦。雙子接近于通常意義上的天生的詩人:性靈,隨意揮灑天才,外星人,他們的腦洞是難以捉摸的。但射手則是面對未知領域的探索者。在西方的文化視閾中,最大的未知當然是上帝,所以他們的詩歌就成了對上帝的探索,并在探索中不自覺地發展為對上帝的模仿。眾所周知,西方那位嚴厲上帝不像中國的玉皇大帝那么好欺負,時常愛發點脾氣,帶點洪水猛獸消滅你。所以與神對話的射手詩人們,面對上帝是虔誠信徒,面對人間則難免帶著對社會弊端的不滿、人性弱點的批判。
射手座的小說家們,更多繼承了神話中射手喀戎身為醫生的一面,仿佛拿著手術刀對我們的言行和靈魂進行解剖,仿佛天神打量著不完美的人類,看得我們心里直發憷。但他們比詩人要冷靜得多,所以把主觀的不滿化為客觀的“暴露”,激烈的批判變為冷峻的反諷。醫生世家的福樓拜堪稱這些人的代表,那幅福樓拜拿著放大鏡和手術刀解剖包法利夫人的肖像,就是射手座小說家的真實寫照。
彌爾頓(1608年12月9日)
《失樂園》
彌爾頓和但丁同為宗教詩人,但卻比任何無神論者都更像“異教徒”。但丁的宇宙里,他暗戀的小女朋友貝亞特麗斯簡直比上帝還重要,彌爾頓的科幻大片《失樂園》中,魔鬼撒旦的風采遠遠蓋過了巴頓將軍式的耶穌。然而對宮的雙子座詩人仿佛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幽靈,眼中并無一個活物。(《神曲》中除了詩人自己,可還有一個“人”?)射手座詩人,雖然“他們眼望上帝”,卻仍然是人類,只是不屑與蕓蕓眾生平等對話,但卻奇妙地混雜著對凡人的愛,仿佛IQ160的數學家看著我們解數學題而為我們的智商捉急。彌爾頓為我們是否身處“幸福生活的世界”而憂心忡忡,這還真是應了那句:盲人領著我們,走向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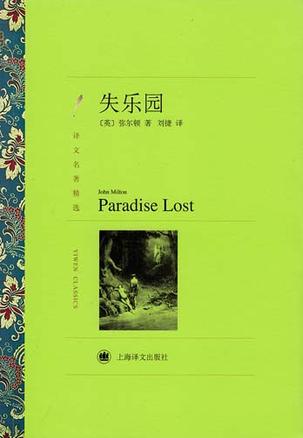
布萊克(1757年11月28日)
《天真與經驗之歌》
布萊克的名聲遠遠抵不上他的詩才,在紀德眼中,他是能與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媲美的人物。大多數讀者都知道他有一首神叨叨的小詩,“從一粒沙看世界,從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恒納進一個時辰,把無限握在自己手心”。能說出如此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神諭,不是天才,就是瘋子。尼采發了瘋,陀氏患癲癇,布萊克據說四歲便已出現了幻覺,說曾看過上帝顯靈——耶穌出現在一間房子的窗戶上。他認為所有人都擁有這項“能力”,只不過有的人在成長過程中將之丟失了。當然我們懷疑他這樣說只是為了逃學。布萊克的偶像理所當然是彌爾頓。據說有人曾看到布萊克和妻子一絲不掛地坐在院子里讀《失樂園》,看到有人來,便高興地喊道:“進來,這就是亞當和夏娃。”仿佛王朔那句“我是你爸爸”,這樣占人家便宜,真不知道是天真還是有經驗呢。

狄金森(1830年12月10日)
《狄金森詩選》
狄金森如今崇高的地位不可動搖。她從二十五歲開始棄絕社交,修女般閉門不出,在孤獨中埋頭寫詩三十年,一千八百多首詩生前只發表了七首。這些詩直到她死后出版,才引起轟動。不過轟動是我們的,狄金森完全不care,她完全沉浸在跟上帝交流的幻覺中。例如那首著名的《籬笆那邊》:“籬笆那邊/有草莓一顆/我知道,如果我愿/我可以爬過/草莓,真甜!/可是,臟了圍裙/上帝一定要罵我/哦,親愛的,我猜,如果/他也是個孩子/他也會爬過去,如果他能/爬過!”如果把這首詩中的“上帝”換成“媽媽”或者“爸爸”,那就是我們的小學生作文了。在她眼中,上帝竟然如此雞婆到連臟了圍裙的事兒也要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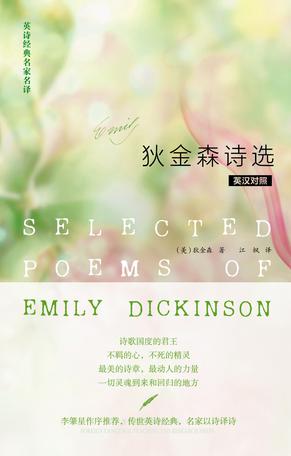
海涅(1797年12月13日)
《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
德國當然是出產大師的,尤其是催眠大師。歌德、席勒、荷爾德林,由于思想太過精深,能讓讀者如墮五里霧中,生怕我們不知道他們也讀過康德。只有海涅,情詩寫得少女思春,論著寫得老嫗能解。舉凡社論、樂評、書評、政論、雜文、隨筆,他都能寫,寫則精彩,語言瀟灑跳脫,如翔天際,諷刺而有分寸,幽默感一流,那感覺正如海涅的詩句:“乘著歌聲的翅膀/心愛的人,我帶你飛翔!”有趣的是,他的抒情詩簡直是泡妞利器,但他的太太瑪蒂爾德一直都搞不清海涅的才華有多大。面對他人的夸獎,瑪蒂爾德的反應是:“他的詩肯定沒那么好,因為他自己都對他的詩不滿意。”甚至,“大家都說海涅充滿奇思妙想,而且寫過美麗的書,可我真的一點都感覺不到。我只好相信大家的話。”海涅知道后卻大喜:“她愛的是我這個人!”其不接地氣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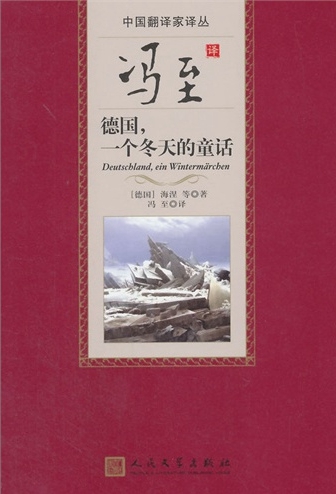
里爾克(1875年12月4日)
《里爾克詩全集》
因為姐姐的天折,里爾克一出生就被母親當作女孩子養,穿女孩的衣服,買布娃娃玩具。在實際生活中,里爾克的內心是柔弱纖細且謹小慎微的,所以只好在寫詩時扮演上帝,說說大話,以至于讀著他的詩會感到受了侮辱。一會兒對著上帝爸爸撒嬌:“主啊!是時候了。夏日曾經很盛大。把你的陰影落在日規上,讓秋風刮過田野。”一會兒扮演房管局領導:“誰此時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其實他極為膽小,時常有被監聽的妄想癥:“究竟有誰在天使的陣營傾聽,倘若我呼喚?”大概見鬼的經歷豐富,所以里爾克感嘆:“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然而不可否認,他的詩句宛如上帝的垂示,完美而充滿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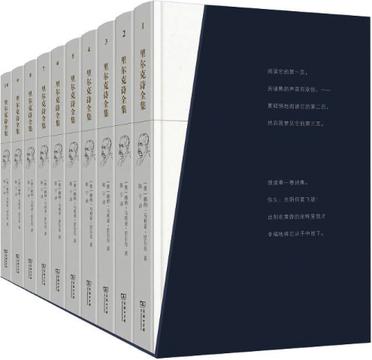
策蘭(1920年11月23日)
《保羅·策蘭詩選》
策蘭的詩歌如希伯來先知的啟示錄,即便讀不懂也能攫住讀者的靈魂。作為一個父母喪生在納粹的猶太人集中營、經歷過多年流亡生活、患有精神分裂癥、最終自沉于塞納河的德語詩人,策蘭的詩歌氣氛完全就是海涅的另一邊:充斥著死亡、絕望、黑暗與神秘。相較他那位樂觀的猶太人前輩,經歷過戰爭的策蘭更加能看到《圣經》預示的末日景象。據說,最后留在策蘭書桌上的,是一本打開的荷爾德林的傳記,他在其中一段畫線:“有時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由于黑暗先于上帝的光芒擁抱裹挾住他的一生,他唯一的反抗之路,似乎只有主動沉入黑暗。

簡·奧斯丁(1775年12月16日)
《傲慢與偏見》
簡·奧斯丁收獲了大量的“普通讀者”,在普通讀者眼中,她的小說就是小清新讀物,書中既無驚心動魄的“戰爭與和平”,也沒有爾虞我詐的“名利場”,都是鄉間莊園的談談戀愛結結婚這樣的“終身小事”,她還會給一個看上去似乎皆大歡喜的結尾,符合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奧斯丁在生活中有普通射手座的一面,喜歡唱歌跳舞,與人調笑,喜歡逛街交友,并不是高冷的文藝女青年。然而回到孤獨的創作中,她便難免“筆中帶刺”,但是一邊諷刺筆下的人物,一邊淡淡地給他們指一條路。奧斯丁的溫情和反諷是同在的,讀者既可以從中照出自己身而為人的愚行與荒誕,但并不因此暴躁憤怒,因為奧斯丁的解剖是無害有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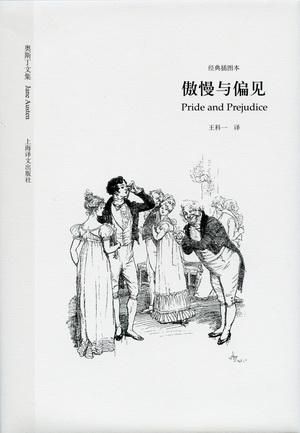
福樓拜(1821年12月12日)
《包法利夫人》
余華出道時曾在作品中假裝殘酷,但很快就暴露出他是個溫情主義者,對筆下的弱者滿是關愛之情。福樓拜在作品中的冷靜和淡漠,那種時時在場的不動聲色,談笑間看著灰飛煙滅,才真正恐怖。他在作品中對情感的淡化到了惜字如金的程度。同是醫生出身的契訶夫曾說:“越是遇到情感色彩濃重的場面,下筆越是要冷靜,出來的效果也越有情感色彩。”這完全就是福樓拜慣用的手法,他對筆下的人物夠狠,冷冷地看著愛瑪偷情、遭情人遺棄、欠債、服毒自殺。這種境界,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上帝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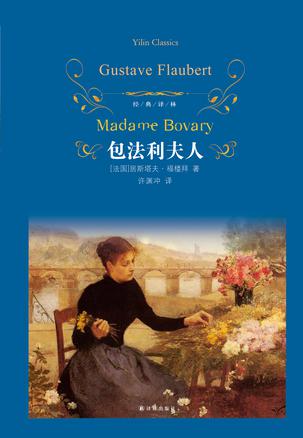
馬克·吐溫(1835年11月30日)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是無可替代的經典,其不分膚色、不分年齡、不分身份,樸實自然得如同大地河流一樣的氣息,還有無論面對什么樣的生活境地都從不更改的童心,是許多過于嚴肅失去了平常心的作家做夢也未想到過的境界。馬克·吐溫的幽默感在于,將孩子的歷險故事對應了古希臘神明般的君王亞歷山大的征戰傳奇。由于小說的敘事被作者訴諸孩子的口吻,讀起來童趣盎然,比《亞歷山大遠征記》之類的歷史書有意思得多。其實從上帝視角看來,成人之間你死我活的戰爭,與孩子之間天真爛漫的游戲,本來就沒有多少差別,倘若拉開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看,戰爭本身就是可笑的,所以經歷過戰爭的海明威才會揮揮手說聲:“永別了,武器。”馬克·吐溫可以讓任何讀者不管如何世故如何圓滑,一旦捧起他的小說,就會變成孩子,回到闊別已久的少年時代。

茨威格(1881年11月28日)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茨威格對心理學與弗洛伊德學說頗感興趣,他擅長人物心理的細致刻畫,對奇特命運下人類心靈的徘徊運轉予以描摹,隨著他的節奏,你的心靈也會不由自主地跟著那脈搏心氣激動,蕩氣回腸。與弗洛伊德的“科學研究”相比,茨威格的“文學探尋”因為細節的真實似乎顯得更有說服力。茨威格對人類心靈的幽微之處洞幽燭微,他曾為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司湯達、托爾斯泰等數十位歷史人物立傳,這些傳主因此獲得了鮮活的性格與生命。他只需要給面貌模糊的泥塑木雕吹一口氣,便能使其立馬活轉過來,這大概是他向上帝習得的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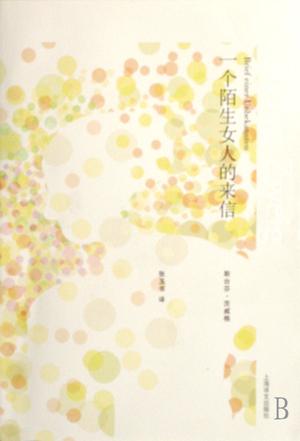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