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賀丨穆時英首度赴日之行及其余波
在現代作家穆時英短暫而傳奇的一生中,有許多未解之謎,其中之一即首度赴日之行。關于其緣起、時間、具體地點、行程、關系人等,向無確說。本來此類謎題,既是學者專攻的課題,一般讀者似無緣置喙,亦不必問津,惟以近來定稿《穆時英年譜》一書,頗感對諸如此類問題亦須向讀者作一交代,以略盡著者之責,不敢謂為“盡其責而善其事”,欲使之名實相稱,似亦難乎其難。雖乎此,仍以“考據癖”時常發作,遂抽暇稍作索隱,草此小文,或可供意者參考,至于所本者,泰半皆手邊之“常見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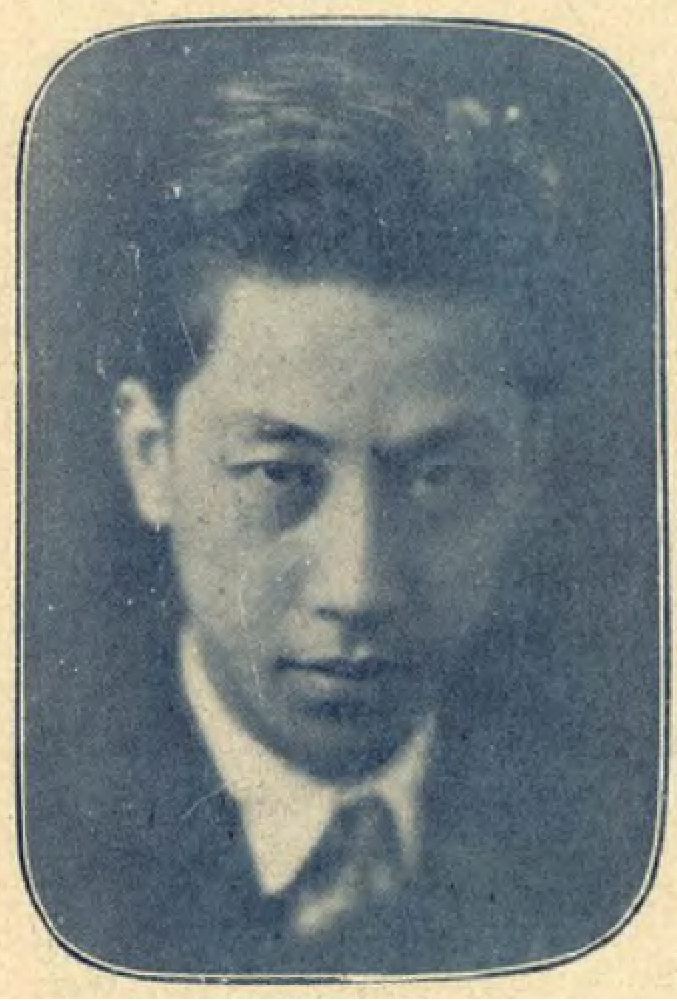
穆時英
一、穆時英首度赴日之行的緣起
穆時英的首度赴日之行,究竟以何緣由、契機而發生?據興亞院華中連絡部調查官增谷達之輔致今日出海一信(1940年7月2日)、松崎啟次《上海人文記:電影制片人手記》可知,乃由興亞院華中連絡部所組織。興亞院設立于1938年12月16日,主席由日本首相擔任,各部職務亦由日本政府高官出任,專事對華關系。次年3月10日在中國境內分別成立華北、蒙疆、華中、廈門連絡部。其中,華北連絡部駐地則在北京,一度扮演著大使館一般的角色;華中連絡部設址上海,起初規模較小,后設官房(辦公室)及政務、文化、經一、經二、經三局,人員亦隨之擴充數倍。1942年11月1日大東亞省成立前一日,興亞院旋遭裁撤,改組為中國事務局。
但增谷并未出現在興亞院華中連絡部成立時公布的主要官員名單、1941年6月1日印刷出版的《興亞院職員錄》之中,至于其何時調入、任職時限(似較短暫)等,俱有待考證。不過,在其所服務的華中連絡部完成的近五百種秘密調查報告(尚不計由其指導成立的中支那調查機關聯合會、中支建設資料整備委員會,所完成的數百種以各地經濟情況為主的調查報告)之中,確乎有不少關于上海電影、戲劇業的專門調查,如第二輯之一《現在上海并奧地活躍中之新劇界主要人物表》、第二輯之二《奧地戲劇運動之概括及上海話劇運動的回顧》、第六輯《電影人名表》、第二十九輯《支那電影的制作傾向》、第三十五輯《京劇改良運動的主張與實際》、第三十七輯《上海劇壇與幫的關系》等。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普通的、不甚引人注意的官員,對于與之接洽的日本影人、中國文人而言,似乎分量很重,也承擔了率領穆氏等人首度赴日參訪的重責大任。但是,關于是次赴日之行的緣起,主事者增谷,并未多加記述。據松崎所講,興亞院華中連絡部的目的,是組織中國電影界人士考察日本電影、文藝、文化事業,但按阿部知二所言,是“非正式”訪問。有意思的是穆氏對此行的態度,依增谷之回憶,其對于此次出行,并不猶豫,而是立即答應,與之同行。“那時他沒有多余的錢,我記得在日旅行他除了書籍以外什么都未購買,至今想起,我仍有些過意不去。他是個舉止禮貌性格溫順但內心具有鋼鐵般意志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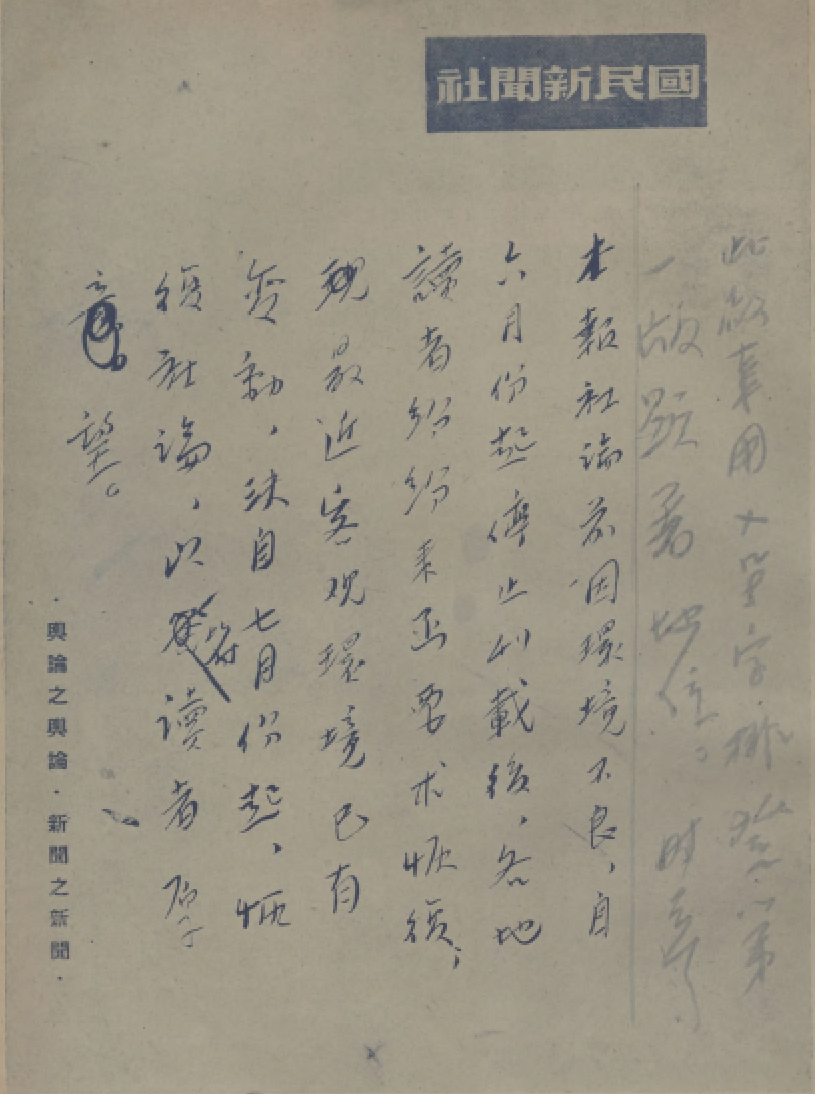
穆時英手稿
二、穆氏首度赴日之行的時間、地點、行程及關系人
關于是次赴日之行的時間,有說是1939年冬者,有說是年秋者,有說是1940年春或2月者,究竟何者為確?其實,增谷在信中明確說,此行是在穆氏自港返滬后不足一星期時間內。而穆氏返滬,時在1939年10月28日,故此,可考定此行始于11月初。而是年立冬在11月8日,已知其在秋季動身無疑,再考慮到當時中日之間多由輪船往返、在日本國內各城市之間則須搭乘火車、旅途中須耗費數日等因素,亦可推定,其由日本返回上海,應在立冬之后。因此,籠統說此行發生于此年秋或冬,似皆無誤,但更準確地說,應是11月上旬間事。
另據松崎所記,是次赴日之前,大約穆氏返滬后的第二天,曾與劉吶鷗、松崎餐敘,席間頗羨慕日本有職業作家、藝術家,可以藝術維生,并吐露心聲道:
第一,目前,我不知道以什么為主題寫怎樣的小說。夢一般的戀愛,在中國已經不存在了;我也不會去重慶,像我的同伴們一般高喊抗戰、抗日的口號。可是對和平救國的理論我還沒搞清楚,總感覺那與藝術表達相去甚遠。
其后,松崎等人偶然接到興亞院華中連絡部選拔中國電影界人士赴日參觀的通知。新華影業公司、藝華電影公司和國華影業公司各派一名代表參加,穆氏與黃謙(黃天佐)蒙選為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與之一同赴日。含率團訪日的增谷在內,此行至少應有六人。但穆氏是此行中唯一的一位作家。
旅日期間,穆氏首先訪問了東京文藝會館。此系菊池寬所辦日本文藝家協會所在地,菊池亦常宿此間,故而先為之舉行一簡單茶會,以事歡迎,且以穆氏之作家身份,決意使之與日本同行見面,擴大交流。據參加茶會的今日出海所記,“穆君像個孩子似的樂了,隨后便在紙上開列作家名單:橫光利一、片岡鐵兵、林房雄……”,請菊池邀請這些同行。
次日晚,在大阪大廈,橫光利一、尾琦士郎、片岡鐵兵、林房雄、久米正雄等人即出席正式餐會,并與穆氏暢敘。席間,眾人先是通過翻譯談話,后用英語交談,賓主盡歡。其中,曾被無聊小報文人稱為“橫光利一第三代”的穆氏與橫光利一的談話,從妹婿戴望舒、瓦萊里、賽珍珠到新感覺派,范圍不出中外文學,而關于新感覺派的部分,殊可注意,橫光本人回憶道:
當初穆先生曾冷不防地問過我:日本的新感覺派如今狀況怎樣?這讓我回想起那時的自己也曾是新感覺派的一員,而當時的我也確實是個很怪異的人。由于新感覺派當時一貫主張應當以悟性活動為中心推進文藝活動,而將感覺置于第二位。但是如何將這種構想傳達給穆先生,著實讓我遲疑了一陣子。最后我對他說,新感覺派目前正致力于從本國的傳統中發現新的意義,并對之作出新的詮釋。
我個人至今都不打算改變這種努力,所以絲毫不改十幾年前作為新感覺派一員的初衷,我依然堅守著個人的信念。對于穆先生的提問我并不感到羞愧,但感到在說明和解釋上相當困難,因為中日兩國的傳統是截然不同的。
作為日本學者,面對自己國家的傳統,我無疑會竭盡全力去尋找新的意義,那么中國學者對本國傳統,恐怕同樣會這么做的。因為今天無論對于哪一方,這都是頭等要緊的大事情,穆時英先生,就是在這兩國新傳統的差別之中,慘遭殺害了。
穆氏另贈今日出海創作集三本,皆其所作“都市文學作品”。按,穆氏一生出版小說集、中長篇小說單行本不足十種(不計其合著),堪稱“都市文學”“創作集”者,則只有《公墓》《白金的女體塑像》《圣處女的感情》三種。
此后,今日出海還收到數封穆氏以英文寫就的信函,并在其第二次訪日時再次得以晤面,“就戰爭引起的蕭條、物價飛漲以及各種各樣的問題依次交談,一直談到文學”。從今日出海的記述中,亦可推斷出,作為中國電影界人士代表的穆氏,此行參訪了日本電影制片廠,惜內情不詳。
松崎的回憶還表明,穆氏是次赴日之行中,可能還有一段浪漫插曲:“他又以他特有的表達方式說道,在長崎偶遇的一個名叫‘雪’的少女,她的美貌將他捆在了日本。”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此行也使穆氏加深了對日本的認識與了解。
三、穆氏首度赴日之行的余波
此行穆氏與菊池寬的交流,雖系二人訂交之始,但似乎給菊池留下了深刻印象。翌年4月,菊池來滬,與穆氏再次會面。5月,穆氏隨汪偽政權答禮使節團訪日,乃有第三次晤面。在東京時,二人數次晤談,頗有知己之感。菊池更欲組織“中日文藝家聯盟”,中國方面之領導人選,亦多所寄望于穆氏。孰料6月末,穆氏即遇刺,不及救治而亡。菊池聞訊后,旋即與今日出海二人,發來唁電,謹表哀悼之意,且在不久之后,寫下一篇文章,以為紀念。文中,菊池坦承自己并未讀過穆氏的作品,而不通日文的穆氏,哪怕讀過菊池作品,或并不為多,且得借助于中譯本,另一方面,我們不難想見,作為中國新感覺派代表作家的穆時英,在日本作家中,更青睞同屬新感覺派的橫光利一、片岡鐵兵等人的小說,而并非菊池等人的作品,乃至于見了片岡,“顯出很思慕的樣子”,也向友人一再剖白,自己念過不少橫光的東西。
穆氏“赍志以歿”后,菊池又將希望寄托在繼穆氏之后出任《國民新聞》報社長的劉吶鷗身上。可惜不久,劉吶鷗亦被刺殞命。菊池所構想的“中日文藝家聯盟”,終于未能如期實現,繼之而起者則有以會議面目出現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942-1944年間,在日本軍部情報局第五部三科指導、監督下,“文學報國會”連續三年,操辦“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此會旨趣,借用文學報國會常務理事、事務局長久米正雄的話來說,是“將士之責,是求前線勝利,文化人之責,是求建設文化”。其所“求”“前線”之“勝利”,自是徹底戰勝中國、由日本主導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囊括日本、朝鮮、中國內地、臺灣、滿洲、蒙疆等地;所“建設”之“文化”,亦是“大東亞”共存共榮、中日親善之文化。前兩回均在東京召開。第一回會議召開前,興亞院再次承擔了邀請中國作家的任務,遭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婉言謝絕。會上,久米亦曾在報告中提及菊池(文學報國會理事、也是會議的組織者)“中日文藝家聯盟”之理想,向其反復致意。次年舉行的第二回會議上,因不滿“和平地區的反動的老作家”(暗指周作人)的合作態度、行為,遠不能達致其預期,片岡在發言中予以公開批評,提出應將其予以“掃蕩”,以致釀成當時華北文壇著名的“反動老作家”事件;菊池亦屬望于年輕作家柳雨生、流亡東北的白俄作家拜闊夫,對其他人則只字不提。第三回移師南京,此時南京為汪偽政權所在地,適堪其用。
不過,在中國召開的這次大會,中國作家的表現似乎并不能使主事者、日本同行滿意。與會的日本作家高見順,曾向武田泰淳說:“支那的作家,無論是上海的家伙,還是從北京來的家伙,他們的發言沒有一個是順應日本國策的。他們只是說怎樣對待我們文學者的生活呀和日常發愁的事情等等,真是壞透了!他們完全不顧精神方面的問題。……(中為引者略)他們表面上還規矩一點兒,而在背后只有他們一伙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就大吃大喝,難道不是這樣嗎?我簡直不明白,對于中國的文學者是喜歡好呢,還是討厭好呢?我真不明白!因為我抓不住他們的實質。”在當日日記中,高見順更如此抱怨道:“中國人幾乎都心不在焉。時而聽一下,更多時候不是看雜志,就是讀桌上的報紙。……”
這些無意公開發表的私人談話、記錄,與今天我們可以掌握的、正式的、關于此次大會的報道之間,不啻霄壤之別。如其所言屬實,則淪陷區中國作家,乃至一般所謂之“附逆”“落水”者,以耽于飲饌、滿腹牢騷、心不在焉、紓解日常生活困厄之提案,抵抗義正辭嚴、富麗堂皇之殖民宣教策略與“大東亞”意識形態,卒使之淪為一紙空言。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