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梁永安:不要迷失在“分配性努力”中
這是一本嬉笑怒罵之書,卻給人欲罷不能的沉思。
作者大衛(wèi)·格雷伯是一位美國人類學(xué)家,2020年9月2日因病去世。在他年僅59歲的人生中,最高光的時刻就是2011年9月17日。這一天成百上千的示威者聚集在紐約曼哈頓的華爾街,搭起帳篷長期駐扎,抗議美國政治的權(quán)錢交易。這突發(fā)的“占領(lǐng)華爾街”運(yùn)動迅速升級,席卷全美國,直至11月15日凌晨,紐約警方發(fā)動突襲,對占領(lǐng)華爾街的抗議者強(qiáng)制清場。這是當(dāng)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蔓延全世界。而這場運(yùn)動的領(lǐng)軍人物之一,就是格雷伯。他不但為整個運(yùn)動“提供了主題”,而且積極投身運(yùn)動的組織工作,提供法律和醫(yī)學(xué)培訓(xùn),甚至還住進(jìn)抗議者的帳篷營地,沖在第一線。頗具反叛意味的是,那時他正擔(dān)任倫敦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院的人類學(xué)教授,從社會身份來說,屬于傳統(tǒng)眼光中安穩(wěn)的精英階層。

大衛(wèi)·格雷伯
深度參加“占領(lǐng)華爾街”運(yùn)動,與格雷伯寫這本書有什么因果關(guān)系?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中,一個震天動地的集體吶喊是“改變”。改變什么?一位抗議者怒聲說:“在美國,1%的富人擁有99%的財富。我們99%的人為國家納稅,卻沒有人真正代表我們。華盛頓的政客都在為這1%的人服務(wù)。”這憤怒的聲音也在這本《毫無意義的工作》中獲得鮮明的回應(yīng),書中寫道:“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財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們所說的‘市場’反映的不過是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除此以外,這還表明大部分從事無意義工作的人最終都認(rèn)識到了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
群眾運(yùn)動往往表達(dá)的是情緒、感受和觀念,對一切大規(guī)模運(yùn)動的歷史性透視還是需要知識分子的反思。2013年春,“占領(lǐng)華爾街”運(yùn)動結(jié)束一年多之后,格雷伯應(yīng)《罷工!》雜志之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談?wù)劇肮菲üぷ鳌爆F(xiàn)象》。這篇不太長的文章尖銳地指出了一個普遍的困境:“在世界上的富裕國家,已經(jīng)有37%~40%的工作者覺得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粗略來看,50%的經(jīng)濟(jì)是由狗屁工作或者支持狗屁工作的工作構(gòu)成的,而且這些狗屁工作甚至沒什么有趣的地方!”這深深地刺痛了千千萬萬工作著的人的心:狗屁工作=毫無意義,這難道是人類應(yīng)有的人生嗎?
格雷伯所說的這種“無意義”狀況,并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指脫離了人類社會真實(shí)需要、人為疊床架屋的泡沫化分工。他說:“(無意義崗位激增的數(shù)字)出現(xiàn)在行政領(lǐng)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務(wù)和電話銷售等行業(yè),以及空前擴(kuò)張的公司法、學(xué)術(shù)與健康、人力資源和公共關(guān)系等領(lǐng)域。這些數(shù)字甚至沒有反映出為上述行業(yè)提供行政支持、技術(shù)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其實(shí)所有輔助性行業(yè)都需要算進(jìn)去(比如,給狗狗洗澡、24小時送比薩的行業(yè)),所有這些工作的存在不過就是因?yàn)槊總€人都花費(fèi)了太多時間在‘工作’上而無暇顧及其他。”所以他無比嘲笑地提議,“以上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這也是這篇文章的精彩之處:我們?nèi)祟惿鐣诖筚Y本的操控下,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些摧毀勞動價值的“新工作”,讓無數(shù)人寶貴的生命在無意義中旋轉(zhuǎn)?這充盈著道義感的喝問,瞬間揭開了“后工業(yè)社會”隱藏的病癥,使太多的人墜入自我價值的痛苦思慮中。文章激發(fā)起“輿論的巨浪”,被翻譯成10多種語言,“《罷工!》雜志的文章頁面點(diǎn)擊量則超過了100萬次。因?yàn)樵L問人數(shù)過多,網(wǎng)頁崩潰了好多次”。
群情鼎沸之中,格雷伯決定寫這本《毫無意義的工作》,目的很簡單,“想提供一個比原始文章更為系統(tǒng)的論述”。他感覺到這個問題的迫切性關(guān)系到當(dāng)今世界每一個勞動者的尊嚴(yán)。這本書的人文基點(diǎn),是文藝復(fù)興以來對個人精神生存的深切關(guān)懷,是對一個價值顛倒的世界的率真審視。書中所展示的是“習(xí)以為常”中的荒誕性:“社會中似乎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的工作越是明顯地對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勞就越低。”這聽上去不可思議,但格雷伯用了蘇格拉底式的歸謬法,連續(xù)追問:“只需要詢問以下幾個簡單的問題:倘若這個專業(yè)人士階層嗖一下消失了,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倘若消失的人是護(hù)士、垃圾清理工、機(jī)械師,那又會發(fā)生什么?顯然,如果護(hù)士、垃圾清理工和機(jī)械師轉(zhuǎn)瞬之間就不存在了,那么我們的生活將會立刻受到災(zāi)難性的打擊。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師,不再有碼頭工人,那我們的生活將會迅速陷入困境。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說家,少了斯卡音樂家,這個世界都會遜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這個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執(zhí)行官、游說者、公關(guān)研究員、精算師、電話推銷員、法警和法律顧問, 那人類是否會痛苦不堪?是否會面臨無法生存的情況?這就不好說了。個人實(shí)際貢獻(xiàn)越多,獲得的報酬越少:除了少數(shù)人們熟知的例外(比如醫(yī)生),這種情況竟然真的普遍存在。”
問題的嚴(yán)重性在于,如此普遍的“無意義的工作”,卻是當(dāng)代世界無數(shù)年輕人趨之若鶩的追求目標(biāo),形成超大規(guī)模的“內(nèi)卷”。成堆成堆的人涌向大公司、大單位的崗位,并不是看重身在其中的勞動價值,而是盡可能多地切下社會財富蛋糕中的一大塊。美國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道格拉斯·諾思提出過“生產(chǎn)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這兩個概念。生產(chǎn)性努力具有強(qiáng)大的創(chuàng)新性,不斷增大社會財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會財富總量的狀況下?lián)屨忌鐣膬?yōu)勢地位,在分配結(jié)構(gòu)中奪取更大的個體利益。在什么樣的年代會產(chǎn)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諾思指出,當(dāng)社會分配嚴(yán)重不公時,生產(chǎn)性努力沒有回報, 分配性努力卻風(fēng)生水起,人們自然不愿再將時間投入生產(chǎn)性努力,紛紛奔向分配性努力。長此以往,整個社會就會失去創(chuàng)造的激情,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趨于單一,失去增長的原動力,從而必然陷入停滯。
日本傳說中有個妖怪叫“忙”,人只要被它附體,就會一刻不停地忙碌,忙得莫名其妙。悲情的是,很多忙都是在“分配性努力”中失去生命的原創(chuàng)性。1987年大熱的美國電影《華爾街》有個熠熠發(fā)光的主題:“金錢永不眠。”整個世界在大資本的驅(qū)動下,青年人的生活陷入“996”的磨盤中,沉重不堪。紐約大學(xué)教授阿納特·利希納說得很形象,長期過度的加班文化是一種迷幻,“我們美化了這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實(shí)際上就是呼吸、睡覺,醒來后整天工作,然后睡覺, 不斷重復(fù),無休無止”。這本書想給忙忙碌碌的人們按一下暫停鍵,在思想的深呼吸中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工作,做出新的選擇。作者的本心能不能獲得理解?社會是無數(shù)差異性力量的匯聚,一本書不可能改變一切,但只要讀者有那么一點(diǎn)點(diǎn)刺痛,這本書也就實(shí)現(xiàn)了它的價值。
這本書的獻(xiàn)詞頁寫了一句十分莊重的話:“本書獻(xiàn)給每一個想要實(shí)實(shí)在在工作的人。”格雷伯在這里表達(dá)了他最本真的心愿:只有認(rèn)清那些無意義的工作,才會獲得實(shí)實(shí)在在的勞動價值。工作是美麗的, 但前提是擁有拒絕無意義工作的勇氣!
本文為《毫無意義的工作》的推薦序,作者梁永安系復(fù)旦大學(xué)人文學(xué)者,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刊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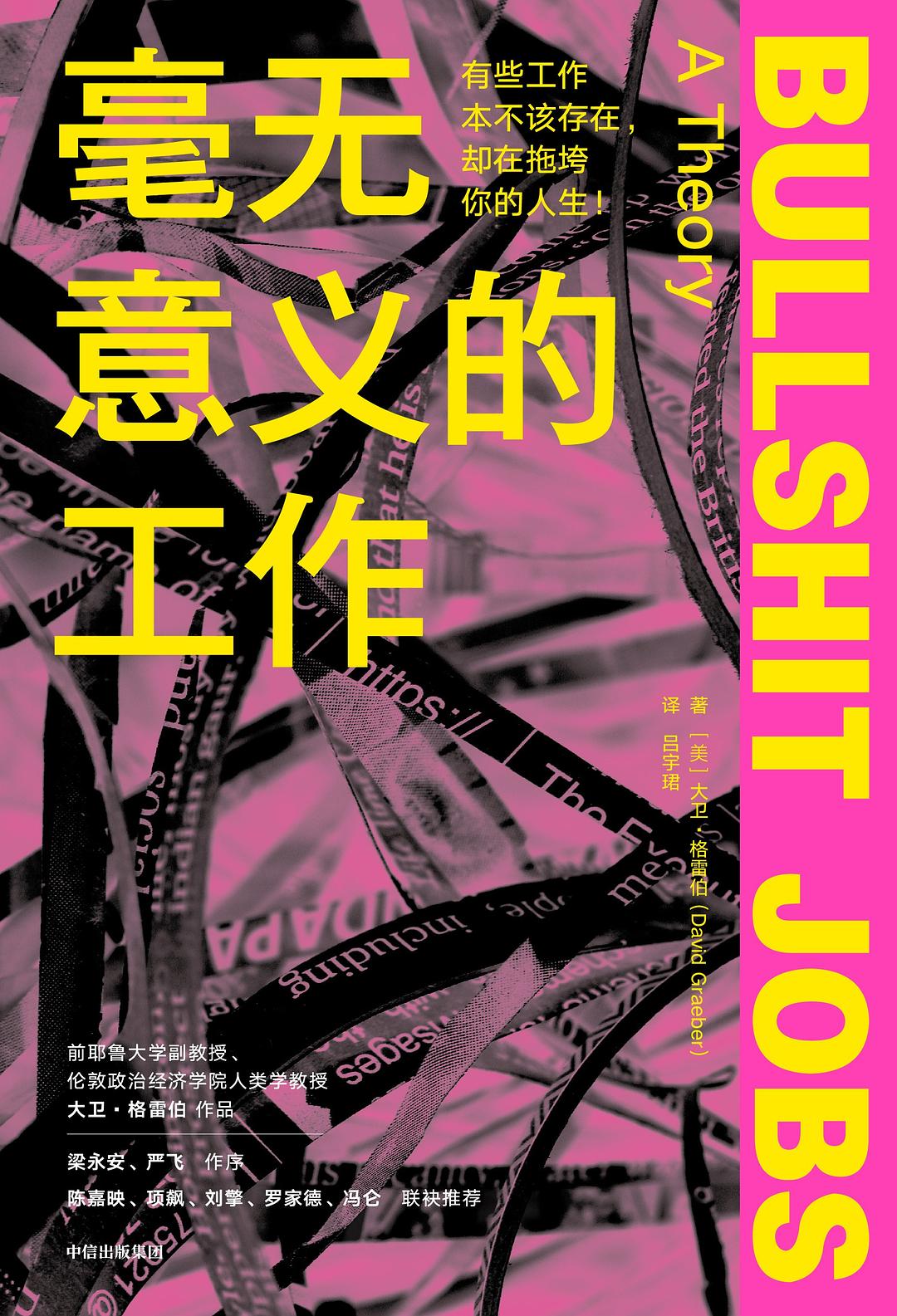
《毫無意義的工作》,【美】大衛(wèi)·格雷伯/著 呂宇珺/譯,中信出版集團(tuán),2022年7月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